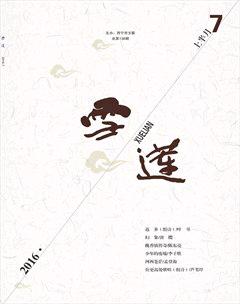為愛癡狂的幾個年輕人
薩拉·蒂斯代爾說過,美始終與人相伴,它讓活著的人精神不朽。
我們總是不斷向往未來的美好,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過去的才是最美好的。寫作是一種修行。修煉了我的浮躁和驕傲,給予了我耐心與安靜。
讓我重新認識了自己和自己所處的世界。
一直以為自己能用一支筆撐起一片天空。
31 區(qū)
來到深圳三十一區(qū),很大程度上是因王十月對我的蠱惑。還記得剛來時,王十月帶我在三十一區(qū)找房子租,帶我買家具,帶我熟悉一些附近的超市和生活小區(qū)。然后把我?guī)У剿依铮龊芏嗟牟恕YI很多的酒。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我和王十月開始了兄弟般的情誼交往。
友誼確實比寫作來得更有力量,更讓人溫暖可靠。比如王十月,他多么像我的大哥。他影響我的不是寫作本身,而是寫作之外的真誠和態(tài)度。他平易近人的外表,給人的感覺永遠是一個來自鄉(xiāng)下的人。讓我感受到了一種來自泥土的氣息,這種氣息是健康而美好的。
我們在一起喝酒時,他總是自告奮勇地去埋單。要是我們有人提出埋單請客時,他就會找一些最便宜的菜點。服務員推介酒店的特色菜時,王十月就對服務員說,你以為我們很有錢啊。
有次去北京,王十月去看望朋友徐東。徐東特別高興,找了個小酒館設宴款待。酒足飯飽后徐東怎么也不會想到,王十月居然毫不客氣地把單給買了。徐東非常生氣地告訴我,他怎么能這樣呢?我說,王十月把他當成了你的大哥。他處處為別人著想,而自己也是多么的不容易。
是的。王十月就是個有清歡味道的人。這種味道是因為他對于生活和生命有了新的認知。記得王十月說朋友徐東在外那么多年了,和生人在一起居然還臉紅。我為王十月的這句話感到欣慰。說明他發(fā)現(xiàn)了愛的秘密,說明了他有著與常人不同的視角,一種巨大的真實開始被心靈觸摸。禪詩有云:“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第三個來到三十一區(qū)的人是衛(wèi)鴉。
衛(wèi)鴉是三十一區(qū)學歷最高的一位自由作家。生于一九七八年,畢業(yè)于湖南大學。曾在政府部門任職,下海后做過研發(fā)工程師。他是在我來這第二年進入三十一區(qū)自由寫作的。當時尚在一家電子廠打工,月薪近七千元。他能來到三十一區(qū),還是得益于網(wǎng)絡。他在網(wǎng)上貼了自己的小說,被王十月一眼看中,覺得這是一個寫小說的將才。于是聯(lián)系上了他。并將他的一篇近萬字的短篇小說刪改到三千字,推薦給一家雜志發(fā)表了。衛(wèi)鴉很受鼓舞,他覺得王十月是一個很有眼光的人。在征求了王十月的意見后,他欣然來到了三十一區(qū)。衛(wèi)鴉這個名字,還是我和王十月在他的房間里經(jīng)過一個晚上的深謀遠慮而最終得出的結果。取了一個好的名字,就意味著一個偉大的開端。王十月很高興,馬上下櫥做面條以示慶賀!那一晚,我們談到了文學,得到了內心里狂歡的奔騰!
衛(wèi)鴉的房子帶電梯,陽臺很大,光線也很好。這樣的房子,在三十一區(qū)的寫作者中是超豪華的。于是,他家的陽臺成了我們活動的主要場地,那個夏天,我們在衛(wèi)鴉的陽臺上聊文學,也看樓下穿著性感的女人,還學著二流子的樣子,用家鄉(xiāng)話同那些靚妹打招呼。靈感也在這里得到了碰撞和啟發(fā)。
徐東來深圳三十一區(qū)之前,還在北京《長篇小說選刊》做編輯。他坐火車到深圳的時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十月去接的站。一直等到晚上八九點鐘。我們生怕等錯了地方,兩個人分別站在兩個出口看守。餓了就跑到附近的士多店里買一根冰淇淋。見到徐東時,他走出火車站的第一句話讓我產(chǎn)生了久久的激動:我們將要揭開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的一角。
我們在一起寫小說。大家在一起的好處,就是相互交流和鼓勵,有時誰的小說發(fā)表了,我們就會非常受激勵,也要努力寫一個出來發(fā)表。大家的小說發(fā)得多了,引起了國內文學界的關注。很快媒體都陸續(xù)來我們居住的城中村采訪。
無論是電視還是報紙,經(jīng)常在談論我們。
開始出現(xiàn)了粉絲來找我們。粉絲們拿著一份刊載我們的報紙來31區(qū)找我們,等我們一出現(xiàn)了,粉絲就對照報紙確認無誤時,高舉著手里的報紙大聲喊到:作家作家。沒錯,是你們,作家們,可等到你們了。把我們給嚇倒了一片。
當時王十月還開玩笑說,我們以后出門是不是要戴上墨鏡呢!
跑 步
跑步是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跑步成為了我們小說寫作最重要的一個部分。由于大家都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很多單位當時來邀請我們去工作,都被我們拒絕了。我們當時眼里只認小說,不認其他,我們對來找我們的單位說,我們要寫小說。那口氣,真是拽得有點太不靠譜了。
那個時候,我都已經(jīng)準備去《特區(qū)文學》上班了,去公園里跑了一圈后,大家談到了文學的理想和抱負,我又不想去了。我還是放棄了去《特區(qū)文學》。現(xiàn)在想想,那時的我,真是被小說給迷惑了。寶安汽車站的領導還專門在我們去跑步的路上攔截了我們,問我們哪個作家愿意去車站辦公室上班?當時開的工資也不算低,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愿意去。我們在跑道上牛逼哄哄地跑著,笑著,說著。
這項運動成為我們繼寫作之后的一個習慣。我曾經(jīng)在跑道上開玩笑說,誰在這條跑道上堅持跑步,誰就可能成為世界大師。大家聽了我的話呵呵一笑!開始都覺得是玩笑話,后來跑著跑著就發(fā)現(xiàn)我的話里飽含了更多的人生哲理。以至于王十月后來說我說的那句話很有價值。害得他每天再忙都要盡快趕在下午跑步前完成。他自從堅持跑步,食欲大增,也不怕增肥了。可以放開肚子吃。一個月之后,王十月超胖的體重減了7公斤。有一天跑完步,我們爬到山頂上,眺望山下的樓房和廠房。想起了還有那么多人在加班加點,想起我們還可以用這么珍貴的時間來跑步,多么不容易啊。不知是誰首先發(fā)出了感慨:深圳有一千多萬人,我們應該是深圳前五十萬最幸福的人。徐東修正說,應該是前五萬。我趕緊補充道,前一萬。后來,有人在報紙上說我們是深圳排名前一萬的最幸福的人。
人多了不見得對寫作本身多大的作用,但可以互相打氣,相互鼓勵對方。要是誰的日子難過了,我們還可以相互幫助。我們笑稱幾個人是夢想互助團隊。徐東剛來時,我們知道他有許多困難,眼看又要交房租了。我和王十月就在房間里商議如何幫助他渡過難關,還曾向其他朋友借錢來援助徐東。當我們去找徐東時,這個骨子里充滿了貴族和浪漫情調的男人,居然還在房間里喝著奢侈的長城葡萄酒。徐東看到我們?yōu)樗涣朔孔獾膯巫樱褂辛穗y以抑制的感動。
壓力使我們更努力地寫作,但也不可避免地面臨現(xiàn)實的沉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王十月的夢想是在三十一區(qū)開一個酒吧,使它成為自由寫作者的沙龍。王十月說,三十一區(qū)可能還會有很多人來,也會有很多人走,但不管走到哪里,三十一區(qū)都是他們的一個精神家園。
徐東的夢想更為遠大,他堅信自己的文學一定會成功。徐東成功后,可能會開公司,會有自己的別墅、汽車,還可能在北京有一棟以他名字命名的二十層高的樓房。衛(wèi)鴉的夢想就是希望家人支持他寫小說,他也夢想自己能寫出世界大師級的作品出來。
我的夢想與他們不同,帶著無邊無際的夢幻色彩。我想,當有一天我的作品被全世界接受的時候,我要包一列火車,邀請全國熱愛夢想但沒有機會實現(xiàn)自己夢想的年輕人坐上我的夢想列車。每個車廂安排一兩個大師為他們講述夢想經(jīng)歷。火車將穿梭于美麗的城鄉(xiāng)之間,火車行程一星期,全程費用由我支付。
公園的那條跑道成為了我們小說的起跑線。
就是在那條跑道上,很多看似開玩笑的談話,卻都一一實現(xiàn)了。當時,王十月說,要是我們這一幫人里若果有人獲得魯迅文學獎,那該多牛!我馬上就對他說,也許下一個就是你。王十月當時還說我真是天真,說他這輩子都難以奢望此獎了。可是事實證明,他幾年后真的就獲得了魯迅文學獎。
當我們跑到山語華庭,看到那高高的樓房,徐東感嘆到,要是能在這里買一套房子該多好啊。可事實呢?誰也沒有料到,他的話也應驗了。這就是夢想的力量!
講 課
在電視里看到了自己。那個用男低音講述的人是我嗎?
想起來我就要發(fā)笑了,從來沒有像今晚這么認真地看過自己,不是看人,是看他的眼睛,看他從眼神里浮出來的語言質感。這種質感讓我想到了鄉(xiāng)下的織布,是百分之百的土質織布。不知怎的,我突然有了一種感動。是因為一個多年以來沒有放棄的夢嗎?
這么多年以來我一直奔波在別人的路上,有誰會想到我經(jīng)過的孤獨和痛苦?有誰會想到無人喝彩的寂寞和憂傷?有誰看到一個孩子的心靈深處填滿了夢想的色彩?
再一次來到久違了的深圳。我和我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朋友在三十一區(qū)開始了自由的寫作。他們是王十月、衛(wèi)鴉、徐東等。還有我那個堂兄五定,在另外一條巷子里滿懷對文學的熱愛和癡迷。他們是這個城市打動我的幾個人。
12月13日早上,王十月就在我的樓下按門鈴了。然后又跑去按了徐東的,衛(wèi)鴉的。我跑到樓下,看到了被晨風吹拂的王十月。我的心里涌起了生活的甜蜜,非常清晰。那天,電視臺要做我們的專題播報。
我們是坐臺里的車去的。這一次專題講座除衛(wèi)鴉外,我們三人都參與了講課。我最先講散文和散文詩的專題,徐東談的是小說寫作與生活的關系。王十月最后講,算是壓軸吧。大家都還表現(xiàn)不錯。賺了幾百元的課酬費,回來在愛晚樓慶賀。
主持人說:“昨天,這幾位打工仔出身的作家應邀登上了深圳大學的講壇,給文學院的大學生們作專題講座。一走進郁郁蔥蔥的深大校園里,只有小學學歷的葉耳就興奮不已。”
王十月說:“我一直想進大學,這是我的夢想。沒有讀過大學,沒想到第一次進大學竟然是給學生講課,也找回了很多的自信心。”
和王十月一樣,大學也一直是我的夢想。站在大學的講臺上,我除了激動還是激動!這是我第二次在深大給學生講課了。這種感覺仍然是那么新鮮動人。它一直以深藍色的注視影響了我。我的敏感而變暖的心,有著被遺忘的表達。
我看見自己在大學的另一個角度。我站著。大學就像一棵植入我內心的大樹,有著風雨和陽光縱深的根。
深圳大學中文學院一位女學生說 :“我以為他們在講話的時候,會對生活很批判,其實他們是很溫和的人。而且我覺得他們都是有很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才可以有這樣的作品。”
這輕描淡寫的話在我聽來,卻有了年輕華美的溫柔。她們支撐起我對美向往的天空。
31區(qū)的幾個年輕人,都用小說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后來,我和衛(wèi)鴉,還有王十月等,我們輪流任職過《作品》雜志的編輯。再后來,我們都離開了31區(qū)。
現(xiàn)在,我又回到了這里。
而那些曾經(jīng)為小說癡狂的年輕人卻不再年輕了。他們也都成為了國內重要的小說力量代表。惟有我還是那個默默無聞的小說寫作者。
我有時會在心里想起他們,想起那些純粹而美好的時光,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會像我一樣,時常想起自己呢?
蘇東坡說,“人間有味是清歡”。
我想,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有人還在做著純粹的夢想的人,無疑是幸福的。像寬廣的河流,保持了一顆純凈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