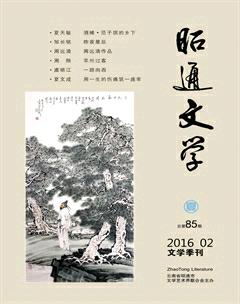放牛
大約是幾年前的事情了,我被派到地處偏僻的鄉野駐村當差,那時候正值草兒嫩綠,野花爛漫的時候,各種植物都在這個季節撥節生長,空氣里彌漫著天籟的馨香。村長從他家里拉出一頭牛到村上的院壩里,語氣誠懇和藹地對我說,這段日子家里的瑣事很多,請你幫我放一下牛。我佇望遠村子外滿山坡的綠草,便在半推半就中攬下了這樁有生以來的放牛活兒。
往事歷歷在目,那頭牛是棕色的,脾氣慢吞吞的,體形半肥半瘦的,它的骨骼和架子卻很挺拔,村長喚它“老把式”。村長把牛牽過來,把牛韁繩遞到我手中,便轉身從村公所的門背后摸出一根結實的棍子交到我中,用手比劃了一下遠處放牛的山坡,說,就到離村只有兩里多些的地方去放牛吧。
我望了望牛,又望了望遠處的山坡,心里老覺得底氣不足,正當我想開口推脫放牛之事,村長早已心領神會地開口說,兄弟,這牛性子溫和,我是有把握才把它交與你的。放牛對于我來說,可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的事情。我有些害怕,說,我怎么認得路呢?村長迫不急待地說,跟著老把式走吧,老把式經常到山里去吃草,它認得路。太陽掛上樹梢的時候,你就跟著牛下山回家。
此事已過去好幾年了,現在想起來仍覺得有些膽寒,把一頭牛交給一個在城里長大的人,并且壓根兒沒有放牛史的人,說話像炸豆子似的村長竟然那么放心。那時的我只知道村長讓我替他放牛的原因,是想白撿一個勞動力為他分擔家務。現在看來,一定是貧困艱難的生活把他的心打磨得過于粗糙,生活給他的負重太多了,他也就沒有那種瞻前顧后的個性,純屬一根腸通屁眼的山里漢子。我當時暗自責怪,他做事怎么這樣草率,但既然已經駐村蹲點當差了,只好把委屈咽進肚子里,硬著頭皮接受那樁放牛的差事。
于是,好些日子我披著晨曦,跟著老把式向村子遠處的山坡走去。
上山的時候,由于在城里出則乘車,上班也是坐著,缺乏鍛煉的我,動作遲緩爬得很慢,遠遠地落在老把式的后面,我怕追不上它我會迷路,很著急,汗水很快就濕透了衣服。
我看見老把式在山路轉彎的地方把頭轉向后面,見我離它很遠,就停下來等我。這時候我發現老把式對我這城里的陌生人,也不欺生,相反倒有些體貼的成分。我對它油然而生了好感,宛若旅行在外的人遇到家鄉人一樣,彼此有了一個噓寒問暖的照應。但是我仍存有戒心,因為孩提時候我母親跟我講過,牛生氣的時候,會用蹄子踢人。我可千萬不能讓老把式生氣,不然,在高山陡坡上,他輕輕一蹄子就能把我踢下高達百米的山坡,我且不是粉身碎骨,永遠地跟老婆兒子bye bye了。
村干部們回家忙活莊稼地的農事去了,村長安排我給他放牛,我牽著牛的繩索,牛也用繩子牽著我,打發那些寂寞而彌漫著鄉土氣息的時光,村公所的院壩成了老把式和我交流的家,我用一根稍微長一些的繩子,將老把式拴在一根木柱上,遇到毒辣辣的太陽抑或是刮風下雨之時,老把式便直起身來躲藏在村公所的屋檐下。每當旭日東升,我牽著老把式,沿著它的腳步上山放牧。路遙知牛力,日久見牛心,漸漸地我熟悉了老把式那忠厚老實的個性,可我老覺得它的行動和神色慢悠悠的,我時常想莫非老把式也在想,我這個城里人和它朝夕相處也不容易,所以才行動神色慢悠悠的,生怕惹我生氣,害怕嚇著我。
寧靜清爽的鄉村日子讓我思考動物和世界的關系:茫茫人海中,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自我;在動物面前,尤其是在我眼前的動物——牛的面前,我是一個睿智的化身,我能思索和主宰牛做不成的事物。但從我熟悉的老把式的眼神和步態里,它大概覺得我就是一個還沒有翻過大山,趟過大河的城里人。換句說,就是沒有吃過苦頭的小牛犢,需要涉世很深的老牛的照顧。經過幾天的周旋,我和老把式便成了老相識,和它一起外出上陡坡的時候,我試著抓住牛尾巴借助的力氣爬坡,老把式沒有拒絕我,感覺得到它多用了些力氣,它顯然是幫助我,拉著我爬坡。有時還把頭調轉過來,睜大眼睛看著我,仿佛在對我說,不要顧及什么臟了臭了的事,拉緊拿穩我的尾巴爬坡上坎會輕松一些。
老把式像一個土生土長的山里人,對自已家鄉的一草一木熟透了,尤其是對去地方,會什么樣鮮美草色,真是到胸有成竹的地步。即使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它也能找到隱藏在巖石和土包后面的草叢。我發現它會用鼻子聞著土地的氣味走路,那灰不拉嘰的鼻子好象是它行走的最好導航儀。它很會選擇路。在陡的地方,老把式一步就能踩到最合適、最安全的路;在幾條路交叉在一起的時候,老把式選擇的那條路,一定是到達目的地最近的。我心里暗暗佩服老把式的本領。有一回我不小心在一個陡坡梁子上摔了跤,膝蓋也被摔破了,鮮血沁透了褲子,我趕快用手絹和新鮮泥土止住血,腿的疼痛難捱,我不得不趴在地上動彈不得,眼巴巴地望著夕陽緩緩落山,無可奈何地看著月亮慢慢出來,月亮逐漸的越升越高越明亮。老把式已將此處山坡上,邊邊角角的青草搜了底朝天,然后昂起頭滿足地吼叫起來。它扭頭見我趴在地上捂著褲褪,索性走過來臥倒在我面前,隨即仰著脖子嗡、嗡的哼了幾聲,仿佛在說,城里人,時間不早了,該回家了。又餓又怕的我忍著腿部的傷疼,掙扎著爬上了牛背,老把式馱著我行走在月亮朗照的山野里,整個夜空在牛背上起伏,月亮越來越明凈透徹,讓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嫦娥奔月”的傳說故事。
牛馱著我,我馱著月亮回到家,天已經黑了多時。村子附近的老農看見老把式馱我回來,都深有感慨地說,算得牛把你給馱回來,不然的話,出了事都沒人曉得。老農一邊說一邊伸手往背籮里抓出大把青草喂老把式,以表示對它的感激。之后,還不時的撫摸著牛的身體,自言自語地說,呃,真是一條通人性的牛。兩個多月的駐村生活一晃就結束了,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把牛移交給了村長的二兒子。那天我記得很清楚,老把式被牽出村公所院壩里,還不時地扭過頭來看它的“朋友”,我噙著淚水在忍痛割愛中注視老把式離我而去。
兩年后,老把式死了。這個消息是從來城里辦事的村里人的侃談中獲悉的,我幾乎不能置信,但的確是可靠消息,那頭牛是從陡坡摔下來摔死的。村上的人說,我走了以后,村長就把拿去拉犁拉車,還讓它推磨,這種超負荷的勞累,加之又沒有給牛喂足飼料,幾個月時間就把老把式折騰得骨瘦如柴。有一天夜里,主人忘記了給牛喂食,饑餓難忍的老把式便用力撞壞了牛棚,偷偷地溜出來,獨自上山尋找食物,不慎失足摔下山來,天亮時,有人從山下看見它,已經摔死了。當我獲知此事,我的鼻子有點酸,我真想大哭一場來祭祀這已故的牛——老把式。青草邊月光下老把式的身影又浮現在我的腦海里,它雖然不會說話,卻又那么通情達理,甚至在我身處危困之際救過我。淚水已身不由已的奪眶而出。
我隨及尋找了一個下鄉的理由,車子載著我行進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我的心早已飛到老把式和我經常出入的山坡,我很想去看一看兩三年前的初夏,我回到鄉下,專門到我駐村蹲點放牛的山上走了一趟,在一個叫“石板溝”的陡坡上,我找到了我第一次拉著牛尾巴爬坡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大石階。它已比當年平整了許多,石階上隱隱約約印著兩個凹下去印跡,是兩個牛蹄的形狀,那是無數頭牛無數次地踩踏形成的。幾年前,包括老把式也踩著這兩個凹處一次次領著我上坡下坡的。我凝望著這兩個深深的牛蹄窩,我嗅著微微飄出的泥土的氣息和牛的氣息。我在記憶里仔細捕捉老把式的氣息,我似乎呼吸到了老把吹進我生命的氣息。
和我同行的人,嘲笑我說,這有什么難過的,不就是一頭牛嘛!他們不懂我和牛的感情。
我忽然明白,我放過牛,其實是牛放了我呀。我放了兩個月的牛,那頭牛卻放了我這一輩子,我的靈魂被一頭牛牽在骨子里。
每到月朗星稀的夜晚,我感覺老把式好像還在馱著我行走夜的呢喃,行走在如水的月光下,和山的皺紋里……
作者簡歷:唐勇,1968年生于云南昭通。1997年開始文學創作,散文作品曾獲2010年度《中國散文年》征文二等獎, 曾在《散文選刊》《文學月刊》《西部散文家》《昭通文學》《楚雄文藝》《烏蒙山》等省、市、區級刊物上發表過散文多篇,并獲2011年昭通市文學創作獎,昭陽區首屆、二屆政府文學獎,現供職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委宣傳部文明辦,系西部散文家協會會員,昭通市作協會員。
【責任編輯 趙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