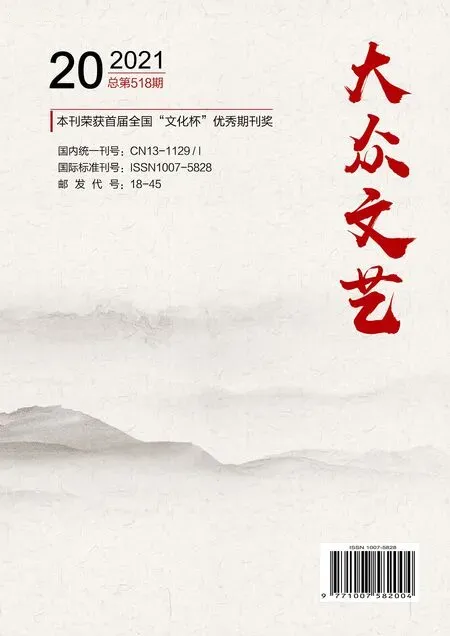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詩史互證”源流小考
沈桂登 (揚州市職業大學 225000)
“詩史互證”源流小考
沈桂登 (揚州市職業大學 225000)
“詩史互證”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著重對該方法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總體的梳理,突出了重要的學說,并對其學術價值作了評估。
“詩史互證”;源流
“詩史互證”作為系統的理論在明清之際得以正式確立,對后世詩歌理論以及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自錢謙益的《錢注杜詩》開創了“詩史互證”的方法以來,后世學者不斷加以開拓,最終將“詩史互證”作為一種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引入現代學術研究中。
最早注意到“詩史互證”方法的是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清初虞山詩派代表人物。有人可能對他的“遺民”身份表示質疑,但本文仍然將其作為“遺民”看待。第一,他曾為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授編修,參加過東林黨的活動。崇禎元年(1628年)任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后被革職。南明弘光朝,為禮部尚書。大半生侍明和做“遺民”的,雖然晚年仕清,但時間不長,順治三年(1646年),托病回鄉。順治四年(1647年),因黃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獄,其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位漢臣。第二,失節后他對明朝仍有深厚的感情,精神深處仍然自認是“遺民”。明亡以后,他創作大量詩歌,寄寓滄桑身世之感,哀感頑艷,激楚蒼涼,表現了他對晚年失節是自責的。
他的代表作《錢注杜詩》,系統地運用“詩史互證”方法,通過對歷史的考察進一步考證杜詩。這是一大創舉。它首次嘗試將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進行打通,是自宋以來,注杜詩的集大成之作。《錢注杜詩》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字詞典故的訓詁,第二部分是解釋詩歌的意思,考證詩歌與史實的關系。以史實闡述研究詩意,又以杜甫詩歌考證唐史,把兩者有機結合,將考證本事與發揮作品原有旨意結合,更為致用。相比宋人是新的突破。關于他的創作動機,有多重說法,最為通行的觀點認為,錢謙益借本書以表達對清庭的指斥,和對自己降清的懺悔。這里不再深究了。
這部用三十余年完成的《錢注杜詩》可謂作者的“心史”,它可以看作是“詩史互證”理論正式確立的標志,開一代學風。陳寅恪先生說:
牧齋之注杜,尤注意詩史一點,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如牧齋所為之詳盡者,尚未之見也……細繹牧齋所作之長箋,皆借李唐時事,暗指明代時事,并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蛻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錢注杜詩》也有許多牽強之處,而且這種注釋的方式對后世的學風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清代相當長一段時期,大凡被認為反映社會現實傾向的,都被以“詩史”論之。注詩走向了附會穿鑿的歧途。可見,單純以史論詩的方法是局限性的。
自清代中葉開始,學者們開始反思這種傾向,以此表達對當時盛行“考據之學”的不滿。如畢沅就反對以純粹“詩史”的眼光看待杜詩,他在《杜詩鏡銓》中提倡讀詩要復歸風雅的傳統。
扶輪大雅,抉草堂之精髓,求神骨于語言文字之外,而棄初得之筌蹄也;由后之說,今日杜詩之不可無注,又以風雅夐絕,迷途未遠,探浣花之門戶,俾端趨向而識指歸,為后學示以津逮也。
他同樣反對錢謙益的“詩史互證”方法,對“注杜詩”之風提出異議:
宋、元、明以來箋注者,不下數十家,其塵羹土飯,蟬聒蠅鳴,知識迂謬,章句割裂,將公平生心血跡于古人事跡牽連而比附之,而公詩之真面目、真精神盡埋沒于坌囂垢穢之中,此公詩之厄也!而注杜而杜詩之本旨晦,而公詩轉而不可無注矣。
有友人株守明人箋注一冊,珍為枕中秘本,謂能箋釋新、舊《唐書》時事,確當詳瞻,此讀杜詩之金針也。余應之曰:“如此何不竟讀《唐書》?”友人廢然而去。
學者錢鐘書多次批評“詩史”, 如《管錐編》說:
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為詩道之尊,端仗史勢,附和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眾殊,謂唱嘆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所樂道優為,而亦非慎思明辯者所敢附和也。”
上述觀點都反對把詩歌純粹的當作歷史來讀,我認為這樣的反省是很有必要的,詩歌的“詩史”功能只是詩歌諸多功能中的一種,切不可成為唯一的閱讀標準,把詩歌的“比興”牽強附會于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描述。我們必須注意到明清之際的特殊時代背景,這是一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史書的年代,缺乏史料,詩歌自然承擔起“補史”的作用。并不是每一個時代的詩歌都可作為“詩史”的。后人的這種批評,雖然不免有些極端,也不失為對當時學風的一種匡正。
以上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歌而言的。需要說明的是,“詩史互證”在錢謙益那里還主要著眼于文學研究,并非系統的史學考證方法,更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文與史的交互。然而,如果拋開文學意義上研究和閱讀不談,單純將詩歌視為歷史研究素材的話,則“詩史互證”的確立對后世有著不可磨滅的開拓性貢獻。這里,必須提到陳寅恪先生的貢獻。陳寅恪(1890-1969),近代著名學者。陳寅恪繼承了錢謙益的“詩史互證”理論,將其系統廣泛的運用到歷史研究領域,更為重要的是陳氏的“詩史互證”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史互通,在錢氏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
其實,單純就歷史學研究而言,把詩歌看成單純的史料來呈現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詩證史”并非陳氏的創建。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所謂的“六經皆史”。六經當然包括《詩經》。如《藝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內篇·易教上》也提出:“六經皆史也。”他認為六經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歷史記錄,他提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器”等命題。近人章太炎指出 “六經都是古史”“經外并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經”。這里,顯然都把《詩經》作為史書看。還有一種觀點,民國年間,胡適、梁啟超、錢玄同、顧頡剛、周予同等人認為六經是史料,就像周予同所明確指出的,“我們不僅將經分隸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張‘六經皆史料’說。”可見,將詩歌看作歷史研究的素材,而非文學作品來研究,已被廣泛運用。如顧頡剛通過《詩經》對歷史的考辯等等。但這種證史往往是單向的由詩到史,孤立的將文與史割裂開來,未能達到較高的水平,最終走向了狹隘的“疑史”。
這里要說的是陳寅恪與錢謙益的傳承關系。陳寅恪作為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家,很推崇錢謙益的這種以詩歌證史的方法,將其運用在《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等著作中。他力求將詩與史合二為一,開拓歷史研究的新方法。《柳如是別傳·緣起》說:
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寅恪平生才識學問固遠不逮昔賢,而研治領域,則有約略近似之處。
陳寅恪首先將錢謙益的這種“詩史互證”方法運用到《元白詩箋證稿》的寫作當中,元白詩與杜詩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同樣繼承了“美刺比興”的傳統。元白詩的敘事性較之杜甫更強,包含了許多中唐史的素材,可以充分加以考證和考索。如《元白詩中的俸料錢問題》等文,都把元白詩作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其次,陳氏晚年的名著《柳如是別傳》又是“詩史互證”的一座高峰。他把錢謙益,柳如是二人的詩詞作為分析明末清初史實的的切入口,進一步拓寬了詩史研究的領域。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有比較公允的評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柳如是別傳》與《錢注杜詩》相較,不難發現兩部書,不僅在學術方法上相近,在創作心境上也如出一轍。《錢注杜詩》是借評杜詩,表達對晚年失節后內心的掙扎,作者內心仍然希望做一個“遺民”,《錢注杜詩》是作者內心這種文化身份的表征。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時,已經是風燭殘年,雙目失明的老人了,一身坎坷無數,作者將《柳如是別傳》看做是對其一生學術思想的一個總結,更是對自身人生道路的詮釋。其中亦不乏夫子自道。兩部書同是晚年的“瀝血”,兩人似乎心靈相通,堪稱“異代知己”。
最后,我們還要注意陳先生對錢氏“詩史互證”的進一步發展。陳氏的“詩史互證”是一種雙向的互動,詩與史的轉換游刃有余,是不可分割的兩個環節,他著力做到文史打通,把文學和歷史的研究相融匯,把古學與今學相貫通,“為不古不今之學”。
陳氏的學生胡守為評價:
先生倡導的詩文證史包括兩個方面:一種是以詩文為史料,或補證史乘,或別備異說,或互相證發;另一種方法是以史釋詩,通解詩意。
汪榮祖也說:
其箋詩、證詩所憑借者,乃是歷史的眼光與考據的方法;一方面以詩為史料,或糾舊史之誤,或增補史實闕漏,或別備異說;另一方面以史證詩,不僅考其“古典”,還求其“今典”,循次披尋,探其脈絡,以得通解。
又如他自己所說:
今之讀白詩而不讀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
陳寅恪“詩史互證”的科學性還體現在他淵博的學識和嚴謹的態度,較之錢氏更加充分地運用和甄別各種材料。把西方現代學術方法,諸如心理學、哲學等與樸學的傳統相結合,在此基礎上,充分尊重中國民族語文及傳統歷史研究的本土特性,做到在大膽學習西方的同時,知白守黑,始終不忘民族本位,力求“四庫兼通,中西融通,文史打通”,陳寅恪的“詩史互證”真正將文與史相交涉,打通了各自學科的界限,又能做到保持兩學科自身獨有的學科功能,有膽有識,視野開闊,卻又不失極精細的考證。陳寅恪的這些努力不僅推動了我國近代學術的發展,促進了中國學術與世界接軌,把“詩史互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還為中國現代民族史學的科學化、規范化建設開拓了新道路。《劍橋中國史》這樣評價:把中國古代史研究引向現代的開拓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做出的。這樣的評價陳氏當之無愧。
[1]方弘毅.柳如是別傳探微[J].安徽文學,2013(9).
[2]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D].南京大學,1999.
沈桂登,大學本科,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職稱:講師,工作單位:揚州市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