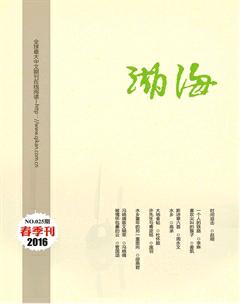時間追擊
趙剛

李衛和蘇劍波是在大學剛畢業不久結婚的(又是一種時間的概念)。大約是在他們結婚半年之后,馬非來了。
馬非是他們的同學,整個大學四年的時間里他和李衛一直睡上下鋪,兩個人的關系鐵得不行,如果后來不是因為蘇劍波,他們的友誼或許還會更進一步。
蘇劍波在一次周末舞會上認識的馬非,舞會臨近結束時馬非連著請她跳了三支曲子,那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沒等第三支舞跳完,蘇劍波便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姓名和宿舍。剛認識的那一二個星期馬非十分積極,一沒事就去女生宿舍找蘇劍波,多的時候一天能跑四五趟,又是送花又是請吃飯的,讓蘇劍波特別緊張。等她像一臺機器似的真的被發動起來了,馬非又毫無預兆地突然松弛下來,借口要寫畢業論文或者聯系工作單位什么的主動減少了來找她的次數,蘇劍波有時一連三四天都見不著他的人影。但是機器一旦被激情發動再想熄火顯然不大容易,自己也不會甘心一味地空轉,蘇劍波只好主動去男生宿舍找馬非。大多數的時候的確能在宿舍找到無所事事的馬非,偶爾也會撲空;遇到馬非不在她就坐在宿舍里等他,一來二去就和馬非同宿舍的人熟悉了,遇到他們玩牌什么的也敢坐下來跟他們一起玩。馬非同宿舍的幾個人都覺得蘇劍波挺不錯,私下里也鼓勵馬非在她身上多花點心思,可是馬非卻跟有病似的,對蘇劍波一陣冷一陣熱的若即若離,也不知道心里究竟在猶豫著什么。如果真對蘇劍波沒有什么感覺那倒也也無可厚非,在大學里面類似這樣的感情客串或者說感情搭伙的現象比比皆是,大家也完全可以互相不當真地相互溫暖著直到畢業。可后來發生的一切證明蘇劍波在馬非的心目中絕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當時馬非對于蘇劍波的態度也肯定不是他內心中真實的情感反應,只是由于當時他的一時糊涂才拉大了自己與蘇劍波之間的感情空間,被狡猾的李衛鉆了空子,半路上截走了本屬于自己的一段感情。
李衛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琢磨起蘇劍波的已經無從考證,他的城府極深,從沒在別人面前透露過一點心思,遇到蘇劍波來宿舍里玩也從不跟她多話,老實、本分、靦腆的扮相麻痹了包括馬非在內的宿舍里一干人,直到兩個人后來出雙入對了,馬非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犯下了一個重大錯誤。也是到了這一步他才突然發現蘇劍波對于自己重要,接下去的那一二月的時間里他展開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一沒事就去宿舍和教室堵截蘇劍波,抒情。開始蘇劍波還對他好言相勸,可時間一長便沒了耐心,態度逐漸變得惡劣起來,再沒給過馬非好臉色。說到底人就是賤,以前蘇劍波對馬非情愫涌動之時,馬非根本不當一回事,心里甚至還有點厭煩,可是真當蘇劍波離開自己跟上了李衛之后,他又受不了啦。這時候的蘇劍波在他眼里完美的跟菩薩似的,連以前令自己深惡痛絕的那一口夾雜著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也覺得動聽了許多;而且蘇劍波對他的態度越惡劣,他對蘇劍波就越是死心塌地,又是寫血書又是絕食的花招迭出,整個人顯得極其地癲狂。隨著畢業時刻的臨近,馬非的心情愈發急迫,在一系列的舉動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后終于孤注一擲,在一個黃昏里用一把水果刀勇敢地割開了自己的手腕,然后抱著手腕滿校園地尋找蘇劍波。那天蘇劍波和同宿舍的二個同學剛逛完街回來,在宿舍門口遇到了已經紅了眼睛的馬非。見到蘇劍波的那一刻,馬非甜蜜地笑了,那一幅病態的笑容蕩漾在昏暗、溫暖的光線中,令人心醉……這件事為整個校園增添了一份額外的感動,并且使得大多數的人對于馬非寄予深切的同情,這無形中增加了李衛的精神壓力,在校園里的最后一段日子他活得極為孤獨和寂寞,平時遭盡別人的白眼和冷淡,很多時候他連一個說話的人也沒有。好在不久他們這一屆學生畢業了。
畢業后李衛和蘇劍波都留在了南京工作,李衛進了一家中外合資單位,蘇劍波則分在外國語學校任英語老師,而一直威脅著他們之間愛情的馬非則傷心地遠走深圳進了一家保險公司。直到這時李衛才得以在愛情中長長地松了一口氣。工作半年后兩個人結婚了。那一場始于大學里的戀愛讓他們心力交瘁,仿佛是為了掐斷關于這一份慘痛的記憶,當一方提出結婚的建議時,另一方絲毫沒有猶豫地迅速答應下來。
兩個人的新家固定在城北的一間三十個平米的單室套房里,這是蘇劍波單位里的福利。結婚時沒有任何的儀式,簡單裝修了一下房間后兩個人在同一天搬進了新居。婚后的生活于平淡中展開,兩個人每天早出晚歸,白晝里的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單位和工作之中,傍晚時分的下班路上還要拐進菜場去跟青菜、蘿卜、豬肉等討價還價,回家后則要迅速地淘米、摘菜并等著另一個人回來,然后吃飯、洗碗、順便交流一下白天中的見聞,再看一會兒電視或者接一二個電話最多再活躍一下身體就睡了。生活日復一日往下持續并深入,一晃半年過去了。有一天蘇劍波下班后順路去菜場買菜,在各個柜臺轉了一圈后卻拿不準究竟該買什么。僅僅半年的時間,她已經對眼前這千篇一律的青菜、花菜、芹菜等失去了敏感。結婚后他們的伙食結構一直是在以青菜為首的一批素菜品種中轉悠,盡管她也曾積極嘗試過利用自己的智慧在有限的品種中多變換幾種搭配花樣,但是效果也只是暫時的,繼續下去后不久又窮盡了,還惹得李衛不住地向她抱怨,鬧得兩個人都很不愉快。現在蘇劍波覺得自己從生理上已經對菜場產生了一種排斥感,即使是很餓的時候只要一進菜場立刻就飽了。在菜場里徘徊再三,她還是買了一把大蒜,半斤茨菇和一把用作燒湯的菠菜。付完錢拎起菜正要離開,一抬頭突然發現在對面一個賣土豆的柜臺前有一個人正盯著自己。蘇劍波本來也沒有在意,只是當她的視線無意中掃過那人時,那人迅捷地將腦袋垂下了,一只手在土豆堆里翻翻揀揀的,故作一副專心買菜的神態。蘇劍波感到很奇怪,不由又看了那人一眼,也沒多想,轉身離開了菜場。
回到家后迅速地淘米燒飯,然后坐下來開始摘菜,心中回味著菜場里的那個男人,隱隱覺得那個人好像在哪兒見過似的,菜快摘完的時候,她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一念至此心慌張地急跳了數下,心緒亂了,手里抓著一根大蒜愣怔了好一會兒轉臉一想又覺得不大可能。他已經去了深圳,應該不會是他的。看來還是自己認錯人了。
摘完菜洗凈切好李衛就回來了,兩個人一起動手,半個小時不到飯菜上桌。吃飯時李衛告訴蘇劍波自己單位里有一個去美國培訓的名額,今天下午經理找自己談話,要他作好去美國的準備。蘇劍波聽了也為他高興,細心地問李衛要不要給他們的經理送送禮強化一下這種可能。李衛說不用,這樣反而不好。因為有這件事佐料,兩個人的胃口大開,李衛也沒像往常那樣對她燒的菜妄加挑剔。吃完飯李衛去房間看《新聞聯播》,蘇劍波拾齊碗筷逕自去廚房洗碗。她習慣將水龍頭開得很大,嘩嘩的水流伴隨當當的碗與碗的磕碰聲。房間里的李衛不知是不滿電視中內容還是激動于要去美國的情緒,在電視機前坐了沒多久也進了廚房。蘇劍波正弓著腰在水池前忙碌著,他走過去從后面抱住了她,身體膩味地貼在她身上,蘇劍波感受到了來自于身后的那一份作弄似的輕薄,本來連貫的動作僵硬了許多,嬌嗔地罵他,去去去,別瞎折騰!李衛沒理他,她放下手中的碗說你要再這樣我就不洗了。李衛微微一笑放開了她。他并不是一個善于表達感情的人。蘇劍波洗好碗收拾停當后對一旁的李衛說,你好幾天沒洗澡了,去洗一把吧。李衛說今天挺累的明天洗吧。眼睛色迷迷緊盯著她,蘇劍波臉又是一熱,扭身往房間走,李衛正要跟進去,門鈴突然響了,叮鈴鈴鈴。兩個人停住身互相看了一眼,猜不出這么晚了有誰會來串門。李衛站在原地問了一句,誰呀?門外無人回答,就看見從門縫下面緩緩塞進來一個信封,信封擦著地面時還發出刺那一聲清響。李衛走過去一把拉開房門,門外空蕩蕩的連人的一絲氣味都沒有。他站在門口疑惑了片刻關上門揀起地上的那封信。信封沒有封口,他掏出里面的信展開看了一眼,一眼之下神色忽變,疑惑的眼神不住地掃向蘇劍波。蘇劍波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了,問怎么回事?李衛默默地把信遞給她。蘇劍波接在手中看了起來。信很短只有二行字:你是我寄存在別人身邊的幸福,現在是收回的時候了。署名是馬非。信中的話似乎并沒有確指什么,但是聯系起后面的署名便十分清楚了。蘇劍波緩緩地放下信不解地問李衛,怎么會是他,他不是去深圳了嗎?李衛搖搖頭無言以對。蘇劍波似對李衛又似自言自語地問,他究竟想干什么?李衛看著蘇劍波的眼神逐漸地渾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