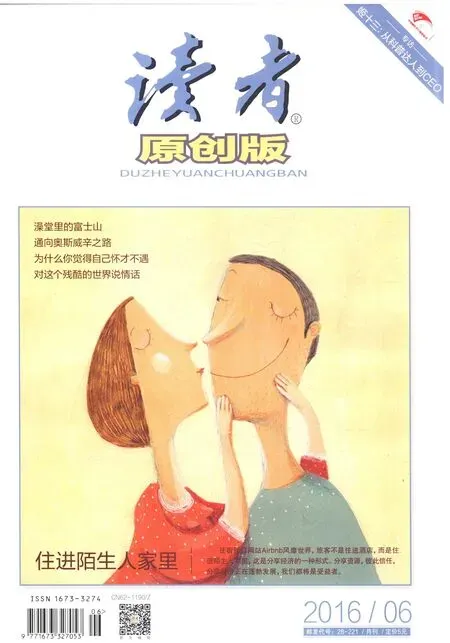少女的狂奔
文_白云蒼狗
?
少女的狂奔
文_白云蒼狗

小時候,天知道,我為什么那么喜歡針管子,那種打針的玻璃注射器讓我向往到癡迷。
那個時候,我酷愛用一根長長的自行車氣門芯、一個鐵夾子和一個取掉圓珠的圓珠筆頭做水槍。方法是把氣門芯的一頭打上一個死結,另外一頭用一個吸滿水的注射器頭對準,堵上,然后使勁把注射器里的水推到氣門芯里,于是氣門芯就咕的一聲胖了一截,像蛇吞進了整個的青蛙。隨后我趕緊用鐵夾子把氣門芯鼓起那部分的前面夾住,不讓它松氣,然后把注射器拔下來,吸了水再推進去,這樣反復幾次,氣門芯就整個鼓了起來,最后把圓珠筆頭安上,這樣一個水槍就做成了。
控制的機關是鐵夾子,選準目標后,我就把水槍對準對方,松開鐵夾子,水就噴了出去。要是我稍微貪心一點兒,最多30秒鐘,水槍就癟了,就得重新裝水了。小時候,快樂來得簡單,30秒的快樂讓我很滿足,而且樂此不疲。
那個時候針管子很少,即使我有兩個表姨當護士,我依舊沒有機會得到這個寶貝,只好到處搜集眼藥水瓶子充當給氣門芯充水的工具。但是眼藥水瓶子實在用得不爽,一是它開口不光滑,跟氣門芯對不嚴實;另外一個問題是它裝水裝得太少,這對著急去玩的我來說實在是太不方便了。
于是,針管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最大的奢望,做夢都想擁有一個。
那個時候我臉皮薄,又被父母教育得“堅貞不屈”,對于想要的東西,最好是看都不要看,不能讓別人看出一點兒羨慕、垂涎、貪婪、渴求之心,更不能張嘴去要。
于是,就算我有兩個當護士的表姨,有在注射器廠工作的三嬸,我最好的小伙伴他爸是注射器廠廠長,只要我開口,或者有一點兒賊心的話,這不過是唾手可得的東西。
但是,我始終很有骨氣,就算再想要,也沒跟他們開過口。
街上有個老光棍,跟他母親一起過日子,他母親已經耳聾眼花背駝了,有六七十歲了吧,全靠兒子從淮河挑水賣水為生。他家窮得叮當響,兒子又長得賊眉鼠眼一副猥瑣相,所以一直沒有老婆。那時沒有自來水,注射器廠這種需要大量用水的單位就雇他來專門挑水,于是,我常常看到他進出注射器廠大門。
他家住在一個七拐八彎的小巷子里,隔壁住的是我爸公司的一個同事,我和他家兒子磊磊是小伙伴,有時候一起玩。他家對門是一戶姓萬的人家,這家有個女兒叫敏兒。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這里發生了一起案件,一個小學老師強奸了多名女學生,美麗動人的敏兒是其中我唯一認識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強奸,但是我和同學都多次專門偷偷地去看敏兒,想搞清楚被大人們說得神神秘秘、無限惋惜的強奸后是什么樣子。看了之后,我們都沒有看出來什么區別,但是都裝出看出來什么的樣子,說:“哦,被強奸后就這個樣子啊!”然后各自回家。但是我再走過敏兒家門前那條小路的時候,總會本能地避開她家的那邊,繞一個弧形過去——心里覺得強奸是個不好的事情,要離遠點兒。
放學路上,小孩子總是喜歡到處亂竄,專門走小路,我也不例外。一天傍晚,我從主干道拐到一個岔街上的時候,遇到了老光棍,他滿臉堆笑地問我:“想不想要針管子啊?我家有,跟我去拿吧!”
我聽到“針管子”三個字,人就癡了。我本來沒打算走磊磊、敏兒家的那條小巷子的,但是聽了老光棍的話后,我就乖乖地跟著他走了。這一走,就走了差不多500米,一直跟著他進了他家的大門。
一進門,他轉身就把大門插上了。我突然害怕起來,轉身就要走,但是顯然已經無法脫身了,他拖住我就要把我往屋里拽,掙扎中,我看到破落的院子里,兩間破房子,對面是一個老太太佝僂著坐在灶臺前燒火的背影。
沒有等我喊出來,他立刻放下了我。我趕緊就往門口跑,拔掉門閂跑了出去,胯下被他的胳膊勒得很疼。我沒有立刻走,在門口站了一會兒,驚魂未定。他居然跟了出來,手上拿了一個5毫升的玻璃注射器,說:“給你!”我居然真的下意識地接了過來,放在手心里,攥得緊緊的。他進去之后把門又插上了。兩分鐘后,我舉起右手,把注射器狠狠地摔在了那扇破舊的木門上,摔得粉碎。
我想了那么久的寶貝,從此再也沒有讓我牽掛過。
天快黑了,我飛奔回家,又怕又氣,還在喘,沒有人發現我和往常有什么區別,我也只字未提。后來我和好朋友娟娟隱隱提起那個老光棍是壞蛋,千萬不要理他的時候,她曖昧地問我:“人家怎么壞了,騙過你?”
我看著她的一臉壞笑,才意識到,這個事情今后是死都不能再說出半個字了,要不然,我也會成為敏兒那樣的女孩兒了。
若干年后,我當了護士,有一次下班前刷洗注射器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有個女孩子曾為了一個5毫升的注射器,差點羊入虎口,萬劫不復。
圖/叢 威
我說:“針管子我不要了,讓我走!”他突然獰笑著喃喃自語:“讓我抱抱你,讓我抱抱你……”他一下子把胳膊伸到我的兩腿之間,用小臂把我舉了起來,我的臉就和他平行了。我看著他瞇成一條縫的眼,氣極了,壓低聲音說:“快放下我,快點讓我出去,要不然我喊磊磊家人了……”他并沒有把我放下來的意思,還企圖往里面走,我狂抓亂踢,聲音更大了:“我真的喊了,磊磊爸和我爸是一個單位的,他們家人聽到了一定會來救我的!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