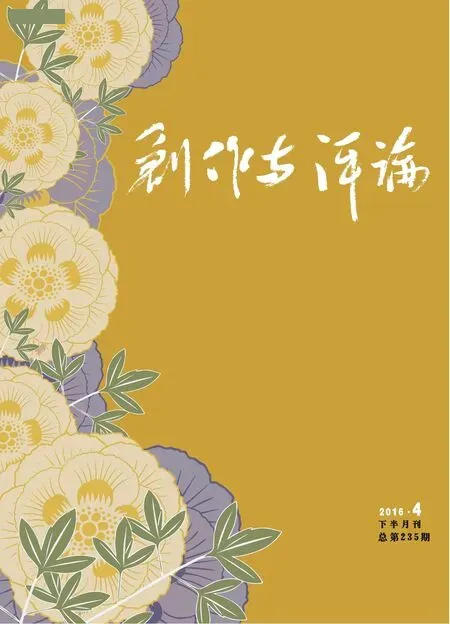百年鄉土中國的痛徹解析與深刻書寫
○劉永春 葉煒
?
百年鄉土中國的痛徹解析與深刻書寫
○劉永春葉煒
主持人語:
本篇對話由作家葉煒和批評家劉永春合作完成。葉煒以寫作長篇小說見長,尤其是他的“鄉土中國三部曲”《富礦》《后土》《福地》,出版后得到廣泛的關注。從目前的狀況來看,70后作家顯然更偏重也更擅長寫作中短篇小說,并且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從世界文學的范圍來看,也不比其他國家的同齡作家遜色。相比之下,有厚度、廣度與深度的長篇并不是特別多——國外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葉煒的這次寫作實踐,可以引發的話題是非常多的。葉煒與劉永春的這次對談,主要是以這部作品為基點,涉及70后一代人的精神特征、鄉土寫作的困境與前景、什么是好的文學等問題。對談中提出的不少觀點也值得注意,比如:“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是:身體在城市,精神在鄉村,靈魂在路上。這決定了我們始終活在一種‘分裂’的狀態之中,精神免不了要不時地出現膠著和矛盾。”“我一直在努力實踐一種‘大格局’的寫作,從自身的‘小宇宙’出發,不斷抵達‘大宇宙’的奧妙和深邃。”
李德南劉濤
一、“以畢生書寫向鄉土中國致敬”
劉永春:葉煒兄好!你的《鄉土中國三部曲》對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進行大視野的刻畫,尤其是對鄉土中國的精神結構與命運變遷做了非常動人的重構。對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我們來說,厚重沉痛的鄉土情感是我們的人生底色,是我們終其一生都難以擺脫的情感處境。那么,你在動筆之初是如何構思如此浩繁的大規模書寫的?
葉煒:的確,鄉土是我們這一代寫作者較為顯著的成長底色,它因此也成為了我們較為深刻的人生記憶。雖然在城市工作多年,但我們的身上仍然有著較為濃重的“土”味兒。對于鄉土中國,對于蘇北魯南,對于生養我們的村莊,我們始終心懷感恩。無論是歷史課本,還是老人們的口口相傳,都在告訴我們:中國的這一百年是不平凡的,中國的農村在這一百年歷經了上天入地的變化。但我很好奇:百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中國農民到底經歷了什么?中國這一百年的精神底色有無改變?鄉土中國的精神結構是處于劇烈變動還是所謂的“超穩定”狀態?我想到生我養我的村莊去尋找答案。

葉煒
真名劉業偉,文學博士。1977年出生于山東棗莊。2000年開始發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鄉土中國三部曲:《富礦》《后土》《福地》等,在期刊發表各類文字200余萬。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江蘇師范大學作家工作坊主持人,美國愛荷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于是,我從最容易著手也是最為熟悉的《富礦》開始,尋找鄉土文明不斷式微的根本原因,試圖給出自己的回答。構思寫作《富礦》,是帶著感傷情緒的,字里行間免不了有些許憤激的情緒和先驗的設置。《富礦》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我發現一味去哀歌和憑吊是不能找到答案的。當下的新鄉土寫作一定要超越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書寫,這就要求作家一定要善于“去蔽”。于是,我又構思了更接近當下農村生活的《后土》,想以蘇北魯南的一個小小的麻莊的基層政權生態,窺探中國鄉村治理制度史。與《富礦》比,《后土》更加“溫情”一點。而在構思剛剛完成的《福地》時,則把這種“溫情”上升到對人性的觀照,把視角從《后土》的鄉村治理擴大到國家政治,把鄉村倫理道德置于中國近現代史的大背景之中,想以此“還原”我心目中的鄉土中國。
劉永春:相對于當下中國社會的其他年齡段作家,70后作家是較為沉默的一個群體,在中國文學格局中處于相對邊緣的狀態,但部分70后作家已經展現出了扎實厚重的精神容量、輕盈自如的文本形態和自省內斂的主體特征。經由《鄉土中國三部曲》,你的敘事能力和精神向度已經得到充分展示,兄如何概括自己作為70后作家所具有的寫作初衷,自己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又受到哪些因素的觸發呢?
葉煒: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是:身體在城市,精神在鄉村,靈魂在路上。這決定了我們始終活在一種“分裂”的狀態之中,精神免不了要不時地出現膠著和矛盾。在這種狀態中,我最想探求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來路,以此解答人生的困惑,尋求思想的文學表達。我無意代表任何群體,也不為任何人代言,我只想代表我自己。雖說在文學不斷式微的當下,抱團取暖不失為一種策略,但這種“抱團”在某種程度上彰顯的往往是自身的“無力”。或許一個人的尋找免不了注定會“百年孤獨”,但恰恰是這種“孤獨”才最有力量。我一直倡導有力量的文學和有思想的學術,惟有有力量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
回首我的創作之路,多半是出于自身的興趣所在,興趣的激發是我長久寫作的力量之源。從小學開始,“我要寫作”一直是我的人生理想。為此,在報考大學時,我對我的老師說:只要能讀中文系,什么學校無所謂!大學本科我讀的是漢語言文學,碩士階段也是漢語言文學,到了博士階段,我干脆選擇了國內唯一的創意寫作專業,成為國內第一個創意寫作方向的文學博士。我始終認為,能夠接受系統的文學訓練是這一代作家的幸運,有了文學學科專業的鍛造,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知識素養,更能提升我們的精神境界,擴大創作的視野。在大學階段,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和思想類著作,這讓我很早就確立了文學的啟蒙意識和哲學追求。我一直在努力實踐一種“大格局”的寫作,從自身的“小宇宙”出發,不斷抵達“大宇宙”的奧妙和深邃。
劉永春:據我所知,如眾多70后、80后作家一樣,你也是從青春校園文學起步的,并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是什么因素引領你轉向了鄉村書寫呢?
葉煒:我的寫作一開始主要集中在青春題材,只有很少的鄉土寫作。盡管大學時代我發表在文學期刊的第一篇作品是農村題材的《民間傳說》,最后一篇作品是《母親的天堂》,但大量的作品還是集中于青春校園,比如“大學三部曲”《大學.com.狼》《大學. com.羊》和《中毒》等。大學畢業以后,我進入高校工作,按照常理應該繼續書寫青春校園。但我在寫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對于文學創作來講,大學校園所在的都市盡管十分“有料”,但并不是當代中國的底色,尤其不是我自己的精神底色。我在鄉村長大,童年的經驗是無法割舍的,也是不應該舍棄的。而且,在我最初的寫作中,最滿意的也不是校園題材,而是不多的鄉村書寫。我應該聽從內心的召喚,回到我的村莊,去書寫我的父老鄉親。土地里面有真正關乎中國的故事,我的任務是如何找到最合適的方式把它們講出來。歸根結底一句話,當下中國的底色是鄉土,探求中國避不開鄉土書寫。這是我的內心選擇,我要以畢生的書寫向鄉土中國致敬!
二、“以敘事創新向現實正面強攻”
劉永春:在我看來,《鄉土中國三部曲》包含的《福地》《富礦》和《后土》組成了一個視角交錯、時空融合、方法各異的文化多面體。其中,《福地》側重辛亥以來風云詭譎的中國現代史,尤其是艱苦卓絕的抗戰。以萬仁義所代表的“仁義”精神與萬家幾兄妹為象征的現代家族革替構成了小說的敘事主線,而小說努力弘揚的是傳統文化中優良的精神土壤,而這片土壤在現代社會已經逐漸風化直至流失殆盡。這種文化轉型導致了兩個結果:一個是現代中國社會與歷史的多災多難,一個是現代人精神世界的日益虛無與人性狀態的不斷惡化。我覺得你的這種文化姿態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20世紀中國文學是以反叛傳統、批判歷史而確立其合法性的,但其后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與精神資源的“返回”卻從未停止。你在《福地》中很好地處理了對鄉土中國的精神認同與文化反思兩者之間的關系,這種特點也同樣集中表現在萬仁義這個復雜的人物形象身上。那么,你為什么要設計這樣一個既保守又先進、既為己更為人、既持家教子又護佑鄉鄰的鄉紳形象?這個人物身上閃爍著令人困惑又令人欽佩的光輝,與以往的意識形態書寫中的鄉紳完全不同,他反而是鄉土中國最具“鄉土精神”的一個代表,這種書寫對以往的鄉土敘事是極大的顛覆,你在構思時進行哪些方面的嘗試,你對萬仁義這個形象又會如何評價呢?
葉煒:塑造萬仁義這個不同于既往文學史的鄉紳地主形象,源于我的真實生活經驗。我生活的村莊里有一個韓姓地主,盡管我和他一個村東一個村西,但因為村莊不大,見到他的機會很多。我記得報名上小學的時候,第一天上課正是在這個韓姓地主的大院。他留給我的最初印象并沒有那么壞,反而有一點點溫和。在我的家鄉,有一個講故事的傳統,而在這些被不斷講述的故事中,最多的就是關于這個韓姓地主的事情。在耳濡目染中,一個鄉紳地主形象逐漸立體起來。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個既保守又先進、既為己更為人、既持家教子又護佑鄉鄰的鄉紳形象。像這樣的人物在魯南大地廣泛存在。
我試圖寫出地主的兩面性、多樣性和豐富性。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觀察地主有一個階級的視角,就是地主是一個惡的代言人,很多文學作品都是這樣寫的。其實地主(也就是鄉紳)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社會存在,他的身上有兩面性,有兩個角色,一方面有他的社會管理的角色,鄉紳在鄉村的風俗禮儀、生活習慣等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管理的時候有他暴力的一面;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保護鄉村的作用,是守護者的角色,為什么有些鄉紳都是名人,就是他保護鄉村的能力發揮得非常充分。
有些人或許認為,這是一部為開明地主正名的小說。任何事物都有其復雜的一面,歷史的敘述多數時候都是在做披沙揀金的工作,而文學,尤其是小說,卻不能忽略那些個體。或許這些個體微不足道,但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老萬這一形象是有真實人物原型的,在蘇北魯南的抱犢崮山區,像老萬這樣的開明仕紳并不少見。所以,在歷史遺漏之處,正是文學出發之地。這倒不是說歷史敘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說文學完全可以提供給讀者另一種真實。這樣的真實有別于冰冷歷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溫度的感性存在。歷史常常喜歡關注整體和大人物,而小說則常常在個體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興奮點。
人是復雜的,而像鄉紳地主這樣的人物更復雜,對他們進行對錯和道德等方面的評價沒有那么簡單。我自認為這個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個能夠立起來的人物,經得起文學史的檢驗。
劉永春:小說中還有一個引起我極大興趣的人物,就是繡香。她早早就死去了,卻在小說中無處不在,既充當了某種預言者,也充當了萬仁義很多行為的引領者,時時提醒著萬仁義,成全著其“仁心義舉”。萬家的其他女人,不管妻妾還是女兒,絕大部分都是時代和命運的犧牲品,肩上承擔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歷次苦難。與她們相比,繡香在死后反而具有了省察一切的超能力,因而其命運中的悲劇色彩最淡。這個人物形象雖然不構成小說故事情節的主要動力,卻是深化小說主題的絕佳途徑。這種人物形象的設置方式及其敘事功能的充分利用,展現了你不俗的敘事能力。你在設置繡香這個人物形象時,是否已經意識到了她可能帶來的敘事便利和對小說主題展開帶來的開闊視野呢?
葉煒:的確有這方面的考慮。
鬼魂敘事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偉大傳統,蒲松齡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聊齋志異》是這方面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這個敘事傳統在當代作家這里沒有能夠繼續發揚光大。自從現實主義寫作成為時代文學主潮以后,亂力鬼神之類的東西已經被文學逐漸拋棄。殊不知,鬼神敘事正可以彌補文學的單調,能夠為現實主義寫作注入靈動色素。其實在《富礦》和《后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敘事,但多是經由“夢”這一載體來闡釋。比如在《富礦》中,麻姑多次與二姥爺的對話,《后土》中劉青松和土地爺的對話,都是通過做夢這一心理學方式來完成的。與此不同,《福地》的鬼魂敘事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成為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手段。《福地》中的鬼魂不需要再經由“夢”的媒介,而是直接由鬼魂出來說話。在第一章中鬼魂就出場了。為何要在小說一開始就進行鬼魂敘事?在我看來,這一敘事很重要。一方面是情節需要,更重要的是對于老槐樹敘事的補充。每當老萬遇到難事,繡香總要出來勸慰或者支招,在重大困難面前,甚至會直接現身施以援手。鬼魂敘事在小說中是一個完整的存在,力圖構建一個混沌的文學氣氛。
此外,我之所以在《鄉土中國三部曲》中采用鬼魂敘事,還有一個考慮,就是我正在努力實踐的超現實主義寫作需要。
劉永春:如果說《福地》主要刻畫現代中國農民在歷史與命運中的浮沉悲劇,那么,我覺得《富礦》則側重書寫當代農民在欲望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最終自我毀滅的人性悲劇。當然,這種悲劇仍然與單純重視經濟開發而忽視文化發展有著直接關系。前者是人被歷史壓迫,后者則是歷史通過欲望潛入人性造成自我異化。從閉塞的鄉村到現代礦區的轉變,使得麻莊人親眼見證了現代化的神奇力量,也使得他們對礦上的城鎮化生活趨之若鶩。傳統的鄉土道德轟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就是盲目遵從內心欲望而導致的利己主義。城市文明帶著自己的病菌侵入鄉村,改變人的精神結構與人性結構,這其實是現代鄉土書寫常見的方式,但很少有作家會利用礦區作為敘事場所和推進方式,這種構思與你的人生經歷有關嗎?在你的心目中,麻莊所代表的傳統鄉村出路何在呢?
葉煒:蘇北魯南有很多煤礦,蘇北重鎮徐州和魯南明珠棗莊,都是因煤而興、因煤而富、因煤而變的城市。在我的生活中到處都可以接觸到煤礦和礦工。我的一個姨夫就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煤礦工人,我從小就聽他講許多關于礦工的故事。來到徐州以后,又多次到礦區考察。這里曾經是經濟上的高地,也是人人稱道的能源富礦。當地下的黑金被過度開采,這里逐漸從一度繁華的能源大戶淪落為亟需改造的經濟洼地,由煤城明珠成為老工業基地。就像曹雪芹筆下的那座大觀園,繁花落盡之后,絢爛終究歸于平淡。巨大的經濟落差是難以讓人接受的,然而卻讓這里成為文學的“富礦”。
在我的心目中,中國的傳統美麗鄉村應該是這樣的:首先,它的底色一定是田園的,而不是城市化的,甚至也不是城鎮化的,它是中國獨有的村落存在;其次,生活在這里的人身上保留著中國典型的傳統美德,更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再次,村莊的民風是淳樸的,這里的人身上閃耀著善良的光輝,而少有都市的污濁;最后,鄉村自治功能能夠得以高度實現,鄉賢名士的風范得到極力張揚;等等。由此,我認為,中國的鄉村改造,重點在于人的現代化,而不是人居環境的城市化,在這方面,反而要盡量保存傳統的東西。
劉永春:在整個三部曲中,最打動我的是《富礦》的后半部,尤其是作為官婆轉世的麻姑再一變而成為“大洋馬”,這種巨大的、撕裂性的轉變所蘊含的巨大悲劇性讓我久久難以釋懷。在我看來,這個人物形象是20世紀文學中難得一見的鄉村女性,她的悲劇命運在周圍女性同樣的悲劇命運襯托下,沉重得讓人窒息。是的,“窒息”就是我在讀到《富礦》后半部時的直觀感受,而且的確讓我長久地沉浸其中,欲哭無淚。與《福地》不同,《富礦》主要由麻姑這樣一個女性而不是萬仁義那樣的男性來承擔現實苦難和歷史重負,為什么?你覺得麻姑這樣的悲劇女性在哪些方面、以哪些途徑與當代鄉土中國的命運相契合呢?
葉煒:我認為中國所謂的現代化存在著一個不斷“粗鄙化”的問題,包括發展的盲目性、造城的暴力性、文化的欺騙性、經濟的泡沫化。這樣的“粗鄙化”在鄉村改造中處處可見,這造成了鄉村不可承受的現實苦難和歷史重負。我覺得,文學在表現這些時,不能回避,應該正面強攻。在這方面,女性比男性更能彰顯矛盾的對抗性。所以,我選擇了麻姑。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麻姑的自我選擇。麻姑身上有著中國婦女的某些美德:勤勞,單純,向往美好,等等。但也有不少缺點:對物質化追求的向往,對欲望化生存的轉變等。這一點與當代中國的命運是契合的。當代中國鄉村經受了城鎮化的擠壓之后,焦慮感、矛盾性不斷凸顯。這些在女性身上有著更為集中的表現:一方面,留守在村莊的女性或主動或被動地走向了與傳統婦女美德相違背的歧途;另一方面,從女性打工者的城市遭遇反觀她們與鄉村的關系,其緊張程度已經非同一般。從她們身上,可以看到當代鄉土中國的癥候所在。
劉永春:除了被麻姑等人物形象所負載的巨大歷史悲劇打動以外,我還覺得《富礦》比《福地》對中國社會的精神反思和文化批判更為深入、更為尖銳,也更為有效。麻莊礦與麻莊村構成鮮明的兩極,一邊是夢幻般的現代城鎮生活場景,帶著頹廢的肉欲氣息,另一邊則是逐漸被抽空的鄉土田園。兩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敵視。許多人在兩種場景中來來往往,男男女女都被裹挾進“現代化”這個巨大的漩渦中,最終那些美好的生活和人性都不復存在,直到下一場大洪水與末日一起來臨。在那場大洪水之前,我注意到小說中美好的人物與人性都被毀滅了,而大多數人遵從自己的欲望卑微地茍活著。這是城鎮帶給鄉土的必然命運,還是人類歷史車輪碾壓下的暫時黑暗?這種人性的坍塌是我們為社會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嗎?你鮮明地用了“輪回”一詞,我理解為它代表了向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回歸,可以這樣理解嗎?
葉煒:在寫作《富礦》的時候,我有意把人物的命運推向了一種極致,正如你所說,美好的人物與人性都被毀滅了,沒有毀滅的都在遵從自己的欲望卑微地茍活著。表面上來看,這是城鎮帶給鄉土的一種必然命運,但這種結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來,這正是現代化“粗鄙化”發展的后果,是現代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必然代價。但我寧可把它理解為暫時性的黑暗。
在《富礦》中頻繁出現的“輪回”一詞,可以看作是向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回歸。事實上,《富礦》的結構也是一種“輪回”式的結構:從零到零。《后土》《福地》同樣如此:《后土》采用的是二十四節氣,《福地》是天干地支。這都是循環的結構。我有意在彰顯“輪回”的生命意識和文化意識。可以說,這也是我的哲學觀。
三、“以溫情思考與生活努力和解”
劉永春:《富礦》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現在,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這場制造城鎮的運動中,樓房越蓋越高,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礦工們努力工作然后到娛樂場所盡情揮霍,而附近村民為他們提供著揮霍的資源。”城鎮文明對鄉土中國的入侵當然是無情的、勢不可擋的,可是你的小說中也深刻描寫了鄉土社會本身對城鎮文明欲拒還迎的復雜姿態。在此背景下,出賣肉體、獲得金錢,在城市人紫秀的眼里“是無煙工業,是綠色生產,是姐姐妹妹站起來后的自主選擇,是勞動光榮身體致富”,而在麻姑眼里則是“用身體糊口活命”,“礦區越發展,對于那些沒有錢的窮人越是刺激,他們在心理失衡的情況下,會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來。”兩個人分屬于完全不同的兩套話語系統,前者是城鎮話語,后者是鄉土話語。兩種話語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無法截然地判定誰對誰錯。《福地》《富礦》與《后土》同樣充滿著對這種復雜關系的探析與思索,或者也可以說,《鄉土中國三部曲》是在城鄉互動的總體背景中思考鄉土中國的精神結構及其歷史命運的。當然,主要的敘事場所仍然是鄉村,而非城市。麻莊,就是鄉土中國的縮影。由此,麻莊的歷史變遷理所當然也能折射出鄉土中國的文化悲劇。
我的閱讀感受是,這種悲劇色彩到了《后土》就有所減弱,雖然小說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力度和對復雜人性的思考深度絲毫沒有減少,但矛盾沖突明顯變弱了,甚至有了些中和的趨勢,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尤其是小說對前任的村支書王遠既有深入的揭露,也有溫情的理解,這與傳統的鄉村惡霸形象截然不同,反而具有別樣的藝術魅力與思想深度。在你看來,這是否來源于三部曲反思道德失范、呼喚精神重建的主題呢?同時,這樣的結局安排對劉青松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重要,他身上呈現出來的鄉土智慧和寬恕之道與萬仁義遙相呼應,二人都寬厚待人、以鄉鄰的命運為己任,堪稱傳統美德的化身。我理解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鄉土中國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兼具傳統文化的天下情懷和現代社會的寬廣視野。可以這樣理解嗎?
葉煒:你可能已經看出來了,從《富礦》到《后土》,我在努力試圖與生活達成一種“和解”。現實是殘酷的,但生活依然在向前。當我們無法與生活決絕對抗時,只能選擇和解。隨著閱世的深入,我對當代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一些改變。有時候,我們發現了問題所在,但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個時候,我們怎么辦?問題當然要暴露,答案也要不停地去追尋。但在追尋答案的時候,我們和現實的緊張關系應該有所緩解,以便能有一個更為客觀的視角。
在現實生活中,王遠這樣的村干部廣泛存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主流”。我認為通過反思他們,可以反思現在的的鄉村基層政權的生態,也有利于深化反思道德失范、呼喚精神重建的主題。
劉青松和萬仁義是我所鐘愛的人物,如你所說,他們兼具傳統文化的天下情懷和現代社會的寬廣視野,不但是《鄉土中國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更是鄉土中國的希望所在。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劉永春:在悲劇色彩有所弱化的同時,《后土》的敘事結構和人物設置也與前兩部不同。《福地》以萬仁義和繡香一男一女、一生一死、一明一暗、虛實結合的手法結構起整部小說;《富礦》以麻姑(大洋馬)為敘事單線,勾連起六小、蔣飛通、胡列等男性與笨妮等女性、麻莊村與麻莊礦兩個文明場域,從而刻畫了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欲望膨脹與人性畸變。《后土》雖然以劉青松為主要敘事視角,卻集中展示曹東風、劉青松與王遠三人之間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與心理糾葛。如果說前兩部因其敘事結構而更具深度的話,《后土》則因其立方體一般的敘事結構而更具廣度,更能呈現當代中國鄉土社會的復雜性,在藝術上雖不具備前兩部同樣的悲劇色彩和人性深度,但也能夠別辟蹊徑地從政治角度展示鄉土社會的當代命運,同樣也有其成功之處。《福地》與《富礦》更具傳奇性和戲劇性,而《后土》回歸到生活本真,更具日常性和寫實性,是“生活流”,表面上波瀾不驚,但其實水面之下卻也有著各樣的人性漩渦。小說不緊不慢地處理著當今鄉土社會的種種矛盾,將筆致指向鄉土社會的底層結構和日常狀態。這種變化是有意為之嗎?如果將《后土》中溫情的社會改造與《福地》呼喚的文化重建、《富礦》呼喚的道德回歸相結合,是否可以看做是你對鄉土中國未來出路問題的最終答案呢?
葉煒:你敏銳地捕捉到了三部曲的內在韻律。從《福地》與《富礦》的傳奇性和戲劇性凸顯,到《后土》對日常鄉村生活本真的發掘,其間的變化明顯。這種變化既是我的有意選擇也是無意為之。“有意選擇”是指我在體悟生活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認識上的變化:絢爛總是歸于平淡。“無意為之”是指我在寫作之初確實是我控制著文本,但在寫作開始之后,文本慢慢有了自己的“選擇”,人物的命運有了自己的脈絡,既是可控的,又是不可控的——它們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內在邏輯。
在《鄉土中國三部曲》創作中,《后土》著眼點偏重于政權改良和社會改造,《福地》著重于觀照鄉村倫理和傳統文化,《富礦》側重人性輪回和道德回歸,三者相結合,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看作是我對鄉土中國未來出路問題的答案。至少,這些都是我自己對鄉土中國的思考。
劉永春:《鄉土中國三部曲》搖曳多姿,仿佛奔流的大河,不斷生出令人嘆服的美麗浪花,風格豐富多彩、敘事角度多變、主題立體充實。這在近年來的70后作家創作中并不多見。總的來看,三部小說都屬于鄉土書寫中的現實主義流脈,具有尖銳深刻的問題意識、厚實沉重的文化含量與獨具特色的敘事形式。可以說,《鄉土中國三部曲》的現實主義特征十分明顯。但是,還有另外一面,也是我特別感興趣的,那就是三部長篇中都有一些超驗性的人物、神祇或者現象存在。這些敘事要素與明朗、尖銳的現實主義藝術特色既然不同,它們帶來的是某種神秘感、宿命感與無助感。它們構成了一個與主要情節相互映射的鏡面世界,有時候是平面反射,有時候是曲面反射,十分有趣。比如幾部小說都寫到鄉村中的土地神信仰、看似瘋癲實則清醒的男女瘋子、可以俯瞰世界的死者或者樹靈,諸如此類的超驗性要素在小說中承擔了怎樣的敘事功能和藝術功能呢?這些帶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與情節要傳達怎樣的主題呢?這種敘事手法更多受到中國的志怪志異傳統影響呢,還是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
葉煒:當代中國的現實是如此復雜,鄉土中國的歷史又是如此吊詭,以至于探尋現代中國的現實,不得不回到古老的中國。在我看來,這樣的時間跨度和題材書寫非常適合一種超現實主義寫作。《鄉土中國三部曲》中所使用的老槐樹視角以及時或閃現鬼魂敘事和土地神以及男女瘋子等,讓小說有了超越現實的靈動幻象,既讓所書寫的故事既附著于現實存在,又充滿了歷史的想象。整個小說可以說是一次超現實主義的寫作實驗——既有現實主義的色彩,又有魔幻主義的營構。
《鄉土中國三部曲》描繪了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有現實的書寫,更有歷史的回望,有民風民俗的展示,更有鄉村精義的探求,其書寫對象是很廣闊的,必須有一個科學合理的視角。比如,在《福地》中,老槐樹不但知曉麻莊所發生的一切,能夠和麻莊那些死去的魂靈對話,也可以和麻莊的老鼠等動物交流,更可以穿越歷史,和天地人鬼神溝通。所有這些,都是其他敘述視角所不能承擔的。對我來講,這也是打破當代文學中的敘事成規的有益嘗試。從效果來看,這些讓小說文本更加靈動,敘事更加豐富,藝術更加搖曳。
我從小所接受的故事傳統是鄉土大地萬物有靈,長大后我接受的教育則告訴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人類對未知世界應該有自己的敬畏感。中國是一個缺少宗教意識形態的國家,作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以文學的方式尋求真理真相,探求和構筑中國的信仰系統。這也是我在《鄉土中國三部曲》的創作中所隱含的主題之一。
如前所述,這種敘事手法受到了中國的志怪志異傳統的影響,當然也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子,可以說本土和外來的兩個影響都有。但從我的閱讀視野和知識結構來看,本土的影響是根本的,外來的啟示是次要的。
劉永春:麻莊,是三部曲共同的敘事場域,我注意到它既是文學化的虛構也是現實文化地理的真實呈現,尤其在《福地》中,麻莊有著明顯的地理坐標。三部曲始終將麻莊放置在“蘇北魯南”的位置上,多次對這塊地域的地域特征、文化內涵做出闡釋。例如,“這里是蘇魯大平原,齊魯大地南大門,蘇豫皖銜接帶,為孔孟老子等圣賢之地,既上承曲鄒孔孟之禮,又下納豐沛漢王之風,為一代帝王之鄉;既北蓄泰岱之豪放,又南收江淮之靈秀;既西取微湖之廣闊,又東收沂蒙之厚重;既有‘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的豪放,又有‘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的悲壯……”可不可以認為,麻莊、蘇北魯南,既是你的生命故鄉,也是精神故鄉呢?
葉煒:是這樣的,你的解讀非常準確。《后土》在《作家》發表時,附了我的一個創作談,我在創作談里寫到村莊是我出生的“血地”。那里,已經成為了我創作的永遠的精神出發地。換句話說,麻莊和麻莊所在的蘇北魯南既是我的生命故鄉,也是精神故鄉。我深深地愛著那個村莊,愛著那片廣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莊以及村莊所在的蘇北魯南大平原將成為我終生創作的文學地標,我將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對它們頂禮膜拜和深刻反思。我要在持續不斷的“精神還鄉”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來路,建立我自己的精神王國和生命信仰。
劉永春:《鄉土中國三部曲》展現了你良好的寫作狀態和美好的創作前景。尤其是其中的反思精神、求索姿態和辯證思維,令人十分敬佩。你的鄉土寫作業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壇中一道獨特的風景,作為同齡人和忠實讀者,非常期待你的下一部大作問世。
責任編輯馬新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