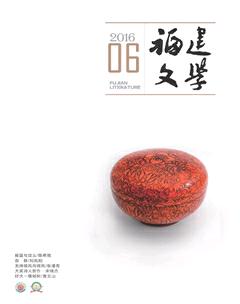西流:為打結(jié)的歷史松綁
中國(guó)自古重史,所以有良好的修史傳統(tǒng)。古時(shí)修史,其中一個(gè)功能是監(jiān)督帝王,所以有“董狐直筆”之說。到了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主要功能似已蛻變?yōu)楣┙y(tǒng)治階層維護(hù)統(tǒng)治作參考了。只可惜“以史為鏡”也不容易做到,因而歷史就不斷地重演,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也。
現(xiàn)代的史觀當(dāng)然不會(huì)如此膚淺。不過要搞明白歷史,說實(shí)話也并不容易,司馬遷修《史記》,彪炳千秋,現(xiàn)在看來(lái),有些地方也不合史實(shí),甚至類似小說家言。多弄玄虛的《晉書》更不用說。有人說“歷史從來(lái)都是一筆糊涂賬”,說得并不錯(cuò)。
一口氣讀完鴻琳的“梨城系列小說”,更加深了這種印象。“梨城系列”算歷史解密小說,這種小說往往有著偵探推理小說的外殼,所以好看;又因與歷史有關(guān),有時(shí)空的縱深感,所以顯得有深度。但是寫好也并不容易,寫得不好即容易流于通俗,變成獵奇;太嚴(yán)肅、古板又容易演變?yōu)閷W(xué)術(shù)論文。這種小說拿捏得好與不好,以我之見,最關(guān)鍵的不是技巧,而是寫作的出發(fā)點(diǎn),作者的歷史洞察力與思想深度。
所幸,鴻琳在這個(gè)方面做得極其出色。因?yàn)槭窍盗行≌f,鴻琳賦予了三篇小說形式上的一致性,內(nèi)容上的相近性。故事背景都設(shè)定于上世紀(jì)四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要解密的歷史都是“黨史問題”:《梨城叛徒》要解決的是作為“新四軍清源山軍分區(qū)派往梨城的交通特派員”的“我二叔”在被日軍俘虜后是否真的做了叛徒?《尋找慈恩塔》要解決的是慈恩塔塔頂?shù)降资窃趺礆У舻模渴欠衽c新四軍有關(guān)?《告密者》要解決的是“梨城城工部組織部長(zhǎng)章文”是否真的是因朱滿倉(cāng)告密而被捕?鴻琳都在一開篇即拋出問題,然后用幾乎通篇敘述的語(yǔ)調(diào)講述整個(gè)解密過程,歷史與當(dāng)下不斷交織,形成一種藝術(shù)特色。鴻琳似乎刻意選擇了平靜的敘述語(yǔ)氣,讓整篇行文顯得客觀、冷靜、嚴(yán)謹(jǐn),仿佛真的只是在做一個(gè)學(xué)術(shù)上的探究,但是你分明能透過紙背,感覺到作者刻意壓抑的心跳和體溫。這是鴻琳控制能力的高明處。
鴻琳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總能很好地選擇歷史的打結(jié)點(diǎn),然后通過解密的方式,為它松綁。前文說過,歷史就是一筆糊涂賬,認(rèn)真梳理,總有很多疑點(diǎn)值得發(fā)掘。有想象力的作家總能就此取材,從這些疑點(diǎn)出發(fā),任意馳騁想象。但僅有疑點(diǎn)還并不足以成為“打結(jié)點(diǎn)”,打結(jié)點(diǎn)必須是矛盾的聚焦區(qū),反映的往往不是證據(jù)的問題而是價(jià)值觀的不同選擇,甚至是人性的不同展示。就像《告密者》中在朱滿倉(cāng)是否告密這個(gè)問題上,不同人的不同反應(yīng)一樣。截然不同的反應(yīng),加上互相提供的恰恰矛盾的證據(jù),使這個(gè)問題成為歷史的一個(gè)打結(jié)點(diǎn)。所以從表面上看是一個(gè)史實(shí)問題,深入探究下去,卻發(fā)現(xiàn)實(shí)際上這是一個(gè)如何評(píng)價(jià)歷史,以及如何評(píng)價(jià)歷史中的人的問題。從問題指向人,這才是小說家要做的事。好的小說家絕對(duì)不會(huì)滿足于單純的歷史解密,因?yàn)槲覀兒苋菀拙蜁?huì)發(fā)現(xiàn),雖然解密者的解密之路貌似十分艱難,但其實(shí)不然,因?yàn)榭倳?huì)有知情人存在。知情人閉口隱瞞,甚至故意為之遮掩、撒謊,其背后的深層動(dòng)機(jī),才是好的小說家真正要探究的。《梨城叛徒》中鴻琳就是抓住了“我二叔不能死”這句話作為突破口,在《告密者》中他再次通過“章文”不能死強(qiáng)調(diào)了這個(gè)發(fā)現(xiàn),從而向自己——也向讀者——提出了這樣一個(gè)問題:革命者出于更重要的革命目的忍辱偷生,甚至成為“叛徒”,對(duì)此歷史——主要是作為后人的我們——究竟該如何評(píng)價(jià)?比這個(gè)更難評(píng)價(jià)的還有,比如《尋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出于保護(hù)大多數(shù)無(wú)辜群眾故意違抗上級(jí)命令放棄炸毀日軍軍火庫(kù),《告密者》中的朱滿倉(cāng)為了挽救整個(gè)村的村民充當(dāng)了可恥的“告密者”,對(duì)此歷史究竟該如何評(píng)價(jià)?
鴻琳殘忍地把我們逼到了一個(gè)兩難處境。也正因?yàn)榇耍瑲v史的當(dāng)事人只能或者隱瞞或者掩蓋歷史的真相,任歷史漸漸變成一筆糊涂賬。后世的探究者,即使探究出了真想又能如何?這注定是一場(chǎng)無(wú)用功,就像鴻琳在小說的結(jié)尾,讓辛辛苦苦探究出的真相仍然只能繼續(xù)埋藏。
然而,誰(shuí)能說這真的只是一場(chǎng)無(wú)用功?鴻琳通過他的小說,讓讀者在跟著他一起解密歷史的過程中,真切地從人的角度貼近了歷史真相,增加了一份對(duì)歷史人物的理解和同情,這正是文學(xué)的一大功用。
如果說還有不滿足,我必須指出鴻琳其實(shí)完全還可以再進(jìn)一步,在他的筆下,無(wú)論是“我二叔”(《梨城叛徒》),還是“章文”(《告密者》),鴻琳寫出的主要還是他們的革命性,盡管他們出于特殊的目的作出了惹來(lái)爭(zhēng)議的選擇,但解密后作為讀者的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思想上還是單純的、立場(chǎng)是堅(jiān)定的,他們并沒有作為普通人的軟弱和動(dòng)搖,沒有真正的矛盾和爭(zhēng)議,這必將削弱他們?cè)谖膶W(xué)上的意義。倒是《尋找慈恩塔》中的“我父母”以及《告密者》中的“朱滿倉(cāng)們”的舉動(dòng)更有文學(xué)意味一些,也真正值得我們深思和探究。從這個(gè)意思上來(lái)說,鴻琳的任務(wù)才只完成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