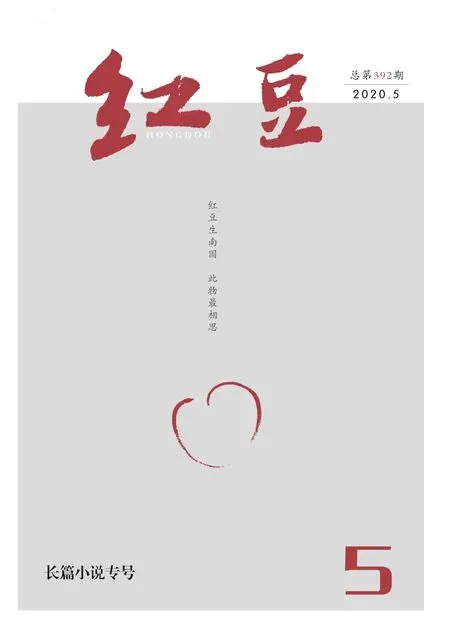菩薩保尋妻記(短篇小說)
扎西才讓,70后藏族作家,甘肅甘南人。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理事,第二屆甘肅詩歌“八駿”之一。作品見于《民族文學》《十月》《散文》《山花》《北方文學》《芳草》《西藏文學》《飛天》等文學期刊,作品入選《當代西藏漢語文學精選1983-2013》《中國好文學》《散文2015精選集》等多種選本。已出版詩集兩部。
藏戲場
太陽懸在空中,照耀著北方藏地。一個名叫尼瑪的村寨里,厚實的柏木板搭建成的露天舞臺上,正在上演藏族最古老的傳統戲劇《諾桑王子》中的經典一幕:忠勇的諾桑王子即將遠征,他的新妃——天界仙女云卓拉姆揮淚送行。身著華美服飾的女演員在扮演諾桑王子的男演員身邊徘徊,留戀,難分難舍,痛不欲生,顫著低沉舒緩的唱腔:
國王之令是山上滾下的石頭再也不能回山,
國王之令像河里流下的河水再也不能回流。
我想敬他三碗酒可眼淚就像斷了弦的珠子,
賢明的王子親愛的夫君左思右想難離開你。
馬駒雖與母馬分離遠不過隔墻的嘶鳴呼應,
你和我一別千里定然望不見身影聽不見聲。
看那湖中鴛鴦雙雙游走形影不離相愛相親。
看那山巖雄鷹雙雙振翅翱翔藍天相依相偎。
祈求天界各方諸神憐憫我這個苦命的人吧,
我英勇的王子要去冰雪覆蓋的北方荒原了!
舞臺下擁擠的看客中,一個身穿灰色夾克衫的鬈發青年,顯然未被云卓拉姆深情而動聽的唱腔吸引,他只盯著人群那邊的一個紅衣女子。那女子似乎已經深陷在劇情當中,半張著嘴巴,眼里洇淫著哀傷。她的旁邊,是個年老的婦女,長時間地看著仙女云卓拉姆的扮演者,嘴角流露出一絲笑意。或許感覺到了有人在注意自己,她下意識地回過頭來。青年趕忙低下頭,身體往后一縮,把自己隱在旁邊粗壯漢子的身后。
漢子奇怪地問:“菩薩保,你躲啥呀?”
菩薩保斜瞥了漢子一眼,不吭聲。
漢子笑了:“看樣子你不是來看《諾桑王子》的,你是來搞女人的!”
菩薩保低聲罵:“甭放屁了,看你的戲吧!”
漢子也惱怒了:“你有這想法,我還不能說?!”
菩薩保不再搭腔,從人伙里往外擠。被擠的人開始嘟嘟囔囔地抱怨,但剛一接觸菩薩保陰冷的眼神,就都閉了嘴。
菩薩保擠出人群,坐到院墻上,從皺煙盒里抽出一支干癟的香煙,點著,深吸了一口。
再看那舞臺上,諾桑王子正行走在人們看不見但都想得著的密林中。人們觀察著他的動作,想象他分開密集的灌木,涉過湍急的河流,爬上陡峭的高山,鳧過漆黑的深淵,終于疲倦地靠在一塊巨石下,開始了長途跋涉后的第一次休息。他的眼前,定然是一灣寶藍色的湖水,在昏黃的斜照里,波閃著秋天的鱗光。高高的天幕投影在水中,那些云也在湖中舒緩地飄蕩,慢慢地,凝聚成了仙女云卓拉姆美麗的容顏。諾桑王子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面對湖面深情地吟唱:
當一月前的圓月再次升起在那東山之巔,
云卓拉姆啊我始終在尋覓你嬌媚的容顏。
在蒼茫的云霧中我曾經那般的失魂落魄,
心中的花蕊啊若你有知就要祈禱我平安。
格烏日楚山洞的隱士指引我來到了這里,
他把辟邪去污的美麗指環套在我的手腕。
亂如細麻的路線圖在我心中被深深刻印,
我終于看到了你曾經洗浴的鏡湖的湖面。
雖然前面還有那嗜血的蚊子群居的山谷,
我定會穿越猛惡林和毒蛇山到達你身邊。
菩薩保看到這里,用食指揉滅了炙熱的煙頭,他感受到了高溫灼傷指頭時的鉆心的疼痛,皺了皺眉,發出一聲冷笑,自言自語:“哼,把和壞人爭斗的,都不演了,盡演這男人女人間的破事。都他媽的是騙人的故事,人間哪有這樣相愛的一對?!”
他是藏戲迷,尤其對流傳很久的八大藏戲中的《諾桑王子》的劇情最為熟悉。
在這北方藏地,藏歷新年一到,初一到十五,總有民間藝人在人口較多的村落,寺院僧人在規模較大的寺院,戴上紅綠黃白各色面具,敲鼓鳴鑼,穿紅著綠,把《文成公主》《諾桑王子》《朗薩雯蚌》《卓娃桑姆》《蘇吉尼瑪》《白瑪文巴》《頓月頓珠》《智美更登》等八大藏戲搬上舞臺。這時候,人們就會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梗著脖子觀看。看到激動處,會發出大的動靜來。若演出地在村落里,吼叫聲、大笑聲、鼓掌聲甚至怒罵聲,會比鑼鼓聲還有喧囂。若是在寺院里,大家就安靜得多,看到要緊處,只會發出嘆息,像被堤壩圍住的激流的濤聲,剛剛激蕩起來,頃刻間就又平息下來。
這一天,是燃燈節。按常理,尼瑪村在這天是不演藏戲的,然而這些年來,非遺文化搞得紅紅火火,總有官方的人出面,專門組織那些打工回來會唱戲又愛熱鬧的人來排練藏戲,這樣堅持了三五年,像尼瑪村這樣的大村落里,以民間藝人為主要組成者的藏戲演出團就漸漸被恢復了。為了湊個熱鬧,圖個高興,也就不單單只在雪頓節那天演出,像燃燈節這樣的與佛的使者有關的節日上,也熱熱鬧鬧地上演著,算是對快要到來的藏歷新年的某種期盼。
菩薩保喜歡看藏戲時的那種熱熱鬧鬧的氛圍,更喜歡以局外人的身份關注別人的人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他才覺得自己才是活得清清透透快快樂樂的。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他才覺得活著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事。
但在今天,他的心思顯然不在看戲上,對戲中演的內容,也帶著強烈的反感情緒。
墻角下,立起一個老頭,穿著寬大的皮襖,身上散發著一股若有若無的膻味。老人瞪了菩薩保一眼說:“尕崽娃,你這話說得太過了。我看這藏戲看了五十多年,還沒看厭煩呢!”
菩薩保不理老人,從院墻上跳下來,拍了拍屁股上的白土,身后頓時彌漫起一團土塵。
老人生氣了:“哎,尕崽娃,講點禮貌行不?”
菩薩保說:“讓諾桑王子給你講道理吧,我可是個粗人,不懂禮貌這玩意兒!”
老人張口想說什么,但只說了半句,就被菩薩保拍起的土塵給嗆著了,大聲咳嗽起來。
菩薩保趁機重新鉆進人群,挨挨擠擠往前走。終于選好一個地方,站定了。卻不看藏戲,抻著脖子找那紅衣女子。東張西望了一會,看清了人伙里隱藏著的那片紅,心跳也快了起來。這時再看舞臺上,諾桑王子正在做出彎弓射箭的動作。只聽嗖的一聲,利箭一下子就勁穿了三棵白楊。臺上臺下轟然叫好,口哨聲、撫掌聲、嘖嘖聲……就像青海湖的濤聲那樣此起彼伏地響起來。
菩薩保側首再看不遠處的紅衣女子,那女子目不轉睛地盯著舞臺上的諾桑王子和云卓拉姆,或因為激動,或因為躁熱,漲紅著臉。看到這一幕,他的心忽然就收緊了,有一個聲音在腦子里回響:“這臭婆娘,還看上癮了呢!”
人群忽又騷動起來,原來有幾個王子在朝云卓拉姆拋灑彩箭。那幾個王子的彩箭紛紛墜落在云卓拉姆的周圍,就是落不到她的身上。輪到諾桑王子時,那演員在原地轉了三圈,嗖然就拋出了彩箭。彩箭像長了翅膀,飛旋著落到云卓拉姆的懷中。臺上臺下,再次爆發出轟鳴般的喝彩聲。
喝彩聲中,菩薩保突然覺得有什么不對勁,往紅衣女子所在的位置瞅去,眼光撲了個空。他快速地在密集的人群中搜索那耀眼的紅色,捕獲的卻是一團又一團的灰影。
“她們離開了。”他想,“大概發現了我,跑了!”
他匆忙擠出人群,在場院周圍搜尋,還是找不到紅衣女子的身影。
他離開露天劇場,緊跑幾步,趕到村口,眼睛霎時就亮了。不遠處,那紅衣女子正緊隨在老女人的身后,急匆匆地順著山谷里的小路往外走。偶爾扭頭回看,顯然是觀察有沒有人尾隨的樣子。
菩薩保閃身在半截矮墻后,感覺到心臟怦跳得分外厲害。他將手伸進夾克衫內,摸著了一個硬硬的溫乎乎的長家伙。
“今兒個,就要靠你說話了!”他對懷里的長家伙說,口氣也是硬硬的。
路途中
“阿媽,你,你真的看到他了嗎?”
紅衣女子結結巴巴地問走在自己前面的老女人。
老女人正在用右手搓動一串紫色佛珠,嘴里念叨六字真言,對于紅衣女子的詢問,似乎不曾聽聞。
“阿媽,我在問你呢!”紅衣女子惱了!
老女人停止了念叨,回頭答道:“急啥?我正給你祈禱呢!”
紅衣女子說:“戲看得好好的,你就心急火燎地喊我回去,你說能不叫人擔心嗎?”
“他肯定是奔著你來的,我們要防著他才對。”老女人說,“愿佛祖保佑我們平安!”
“那我們怎么辦呢?”
“怎么辦?要趕緊回,越快越好!”
老女人攥住紅衣女子的手腕,拽著女子往前走。
紅衣女子“哎呦”一聲:“阿媽,你攥疼我了!”
老女人:“云卓瑪,你再不快點走,他追上來,就麻煩了!”
被稱作云卓瑪的女子下意識地扭頭往村莊的方向看。這不看倒好,一看,兩腿就僵硬起來。她果然看到一個黑影,閃到半截矮墻后了。
“阿媽,我好像看到他了!”
老女人吃驚地叫起來:“啊?他真的跟著來了?”順著女兒眺望的方位看,卻沒看到什么動靜。
云卓瑪不搭話,頻頻扭頭往后看,眼里蓄滿驚慌。
兩人一前一后匆匆走了兩里多路,都感覺有點累,腳步明顯放慢了。山谷小路上行人稀少,下午的陽光,鋪在初冬枯黃的田野里,到處都是溫暖的色澤。有兩三只鳥從遠處啾啾啾地鳴叫過來,掠過她們的頭頂,遠去了。
云卓瑪跟在母親身后,看著那矮胖的背影說:“阿媽,我想好了,我還是回去跟他一起過吧!”
老女人愣住了,停下腳步,扭頭訓斥自己的女兒:“跟那個敗家子過日子?你都是兩個娃娃的人了,還說這種可笑的話!”
云卓瑪說:“他就是好吃懶做慣了,倒沒有其他的毛病!”
“還沒毛病?”老女人拉著女兒繼續往前走,“早就罵你打你了,還說沒毛病!”
云卓瑪說:“那是他喝醉了嘛!”
老女人說:“那他上次打你,是怎么回事?”
云卓瑪說:“他生氣了!”
老女人說:“生氣了就打自家的媳婦?他不心疼你,我可心疼呢!”
云卓瑪看了看母親,眼圈紅了,一滴淚落在袖口上,紅色的布面上洇出一團深色來。
女兒一哭,老女人的口氣就變得溫柔了:“不是我不讓你和他過日子,是他不想和你過。”
云卓瑪噙著淚點點頭:“你說得對,他就沒有個過日子的樣子。”
“就是嘛,”老女人說,“你看他田剛剛種上,就借口出去打工,一跑,一年半載不回來。終于回來了,兩只手都是空的,就不是個想活人的樣子!”
云卓瑪辯解:“他說他沒掙到錢。”
老女人說:“屁話!人家們能掙到錢,彩電呀組合柜呀一件一件往家里搬,白面一袋一袋往柜里倒,有的人家都買上小車了。他倒好,做甩手掌柜,還愛喝酒,喝醉了就打你。你是我的心頭肉,打你就是打我,我可難受得很呢!”
云卓瑪說:“阿媽,你別說了!”
這時兩人都走得渾身出了汗,就停住腳步,在路旁枯黃的草地上坐下來。抬頭看看太陽,已經朝西山那邊靠近了。西山背后,是另一座高聳入云的山,山頂積著雪,閃耀著銀光。天空里,是那種令人絕望的沉重的藍色,一大片灰白色的云,凝滯著,一動不動,只把深色的暗影投在南山林里,看著就讓人覺得焦慮。
老女人看看南山,又看看女兒,問:“你跑回來后,他給你打過電話嗎?”
“沒有!”云卓瑪低著頭,用路邊雜草擦拭皮鞋上的灰塵。
“那他托人給你帶話了嗎?”
“也沒有!”
老女人有點奇怪:“啥動靜都沒有?”
“沒有!”云卓瑪不像在回答,倒像在呢喃。
“你看,你看,”老女人狠狠地說,“人家就根本不把你當人!”
云卓瑪的淚流了下來:“不是的,我聽別人說,他一直在喝酒,都沒從家里出來過。”
“哼,掙點錢,光知道喝酒,就不是個有志氣的人。”老女人說,“你和他離婚,這個選擇,是對的!”
云卓瑪突然站起來,指著唱藏戲的尼瑪村說:“阿媽,你看,你看,那個人是不是他?”
村莊外大路旁的一塊巨石上,坐著個瘦瘠麻稈的男人,臉朝著她們的方向,遠遠張望的樣子。
老女人站起身看了半晌,揉揉眼睛說:“我看就是。他就穿著那衣服,在人群里賊頭賊腦的,像是在找我們。”
云卓瑪慌了:“那我們趕緊走吧,別叫他追上來!”
老女人說:“就是,趕緊走,天黑前趕到家里!”又說,“我說別來看戲,你偏要來,還說心情不好。我看這心情,在這時候才不好呢!”
云卓瑪:“阿媽,你就甭抱怨我了,你不是說好幾年沒看戲了,也想來嗎?”
這次是云卓瑪走在前頭,老女人跟在后頭,邊走邊喘氣。
云卓瑪挽住老女人的胳膊:“阿媽,自從阿爸離開人世,你的身體弱了!”
老女人:“不是身體弱了,是心力弱了,再也打不起活人的精氣神了。”
其實,自從男人過世后,老女人覺得自己的天空就傾斜了,惶惶然不知該怎么活下去。她原先就信佛,這次索性把自己完全交給佛祖,只聽心里頭的那個聲音來左右自己的命運。時間一長,她就完全靜了心,似乎能感知到自己的靈魂,覺得這樣活著挺好的。
不曾想女兒的婚姻也有了裂紋,眼看就有破裂的危險。這又使她的靈魂無法安靜了。她本想勸女兒維系婚姻,但卻直覺女兒跟著菩薩保,肯定沒啥好日子過,也就站到了女兒這一邊。
“我也想好好過日子。”云卓瑪說,“他可好,光顧他自個,根本就不管家。”
“這時候你看清他了?遲了!”老女人說,“當年人家來相親,你一眼就看上了。我們不愿意把你嫁給他,可你倒好,犟得很,尋死覓活的,硬是要跟人家。你阿爸又沒啥主意。結果你看,走到這個程度了吧!”
云卓瑪說:“阿媽,你就甭說啦,我哪知道人心會變得這么快!”
“那不是人心在變,那是有的人的本質就壞。”老女人說,“你看他今個這架勢,就是要跟個來的意思。”
說著回看村莊外巨石上的男人,發現那人還頂著冬日的太陽,禿鷲一般焊在那里,兩人不再緊張,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來。
老女人問:“兩個娃娃還在前房大伯那里嗎?”
云卓瑪:“就是,聽說他的大媽看著呢,見不到我,總是哭鬧。”
老女人:“他們再哭再鬧,你還是不能回去。你要強硬些,不要給他慣毛病!”
云卓瑪:“知道了。我就是心疼娃娃,他們跟著他,吃不飽,穿不暖,會受罪的。”
老女人:“這罪得受。你心軟了,他的心就硬了,你在他家里,就再也沒有地位了。”
說話間,已經快到谷口了。出谷口左轉,就是直通達娃村的另一條山路了。
云卓瑪突然“哎”的一聲:“阿媽,他不見了!”
老女人也回頭看,村外那塊巨石上,果然沒了那個男人的身影。村莊里,有鼓樂聲隱約傳來,斷斷續續時有時無的。
云卓瑪:“他哪里去了呢?我有點害怕!”
“你被他打怕了!”老女人說,“估計回去看戲了,這戲要演完,天就黑透了!”
塵埃里
在尼瑪村外巨石上呆坐的男人,確實是菩薩保。
他在石頭上坐了很久,屁股都被凍麻了,還是下不了該不該追上媳婦問個究竟的決心。村莊里不間斷地傳來鑼鼓聲,告訴他這可以演三天三夜的《諾桑王子》,還沒到完全結束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和媳婦的婚姻,也還沒到魚死網破的時候。
“那諾桑王子能找到云卓拉姆表達愛意,我也該追上她們問個究竟。”
他這樣想著,暗暗地強迫自己要下決心。
他并不是專門來看藏戲的,而是借看戲之名來找自己的媳婦的。他的媳婦,就是那個紅衣女子——云卓瑪。那老女人,正是他的岳母。
一月前,他從外地打工回來,一進門,就把媳婦掀翻在炕,胡天海地地折騰起來。兩個年幼的孩子以為父母開始打架了,嚇得哇哇大哭。云卓瑪也很激動地接受了丈夫的安慰,也許因為兩人都很投入,都累出了一身臭汗。事后,菩薩保才打開隨身挎包,掏出個黑色塑料袋,打開,是一沓紅丟丟的鈔票。
菩薩保數了三千元,遞給云卓瑪:“掙得不多,只掙了六千,這三千給你,剩下三千,我留著。”
云卓瑪接過錢,吃驚地問:“你都出去快一年了,就掙了這么點?!”
“找不到活嘛!”
云卓瑪蹙起了眉頭:“別人都兩萬三萬地往回拿,你只掙了這么點,還要自己留一點,像話嗎?”
菩薩保的臉上涌起了潮紅,問:“你說啥?”
云卓瑪的聲音明顯小了下去:“你別留了,都給我吧,家里到處都用錢呢!”
菩薩保:“你嫌我掙得少了,對吧?”
云卓瑪低著頭,不敢看菩薩保。
菩薩保:“我如果不留些,連手們來了,吃土呢還是喝風呢?!”
“你把那煙酒不抽不喝不行嗎?”云卓瑪嘟囔了一句。
“你說啥?”菩薩保惱怒了,“不抽不喝,像個男人嗎?”
“抽煙喝酒就是男人了?哪有這種道理!”云卓瑪快要哭了。
菩薩保一把搶過云卓瑪手里的錢:“不要了算了,這可是我的血汗錢!”
云卓瑪隔著炕桌來搶被菩薩保搶去的錢,不小心竟刮破了男人的手背。菩薩保把錢往空中一甩,順手就給了云卓瑪一記耳光。
兩個坐在炕里頭的小孩,又被響聲驚得尖叫起來。
云卓瑪捂住臉,呆住了。瞬間又反應過來,就不管不顧地撲向菩薩保,一邊凄烈地號叫,一邊伸手朝男人的臉上又撕又摳。
菩薩保抓住女人的兩個手腕,一用勁,就把女人壓倒在炕桌上。云卓瑪想用腿踢,又被男人翻過去,面朝向了桌面。菩薩保跨腿騎在女人的背腰上,把女人的雙手反扣在背后,左手扼住,騰出右手揪住女人的頭發,把女人的腦袋使勁往桌面上按。云卓瑪的嘴唇一陣疼痛,牙齒啃上了桌面的油漆,想罵,卻無法開口,只好徒勞地掙扎,發出“呃呃呃”的反抗聲。
兩個小孩扯著嗓子驚慌地哭叫,房間里亂成一團。
“甭哭!”菩薩保訓斥兩個孩子,“再哭我就揍你們!”
兩個孩子張口結舌,眼淚和鼻涕流下來,流進了嘴里。
菩薩保問云卓瑪:“服了嗎?”
云卓瑪激烈地扭了扭身子,發出“呃”的短促的聲音。
菩薩保:“看樣子你還沒服。我告訴你,男人的事,你一個婆娘家,少管!”
云卓瑪又掙扎了一下,動作有氣無力的。
菩薩保:“說!服了沒?服了我就放了你!”
云卓瑪不掙扎了,又發出“呃——”的悠長的聲音。
菩薩保丟開女人的頭發,跳下炕來,警惕地盯著女人。
云卓瑪仍然趴在桌子上,頭一杵一杵的,像是在暗泣。大一點的孩子爬到母親身邊,抱住母親的頭哭起來。大的一哭,小的那一個,也跟著哭起來。屋子里又是兩個孩子的哭叫聲。
孩子們哭叫的時候,菩薩保彎腰拾起風馬般灑在地上、炕沿上的鈔票,拾掇干凈了,又塞在挎包里。看女人還趴在炕桌上一動不動,就背了挎包,出了門。
云卓瑪在炕桌上爬了好半天,任憑兩個孩子哭鬧。等孩子們停住了哭聲,這才爬起身。兩個孩子一看母親的面相,又驚慌地哭起來。云卓瑪下炕照了照鏡子,才發現自己的嘴上血紅一片,仔細一看,竟是下嘴唇被磨破了。傷悲涌上心頭,禁不住流下淚來。但她還是擦干了淚,做好了回娘家的打算,就開始收拾包袱。這時想起男人掙來的錢,一看,一張都沒有了,心里的傷悲又重了幾分。收拾好包袱,看著兩個孩子,準備也帶走。兩個孩子也圓掙著眼睛看母親,渴望得到母親的愛撫。孩子們求助的目光,使云卓瑪冷靜下來。待在這里,就意味著向男人屈服了,所以這娘家還是要回的。兩個孩子,到底領不領呢?
想了好一陣,終于打定主意:“不領孩子了,兩個都放在家里,叫他也嘗一嘗帶孩子的艱難!”
菩薩保出門,其實是到信用社存錢去了。他拿著存折返回時,感覺到心里頭很是踏實。但當他看到大門被反鎖,院子里有孩子在娃娃大哭時,就知道自家的媳婦已經走了,那熄滅了的憤怒又爆發出來,就搬起石頭砸開了鎖。
他估計女人肯定回達娃村里的娘家去了,就先把兩個孩子寄放在前房的大伯家里,叮囑大媽好好照看,而后反身回來,找了一根麻繩,踏上了去達娃村的路。
他準備把不聽話的女人捆回來!
這時已經是黃昏了,路上竟沒有一輛可以搭載的便車。走了七八里,那憤怒也被山風給吹盡了,人也完全冷靜下來,覺得黑天黑地地去捆媳婦,總是不對的,還不如撇上兩三天再想辦法。于是又反身回來,一個人蒙頭睡了。
沒想到這事一撇就是半月。半月里,村里都知道了他女人回娘家的事,好事者就過來出主意。有的要他置辦些賠罪的禮物,去女人娘家請媳婦。有的說不用請,埋伏在娘家村口,等女人出現后,一麻繩捆回來就行了。有的說不急不急,過幾天女人就想孩子了,自個就回來了。還有人說再過半月,到了燃燈節那天,二十里外的尼瑪村里,就要演藏戲,到時女人們肯定會到那里去看戲,那時說不定媳婦早就想通了,領回來就行了。菩薩保覺得這最后一個主意最好,就做好了在看藏戲時尋回女人的打算。
但他還是心存忌慮:“要是她不來怎么辦?也不能在人群里捆她吧!”
那人說:“那你就帶上你阿爸……留給你的那把刀子。”
那人說到菩薩保的父親時,聲音明顯地停頓了一下。
菩薩保沒察覺到這個停頓,他問:“又不殺人,帶刀子干啥?”
那人說:“女人,光哄不成,還要嚇唬。要嚇唬,女人是最怕刀子的!”
果然,在看藏戲的這天,他找見了自己的女人。
他坐在村外的巨石上,眼看自己的女人被丈母娘領著,走遠了,那潛藏在身體里的焦慮,就漸漸長成一只野獸,在吞噬著他的心。太陽漸漸偏西,南山上的林木,被天上的灰色云團的黑影給遮蔽了,越發顯露出厚重的色調,看起來很不舒服。或許只有等待那云層在空中消散殆盡,南山林的美景才能夠盡收眼底。
在等待那團灰色云層消散的時候,他打定主意了:“臭婆娘,你到底跟不跟我過日子?今個,我要問出個所以然來。”
他站起來,摸了摸懷里的那把藏刀,離開巨石,沿著兩個女人的去路,甩開了步子。他甚至忘記了要拍掉屁股上的兩坨灰塵。
舊年事
行走間,那太陽在不知不覺中就挨著了山頭,孤獨地掙扎了一會,還是無法抗拒滑下去的命運,終于發出輕微的嘆息“哎——”,滾落到山的那頭去了。北國藏地的天空里,先前那些灰白色的云層,瞬間就燃燒起來,但還是漸漸地熄滅了火焰,逐漸擴大了陣容。那藍天,不知在什么時候竟被它們給蠶食掉了,整個天空都變得灰蒙蒙的。
“快走吧,天快黑了!”老女人督促她的女兒。
云卓瑪說:“奇怪,一輛車也沒有!”
老女人說:“都在看戲呢,戲散了,才有車的。”
云卓瑪問:“阿媽,你說他會跟來嗎?”
“不知道,”老女人說,“你男人的心思,你應該最清楚。”
“要是這么說,我估計他不會來的,他都不想理我了。”
老女人說:“誰知道呢?他們家的男人,哪個是省油的燈啊!”
云卓瑪說:“阿媽,你怎么這么說呢?”
老女人訝異地看著女兒:“你不知道他家的事?”
云卓瑪說:“你是說他阿爸的事嗎?”
老女人有點惱怒:“你以為我說誰?”
云卓瑪說:“他和他阿爸不一樣。他只是脾氣大,有兩句話不投就動手的毛病!”
“龍養的龍,鳳養的鳳,老鼠養的愛打洞。”老女人說,“他阿爸就是個臟腑客,做事沒輕沒重的,你還指望他做事有規矩?!”
云卓瑪說:“阿媽,人家阿爸都是過世的人了,你就別提了。”
老女人說:“就是哦,死得不明不白的!”
云卓瑪說:“他有時候說要給他阿爸復仇呢,就是不知道是誰干的。”
老女人說:“誰干的?不是他阿媽的兄弟,就是他阿媽的相好。不用猜就知道的。”
云卓瑪說:“那到底是兄弟干的,還是那個相好干的?”
老女人說:“你男人認為是誰干的?”
云卓瑪說:“他懷疑是他的舅舅們。他說只有姊妹關系的,才會下決心給死者復仇的。”
老女人說:“這個很有可能。假如是他舅舅們干的,他怎么復仇?再怎么說,打斷骨頭連著筋呢。”
云卓瑪說:“阿媽,他父母的事,聽過些,不多。你能給我說說嗎?”
“上一輩人的事,不說,最好。”老女人說,“不過,你和他都鬧成今兒這個樣子了,我估計,還是和他的那犟脾氣有關系。他動不動就動手打人的臭毛病,大概也是因為他父母的事,才讓他變成這樣子的。”
云卓瑪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女人說:“二十多年前,他阿爸是莊子里的大好人,學得一手木匠活,在這一帶名聲大著呢。因為活好,總讓人們叫去蓋房,一年四季,就很少待在家里。他的阿媽,本來也是個挺賢惠的人,壞就壞在一件事上了。”
云卓瑪問:“啥事?”
老女人說:“她長得太好看了。女人,還是長得一般的好,太好看,有人就會打主意。老人們常說的紅顏薄命啥的,大概就是這意思吧!”
云卓瑪急了:“阿媽,到底啥事嗎?”
老女人說:“那年夏天,他家的一個遠方親戚來尋他阿爸,說有重要的事。他阿爸正好去給人蓋房,十天半月回不來,那親戚就等了幾天。等的時候,也幫著干點農活啥的。聽說有一天,鄰居去他家借東西,門開著,就進去了。一進門就聽見上房里有娃娃在哭。隔著窗戶一看,只菩薩保在炕上,蹬掉了小被子,露著個小屁股在哭鬧。鄰居很奇怪,走到了另一扇窗下。腳步聲驚動了炕上的人。一看,他阿媽渾身光溜溜的,在尋衣服穿。她的旁邊,躺著她家親戚,也是光溜溜的,正瞪著大眼睛往外瞅。鄰居一看,嚇出一身汗,趕緊回了。事情傳開的當天,那個親戚就跑了。”
云卓瑪:“哦,那他阿爸也知道了?”
老女人:“這世上哪有不透風的墻?聽說他阿爸是最后一個知道的,一知道,就氣得半死。把媳婦狠狠揍了一頓。第二天,提了刀子,跑了三十多里路,去尋那親戚算賬。那親戚早就不在家里,說是剛回家就走了,再也沒回來,家里人也在著急著呢。他阿爸沒說媳婦和親戚的事,嫌丟人,又回來了。從此不再外出干活,整天喝酒,喝醉了就打媳婦。那一陣子,他阿媽也出來干活,拔田,擔水,飲牛,總是鼻青眼腫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看起來受了很重的傷。”
云卓瑪說:“那后來呢?”
老女人說:“后來有一天,他阿媽出來擔水,把桶扔了,也跑了。他阿爸一聽說,提了刀子就去追。追到丈人家,鬧了個雞飛狗跳。”
云卓瑪說:“阿媽,不說這個事了,一說我就脊背發涼。”
老女人說:“那是太冷的原因。你看,天色都麻乎乎的了。”
身邊的世界,的確變得麻乎乎的了。但還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哪是路,哪是山,哪是石,哪是樹。路越走越窄,突然又開闊起來,一座白塔出現在一片蓊蓊郁郁的白楊林前。她們知道:已經到了達娃村的村口了。這時候,母女倆懸著的心,都平穩地落到實處了。
云卓瑪說:“阿媽,我明白了。”
老女人問:“你明白啥了?”
云卓瑪說:“女人沒有走到絕路上,是不會另走一條路的。”
老女人說:“就是,他阿媽真的走到絕路上了。”
云卓瑪問:“他阿媽為啥要找相好呢?”
老女人說:“不清楚,可能是逼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誰知道呢!”
云卓瑪說:“阿媽,你說他會找相好嗎?”
老女人問:“誰?”
云卓瑪說:“就他嘛,菩薩保!”
“他沒那個膽吧?不過,”老女人說,“他阿媽有找相好的毛病,這毛病,不會像先人的血那樣,也在他身上流吧?”
云卓瑪見母親說得猶猶豫豫的,心里沒底了。想起菩薩保剛回來那天對待自己的樣子,就覺得自家男人說是要抽煙喝酒的錢,那錢有可能是拿去找相好用的。
“那他真的找了相好怎么辦?”
“怎么辦?”老女人說,“那你就把他戳死,就像他阿爸對待他阿媽那樣!”
“他阿媽是他阿爸戳死的?”云卓瑪很是吃驚。
老女人卻別開了話題:“走乏了,稍微歇一會,再進村吧!”
云卓瑪應了一聲,找了個干凈的草坎坐下來。老女人卻徑自走向白塔,循著塔下的碎石路,繞著白塔快步轉了三圈,邊走邊誦六字真言,聲音細如蚊子叫。回到起點后,又面對白塔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長頭。爬起身,膝蓋上、大襟上、手肘上,都沾滿了塵土。她也不拍掉,又回到女兒身邊。
云卓瑪忙起身給母親拍掉塵土:“阿媽,你看你,也太信了吧!”
老女人說:“我在為我們贖罪積德呢。”
兩人就背靠背坐在路邊的草坎上。天色比先前更暗了,北風掠過山上林木的樹梢,發出尖銳的噓噓聲。有幾片小小的雪花被風吹過來,貼在人臉上,瞬間就融化了。
“阿媽,要下雪了!”云卓瑪說。
老女人:“是該下一場雪了,到處都是塵土,到處亂糟糟臟兮兮的。”
“他的阿媽真的是他阿爸用刀戳死的?”云卓瑪又問。
老女人想了想,終于說:“就是,他阿爸到丈人家一鬧,丈人就交出了自家的丫頭。回來的路上,他阿媽乘男人不防,打暈男人,轉身又跑了。大概打得輕,男人醒過來,滿山滿洼地追。追上了,戳了自家媳婦一刀,誰想就給戳死了!”
“那他阿爸就沒進班房子?”
“沒進。聽說兩家人都請了人,有寺院里管事的,有村里專門調節關系的,準備賠錢私了。沒談攏,就散了。過了兩天,他阿爸就叫人給勒死了。”
“勒死了?”云卓瑪把“勒”字咬得特別重。
老女人:“勒死了!”
云卓瑪:“阿媽,不是說佛祖會保佑世上所有人的嗎?”
“哎——”老女人長嘆一聲說,“佛祖只會保佑信佛的人。”
云卓瑪:“他阿爸不信佛?”
老女人:“信的話,就不拿刀子去殺人了!”
云卓瑪皺著眉想了會說:“我現在覺得他很可憐,我也可憐,我們都可憐!”
“他才不可憐呢,可憐的是我們娘倆。”老女人說,“不,這么說還不對,可憐的是我們做女人的!”
忽聽有人在遠處高聲說話,似乎在極力否認著什么。
塵埃里
菩薩保遠離了尼瑪村,也走在通往達娃村的路上了。
這是一條沙石路,不太寬,僅能走一輛小車。路面上積滿灰塵,但兩條常走汽車的車轍印,還是很清晰的。他就走在兩條車轍之間,腳底下的碎石墊著腳心,有種難以言說的不適感。或許因為天快黑的原因,他走得有點快。
前方,晃動著的兩個女人的身影,離他已經不遠了。只要她們還在他的視野里,他就不會急于趕上去。再說,匆匆忙忙趕上去,又能怎樣呢?許多事一兩句話能說得清楚嗎?
他凝視著那兩個身影,其中瘦削又充滿活力的那一尊,讓他覺得又甜蜜又心酸。
忽然想起他去她家相親的那天,天氣格外晴朗,云也是又白又軟的那種,懶懶地浮在空中。當他跟著媒人進入她家院落,溫暖的房檐下,她穿著件粉紅色的衣服,藏藍色褲子,正撅著屁股洗衣服。看到有人來,就羞澀地躲了,她的父母趕忙出來迎接。媒人上了炕,他跨在炕沿邊,紅著臉聽媒人說明來意。他感覺到了她的父母審視的目光,頭垂得更低了。這時,她父親喊她來添茶水,她就來了,紅著臉,和他一個樣。她瞟了他一眼,那眼里有光,也有水。他頓時就喜歡上了那光那水。告辭時,她依在上房門口,背對著他們。但他還是感覺到她后腦勺上長出了眼睛,在目送他呢!
果然,過了幾天,她家回話了:小伙子人挺老實的,這事成呢。結婚后,他才知道,其實她的父母是不同意的,只因她的抗爭,他們在無奈之下,才隨了女兒的意。
“你為啥看上我了呢?”有一天,他問她。這時候,她已經懷了他的孩子。
“就是覺得你害羞的樣子挺好看的!”
“你也害羞了,我看得出來。”
“那樣的場合,哪個女孩子不害羞呢?”她又害羞了。
“你害羞的樣子,也挺好看的。”他把她擁進了懷里。
不知什么時候,也許是大兒子歲半的時候吧,為照看孩子的事,做飯的事,掙錢的事,他倆開始吵架了。剛開始僅僅是吵幾句,在他還在氣頭上時,她又和顏悅色地來逗他,于是又和好如初了。后來,大兒子三歲的時候,出去玩,打傷了別人家的孩子的嘴。她抱怨他太縱容自家孩子,喋喋不休地嘮叨了半天。他惱怒了,扇了她一巴掌。她被打蒙了,清醒過來時,撲向他,要撕他的臉。他躲開了。她嚶嚶嗚嗚地哭!
“我都懷著你的第二個孩子,你還打我!”她邊哭邊罵,“沒知道你是這么狠毒的人!”
他回答說:“不是我狠毒,是你們女的太啰嗦,整天婆婆媽媽的!”
她說:“我好后悔!”
他問:“后悔啥?”
她說:“后悔沒聽阿媽的話,嫁給了你這個土匪!”
她不說還好,一說,他就開始恨她的母親了:“還信佛呢,盡拆別人的姻緣!”
她說:“我倆這樣的姻緣,要叫拆了才好!”
他不再和她爭論,一甩門,走了。
過了幾天,她的父親因病過世了。她挺著肚子去奔喪,他也不陪著她去,仿佛丈人的去世與他沒任何關系似的。
她回來了,從此不再跟他說話,像個啞巴。
第二個孩子出生后,因為是個女孩,圓了他們要一男一女龍鳳呈祥的愿望,他們的關系,又暫時和好如初了。在女孩滿月那天,他們牽兒抱女,去了外婆家,住了幾天。其間,他又無意中聽到了岳母在告誡女兒:“你的男人,心硬得很,你可要小心哪!”
她回答說:“就那樣子。男人們,可能都這樣吧!”
他覺得自家的媳婦還算可以,但對丈母娘,恨得更厲害了:“哪有這樣當娘的?!”
這恨,有時候也會遷怒在媳婦身上,所以當她為家事和他爭吵時,他也不愿動嘴,更愿意動手,對自家女人或扇或踢,直到她完全聽話了,安靜了,也不噙著眼淚發呆了,這才覺得心里很是踏實。
“講道理,還是要靠拳腳的。”有時候,他喜歡這樣給別人總結,別人一聽都大聲說:“好!”
后來,看到別人出去打工,年底都滿載而歸的,他也動心了,也有了出去的打算。他征求她的意見,她不說話。
他生氣了:“聽不懂人話嗎?懂了就放個屁。你又不是聾子!”
她被逼急了:“想去就去!”
他說:“把你尊重著,你就這態度!”
她還是說:“想去就去!”
他說:“那家里的事,你就操個心。地少種些,把我的兩個娃娃看好就成了!”
于是就出來打工,在一個建筑工地當泥水匠。因為工資給得好,就死心塌地待了下來。這期間,倒挺思念自家女人和孩子的,一有空就打電話,在話筒里顛三倒四地說些情話。女人在不間斷的情話的攻擊下,不再冷漠,也開始回應他了。后來,兩人都喜歡在電話里卿卿我我了。
在工地,他和別人不太一樣。別人打工,愿意把工錢都存進銀行。他不,他只存一部分,留下一部分,用來抽煙,喝酒,存話費,偶爾進進飯館,喝喝飲料什么的。他認為人活著,應該這樣,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該玩就玩。能轉世為人,就是上輩子的修行換來的結果,可不能把今世給白白浪費了。
就這樣,辛辛苦苦打了大半年工,掙的錢倒是不多。一回到家,夫妻剛剛恩愛罷,她就問工錢的事,又抱怨又嘲笑的。
這下他惱了,又動手打了她,那段熬電話粥的甜蜜時光瞬間就成記憶了!
想到這里,忽然想起諾桑王子率兵遠征后,云卓拉姆被王子的嬪妃和巫師圍困在城堡里,不得不想法設法擺脫困境時的憤怒和無奈來:
親愛的夫君哪你那么多的嬪妃齊聚樓下,
親愛的情郎哪你那么多的巫師包圍城堡:
他們說奉國王的命令要來抓走你的愛人,
他們說奉國王的命令要來挖走我的心肝。
山頭上經撒下羅網小小鷹兒能逃到哪去?
王宮外已布下人馬云卓拉姆能溜到哪去?
幸好有你留給母后美麗神奇的珍珠項鏈,
幸好還有你臨別時預測困境的萬般叮嚀。
我憑借珠鏈的力量騰空而起在屋頂盤旋,
我依靠你過人的智慧脫離困境飛向生路。
既然山頭上撒下羅網那我就飛往高峰去,
既然王宮外布下人馬那我就飛到天界去。
“人家云卓拉姆是被壞人逼著才離開的,”他想著想著就生氣了,“你倒好,撇了孩子就跑了!”
心里抱怨著女人,腳步不由得走得快更快,頃刻之間,他就趕上了她們,他甚至能聽到她們的說話聲了。他仔細聆聽著,模模糊糊聽得她們在說他的父輩的事,心頭一緊,就越發聽得認真。當聽到岳母評價說“他才不可憐呢,可憐的是我們娘倆”時,禁不住大聲嚷道:“你們兩個說的,都不對!”
大雪中
零星的雪花在風中飛舞。灰蒙蒙的道路上,一個黑瘦的鬈發男人直直地走了過來。
“阿媽,是他!”云卓瑪驚叫起來。
老女人:“我知道是他,一直都知道。除了他,不會再有別人。”
走來的男人,確實是菩薩保。
“阿媽,要跑嗎?”云卓瑪緊張極了。
“跑啥呢,遲早得面對。”老女人說。
菩薩保走到離兩個女人三四步遠的地方,微微偏著頭,轉動著眼珠,一會兒審視岳母,一會兒觀察妻子。
云卓瑪被盯得發毛,站起身銳聲問:“你想干啥?”
菩薩保說:“干啥?你以為你把兩個孩子撇到家里,就大吉大利了?”
老女人坐在草坎上,仰著臉說問:“那你到底想干啥?”
菩薩保說:“阿媽,我來請你的丫頭回去啊!”
老女人問:“哪有這樣子的請法?”
菩薩保笑了:“哦,阿媽的意思,是得抬個八抬大轎來?”
老女人也笑了:“八抬大轎?量你也請不來。”
菩薩保說:“在阿媽的心里,我啥都做不成的,這我一清二楚。”
云卓瑪急了:“你就甭跟阿媽爭了,都過去一月了,你還沒想清透?”
菩薩保說:“有啥可想的,我又沒有錯。”
云卓瑪說:“那些錢你不給家里留一分,你還說你沒有錯?”
菩薩保說:“我都存到信用社了,在存折上呢,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云卓瑪說:“你就騙人吧,說不定你早就和你的狐朋狗友們花得干干凈凈的了!”
菩薩保說:“我掙的錢,我花點不成嗎?就說我花完了,你還能把我怎么樣?”
老女人聽得著急,也插了一嘴:“你這就是個敗家子的做法!”
菩薩保說:“哎,阿媽,你這話就錯啦,就說我是敗家子,敗的也是我自個的家,與你沒啥相干吧?”
老女人說:“我可不愿意我女兒跟著你受罪!”
菩薩保說:“她受罪?我在外頭拼死拼活的,掙的就是血汗錢。她在家里只是喂個豬種個藥材啥的,還受罪?我看她才在享福呢!”
云卓瑪氣得罵起來:“你不要胡說,我又拉娃娃又養豬,又種當歸又犁地,都累得半死不活的,你還說這樣的話,你的良心是不是叫狗給吃了?”
菩薩保的臉色顯得更黑了,他逼近云卓瑪。云卓瑪往后一退。菩薩保伸出左手,一把攥住了云卓瑪的胳膊。云卓瑪使勁一甩,沒摔脫,疼得罵起來:“放開,你這個有人養沒人教的!”
菩薩保一聽這話,揚手就給云卓瑪一巴掌:“我就有人養沒人教,怎么啦?!”
老女人一看女兒被打,起身來拽菩薩保的胳膊。菩薩保一甩手,老女人就跌倒在地,手上、屁股上沾滿了泥。手中的紫色佛珠也隨著她倒地的慣勢勁摔出去,恰好撞在一塊石頭上,瞬間就碎了好幾顆,余下的墜落下來,軟沓沓地堆在地上。
老女人驚呼一聲:“哦,佛祖啊!”
云卓瑪見母親被甩到在地,也急了,抬手就撕菩薩保的臉。菩薩保沒防備,左頰上頓時被抓走幾道皮,血也從抓痕處滲出來,紅兮兮的一片。
菩薩保惱羞成怒,左手揪住云卓瑪的頭發,右手啪啪啪地朝女人的臉上摑。女人急得用腳亂踢,男人一甩手,女人就跌出路基,翻倒在旁邊的空地里,也裹了一身的泥。
老女人爬起來,撲過來咬住菩薩保的腿子。男人疼得大叫起來,就朝老女人的頭上擂了幾拳,女人癱軟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菩薩保放倒了老女人,轉身想看云卓瑪的狀況,還沒看得明白,只聽得耳邊風聲響,腦袋就被什么堅硬的東西給擊中了,頓時頭暈眼花,差點倒在地上。仔細一看,認得是塊狗頭石,明白自己被暗算了。
原來云卓瑪見母親被打,憤怒中從地上摸到了石頭,想也沒想就砸在了菩薩保頭上。見男人被砸竟然不倒,就驚呆了,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
菩薩保趔趔趄趄地走過去,再次用手揪住云卓瑪的頭發:“哦,膽子大了,敢打,敢打,敢打男人了!”話沒說完,頭上就流出鮮血,順著臉頰,淌進了領口。
云卓瑪見男人頭上血流如注,傻了,瓷著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父母的事。你們說的,不對。”菩薩保邊說邊用一只手捂住流血的地方,“我阿爸,是男子漢。女人不聽話,就該打。女人找相好,也該打。女人想管男人,也該打,不打不成。”
身后傳來老女人的聲音:“對,就你阿爸那樣的男子漢,戳死了你阿媽,你阿爸真厲害哪!”菩薩保扭過頭,看到老女人坐在泥里,披頭散發的。
菩薩保說:“是不是男子漢,你們女人說了不算,我做兒子的說了,算!”
老女人捶打著胸脯哭喊:“我真的瞎了眼,把丫頭嫁給了你這個畜生!”
菩薩保說:“我是畜生?我比你們明白事理。”
老女人說:“你明白個屁!”
“我就明白個屁。”菩薩保笑了,“我明白人活一世,得活出個人樣。上輩子,我們積了德,轉世成人了。這輩子,就得享受。你們,活得像倉鼠,盡往窩里拉東西。你們想吃幾輩子嗎?下輩子,轉世成啥都不知道呢。你們光知道攀比,眼紅,罵男人沒出息,掙不來錢,活不過人。你們就有出息嗎?活過別人了嗎?”
老女人不哭喊了,坐在那里聽。
菩薩保說:“用嘴給你們講道理,你們不聽。用拳頭講道理,你們才聽。啥世道嘛!”
老女人說:“你再別揪著云卓瑪的頭發了,你看她都傻了!”
菩薩保說:“我偏要揪她頭發,她傻了才好。不傻,我就弄死她。”
嘴里說著,手卻放松了。轉過身,面對著老女人。只聽“當”的一聲響,一個物件從他里掉在路上。
老女人一看,竟然是把刀子,失聲驚叫:“你拿把刀子,要干啥?”
菩薩保彎腰拾刀,那刀卻被身后的云卓瑪搶走了。他剛轉回身,就發現云卓瑪已經拔出了刀子。他裂開嘴笑:“哦,還真的反天了,敢殺自家的男人了。來,我給你當靶子,你戳吧!”
誰知云卓瑪真的動了手。第一刀就插在菩薩保的心口上。刀子被拔出,又插進了胸膛。刀子又拔出,插進了脖子。
菩薩保仰面倒在地上,看著云卓瑪說:“哎,臭婆娘,你還真戳啊?!”
只說了一句,就再也說不出話來。
老女人見菩薩保已經被女兒戳倒在地,大叫:“別戳了,別戳了,再戳就出人命了!”
哪知女兒就是不停手,還攥著刀在男人身上亂插,這才發現女兒已形同鬼魅早已瘋癲,一時就被女兒的模樣給徹底嚇傻了。
不知何時,雪花變大變多了,在風中勁飛。山上、樹上、路上,都鋪滿了雪,整個世界都處在灰白色的寒冷中。疾風將雪花也吹打在白塔上,只一會工夫,各層塔體上,就堆積了厚厚的一層。或許再過一會,那白塔就會被雪掩蓋,只能看清大概的模樣了。
漫天雪花中,尼瑪村的露天舞臺上,那諾桑王子經歷了千辛萬苦后,終于到達了乾達婆的天宮。在云卓拉姆的父親馬頭明王那里,找到了躲在帷幕后暗暗流淚的云卓拉姆。他一把掀開帷幕,將云卓拉姆擁進懷里:
我在一口距你不遠的水井邊長久地停留,
渴望你那如影隨形的侍女能在這里出現。
當我在注滿愛情的水桶里悄悄放入戒指,
你定會知道我諾桑王子悄然到來的消息。
我的美麗善良又溫柔體貼的云卓拉姆啦,
歷經磨難后我倆終于隔著一層帷幕相見。
我要揭開這來自異域的厚重的絲綢屏障,
跪在你面前求得你的原諒得到你的芳心。
責任編輯 侯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