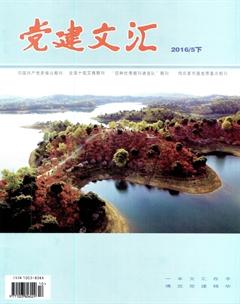有生命的知識
學問的生長是有機體的生長,必須有一個種子或幼芽做出發點,這種子或幼芽好比一塊磁石,與他同氣類的東西自然會附麗上去。聯想是記憶的基本原則,所以知識也須攀親結友。一種新來的知識好比一位新客走進一個社會,里面熟人愈多,關系愈復雜,牽涉愈廣,他的地位也就愈穩固。如果他進去之后,不能同任何人發生關系,他就變成眾所同棄的人,決不能久安其位,或是盡量發揮他的能力,有所作為。我們日常所見所聞的事物不知其數,但是大半如云煙過眼,因為不能與心中已有知識系統發生關系,就不能被吸收融化,成為有生命的東西存在心里。許多人不明白這道理,做學問只求強記片段的事實,不能加以系統化或有機化,這種人,在學問上永不會成功。我嘗看見學英文的人埋頭讀字典,把字典里的單字從頭記到尾,每一個字他都記得,可是沒有一個字他會用。這是一種最笨重的方法。他不知道字典里零星的單字是從活的語文(話語和文章)中宰割下來的,失去了它們在活的語文中與其他字義的關系,也就失去了生命,在腦里也就不容易“活”。所以學外國文,與其記單字,不如記整句,記整句又不如記整段整篇,整句整段整篇是有生命的組織。學外國文如此,學其他一切學問也是如此。我們必須使所得的知識具有組織,有關系條理,有系統,有生命。
一個人的知識有了組織和生命,就必有個性。舉一淺例來說,十個人同看一棵樹,叫他們各寫一文或作一畫,十個人就會產生十樣不同的作品。這就顯得同一棵樹在十人心中產生十樣不同的印象。每個人所得印象各成為一種系統,一種有機體,各有它的個性。原因是各人的性情資稟學問不同,觀念不同,吸收那棵樹的形色情調來組織他的印象也就自然不同,正猶如兩人同吃一樣菜所生的效果不能完全相同是一樣道理。知識必具有個性,才配說是“自己的”。假如你把一部書從頭到尾如石塊一樣塞進腦里去,沒有把它變成你自己的,你至多也只能和那部書的刻板文字或留聲機片上的浪紋差不多,它不能影響你的生命,因為它在你腦里沒有成為一種生命。凡是學問都不能完全是因襲的,它必須經過組織,就必須經過創造,這就是說,它必須有幾分藝術性。
做學問第一件要事是把知識系統化,有機化,個性化。這種工作的程序大要有兩種。且拿繪畫來打比,治一種學問就比畫一幅畫。畫一幅畫,我們可以先粗枝大葉地畫一個輪廓,然后把口鼻眉目等節目一件一件地畫起,畫完了,輪廓自然現出。比如學歷史,我們先學通史,把歷史大勢作一鳥瞰,然后再學斷代史,政治史,經濟史等等專史。這是由輪廓而節目。反之,我們也可以先學斷代史,政治史,經濟史等等,等到這些專史都明白了,我們對于歷史全體也自然可以得到一個更精確的印象。這是由節目而輪廓。一般人都以為由通而專是正當的程序,其實不能通未必能專,固是事實;不能專要想真能通,也是夢想。許多歷史學者專從政治變遷著眼,對于文學哲學宗教藝術種種文化要素都很茫然,他們對于歷史所得的輪廓決不能完密正確。
事實上,在我們的學習中,這兩種貌似相反的程序——由輪廓而節目,由節目而輪廓——常輪流并用。先畫了輪廓,節目就不致泛濫無歸宿,輪廓是綱,綱可以領目,猶如架屋豎柱,才可以上梁蓋瓦。但是無節目的輪廓都不免粗疏空洞,填節目時往往會發現某一點不平衡,某一點不正確,須把它變動才能穩妥。節目填成的輪廓才是具體的明晰而正確的輪廓。做學問有如做文章,動筆時不能沒有綱要,但是思想隨機觸動,新意思常涌現,原定的意思或露破綻,先后輕重的次第或須重新調整,到文章寫成時全文所顯出的綱要和原來擬定的往往有出入。文章不是機械而是自由生發的,學問也是如此。節目常在變遷,輪廓也就隨之變遷,這并行的變遷就是學問的生長。到了最后,“表里精粗無不到,然后一旦豁然貫通”,學問才達到了成熟的境界。 (摘自《朱光潛談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