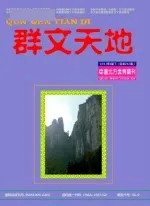大師與優伶
陳益
今年是偉大的戲劇家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兩位從未晤面的大師,幾乎同時鑄造了戲劇豐碑《羅密歐與朱麗葉》和《牡丹亭》,且都用浪漫主義手法表現了永恒的主題——愛情高于生命。難怪,上世紀30年代,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將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并論:“東西曲壇偉人,同出其時,亦奇也”。
耐人尋味的是,他們與優伶都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別以為大師與優伶本該如此。要知道,在那個以權勢和金錢論貴賤的時代,優伶——演員的地位只相當于奴婢。當昆山腔興盛時,官僚士大夫和巨商蓄養家班成風,家班成員不過是供主人玩樂的工具,從來也不被看重。湯顯祖卻把他們視為戲劇藝術的實踐者。從湯氏詩文集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同道的名字,如屠隆、梅禹金、謝久紫、呂玉繩、姜耀先等,也有不少優伶,如羅章二、于采、王有信等。常常是這樣,在欣賞了優伶上乘的演出后,湯顯祖很高興,立即賦詩為贈:“韻若笙簫氣若絲,牡丹魂夢去來時。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銷魂不遣知。”(《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不肯蠻歌逐隊行,獨身移向恨離情。來時動唱盈盈情,年少那堪數死生。”(《聽于采唱牡丹》)在湯氏眼里,優伶們不啻是知音、知己。
他甚而直接給優伶寫信。如著名的《與宜伶羅章二書》,不僅鮮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戲劇理論,信中還流露了他對藝人生活和經濟收入的關切,叮囑他們演出《壯丹亭》務必用原本,索取報酬和酒食招待不要過分等等。他還熱忱為優伶們教曲:“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七夕醉答君東二首》),輔導演出,或者差遣他們去外地為他的友人演出(《遣宜伶汝寧為前宛平令李襲美郎中壽》《九日遣宜伶赴甘參知永新》)。興起時,自己也可以袍笏登場(《作紫襴戲衣二首》)。能主動地與演員交朋友,把與優伶的通信編入詩文集,這在士大夫中是很罕見的事,何況他又有那么高的才情。
湯顯祖出身于江西臨川的書香門第,他的名字本身就含有光宗耀祖的意思。科舉入仕是湯顯祖的主業,治國平天下是他的抱負,寫作只是在政治抱負難以實現時所做出的一個選擇。后來,由于種種(包括性格)原因,他無奈辭去官職,專心致志地投入到了寫作中。事實上,與優伶關系密切,除了藝術交流的因素,更由于他接受“左派王學”的思想。錢謙益《湯遂昌顯祖小傳》中提到,湯顯祖少年時代的老師羅汝芳,是“左派王學”創立者王艮的再傳弟子;釋真可(達觀大師)比湯氏年長七歲,相互友善。他們對湯顯祖的一生影響很大,甚至在“臨川四夢”中都能尋覓痕跡。“左派王學”蔑視傳統禮教,倡導“百姓日用即道”,顯然是無法為統治者接受的異端邪說,卻讓湯顯祖的內心引起很大共鳴。他在遂昌知縣任上“縱囚放牒,不廢簫歌”,在玉茗堂“文史狼籍,賓朋雜坐,雞塒豕圈,接跡庭戶,蕭間詠歌,俯仰自得”,與優伶們親密相處,詩文酬往,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志也者,情也。”湯顯祖評點《西廂記》說的這句話,是他戲劇創作的主旨,同樣也是他為人處世的準則。這恰恰是最富有生命力,最具文化意義的。
再來看莎士比亞。他是一個小工匠的兒子,只受過初級教育,很小就離開家鄉斯特拉特福德鎮,跑到首都倫敦去找出路。為了生存下去,他幾乎什么苦活都干過,后來進了一家劇院打雜,登臺跑龍套。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他的編劇天賦被人們發現,于是獲得了寫作權。他的寫作無非出自經濟利益的驅使。由編寫腳本,成為戲班子的股東,繼而有條件出入于宮廷、王府。賺到了錢,他就能讓家庭擺脫困境,自己也能回家鄉告老退隱。這個大劇作家,不僅跟演員親近,本身就當過演員,而且是低微的“龍套”。然而,豐富的生活閱歷加上天賦,讓他的三十七件戲劇作品(包括與別人的合作)既陽春白雪,又下里巴人,顯示獨有的藝術功力與社會價值。
如果說,湯顯祖不能擺脫傳統士大夫“立言”的模式,在作品中注入了許多的理想和抱負,莎士比亞則為了生存而寫作,藉以糊口,才干上編劇的行當,觀眾滿意就是對他最好的報答。在文藝復興的大背景下,他的創作恰好與那個時代相合拍。其實,這個曾經的劇院雜役,并不懂得400年后的所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更無從理解今天的批評家解剖死人活人的標新立異的理論。我們該如何詮釋他的寫作?憑藉內心充溢的激情,繼承中世紀民間戲劇傳統,牢牢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沒錯,但似乎不盡然。
在悲劇《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場中,哈姆雷特說過這樣一番話:“演戲的目的,從前也好,現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給自然照一面鏡子,給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給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態,給時代和社會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記。”這正是莎士比亞的心聲。他不過是借著哈姆雷特的嘴說出來而已。同時,他又諄諄告誡伶人甲:“要是表演得過火了,或者是拖泥帶水了,盡管會博得外行人開懷,只能使明眼人痛心,你們把這種行家一個人的意見必須估計到重于一院子其他聽眾的信口雌黃……”這跟湯顯祖在夜色闌珊中一遍遍拍打檀板,教優伶們拍曲,如出一轍。
關于優伶,莎氏在《第十二夜》中,也有這樣一段說白:“這個人去做個傻子是夠聰明的了。干這個營生,真是很需要一點聰敏,他必得觀察他們所取笑的人的心情,那人的人品,與時間的當否。并且還要似未受過訓練的蒼鷹,對于面前的每一個飛禽都要追逐,這是一種工作與智慧的精心藝術,像能工巧匠一樣充滿了辛苦。因為他用聰明表現的愚蠢才是恰當的,但是聰明人若躍在愚蠢里,就要把聰明污損了。”
終究是大師,優伶們戴著各種各樣的面具,以愚蠢為聰明的人生,他揭示得形象而又深刻。
人究竟是什么?人為什么而活著?人應當怎樣活著?什么是真正的愛情?這是偉大的劇作家時刻在思考的問題。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用手中傳神之筆,通過不同的途徑探究,以不同的方式體現了自己的理解,也讓優伶們替代自己,在舞臺上回答了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