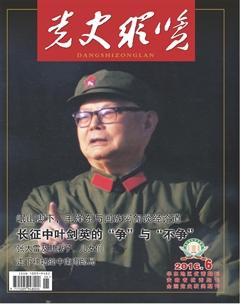作家陳學昭和女兒陳亞男的感人往事
徐忠友
翻開厚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有一位著名作家及其作品早已載入其中。她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女作家,1924年元旦在上海《時報》上發(fā)表《我所希望的新婦女》一文,并以此獲乙等獎而步入文壇,此后還結識了魯迅、茅盾等文學大家。她是中國第一位留洋文學女博士,卻謝絕了法國巴黎大學東方語言學院院長格拉耐的執(zhí)教邀請,回國后曾三赴革命圣地延安,最初以《國訊》特派記者的身份采訪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陳云、李富春等老一輩中央領導人,還有丁玲、周揚、沙可夫等名家,一年半時間里寫下了15篇文章,后集成了22萬字《延安訪問記》一書。1942年5月,她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此后創(chuàng)作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上卷,這一名著可以說影響了幾代人。毛澤東曾稱贊她“又是文學家,又是教育家”。她就是原中國作協(xié)顧問、浙江省文聯(lián)副主席和名譽主席、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陳學昭。
陳學昭的女兒陳亞男,也是浙江省作協(xié)會員,幾十年來與母親相依為命,年少時對母親多有誤解。母親逝世后,她為其整理出版多部著作。長期以來,她漸漸從母親的身上學到了“認真學習、勤奮創(chuàng)作、低調做人”等許多優(yōu)秀品質,也深切感受到了母親“工作著是美麗的”的豐富內涵,最終視母親為她一生的學習榜樣。2016年1月9日,筆者來到了杭州大運河畔的一個居民小區(qū)里,采訪了陳亞男女士,從中了解到母親陳學昭和她之間的一些感人往事。
漂泊歲月
陳學昭原名陳淑英、陳淑章,于1906年4月17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寧縣(現(xiàn)為市)鹽官鎮(zhèn)陳家埭一個書香門第。她在家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稱她為“九弟”,“學昭”是她讀了《昭明文選》后取的筆名。她父親陳典常,曾擔任過海寧州小學堂學監(jiān)和民國后海寧縣立第一小學校長,具有民主思想,只可惜在她6歲時父親就病故了,陳家生活開始走下坡路。
在母親李氏和兄長的養(yǎng)育下,陳學昭1920年夏天在本地女高小學畢業(yè)。不幸的是,母親不慎摔倒癱瘓在床,家中更困難了。為了節(jié)省學費,陳學昭便考進江蘇南通縣立女子師范學校學習,這時她的文學天賦已經(jīng)初現(xiàn),作文寫得不錯。1922年初,她又進入私立上海愛國女學文科班學習,與張琴秋(后為紅軍女將領)、陳竹影和季湘月等為同學。1923年夏畢業(yè)時,中國正處在五四運動后大革命風暴興起之際,17歲的陳學昭勇敢地走向社會,加入了“淺草文學社”,走上文學之路。在這年底,她在給《時報》的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婦女》中寫道:“我敢大膽地說一句,一個獨身的女子,對于社會上,一定會比家庭的賢妻良母發(fā)展得多……”這句話無疑宣告她選擇走上社會的人生道路。
1924年春,經(jīng)表姐介紹,陳學昭前往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師范學校當國文老師。學校地處黃山附近一個叫隆阜的山村,3個月后傳說有一伙土匪要來襲擊,許多學生都不來上學了,她和幾位老師便向校長辭職。之后,陳學昭到上海尋找工作。最初,她借住在《婦女雜志》主編章錫琛家中,在這里結識了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周建人先生。后來,她又住在愛國女校的同學張琴秋家中,寫出了記錄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師范之行的散文《倦旅》,還有《如夢》《寸草心》等,并在《向導》上發(fā)過一篇稿子。通過張琴秋的愛人、中共秘密黨員沈澤民,陳學昭還結識了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及夫人楊之華。
1925年初,經(jīng)章錫琛、周建人介紹,陳學昭又赴紹興縣立女子師范學校教書,由于學校內斗嚴重,不到半年時間她就辭職了。在這里,她結識了有民國“報紙副刊大王”之稱的孫伏園之弟孫福熙,孫福熙對才貌俱佳的陳學昭一見鐘情。孫福熙是一位五四運動的參與者,1920年由紹興老鄉(xiāng)蔡元培介紹赴法國工讀,進入法國國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5年回國后,在老鄉(xiāng)魯迅的幫助下出版了散文《山野掇拾》、小說《春城》等。雙方家人都極力想促成這樁婚事。不久他倆便結伴西湖,寫文作畫,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戀愛時光。
1925年8月,陳學昭與孫氏兄弟同赴北京。經(jīng)人介紹,她到北京適存、黎明中學當語文教師。這期間,經(jīng)孫氏兄弟引見,她拜會了魯迅先生,并為魯迅創(chuàng)編的《語絲》雜志寫過稿,特別是在孫伏園主筆的《京報》副刊上發(fā)表了《佳節(jié)》《談國慶》等7篇散文。但由于張作霖等北洋軍閥對京津一帶的進步報刊控制很嚴,加上孫氏兄弟與所在的北新書局另一股東李小峰之間發(fā)生了矛盾,對她的寫作也有影響。1926年5月,陳學昭再次辭職回到海寧。不久,孫伏園到上海創(chuàng)辦了《北新周刊》,受聘擔任主編的孫福熙便叫陳學昭去上海幫忙。到上海后,陳學昭的同學季湘月之兄季志仁來看望她,并對她說:“我6月將赴法國留學。”這對陳學昭產(chǎn)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此后,孫伏園去了武漢,擔任《民國日報》副刊主編,著名作家沈雁冰等一批進步人士也到了這里。受其影響,陳學昭也前往武漢,并見到了沈雁冰、惲代英、何香凝等進步人士。何香凝曾勸陳學昭留在武漢做婦女工作,但她還是想去歐洲留學,加上孫福熙不停催她回去,她最終回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四一二政變,逮捕并殺害大批共產(chǎn)黨員,身為進步作家的陳學昭感到生存環(huán)境危險。當她聽浙江作家鄭振鐸說要去法國后,便于5月21日下午和鄭振鐸、袁中道等人一起,搭乘法國郵輪阿朵斯2號赴法留學。到巴黎后,經(jīng)戈公振先生推薦,陳學昭兼任了天津《大公報》駐歐特派記者。不料,此時她接到二哥陳軼凡的來信,叫她回國與孫福熙結婚,并叫《大公報》不給她寄稿費,斷了她生活的來源,逼她回國。陳學昭被迫于1928年10月回到海寧,在與孫福熙見面時,她發(fā)現(xiàn)兩人的感情已經(jīng)生隙。
1929年2月,在哈爾濱領到《大公報》稿費的陳學昭乘火車經(jīng)東北和蘇聯(lián)西伯利亞返回法國。1931年7月與在里昂大學學醫(yī)的何穆結婚,并于1932年4月生下了兒子何棣棣。
1934年11月,陳學昭通過了博士論文《中國的詞》的答辯,獲得了巴黎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文學博士學位。之后,何穆的博士論文也通過了。由于此時法國物價飛漲、法幣大幅貶值,陳學昭又想看望癱瘓在床的母親,并把兒子送回國,于是她與丈夫商量決定回國。
1935年2月,陳學昭一家回到海寧時,母親已經(jīng)不幸去世。何穆回上海金山老家行醫(yī),情況也不理想。后來,何穆到江蘇無錫開了診所,陳學昭與兒子隨行。1936年11月,經(jīng)老同學介紹,何穆又帶著一家到江西南昌一家醫(yī)院工作。“西安事變”爆發(fā)后,陳學昭認為中共處理西安事變的態(tài)度深得民心,便開始關注延安的情況,并從書報上搜集延安的相關資料。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陳學昭一家人逃難到重慶,她在涪陵鄉(xiāng)下收治抗戰(zhàn)傷兵的121后方醫(yī)院工作。正當她對前途感到茫然之時,有一天,她看到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一書,延安的情況讓她深受鼓舞,便回到重慶準備全家去延安。經(jīng)與中共重慶辦事處聯(lián)系,她的這一請求獲得了中共中央同意。正在黃炎培先生主辦的《國訊》周刊擔任總編的孫起孟聽說陳學昭要去延安后,便熱情地聘請她擔任《國訊》雜志特約記者,采寫一些有關延安的報道。于是,陳學昭一家人在1938年6月30日從重慶出發(fā),于8月6日到達延安。
陳學昭到訪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歡迎和優(yōu)待。她被安排住在城里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央交際處招待所,食堂還特地給她燒大米飯,另加一份蔥炒蛋。陳學昭、何穆兩人的積極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長貢獻出來。陳學昭開始動筆撰寫《延安訪問記》。被安排在邊區(qū)醫(yī)院工作的何穆還拿出自己的一部手提X光機供醫(yī)院使用。然而,日子一久,各種問題便接踵而來,在參加籌備中央醫(yī)院時,何穆與領導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多。由于思想尚未適應戰(zhàn)爭條件下的因陋就簡的邊區(qū)醫(yī)院制度,總以為延安辦事方式游擊習氣太濃重,而正規(guī)化籌辦中央醫(yī)院建議因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納,何穆萌生了重回國統(tǒng)區(qū)行醫(yī)的念頭。加上當時陳學昭對延安的生活也不是很適應,故1939年夏全家人一起回到重慶。
再次回到重慶后,他們才發(fā)現(xiàn)由于戰(zhàn)亂,靠行醫(yī)過日子并不容易。而由于此前《國訊》雜志連載過陳學昭采寫的《延安通訊》,陳學昭一回到重慶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盯上,連重慶三聯(lián)書店將她的這些文章結集為《延安訪問記》準備出版,也遭到國民黨特務查抄。讓她更心痛不已的是,7歲的兒子何棣棣因腦膜炎不幸夭折。此時,陳學昭開始想念在延安的日子。
1940年底,在周恩來的幫助下,陳學昭與何穆再次赴延安。這時的陳學昭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去延安的,她把隨身帶的博士學位證書、照片、版稅折子等等所有可以證明身份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撕成碎片,塞在床頭邊地下的老鼠洞里。第二次到延安后,拿起筆當武器為革命而寫作成了她的必然選擇。而讓她想不到的是,這次去延安,何穆與她分了手。
1942年5月23日,陳學昭作為作家代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聆聽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對她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很大。她深刻地反省自己,并將個人情感上的痛苦,歸并于應當在整風運動中被改造消滅掉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范疇。同年12月,陳學昭被安排到《解放日報》社擔任副刊編輯,同時從中央醫(yī)院宿舍搬到報社所在的清涼山上居住。此后,在天寒地凍的陜北農(nóng)村窯洞里,在延安撤退時行軍的間隙中,在用被褥疊成的“桌椅”上,陳學昭寫成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上卷,這部小說可以說是對自己過去那段漂泊生活的回顧與深刻反思。
女兒降生
1941年11月27日,陳學昭在延河邊的一個窯洞里生下女兒陳亞男,孩子出生9個月后,陳學昭與何穆便離了婚。女兒一直跟陳學昭生活在一起,雖然后來何穆曾經(jīng)去看望過女兒兩次,但陳亞男對父親還是沒留下什么印象。
兒時的陳亞男與母親也聚少離多。由于陳學昭當時在延安《解放日報》做副刊編輯,編輯之余還要采訪,后來又被分配到中央黨校四部做文化教員,給團級以上干部教授文化知識,天天在根據(jù)地奔波,無暇顧及女兒,年幼的陳亞男便被寄放在由美國一些友好人士資助建立起來的延安洛杉磯托兒所里。戰(zhàn)爭時期的西北物資供應十分匱乏,小孩們只能偶爾在保育員的帶領下,爬到窯洞附近的小山上采摘幾顆又小又酸又澀的野棗,當作零食解饞。陳學昭只得在空閑時,用拿慣筆桿的手,學習用手搖紡車紡紗,換些麥芽糖塊給長身體的女兒補充營養(yǎng),讓女兒感受到艱苦生活中的難得甜蜜。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機關先后向西柏坡、北平挺進。小亞男和小伙伴們睡在毛驢馱著的“架窩子”里,離開陜北渡過黃河,幾年間輾轉山西、河北等3省16個縣,最后在北平西郊的萬壽寺里落腳。
1949年8月,陳亞男和幾個適齡孩子被送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育英小學讀書,平時就住宿在學校里。這一年,陳學昭分別被選為全國婦聯(lián)執(zhí)行委員、全國文聯(lián)委員和全國作協(xié)委員。
陳學昭對故鄉(xiāng)的感情很深。1949年4月全國婦代會結束后,她就去中央組織部干部處找處長廖志高,要求分配回故鄉(xiāng)浙江工作,決心按照延安文藝座談會指引的方向,深入基層,到工農(nóng)群眾中去。廖志高勸她說:“學昭同志,北京很需要你這樣的女干部,你就不要回浙江了。”但她堅持一定要回去,并把女兒留在了北京。
1949年8月回到浙江后,陳學昭先是滿腔熱情地參加余杭縣剿匪反霸斗爭,接著受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譚震林委托,擔任了浙江大學黨支部書記兼中文系教授。不久,她又到離故鄉(xiāng)海寧縣城不遠的斜橋鎮(zhèn)黃墩鄉(xiāng)參加土改,并深入到杭州的龍井、滿覺隴、梅家塢茶區(qū)體驗生活。工作之余,她每天夜晚堅持在煤油燈下寫作。1953年,她的小說《土地》《春茶》出版,1954年,又出版了詩集《紀念的日子》。這一期間,陳學昭和茶農(nóng)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遠在北京的陳亞男與母親難得見面,對母親有點陌生感,反而和班主任高而恮老師等很親近。
1953年11月,陳學昭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之一赴蘇聯(lián)參觀訪問,回國后,給陳亞男寄去一張?zhí)K聯(lián)的明信片,上面寫著要她好好學習,當個優(yōu)秀少先隊員的話,并托高老師捎給女兒一小袋從蘇聯(lián)帶回來的巧克力,讓她甜蜜地吃了幾天,陳亞男才感受到母親的愛。
飽受磨難
天有不測風云。從1955年起,“供給制”被取消,這意味著黨政機關干部和他們子女衣食住行由國家包起來的日子結束了。已經(jīng)回到浙江工作的陳學昭在給女兒的信中多次提到美麗的杭州,陳亞男感覺母親有讓她也回浙江的打算,可自己已適應在北京的生活,想繼續(xù)留在北京學習,所以她希望母親最好能在北京安個家。然而這年夏天,母親還是帶著她乘火車回到了杭州。
一個星期以后,陳亞男被母親送到杭州眾安橋小學過暑假,寄宿在該校任校長的舅舅家中。安頓好女兒后,陳學昭接到中國作協(xié)的通知,回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藝界開展的所謂“批胡風反黨集團”學習班去了。
從北京回來后,陳學昭的生活總算安定了下來。
可好景不長,一場“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1957年春末,陳學昭參加了浙江省文聯(lián)召開的一個座談會,按照會議的安排,她在座談會上發(fā)了言,未曾想正是這次發(fā)言就成了她“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言論”的所謂罪證。
1957年8月27日至30日,浙江省文聯(lián)機關連續(xù)進行所謂“大辯論”,稱“右派分子”陳學昭“當?shù)氖亲骷摇①u的是毒藥、黨員招牌、叛徒行徑”。《文匯報》于1957年10月13日又發(fā)表了一篇評論《投降者的自白——剖析陳學昭對〈文匯報〉記者的談話》,為批斗火上澆油。這年中秋節(jié)前,新華社播發(fā)了一條陳學昭被劃為右派的消息。幾天后的一個下午,陳學昭被通知傍晚到省文聯(lián)參加支部大會,在會上宣布對她的處分:這位1945年7月入黨的老黨員被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隨后,陳學昭和女兒被趕出在赤山埠的家,停發(fā)工資,取消公費醫(yī)療,母女倆只能靠原有的一點稿費艱難度日。
1958年3月,在和女兒陳亞男搬到杭州獅虎橋附近后,陳學昭又被下放到紹興縣文化館當清潔工。其間,文化館失竊,隔壁農(nóng)具廠的治保委員賊喊捉賊,把臟水潑到陳學昭頭上,使她的身心遭受嚴重折磨,人一下子就病倒了。
1958年,女兒陳亞男的人生也跟著歷經(jīng)波折。初中剛畢業(yè)的她,因受母親株連被當作“小右派分子”不能再上高中,被下放到余杭瓶窯的大觀山農(nóng)場。為免遭歧視,陳亞男曾—度中止與母親通信。
1959年底,紹興文化館“失竊案”告破,陳學昭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寫了信,才獲準回到杭州治病。1960年5月1日,陳學昭被分配到杭州大學圖書館工作,每天干的是做卡片、編資料,還有打掃衛(wèi)生等工作。在這里,她得到時任杭州大學副校長林淡秋的關心和幫助,恢復了公費醫(yī)療和糧食定量。1961年6月,在停發(fā)了4年的工資后,她又開始領行政15級的工資,雖然比她原來的10級工資降了5級,但已經(jīng)不錯了。不久,陳學昭給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寫信,要求將女兒調到身邊以便照顧自己,并得到批準。1960年9月,陳亞男回到杭州。為了讓女兒能繼續(xù)上學,陳學昭又給周揚寫信。在周揚的過問下,次年9月陳亞男進入了杭大附中(現(xiàn)學軍中學)讀書。1962年春節(jié)前夕,陳學昭終于被摘掉戴在頭上的“右派”帽子。
在采訪中,陳亞男不無感慨地說:“我的青春時光都是在可怕的運動中被消磨的,當時母親受批斗,家中的書全被抄光,自己也沒辦法安心讀書。高中畢業(yè)后,我本是準備上大學的,可由于母親是摘帽‘右派,我還是不能升學。雖然我是母親的獨養(yǎng)女,按規(guī)定本可以留在母親的身邊,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又被作為‘知青下放到桐廬縣洋洲公社當農(nóng)民,一去就是7年。由于我的身體較差,最后是我母親寫信給鄧穎超反映情況,并由老省長周建人從中協(xié)調,在1971年以招工的名義,到浙江大學校辦工廠熱處理車間當了9年工人。直到1980年我因病被調入浙大圖書館,才總算有時間來繼續(xù)學習,此時我已40歲了。”陳亞男早前曾跟隨母親學習法語,后來讀了兩年夜校,之后又參加了成人高校自學考試,靠自己的努力,在50歲那年拿到了大專畢業(yè)證書。陳亞男說:“我去上課時,教室里全是年輕人,任課老師以為我也是老師,還向我點點頭。我告訴他,我也是學生,他頗為驚訝。”
粉碎“四人幫”后,那些強加在陳學昭頭上的罪名終于被推倒。1979年3月4日,陳學昭恢復了組織生活。同年10月,她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困難時期構思和寫成的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下卷,與1949年由大連新中國書局出版的上卷合為一集,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隨后,她回到浙江省文聯(lián)工作,并當選浙江省文聯(lián)副主席、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她的家也由原來在文三路河東杭州大學筒子樓宿舍,搬到了西湖附近的龍游路。1984年,為照顧體弱多病的陳學昭,組織上將陳亞男調到浙江省文聯(lián),做陳學昭的秘書,使她終于有了一個比較清凈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寫出了許多新作,先后創(chuàng)作與出版了《工作著是美麗的》續(xù)集、《海天寸心》《野花與蔓草》《蔓草拾零》《天涯歸客》《浮沉雜憶》《如水年華》等數(shù)百萬字的作品集。女兒也在母親身上,學到了許多寶貴的東西。
出版遺作
1991年10月10日凌晨3時45分,85歲的陳學昭在寫完了她的封筆之作《可貴的痕跡》后,帶著對文學、親人和好友的無盡眷戀,在浙江醫(yī)院安詳?shù)仉x去,并以“不開追悼會、骨灰撒入故鄉(xiāng)的大海中”的方式,落下了人生大幕。中央領導陳云、彭真、鄧穎超,中國作協(xié)和巴金、劉白羽、柯靈等發(fā)了唁電。
母親的逝世讓陳亞男悲痛不已。好長一段時間,她都在追憶著母親和自己的一些往事。
陳亞男記得在“反右”運動前,家里曾有一段平靜的生活。陳學昭加強了對女兒的教育。特別是在女兒進入杭十二中讀書后,她要陳亞男讀茅盾的《腐蝕》,讀《三國演義》《史記》,還教女兒讀古文,其中讀《馮煖客孟嘗君》一文,讓陳亞男感受到母親引導她學習古文的良苦用心。
上小學時,陳亞男的數(shù)學成績不太好。為了消除女兒的學習短板,在陳亞男讀初中時,陳學昭便請中國留學德國的第一位數(shù)學女博士、浙江師范學院數(shù)學系主任徐瑞云教授為女兒補課。在徐教授的啟發(fā)指導下,陳亞男的數(shù)學成績顯著改觀。在高二期末考試時,她的立體幾何考了全班唯一的100分。
1953年陳學昭的《土地》一書出版后,陳亞男十分高興,還把這一好消息與同學分享,并愛上了看書。后來她到大觀山農(nóng)場勞動時,每次回家都要到圖書館借些書看,在業(yè)余時間看了茅盾、高爾基等中外大作家寫的一些文學名著。
從1987年開始,陳亞男的散文《桂花樹下》《芬芳的季節(jié)》分別發(fā)表在《香港文學》和《解放日報》文學副刊上,還有《清涼山尋蹤記》《七十一年彈指一揮間》等散文發(fā)表在大型文學雙月刊《江南》上。浙江文藝出版社的著名編輯費淑芬曾稱贊她的散文起點比較高。1990年,她加入了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
在陳亞男夫婦多年的努力下,陳學昭的散文集《心聲寄語》于1992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5卷本《陳學昭文集》于1998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01年,陳亞男編著的文化人影記叢書《陳學昭》卷,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這當中,陳亞男還寫出了一本回憶母女倆生活的文集《我的母親陳學昭》,于2006年4月由文匯出版社出版。陳亞男說:“我在這當中深切地感受到,母親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
在采訪結束時,陳亞男向筆者透露了心中的一個愿望:5卷本的《陳學昭文集》出版后,他們發(fā)現(xiàn)其中還有不少遺憾:如母親的《土地》《春茶》這些特定政治時期發(fā)表的小說,并未被收錄其中;還有母親一些書信、詩歌、譯文、懷念友人的散文也沒有收錄,可以說是不完整的;他們希望能出版一部《陳學昭全集》,將現(xiàn)有的作品都放進去。近年來,他們都在搜集母親的散失作品,并陸續(xù)有新的發(fā)現(xiàn)。雖然書信整理這塊比較困難,其中有一段時間的書信都因“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已被燒毀,但他們仍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完成《陳學昭全集》的編纂,并為此不斷努力著。(題圖為1955年夏,陳學昭與女兒陳亞男在杭州合影)
(責任編輯: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