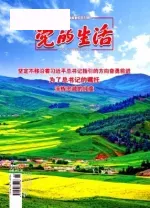剩水剩土
王文瀘
實(shí)際上在人類持續(xù)不斷的開(kāi)墾之下,鄉(xiāng)村已經(jīng)沒(méi)有什么剩余的水土了。尤其是在青海東部這樣的地方。這一片依傍著黃河和湟水的谷地,僅占全省總面積的5%,卻承載著全省75%的人口,哪兒還有剩余的水土?但我說(shuō)的不是這個(gè)意思。我說(shuō)的是在自然經(jīng)濟(jì)時(shí)代,鄉(xiāng)村的房舍布局沒(méi)有統(tǒng)一規(guī)劃,由于莊廓院的隨意分布,以及道路的自由切割,房前屋后,林邊崖旁,總會(huì)剩下一些無(wú)法利用的小塊閑散土地。這些土地參差錯(cuò)落,零七碎八。種上點(diǎn)什么吧,高處澆不上水,低處石頭多。看著順溜些的,不過(guò)是一個(gè)院子大小,駕上犁,牛就轉(zhuǎn)不過(guò)身子,于是就那樣荒著,聽(tīng)任雜花野草繁衍,歪榆瘦柳亂長(zhǎng)。
這些剩水剩土,也是一處處鄉(xiāng)村地理坐標(biāo)。外來(lái)的人如果打聽(tīng)誰(shuí)家在哪里,當(dāng)?shù)厝司蜁?huì)告訴他:“你順著這個(gè)渠邊小路走,上了那個(gè)寬寬的草臺(tái)子,遠(yuǎn)遠(yuǎn)看見(jiàn)一棵大白楊,左手第一個(gè)大門就是。”這里說(shuō)的“草臺(tái)子”就是一處剩土。或是說(shuō):“你往前看,沙棗林前頭那一片水灘灘見(jiàn)了沒(méi)?你繞過(guò)去,一副老莊廓就見(jiàn)著哩。”這里說(shuō)的“水灘灘”就是一處剩水。
鄉(xiāng)村鄰里之間,很少有人為這些荒地的歸屬權(quán)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尤其是在集體經(jīng)營(yíng)核算的年代,爭(zhēng)它也沒(méi)有意義。
還有一些水泊,多在低洼潮濕、有細(xì)小泉眼滲出的地方。大的如游泳池,小的如漚麻坑。說(shuō)它是活水吧,不見(jiàn)波生紋動(dòng);說(shuō)它是死水吧,也從不發(fā)臭。夏天,過(guò)路的黃野鴨們?cè)诖诵_涮洗,梳理羽毛,啄食水藻。休整好之后飛走。冬天,這里就是孩子們的溜冰場(chǎng)。這些水泊,沒(méi)有經(jīng)濟(jì)利用價(jià)值,所以也屬于剩水。
對(duì)于這些剩水剩土的存在,人們從來(lái)寬容。人老幾輩子,沒(méi)有誰(shuí)想著把它們消滅了。相反,它們和莊廓院、麥田、果園、磨坊等事物一起,不分厚薄地被村莊的記憶所接納,也成為游子鄉(xiāng)愁中難以割舍的內(nèi)容。
也許是造物多情,有意留下這些無(wú)法利用的荒地,免得居住空間變成呆板的幾何圖形;也用它們來(lái)緩解莊戶的擁擠。有了它們,村莊就顯得疏朗,空氣就顯得寧?kù)o。
是否還有別的深意?不知道。比如說(shuō),用自然的剩余形態(tài)來(lái)啟示人們:凡事當(dāng)留有余地,不可趕盡殺絕;用生態(tài)類型的多樣化來(lái)啟示人們:人間最好千差萬(wàn)別,不可過(guò)于單一。
凡屬剩水剩土,地貌都豐富。一些適應(yīng)能力強(qiáng)的喬木,比如榆樹(shù),野柳,山楊等,只要土里有潮氣,就能扎下根,放肆地舒展枝葉。野草呢,更是互相較著勁,比賽誰(shuí)更皮實(shí)。有濕度的地方,田旋花(俗名苦子蔓)瘋了似的纏住一切夠得著的草木,賴住別人攀援;在干得幾乎要冒煙的地方,白茅(俗名冰草)不動(dòng)聲色地年年生發(fā)。偶爾,還會(huì)長(zhǎng)出幾叢罕見(jiàn)的干花——金色補(bǔ)血草。它那豆蔻狀的金色花瓣,一經(jīng)開(kāi)放,永不凋謝,插到花瓶里簡(jiǎn)直是神品。芨芨草在石頭灘里奓開(kāi)箭桿般的莖稈,枝頭淡紫色的穗翎卻化解了它的生硬。駱駝蓬有小小的冠蓋,小小的針葉,像袖珍型的馬尾松。杏子黃熟時(shí)節(jié),果園主人常用它們鋪墊籃子,再放上紅杏,提到街上賣。一紅一綠,相得益彰,不由人不駐足一看。
最為搶眼的是錦毛懸鉤子(俗名狗連蛋),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歡往崖沿上攀爬。哪里荒僻,哪里就由它們裝飾。夏天,拇指大小的黃花綴滿藤蔓,像一串串銅鈴;秋初,從這些鈴鐺里抽出一團(tuán)團(tuán)錦毛,銀灰色,蓬松晶亮,像極了歐美兒童的鬈發(fā)腦袋。
臨近河邊的小塊荒地,細(xì)草長(zhǎng)得氈一般瓷實(shí),常年濕漉漉的。濕地的草味道寡淡,大牲口都不愛(ài)吃,只有口粗的山羊有時(shí)會(huì)光顧,但也吃得心不在焉。只不過(guò)山羊和身邊的羊羔被濕地一襯托,就是一幅畫(huà)。
農(nóng)村出身的人,沒(méi)有誰(shuí)的童年生活不與荒地相聯(lián)系。夏天,拿一把小鏟子,選地方“開(kāi)渠”引水,修建“堤壩”,制造“瀑布”。馬蓮草編成的水車,在“瀑布”中咕嚕嚕旋轉(zhuǎn)。溝壑、崖彎,也是排兵布陣、埋伏偷襲的戰(zhàn)場(chǎng)。有時(shí)玩著玩著,腳底下突然嘎嘎一聲,嚇人一跳,草叢里撲棱棱飛起一只野雞。驚魂甫定,轉(zhuǎn)而一喜:敢是有野雞蛋!細(xì)心地分開(kāi)草叢尋覓,果然就見(jiàn)到那一窩潤(rùn)白如玉、渾圓似珠的東西。小心捧起一個(gè),攥在手里,感受著異類的體溫,又像是攥住了大自然的溫存,油然生出一點(diǎn)小感動(dòng)。
在荒地里邂逅野雞蛋的心情,難以名狀,遠(yuǎn)勝別人白送一籃雞蛋。
幾十年后,我讀到現(xiàn)代文學(xué)大家聶紺弩的一首詩(shī),寫他上世紀(jì)60年代在農(nóng)場(chǎng)勞動(dòng)時(shí)意外撿到野鴨蛋的喜悅,引起強(qiáng)烈共鳴。茲錄如下:
七律·拾野鴨蛋
野鴨沖天捉對(duì)飛,
幾人歸去路歧迷。
正穿稠密蘆千管,
奇遇渾圓玉一堆。
明日壺暢端午酒,
此時(shí)包裹小丁衣。
數(shù)來(lái)三十多三個(gè),
一路歡呼滿載歸。
荒地里還適宜瞞著大人埋鍋造飯。這又激發(fā)了孩子們的另一種創(chuàng)造欲望。八月未盡,地里的洋芋還沒(méi)長(zhǎng)足,孩子們就迫不及待地行動(dòng)了。選中一處土坎,用鏟子挖出直徑一尺多的灶坑,在灶沿上小心地堆壘土疙瘩。這個(gè)技術(shù)活由有經(jīng)驗(yàn)的人來(lái)做,其他人各有分工。膽大腿快的,去偷洋芋;膽小老實(shí)的,搬運(yùn)土疙瘩。壘土塊的人,全神貫注,目不旁騖,邊往上壘,邊往里收,常常功虧一簣,中途垮塌,換來(lái)一片惋惜之聲。那也沒(méi)關(guān)系,孩子們有的是耐心。如果壘成功了,就是一個(gè)寶塔狀的建筑。接下來(lái)四處檢拾燒柴,小心地填進(jìn)灶門,點(diǎn)燃,輪流趴下來(lái)用嘴把火吹旺。一個(gè)個(gè)吹得臉紅脖子粗,煙熏得淚流滿面。
土塊終于燒得暗紅。小心地把偷來(lái)的洋芋填進(jìn)灶門,往“寶塔”頂上輕輕一腳,熱灰飛揚(yáng),火星亂迸,“寶塔”轟然倒塌,剛好埋住洋芋。拿起柳條棍把熱灰拍嚴(yán)實(shí)了,大功告成。立即撤離現(xiàn)場(chǎng),到視野開(kāi)闊的地方一邊玩,一邊觀察“敵情”。
從熱灰里扒出來(lái)的洋芋又燙手又可口,拍著吹著吃著,誰(shuí)也顧不上嘲笑對(duì)方嘴巴上的黑灰。這項(xiàng)活動(dòng)帶給人刺激、隱秘和空前團(tuán)結(jié)的興奮,在學(xué)校里可是體驗(yàn)不到。
冬天,荒地蕭條了,但也不寂寞。水泊結(jié)了冰,鏡面一般干凈。撿糞的孩子們只要路過(guò),就不想走了。把肩上的背篼往冰面上一放,趴上去,兩腳一蹬,嗖的一下滑出好遠(yuǎn)。七八個(gè)背篼聯(lián)接起來(lái),就是一列在冰面上行駛的火車。
天寒地凍,荒地里枝條稀疏,麻雀奇多。樹(shù)下空地上,白花花的麻雀屎落了一層。婦女們就會(huì)打發(fā)孩子拿瓶子去撿,準(zhǔn)備做護(hù)膚品。還必須是母雀屎,公的不好用。怎么區(qū)別?很容易:端直如米粒的,那是公雀屎;微微彎曲的就是母雀屎。麻雀屎用童便浸泡三天,搖勻,就寢前用來(lái)擦手擦臉,雖然騷臭難聞,效果奇好。擦上幾天,皴裂消失,皮膚細(xì)膩,容光煥發(fā),遠(yuǎn)勝雪花膏。今天一想,麻雀屎必定含有某些寶貴的活性物質(zhì),用童便把它們逼出來(lái),才有如此奇效。當(dāng)今研發(fā)生物美容品的人還不知道這些。如果知道了,經(jīng)過(guò)一系列脫臭和提純技術(shù)的深加工,麻雀屎說(shuō)不定會(huì)身價(jià)百倍。
冬天,孩子們的活動(dòng)半徑小了,又不甘心窩在家里。野地里背風(fēng)的坑洼,干爽的林地,是晚上開(kāi)神仙會(huì)的好去處。在那里,圍成一圈,升起篝火,就開(kāi)始交流鬼故事。篝火跳躍著,稚氣的臉龐,畏懼的眼睛在火光中愈顯生動(dòng)。越聽(tīng)越怕,越怕越想聽(tīng),直至北斗西斜,懾于回家后挨打,這才戀戀不舍地離開(kāi)。臨走前不忘一人一泡尿,澆滅余燼。
荒地是農(nóng)村孩子的第二生活空間。
上世紀(jì)60年代初,填飽肚子成為全國(guó)頭等大事。為了向土地多要糧,除了大規(guī)模開(kāi)荒種地,政府還號(hào)召開(kāi)發(fā)利用“十邊地”:房邊、路邊、水邊、渠邊……等等。羊皮大的地方,也種上了莊稼。但收獲總不如意,這一坨地收了半升油菜籽,那一坨地收了幾把秕麥子。所以災(zāi)荒過(guò)后,農(nóng)村人立刻放棄了“十邊地”。剩水剩土,就讓它那么剩著吧。雖說(shuō)沒(méi)什么產(chǎn)出,但它們并沒(méi)有擠著誰(shuí),擋著誰(shuí),只不過(guò)謙卑地在村前屋后存在著,襯托著田地莊園,接納著孩子們的游戲欲望。
然而后來(lái)的孩子們漸漸顧不上荒地了。課業(yè)、升學(xué)、就業(yè)等問(wèn)題,壓得他們喘不過(guò)氣來(lái),他們常年拘囿在學(xué)校。春游和秋游,是教育部規(guī)定的學(xué)校活動(dòng),為的是確保學(xué)生有與大自然接觸的機(jī)會(huì)。一年兩次集體郊游,已屬珍稀難得,但出于對(duì)安全的擔(dān)心,所有的學(xué)校都不謀而合地把這項(xiàng)活動(dòng)取消了。孩子們還沒(méi)品味到童年,就被拽進(jìn)成人世界。許多人,個(gè)頭快趕上父母了,嗅覺(jué)記憶庫(kù)里還空缺著野花野草的信息;細(xì)白的雙腳還沒(méi)有被山間溪流撫摸過(guò);舒展的四肢還沒(méi)有被開(kāi)滿馬蓮花的草地?fù)肀н^(guò)。
沒(méi)有了孩子們的嬉鬧,剩水剩土略顯寂寞。幾十年后,時(shí)代的步伐驟然提速。旅游開(kāi)發(fā)、商業(yè)開(kāi)發(fā)、城鄉(xiāng)建設(shè)和工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等,以所向披靡之勢(shì)橫掃一切,許多大有保留價(jià)值的事物都迅速消失,何況本來(lái)就荒置著的地和水。
既然荒置著,為什么不利用?這是簡(jiǎn)單到不需要解釋的邏輯。
頭戴安全帽的技術(shù)人員,安裝在三腳架上的水準(zhǔn)儀,鏟車,挖掘機(jī),裝載機(jī),這已經(jīng)是鄉(xiāng)村里隨處可見(jiàn)的風(fēng)景。而混凝土和鋼筋則是黃土的替代物。擋路的,移走!凸出的,鏟平!低洼的,填平!彎曲的,取直!你昨天看見(jiàn)的,還是一處“平崗細(xì)草鳴黃犢”的閑地,今天看見(jiàn)的,就可能是一片空心磚預(yù)制場(chǎng)。
在藍(lán)圖的設(shè)想者或開(kāi)發(fā)者眼里,一切閑置著的水土和草木都是無(wú)價(jià)值的,滅掉它們是天經(jīng)地義。
閑置著的水土和草木,確實(shí)與人性中某些比較消極的因素相一致,比如懶散。然而對(duì)于自然界而言,懶散一定是種壞行為嗎?比起瘋狂掠奪?
新疆的農(nóng)民作家劉亮程說(shuō):“有人說(shuō)庫(kù)車那個(gè)地方的農(nóng)民太懶散,莊稼地里的雜草也不認(rèn)真拔,地邊的果樹(shù)上有好大的鳥(niǎo)窩,那么低,伸手一棒子就可以打下來(lái),也不去打,聽(tīng)任鳥(niǎo)雀糟蹋糧食。太懶了。我不這么認(rèn)為。我認(rèn)為這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在這個(gè)地球上,由于人們過(guò)于勤快,已經(jīng)把大地改變得不成樣子,地里除了莊稼,其他萬(wàn)物都失去了生長(zhǎng)的權(quán)利。這有什么好?”
劉亮程是帶著激憤的感情說(shuō)出這一番有失偏頗的話語(yǔ)的。而他的激憤,也有點(diǎn)舉一反三的價(jià)值。比如說(shuō):
凡是閑置不用的物質(zhì)存在是否都無(wú)意義?是否都應(yīng)該被拋棄?譬如一個(gè)家庭里,總有一些舊物件,算不上珍品,換不來(lái)金錢。為什么主人還愿意保留著它們?
——這涉及到人的情感寄托方式。
是不是把每一寸荒置著的水土都開(kāi)發(fā)凈盡,才算沒(méi)有辜負(fù)人的創(chuàng)造力?
——這涉及到生態(tài)理論和發(fā)展觀念。
村前村后,那些散亂生長(zhǎng)的樹(shù)木,曲曲彎彎的溪流,高低不平的崖彎,是否真的與自家房屋的整潔敞亮毫無(wú)關(guān)系?
——這涉及到居住心理學(xué)。
是不是把所有雜草叢生的地方都用水泥地坪覆蓋;把所有水泊周圍都裝上大理石護(hù)欄,安上彩色射燈;讓每一棵樹(shù)都站在指定位置,環(huán)境才算美麗?
——這涉及到環(huán)境理論和審美觀念。
“無(wú)用”和“有用”之間,究竟有沒(méi)有絕對(duì)的界限?“無(wú)用”是不是“有用”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
——這涉及到哲學(xué)問(wèn)題。
這一切問(wèn)題——這些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目標(biāo)似乎無(wú)關(guān)的問(wèn)題,如果也算是問(wèn)題的話,又應(yīng)該由誰(shuí)來(lái)關(guān)注、研究和尋找解決辦法?
國(guó)外早就有一些探討荒野價(jià)值的理論。比如美國(guó)的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在《哲學(xué)走向荒野》一書(shū)中,詳細(xì)地論述了關(guān)于荒野的價(jià)值。不過(guò)那些“荒野”的概念,與本文所描述的剩水剩土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相信,終有一天,當(dāng)人們把鄉(xiāng)村拾掇得不剩一撮閑土,不余一掬野水的時(shí)候,會(huì)想起:無(wú)論什么東西,還是剩余一點(diǎn)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