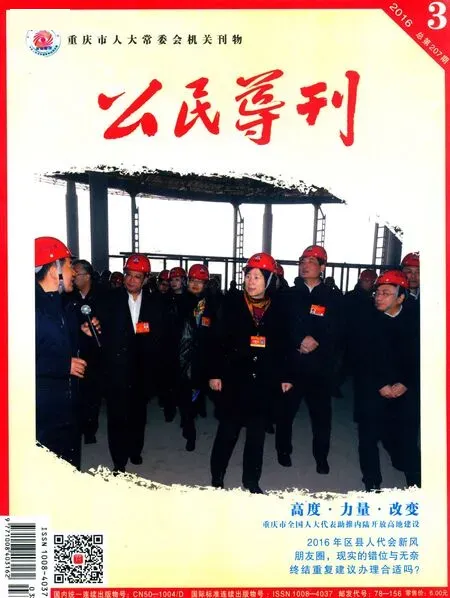人大立法權限須合理平衡民主與效率
2016-04-29 03:22:11阿計
公民導刊
2016年3期
關鍵詞:法律
(阿計:著名媒體人,資深人大新聞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會員)
國家立法權是立法體制的核心所在,只有清晰劃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限,并構建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才能確保立法同時行進于民主、高效的軌道上。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審議慈善法草案。這是繼去年全國人代會審議、通過立法法修正案后,全國人大連續兩年行使立法權。
近期已經召開的地方人代會也不時傳出立法消息,比如今年廣東省人代會就通過了廣東省地方立法條例修正案。相對于全國和地方人大常委會頻繁立法,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由沉寂漸趨活躍,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改革信號。
這一變化潛藏的追問是,究竟哪些立法權應當由人大行使?哪些立法權可以由人大常委會行使?
1982年頒布的現行憲法,構建了統一、分層級、多種類的立法體制,并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2000年出臺的立法法,進一步明確了縱向的中央與地方之間、橫向的人大與政府之間的立法權限,并設定了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訂法律的中央專屬立法范圍,不過,兩者之間內向的立法權限并未得以清晰劃分。
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全國人大的立法數量不斷萎縮,而常委會的立法數量急速遞增。
有統計表明,1979年至2009年,全國人大立法占全部立法的比例在第一個十年為33%,第二個十年下降至13%,第三個十年更是驟減至4.2%。自2008年至2015年年底,全國人大僅僅修改了3部法律,同期常委會制訂和修改的法律卻多達101部。……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3年9期)2023-10-14 15:57:47
法律方法(2022年1期)2022-07-21 09:17:10
法律方法(2021年3期)2021-03-16 05:57:02
法律方法(2019年4期)2019-11-16 01:07:16
法律方法(2019年3期)2019-09-11 06:27:06
法律方法(2019年1期)2019-05-21 01:03:26
法律方法(2018年2期)2018-07-13 03:21:38
學生天地(2016年23期)2016-05-17 05:47:10
山東青年(2016年1期)2016-02-28 14:25:30
中國衛生(2015年1期)2015-11-16 01: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