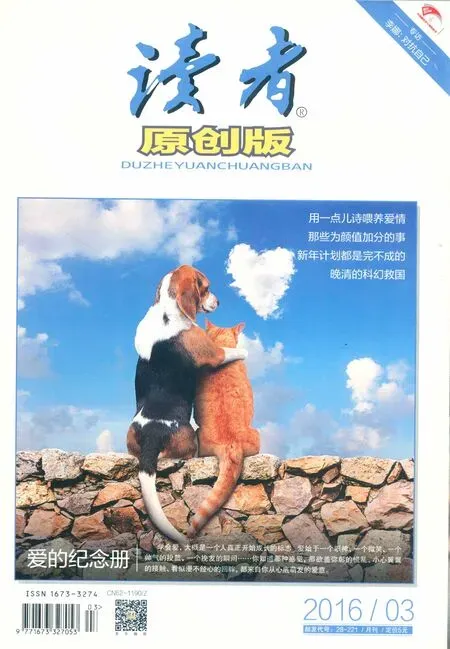用一點兒詩喂養愛情
文_劉云芳
?
用一點兒詩喂養愛情
文_劉云芳

深夜,孩子已經睡熟,老黃正用3000號砂紙打磨一件木雕。看我拿著一張紙走過來,他停下手里的活兒,聽我輕聲讀詩。讀詩是我們生活里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老黃稱其為“私人廣播”。
一
2008年春天,我千里迢迢來到唐山。那天火車晚點,半夜才到站。我懷里抱著一個長耳朵的毛絨兔子玩具,右手的大包里塞了件厚實的粉紅色外套,像個夜歸人,但那是我第一次來這個城市。在一個月前,我還忙著相親,在A君與B君之間選擇到底該赴誰的約,直到紅鼻子老黃從天而降。
這像一場賭局。當時我只見過老黃的照片——瘦高個子,眼睛細長,鼻子大而紅,像在臉上扣了個草莓,讓我想起麥當勞的小丑。
那時,我在一家大型企業工作。對于一個總板著面孔訓斥別人,也要厚著臉皮隨時受領導訓斥的白領來說,詩是我生活中的調劑品。我將它們放在博客上,在小圈子里交流。不知誰將其中幾首傳到一個論壇上,被遠在唐山的老黃看到了。其中一首《流轉》,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我想應該把你隱在草原
或者藏在某個樹洞里
你卻獨自跑到馬背上
你趕著一群羊
在我揮動鞭子的時候說
我愛你
老黃大學時學的是國畫,卻對文字情有獨鐘。他有很深的草原情結,曾在一篇文章里,想象自己是一只沉默的羊,被美麗的姑娘牧放。他說讀到我的詩句時,覺得心里某個地方被照亮了。
這首《流轉》就這樣流轉到了他心里。他從網上找到我的那個下午,我忘記了自己是個工作狂,將手頭的事情一放再放。我們從金農、八大山人聊到馬蒂斯,從《詩經》聊到以一截褲腿做王冠的詩人顧城……我相信對面的人像我一樣陷入狂喜,我臉色泛紅,似有醉意。
一下午的網聊,讓我不得不加班到深夜。獨自走出辦公室,看到天上的星星用力睜眼,路旁的樹木正準備吸精吐綠,似乎世間萬物的靈魂都在狂歡。
與老黃相識后的第四天便是愚人節,下班后,我撥通了他的號碼。那個聲音自此一天天熟悉起來。之后的幾天,朋友從我的臉上看到了愛情的光輝,他們見我就要落入“陷阱”,忍不住勸解:“多少網絡騙子把無知少女的青春和錢財都騙得精光……”我直接跨過這些良言,執著地與老黃交往。很多東西可以編造,但對詩的感覺和喜好是無法騙人的。
二
老黃當時正迷戀在葫蘆上烙畫,我時不時把新寫的詩傳給他看。對于“牛的犄角劃破天空,故鄉流淌出來”這樣的詩句,他很喜愛,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原本說好年底見面,后來變成了國慶節,又從國慶節提前到中秋,中秋又提前到端午。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內心的方向,于是,那一個個靠近的節日變成泡沫。他說:“兩個小時后有趟來我這里的火車。”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請假、收拾行李、買票上車……這時距離他看到《流轉》只有20天。
與想象中的不同,我沒有在人群里尋覓、辨認,一下車便看到車站燈光下他瘦高的身影,世界上的人和物頓時灰暗了下去。我故意放慢步子走過去,問:“是你嗎?”他先是笑了笑,然后把藏在身后的右手伸出來——是一個嫩綠色的毛絨七仔,之前我說過喜歡那個形象。
當時,飯店都已經關門,他只能帶我去吃麥當勞。那個小丑蹺著腿坐在長椅上,迎接我們。在空曠的大廳里坐定,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荒唐,卻在吃東西的時候故作自然地看他。他非常靦腆,不像是會做瘋狂事情的人——后來,我從他朋友那里得到證實,沒人想到他會網戀。
我看他的時候,他也正在看我,是在尋找一扇時間之門,也是在確定。飯后已經接近清晨,路燈閃爍,我隨他回到他的住處。整潔的小屋里,一張桌子上放著電腦,它和詩一起成了我們的媒人。旁邊的三層架子上是碼放整齊的書籍,統一用牛皮紙包了書皮,可以看出它們的主人是何等細心。葫蘆整齊地排列在一處,有一個上面烙的是觀音坐蓮,一半還是線稿,一半已經烙燙好。我在他的引導下,觸摸那細致的線條,他說這是給我的。墻上掛著把吉他,正是他每天晚上通過電話為我彈奏的樂器。他站在我身邊,忽然念起我寫的句子:“時間站在你身后,卻從不出手相救。”此時,我們終于從陌生的軀殼里找到了那個熟悉的靈魂。
我們忘了已經一夜未眠,任語言碰撞、目光干杯,越來越確定對方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個人。他握著我的手說:“同志,可找到你了!”兩個人的手在燈光下變成了墻上的一只飛鳥,“得感謝詩歌,它是打開我們緣分的鑰匙”。
那次離開唐山,我檢票進站,回頭,他的身影已被人流淹沒,淚水頓時溢出眼眶。我那件厚外套,已經跟吉他一起掛在他的墻上,一直在我床邊靜坐的長耳朵毛絨兔子玩具,如今正坐在他的床邊——這是最好的允諾。即便這樣,他還是覺得我是從夢里穿越來的,他感覺自己像《聊齋志異》中那些幸運又不幸的書生。
三
兩個月后,我在朋友驚訝的目光里辭去了工作,奔他而去,閃電結婚。我們租的小屋無比簡陋,廚房里的柜門開關時能聽到噼里啪啦的聲響,再打開,可以看到許多蟑螂的死尸。我依舊在半夜寫詩,完成之后,將他晃醒。有時候,他畫畫,我在電腦上敲著文字,寧靜的空氣里流動著一份默契。
后來,我們搬了四次家,時光因為詩歌的摻入,雖淡,卻有味。下班后,我做飯,他為我讀詩,那些詩句落在家常的菜肴上,讓它們變得更加豐盛。再后來,我們成了房奴、孩奴,我不得不辭去工作,居家帶孩子。有一段時間為了生活,我還去小區附近的市場擺攤。但因為有詩歌,我們的心靈更有韌性,那些詩句可以把心里的塵土洗凈。我們都深信,詩歌是永恒之光。
我無心寫在紙上的詩句,被他記著并念起,他會講起它們投射到他心底的那些畫面和聲音。我從老黃的畫里,看到了詩意,并為之感動。后來他開始雕刻桃核,也做木雕。那些桃核經他的手,忽然變作一個慈眉善目的菩薩,或者莊子。他用看似無用的邊角料雕刻出微小的眾生。這何嘗不是一首詩?似乎菩薩及眾生都在木頭和桃子的深處修行,只等著他去發現、去挖掘。
有了孩子之后,我們忙碌地生活,涉及詩的交談變少。但陪孩子學走路、學說話,看他為未知而廣闊的萬物命名,也是詩。
那天,我們重回7年前第一次吃飯的那家麥當勞,老黃原來坐過的座位上坐著我們4歲的兒子。晚上回家時,看到道路兩側光禿的樹干,兒子忽然說:“年輪是爸爸,樹干是媽媽/他們生出了許多樹葉/大部分時間,樹葉寶寶都在用力吃奶/到了冬天,他們就離開家/跟土地說悄悄話……”
我們用詩喂養了愛情,現在愛情的結晶又用新的詩句喂養著我們。我記錄下這些句子,希望多年后,他能回頭看到自己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