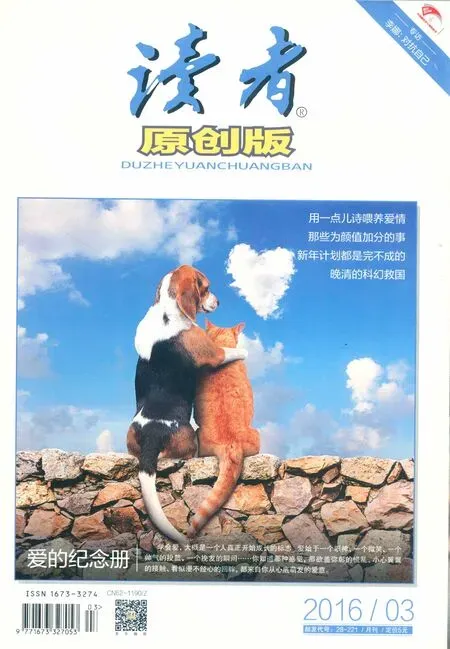報警器
文_張悅芊
?
報警器
文_張悅芊

1
周六的某個下午,我正在房間里寫東西,忽然聽到走廊上傳來尖厲的警報聲。
法國對于防火防盜的技術性保障做得很好,所有房屋竣工時都要安上煙霧報警器才算合格。奈何這小小的圓盤對中國人的烹飪方式太過敏感,往往油鍋一熱青煙一騰,小家伙就恨不得讓全街道都知道似的,大叫起來。
盡管如此,我還是有些擔心,便迅速打了盆水循聲跑去。剛跑出去,就看到對面的窗戶大開著,一個男生站在椅子上,拼命伸手去夠屋頂的報警器,像極了我家第一次“著火”時的情景。
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而那男生也發現了我,一臉無奈,不知如何是好。
報警器終于出盡風頭,便很通情達理地停了下來。
我正打算回去,卻聽到對面窗戶里傳來聲音:“我叫Matthew。”椅子上的男生朝我揮揮手,“要來‘火災現場’喝杯咖啡嗎?”
2
但于我而言,煙霧報警器的麻煩并沒有解決。我既沒有鄰居大手一揮直接將其拆除的勇氣,也沒有中國同學為其套上塑料袋的機智——馬虎如我,若哪天真著起火來,恐怕還得仰仗它救我一命。不得已,我便養成了一做飯便開窗的“好習慣”,雖然每每炒菜都凍得跳腳,卻也暫時封住了報警器的喉舌。
有天夜里,苦學法語一整日的我突然餓了,遂開火起鍋,準備煎塊雞排果腹。法國超市里最便宜的肉是火雞肉,我也囤了許多放在冰箱里。拿出兩塊雞胸肉沖沖水,放在塑料袋里反復敲,再倒入料酒、醬油,撒鹽腌制。熱鍋里放了油,稍見油熱便將雞胸肉放入,刺啦一聲便香氣四溢。不一會兒,肉的兩面皆金黃,再加些料酒,燉幾分香氣進去。正當我準備蓋鍋蓋時,有人敲門。
“我是Matthew。”他隔著門喊,“你做的飯太香了……能不能教我做中國菜?”
后來他吐槽:“每次一看你開窗就知道你又要做飯了,果然,三五分鐘一過,滿走廊都是香味,我的窗戶正對著你的,近水樓臺。”于是,他決定親自來嘗一嘗。
我盛了一塊雞排,撒上孜然遞給他。他問我:“這是什么?”我絞盡腦汁也沒想到這玩意兒用法語怎么說,只得搪塞說是一種祖傳的中國香料。他的表情立刻肅穆起來,非常莊重地接過了雞排。
法國人吃飯是無紅酒不歡的。大大咧咧如Matthew,一點兒都沒有初入女生閨房的矜持,反倒一眼瞄到我櫥柜里的瓶子,看到了瓶身上的單詞“酒”便興高采烈地要拿來配雞排。我欲言又止:“這是酒沒錯……”Matthew已經仰脖一飲——不到3秒,他的表情迅速凝固,奔向廁所,即刻傳來響亮的漱口聲。
他一臉懊惱地問我:“這到底是什么酒?”
我看了看瓶子上孔武有力的“紹興廚房酒”五個大字,嚴肅地說:“這是一種中國宮廷御用飲品。”
自那之后,Matthew便常常帶著些原料來蹭飯,我倒也樂得向高傲的法蘭西人輸出中國美食文化,就這樣,我們湊成了一對飯友。
中國的種種食材成了我捉弄Matthew的不二法寶——從國內帶來的辣椒面,我告訴他是草莓果珍,他沖水攪拌,卻怎么都不溶解,于是氣沖沖地一飲而盡,接著臉頰、雙眼飆紅,淚水漣漣了好久;后來是珍藏的干木耳,我叫他拿水泡著,5分鐘后便聽到他驚叫:“怎么辦,它在長大!”我一邊用長勺攪湯,一邊認真地說:“對,其實那是活的,等一下我們拿來燉湯喝。”
因此,他素有耳聞的“中國人什么都吃”的謠言似乎得到證實。有一次同他一起去超市,途經廣場草坪,許多肥大的鴿子悠閑地踱來踱去。我玩心大起,伸手向它們撲去,鴿子還沒反應過來飛走,就聽見Matthew在后面驚慌地喊道:“那個不能吃的!”
3
總叫我做飯Matthew似乎有點兒過意不去。某個周日,一陣突如其來的敲門聲吵醒了睡眼蒙眬的我,Matthew興高采烈地宣布要親自下廚。
在超市,他自信滿滿地要我自己挑食材,我看了一圈,似乎還沒吃過長相清奇的洋薊,便挑了一顆塞給他。他看到時,一臉“這是什么玩意兒,我也沒吃過”的表情。我貼心地問:“要不換個別的?”他立刻正義凜然地說:“法國人怎么可能不會做洋薊!”便氣沖沖地拿去付款了。
回家后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他敲門,我一開門便看到了哭笑不得的一幕:一整顆洋薊擺在盤子里,它除了看上去被煮過之外,和一個鐘頭前在貨架上的樣子別無二致。我們同時開動,剝了一片下來塞進嘴里,又同時吐了出來。Matthew終于攤手投降:“我也不知道這玩意兒要怎么做……說實話,上大學之前我從沒自己做過飯,弄響報警器那次是第一次。”
我哈哈大笑,又不愿浪費那顆洋薊,遂掏出手機搜索烹飪方式——將堅硬的外殼全都剝去,只留下柔軟的心,切成小段,拌入櫻桃番茄和芝麻菜,放醋與香油,“挽救”成一盤差強人意的沙拉。
從此,Matthew徹底被中國廚藝降服,再也不在我嚇鴿子時大驚小怪了,反而悄悄地問我:“你覺得它們是烤了好吃還是蒸了好吃?”
有一周我去了巴黎,回來后才覺得很久沒見到Matthew,遠遠看他的窗戶緊閉著,便去看他。沒想到他已經發燒兩天了,桌子上堆著切片面包和幾乎見底的果醬瓶。
我趕緊回房提來半只雞,大火煮開撇沫,一邊泡了香菇和枸杞,一邊從櫥柜里摸出紅棗和桂圓,和雞一起放入高壓鍋。他聞見香味,掙扎著爬起來問我什么時候好,我坐到床邊安慰他:“中國人病了,家人都會熬雞湯給病人喝,喝完好好睡一覺,明天就能‘滿血復活’啦。”
他點點頭,完全相信的表情:“每個中國人都會熬雞湯嗎?”
我想到“朋友圈”里漫天飛舞的勵志“雞湯”:“會不會熬不知道,但好像大家都挺愛喝的。”
他點點頭,把臉貼在我的胳膊上,似乎燒能退得快一點兒:“你做的我都喜歡。”
我估計是被他傳染了,臉騰地紅起來。
第二天,Matthew活蹦亂跳地來找我,大喊:“我的冰箱都空啦,快陪我去超市!”我一邊滿心嫌棄,他要冰箱做什么,還不都是我做菜;一邊揣測,他生病一定是因為被中國菜養刁了胃,吃不慣法棍奶酪了。
我依然陪他去了超市,而且這次比哪一次都認真。我帶他去蔬菜區,認真教他,只有長形綠葉的白菜才是中國白菜,比一大顆的法國卷心菜更好吃;圓粒的糯米煮熟了很黏,其他快熟米只能做飯不能熬粥……他聽了兩句就不耐煩地擺擺手:“太多啦,我記不住。”又一臉傻笑著環住我的肩膀,“我不是有個中國廚娘嘛!”
“是呀。”我假裝低頭去挑土豆,“可是我下周就要回國了呀。”
4
離開的時候,Matthew送我上火車。我心里默念了無數遍“Jet’aime”(我愛你),最終還是被中國式的矜持堵在嘴邊。
他塞給我一個小盒子,叫我回國后再打開。我卻按捺不住,火車一開動就拆開了包裝——是一個小小的鑰匙鏈,拴著一個微縮版的煙霧報警器,一摁就嗶嗶響起來。
那小小的警報聲立刻將我帶回到半年前的那天。報警器響得滿樓皆知,我端著一盆水,撞見狼狽不堪的他。
人們總說“唯美食與愛不可辜負”,但人生就像一場匆匆的旅行,怎會總如故事般兩全?
認真愛,用心體味,便不算辜負美好的邂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