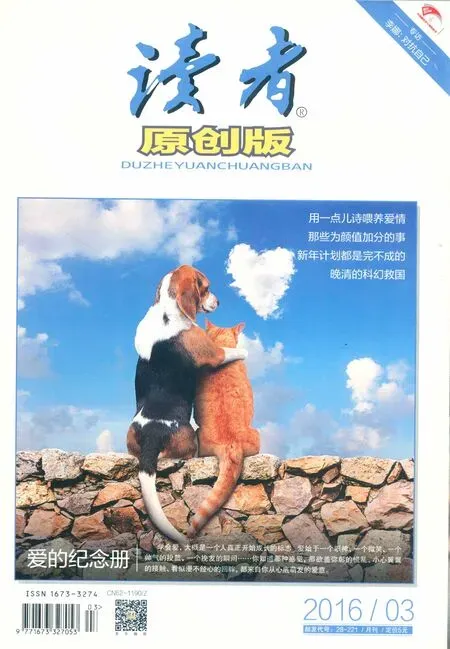夏令時
文_韓雅暉
?
夏令時
文_韓雅暉

一
穿過一片擺放著若干個廢棄鍋爐的土地,迎面是幾棵細瘦的松樹,一旁有三個碩大的水泥管呈“品”字形堆放。站在水泥管上眺望,能看到一片灰色磚墻的老式居民樓,與總是飛揚著塵土的道路連成一片,骯臟、陳舊,怎么看也不討人喜歡,這里就是我和姜飛一起長大的地方。
我和姜飛同是“70后”,他比我大3歲。我們是死黨,是那種蹲廁所都要勾肩搭背的鐵哥們兒。與我相比,姜飛膽子大、性子硬,從小就是個敢想敢干的狠角色。他爸爸是工廠里的車床維修工,脾氣暴躁,思想傳統(tǒng),教育孩子的方式就一個字——打。犯錯必打,每打必狠,越哭越打。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孩子沒幾個嬌生慣養(yǎng)的,然而論起挨打的頻率、時長,特別是挨打后的身心恢復能力,我們那一撥兒誰也比不上姜飛,所以,他是大院里的孩子王。
1986年,北京實行夏令時,那一年我倆還在上小學,并不能理解為什么要把時鐘撥快一小時,只是覺得這件事相當刺激。在那個剛剛入春的夜晚,我們并排坐在水泥管上,頭挨頭盯著姜飛從家里偷出來的老式上海牌手表,仿佛在進行某種宗教儀式,肅穆、虔誠,充滿敬畏。
“開始吧。”我催促道。
可是,由誰來執(zhí)行這項神圣的任務呢?我知道姜飛為拿出這塊手表所冒的風險,于情于理,這任務都應該由他來完成。然而,姜飛猶豫了一下,把表遞給了我,說:“你來吧。”
那塊表握在手里沉甸甸的,表盤上有好幾處清晰的劃痕。我輕輕拔起表盤旁的旋鈕,緩緩撥動,分針轉了一圈,停下,再用力按下旋鈕,表發(fā)出一聲脆響。我們不約而同地呼出一口氣,又不約而同地抬頭望向黑沉沉的天空,四周的一切依舊默然不動,但我們都相信,這世界已經被我們改變了。
當夏令時默默輪轉到第三個年頭時,姜飛攤上事了。那年他上初二,因為勇斗校外不良少年,失手打傷了對方,賠了一大筆醫(yī)藥費,還被學校記過處分。姜飛爸爸盛怒之下,一巴掌把他的右耳膜打穿孔,姜飛變成了弱聽。從此,姜飛與人說話總要偏著頭聆聽,倒給他略添了點兒可愛,不知算不算因禍得福。這場變故讓他休了半年學,之后,他的功課就再也跟不上了。中考前,他被學校勸說分流,進了一所技校,畢業(yè)后接了他爸爸的班,在工廠機床車間當學徒。而那年,我考上了市里的重點高中。
二
我所在的高中常常補課到晚上,每晚往家走時,總會看到姜飛坐在路旁的水泥管上抽煙,那身影在如水的月光下鋪出一片落寞的黑,甚至連煙頭的明滅都給人一種憂郁的感覺。我走過去坐下,不必跟他寒暄或客套,也不必有熱烈的對話,很多時候我們就默默地看樹、看天,偶爾姜飛會哼起趙傳的歌,這時我就會與他合唱,聲音飆著升高,直到兩個人嗓子都啞掉。即便如此,姜飛也仍是一副郁郁寡歡的模樣。他這樣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很久,直到半年后的一個晚上,他說他交了個女朋友,是廠里的技術員,大學生。
這之后不久,我就見到了姜飛的女朋友董欣華,準確地說,是他正在追的女性朋友。董欣華的相貌并不出眾,說話細聲細氣的。我們仨在王府井附近閑逛,然后坐在路邊的冷飲店喝酸奶閑聊。姜飛的臉上一直掛著笑容,點頭如雞啄碎米似的。只是在董欣華轉頭看街景時,他會迅速湊到我耳旁問:“喝第一口酸奶時,她說了什么?”或是:“她撓臉時笑著說的那句話是什么?”這讓我不得不全神貫注于他們的對話——大部分時間里,董欣華在說工廠里的科技改革,而姜飛除了評價食堂伙食,就是分析勞保用品的優(yōu)劣。
回家的路上,我勸姜飛要多看書來提高檔次,否則他跟董欣華遲早會上演現(xiàn)實版的《渴望》,而他的角色肯定不會是王滬生。姜飛側頭想了半天,然后狠狠地給了我一個大脖溜兒。幾天之后,他開始訂閱科普雜志《奧秘》。
三
20世紀90年代是錄音機和磁帶的天下,有段時間,姜飛經常找我錄磁帶——我家有一臺雙卡錄音機,能把他借來的正版錄音帶翻錄到另一盤磁帶上。姜飛找我錄磁帶的數(shù)量幾乎夠判刑了,問他原因,他說董欣華喜歡聽歌。每盤錄好的磁帶姜飛都要親自檢查,他把那只好耳朵貼在錄音機喇叭上,音量開大,半張著嘴,閉上一只眼睛認真地聽。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和他在院子里粘知了的情形,那時我總是站在樹下,由他爬上樹騎在一根枝杈上,用力伸胳膊去粘遠處的知了,他的臉漲得通紅,嘴微咧著,涎水像絲線一樣飄落下來……
接下來的任務是陪他去買隨身聽,毋庸置疑,是要送給董欣華的。我本不想去,卻沒禁住姜飛許下的大餐的誘惑。站在柜臺前的姜飛猶豫不決,左邊是國產的梅花牌,右邊是日產的愛華牌,后者售價高了一倍。我看他實在憋得難受,就湊到他耳邊說:“買個差不多的就行了。”他愣愣地看了看我,然后轉身買下了愛華。
我們坐在路邊的拉面攤上,我問姜飛這算不算重色輕友,說好的大餐成了一頓拉面。姜飛說不僅這頓,未來三個月他都得勒緊褲腰帶。我說,明明告訴你差不多就行,干嗎非要買貴的。姜飛偏著頭瞪了我半天,說他聽見的是“買差的可不行”,我當即失語。
姜飛將隨身聽在董欣華過生日的時候送了出去。這之后沒多久,他所在的工廠倒閉,被另一家大廠兼并了。那正是工廠倒閉大潮正式拉開序幕的一年,大量職工下崗回家看風景,姜飛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與他不同的是,董欣華因為有學歷、懂技術,順利進入新單位后榮升高級技術員,前途一片光明。
姜飛又恢復了默坐在水泥管上吸煙的狀態(tài),只是這次連歌都不唱了。我慫恿他向董欣華表白,我的理由是,既然她收下了隨身聽,就說明她沒把姜飛當外人。姜飛默默地抽完一支煙,然后告訴我,董欣華沒有白要隨身聽,她托人把錢轉給了自己。我說感情這種事就得有點兒死纏爛打的精神,他又沉默了很久,最后對我說,他發(fā)現(xiàn)自己那只好耳朵也出問題了,聽聲音越來越模糊,將來恐怕要聾。我們沉默良久,我問他恨不恨他爸爸,他再沒說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長大成人后我慢慢明白,人這輩子有很多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就像有些錯誤,我們根本不知道錯在哪里。
姜飛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后突然告訴我,他準備去南方跟著自己的叔叔跑運輸,算是個營生,如果能掙點兒錢,或許有機會把耳朵看好。“當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好。”他搓著腦門兒說,“也不知道能不能掙著錢。”我問他什么時候走,他說就這幾天,具體時間卻不告訴我。他說不要任何人送行,不喜歡搞得像生離死別似的。
當天晚上,我把姜飛叫到院子里的水泥管那兒,我遞給他一塊手表,是考上高中那年我爸送我的,不是什么名牌,但很新,很準時。“出門看時間,用得著。”我對他說,隨即又接道,“不是白給你的,回來還我。”他沒再推辭,接過表戴在了手腕上。我們沉默地坐著,抬頭看黑沉沉的天空,剛剛入春的天氣還是寒冷的,猛吸一口凜冽的空氣,再緩緩地吐出,一團似霧似煙的白氣彌漫在空中,像夢境一樣。
很多年前我們做過一個夢,那時我們都覺得很美好。人生有很多美好并不在于事實如何,就像我們無論活得多么落魄,多么黑暗,都不應該忘記——我們相信自己曾經改變過世界。
圖/劉曦
- 讀者·原創(chuàng)版的其它文章
- 數(shù)字
- APP
- 八字和星座一樣,都是用來說拒絕的
- 評刊
- 我在尋找故事,故事也在找我
- 那場盛大的暗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