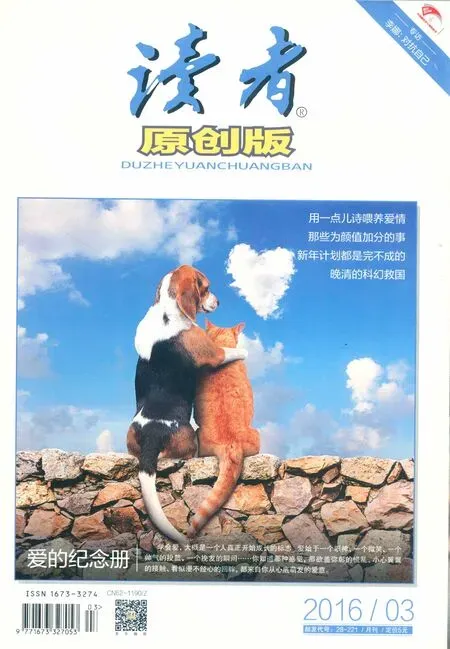你錯了
文_肖 遙
?
你錯了
文_肖遙

一
我一直是個乖順的孩子。小時候,我家樓上有一家臨時住戶,他家有兄弟兩個,跟我和我姐的年紀差不多,他們經常朝我家院子扔東西、吐唾沫,還對我們說臟話,可小孩子的恨意總是很短暫的,有時候,打鬧、挑釁其實是一種接近和交流的方式,于是我們很快被邀請上樓玩。
有一天,我們在他們家玩得正high,聽見我媽在樓下喊我們,聲音很嚴厲,跟平時我們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時的語氣完全不同,但我們正在興頭上,選擇屏蔽了她的呼喚。過了一小會兒,聽到有人敲門,門開了之后,我媽徑直進來,二話不說,擰著我倆的胳膊就把我們扭送回家。那天,我們上了一堂“政治課”,在此之前,我和我姐只有犯了重大錯誤才會被上課,有時是爸媽一起上,你一言我一語地曉以利害,苦口婆心。有時是給姐姐上,我旁聽,名曰“殺雞給猴看”。“猴”沒怎樣,“雞”反正嚇得夠嗆。
在所有令人緊張的“政治課”里,這節課令我印象最為深刻,因為我媽的措辭很嚴厲,讓我感覺到,自己和樓上的小男孩玩這事并非我想的那樣簡單,我可能攤上大事了。現在想來,媽媽數落我的大意是,他們沒教養,和那種孩子玩是墮落。我頭一次有一種羞恥感,這讓我覺得自己哪里被揭開撕破了,這種疼痛,到現在還會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所有媽媽都會如此教孩子——你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大人的怒氣通常會令小孩無比困惑:我這么做,并不是我故意要打破禁忌,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禁忌。即便知道了,我是不是還應該了解,為什么這事不許做?能不能用我能夠聽懂的話,情緒和緩地告訴我為什么不可以,做了的后果是什么?而你說的后果,我未必會同意,所以,我有實踐的權利,直到我自己認識到的確如此,或者并不應該如此。然而,如果真的這么“頂嘴”了,我媽會認為這是無禮的行為,作為孩子,難道不應該像軍人一樣,以服從為天職嗎?
二
青少年時期,我有個同學外號叫彈簧,常給我寫信,貌似有點兒表白的意思。其實,現在想來,這個同學本身就有點兒賈寶玉的氣質,對誰都特別深情、多情。我那年轉學后,跟別的同學都不聯系了,只有他每年給我寄明信片、寫信,也許因為距離產生美,他寄來的信就有了點兒花前月下的意思。這種情緒,將我換成任何與他相熟的女生,都有可能產生,而這些既羞怯又做作的措辭,也是任何一個維特式少年都可能寫出來的。那個年齡,剛剛悟到美感和詩意,又不怎么會抒發,也沒人可以抒發,就找個和自己有距離的人,比如給像我這樣轉學了的女同學寫信寫詩什么的,因為至少我不可能當面嘲笑他,所以給我寫信是安全的,總比給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寫信少點兒尷尬。
糟糕的是,我媽知道了,又給我上了一課。這堂“政治課”帶給我的恥辱,比小時候的那次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差點兒去找彈簧打一架——沒事寫什么信,又沒做啥,也不打算做啥,彼此都鬼鬼祟祟的,從此一想起這個人就別別扭扭的。可我當時沒這勇氣,只是覺得自己很丟人,盡管沒人知道,可自己很鄙視自己,卻又不知到底哪里錯了。這種羞恥感與學習成績不好的那種羞恥感不同,成績不好那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但這種事,咋努力?難道努力把自己弄得邋遢一些,愚蠢一些,丑一些?
三
我不知道孩子長大后特別想離開家的愿望,是不是都出于這種不斷被喚醒的羞恥感,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媽這么喜歡喚醒人的羞恥感。有時她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臉色,比如我早上不起床,她不會叫我,她只會把門推開,使勁拖地,拖把重重蹭在地板上的聲音就像在說:“瞧瞧,我伺候著你,給你打掃衛生,給你準備早點,你還不起來,好意思嗎?”
久而久之,我能很準確地辨別我媽臉色的級別,比如她粗暴且比平時更匆忙地刷碗、水聲很大地洗衣服,表示她已經開始不高興了,就像已經多云的天氣;若我再沒眼色,天氣就要轉陰了;如果再不長眼或因為緊張做錯了事,就等著暴風雨吧!其實在清晨的半夢半醒之間,一聽到拖地或開門的聲音,我慵懶的神經就像上了發條,立馬飛快地彈跳起來,之所以身體沒有跟著跳起來,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晚起”這個錯誤,同時還不想太早面對她陰沉的臉色。
如今的我覺得,世界上最難看的,是一張拉長的臭臉,它從來不告訴你做錯了什么,想讓你做什么,不喜歡你做了什么,而是天經地義地表達著,你就是錯了,至于哪兒錯了,自己猜去吧!
這些拉長的臭臉,成了我判斷人的標準之一,有時候我不小心看到這么一張臭臉,就趕緊后退三步,轉過身去,飛似的,能逃多遠逃多遠。
長大以后,我媽就不太用擺臉色這個武器了。她不再擺臉,是因為她認為我在她的教導下,變成了有眼色且有責任心的人了,雖然我認為會看臉色和有責任心沒有半毛錢關系。
對于她這些想當然的認識,我并不認可。與其說是因為我長大了,會看臉色了,不如說是她的臉色不起作用了。
她還是會習慣性地在孩子們敲門后,打開門,看都不看一眼,扭頭沖到廚房里去,好像孩子的到來給她帶來了莫大的麻煩;在做飯時故意弄出很大的動靜,讓你覺得自己吃的每一口都是欠她的。
總之,在她眼里,你立馬就會變回小時候那個麻煩、不懂事的小孩。
比如,你剛剛坐在飯桌前,她就讓你去坐沙發,因為還沒開飯,別這么“嚴陣以待”;你剛在沙發上坐定,她又命令你站起來,讓你坐在凳子上,因為要準備吃飯了;吃飯時,你剛端起面前的碗,她就會讓你放下——“不是這碗,是那碗,這一碗是我的。”但我看不出來,這碗飯和那碗飯有多大差別,不都是一口鍋里出來的嗎?也許,她只是想用這種方式告訴你:你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