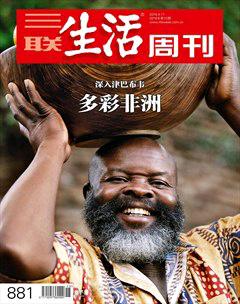沒有事件,就不存在建筑
鐘和晏
“建筑同時是空間、事件和運動,
我們對建筑的觀念取決于建筑中發生的活動,
空間在事件中轉化。”
當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3月中旬出現在天津民園體育場小劇場的“大師講堂”時,意料之中他戴著一條鮮亮的紅色圍巾,猶如巴黎的拉·維萊特公園里那些小建筑物奪目的紅色。多年以來,黑色西裝加上紅圍巾已經是屈米公共場合的標志性服飾。他確實說過,當他贏得職業生涯第一個國際競賽拉·維萊特公園項目時,他佩戴了一條紅圍巾。
他也說過:“紅不只是一種顏色。”他引用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一段話:“思想和現實達成的協議包括:如果我錯誤地說一個物體是紅的,然后一切都一樣,它仍然不是紅色的。”
屈米是今年UIA霍普杯國際大學生建筑設計競賽的評委會主席,始于2012年的競賽受國際建筑師協會UIA支持,由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和UED雜志主辦。每年,競賽評委會主席在“演變中的建筑”主題下擬定一個題目,今年屈米確定的題目是“演變中的建筑——概念和標示”。
“建筑幾乎都是用平面圖、剖面圖、立面圖、透視和軸測等視覺手段來表現,但如何表現建筑中的動態因素,比如空間中身體的運動?是否有新的標示模式適用于觸覺、聽覺、嗅覺甚至味覺等排除在建筑學話語之外的元素?”屈米進一步闡釋說,“競賽者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標示模式,一種引導方案發展的建筑概念。”
屈米在競賽中重申自己的建筑觀點:建筑首先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形式之前先要有概念,有概念支撐的自行車棚可以稱之為建筑,缺乏概念支撐的大教堂只能算作房屋。建筑對事件的講述不亞于對空間的講述,建筑不僅看它的外觀,更應該看它的作為。
屈米1944年出生于瑞士洛桑,父親讓·屈米是瑞士現代主義建筑的代表人物,也是國際建筑師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也許出于這一原因,起初他對文學、電影、哲學的興趣反而超過了建筑。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畢業之后,曾在倫敦AA建筑學院任教。
他形容自己的同時代建筑師是在建筑、權力、金錢的特殊關系中相當疲憊的一代,現代主義運動也已經失去了它的原創性和力量。所以,他希望花一些時間來面對“建筑是什么”的問題,將建筑從純粹的功能中區分出來,往往和一個概念或思想有關。
在建筑領域之外進行研究,以建筑師的視角置換和介入電影、藝術、哲學、文學等領域,也許是一種頗有收效的研究方法。建筑與小說、電影有著相似性,電影導演通過自己的靜態符號結構方式,以時間來描述運動。電影劇本就像建筑空間,建立起個別事件或序列的假想情境,描繪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場地是一條街道,街道的空間就被發生在大街上的事件所定義。
“我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名建筑師,我要編寫的是各種預設了潛在事件的程序化劇本。”屈米回憶說。
為了研究電影對事件、空間及運動的記錄方法,他曾經從電影《弗蘭肯斯坦博士》中選取博士與怪獸搏斗的畫面。例如,先畫出與博士和怪獸的打斗動作一致的箭頭,固定箭頭坐標,把這些運動的矢量轉換成立方體,最后得到的結果就是“打斗的空間”了。
歷時五年的研究成果《曼哈頓手稿》發表于上世紀70年代末,四個組成章節分別與公園、高樓、街道、街區四種城市原型有關。類似電影的主人公,它們在敘事中扮演著角色。
第一部分從紐約中央公園的一起謀殺案開始,追捕兇手的線索與建筑交織在一起,三張并置的圖片代表空間、事件、運動三種符號。這就像分鏡頭劇本,它們的即時性與電影的相似,一幕幕鏡頭組成和發展了空間。如果把重復、疊加、扭曲以及改變畫面比例等電影技巧應用到建筑中,空間元素就會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比例。
《曼哈頓手稿》既不是真正的設計,也不是純粹的幻想,而是圖片式的建筑理論繪本。在書中,屈米論證了空間、事件和運動三個層面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筑同時是空間、事件和運動,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定義了建筑。所以,并不存在所謂的中立空間,如果建筑物里沒有事件發生,建筑就不存在,我們對建筑的觀念取決于建筑中發生的活動,空間在事件中轉化。”
羅蘭·巴特在1966年的短文《敘事文本結構分析導論》中,對文學序列的定義是“由孤立聯系結合而成的符合邏輯順序的核心體系”。他論述存在著閉合或開放的序列:“當序列的某一條件沒有獨立的前項時,它是開放的;當它的某一條件缺少后續結果時,它是閉合的。”
供人居住的建筑中同樣包含著敘事序列,突發事件、活動、插曲等疊加在固定的空間序列上。空間與事件之間、形式與功能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應關系?兩個系統能夠彼此吸引和激發嗎?屈米進一步提出疑問,是否存在建筑敘事學?如果建筑敘事學與文學敘事學相互對應,空間和話語符號有交集嗎?
當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時,曾經給學生布置了名為“喬伊斯花園”的設計作業,隱約基于喬伊斯·詹姆斯的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為倫敦科文特花園設計一系列實驗性的方案。《芬尼根的守靈夜》沒有試圖化解由于不同文本疊置而產生的差異,而是鼓勵相反的甚至相互沖突的邏輯。
他從倫敦的地形測量圖著手,將坐標的十字交叉點連成網格,每個學生以網格中的一個點作為項目地點。屈米自己也圍繞網格,設計了一系列重復的建筑物。正是這一“喬伊斯花園”的點格概念,幾年后被用在巴黎拉·維萊特公園的方案中。
類似從純粹數學向應用數學轉變,經過十幾年建筑理論研究之后,占地760畝的巴黎拉·維萊特公園是屈米建筑師生涯中第一個真正建造的項目,也是他第一次參加國際建筑競賽,并從472名競爭者中勝出。
這座不同尋常的“21世紀的城市公園”舊址是19世紀的屠宰場,屬于法國政府大都市計劃的一部分,從1983到1998年15年間,除了總體規劃外,還建造了25座建筑物,修建園林景觀、步行長廊、橋梁等。屈米當時對建筑法規等還知之甚少,他說:“正是我的無知和天真,幫助我跨越了種種經濟上和建造上的困難。”
在這里,點格法的策略是保留場地上的原有結構,分配電影院、畫廊、酒店等建筑物。總共26座邊長12米的立方體鋼結構小建筑,大多數包含網格結構、立體外殼和坡道式的運動矢量,被漆成耀眼奪目的大紅色,試圖通過非連續性的重復出現,將公園和城市連為一體。
拉·維萊特公園證明了可以不訴諸組合、等級、秩序等傳統規則,建造一個既復雜又靈活系統的可能性。就像愛森斯坦蒙太奇電影中不同形象的疊置,拉·維萊特公園體現著分裂或斷層概念,依賴點、線、面三個特定系統的綜合,它們相互重疊,包含功能活動的點系統,把人的活動導入公園的線性系統以及一系列平面化的空間系統。
圖爾昆勒·弗萊斯諾當代藝術中心屬于改建項目,原址是一處建于上世紀20年代的廢置休閑運動中心,位于法國南部工業小城圖爾昆。老建筑最高部分達到15米,里面有電影院、舞廳、滑冰場和跑馬場等,它需要被改造成集展覽、電影、表演、影像制作、多媒體為一體的跨領域綜合性建筑。
屈米為瑞士蘿實國際學校設計的表演藝術中心
如果不進行新設計而保留原本要拆除的老建筑,結果會怎樣?如何在新舊結構中同時插入一個原創程序?如何在建筑元素的一致性和功能性之間進行協調?
這一次,屈米的并置、拼貼和蒙太奇手法是保留原有建筑,在舊屋頂上加一個現代化的新屋頂。這樣做既保護了原有的結構,又可以加入電暖、空調、通風等現代設備。新屋頂疊置在舊屋頂上,中間夾層設置斜坡和走道,來激活這一夾縫空間。
曾經有人問戈達爾:“導演,您拍攝的電影確實有開頭、中間和結尾嗎?”戈達爾回答:“是的,但是順序不一定如此。”屈米認為,對建筑的不同部分而言也是如此。“建筑師先生,您蓋的大樓有地基、外墻和屋頂嗎?”“是的,但是順序不一定如此。”
藝術中心的夾層變成了基礎,它作為一個新的平面,起著連接上下元素的作用。把一個新屋頂疊置在舊屋頂之上,既是蒙太奇手法也是一種清晰的概念策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滿足新的功能需求。
57歲那年,屈米贏得了希臘雅典新衛城博物館的設計競賽,這可能是全世界任何一位著名建筑師夢寐以求但又望之卻步的項目。作為希臘的神圣象征,帕特農神廟這座公元前5世紀供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大理石廟宇形式完美,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主要的單體建筑之一。博物館場地位于帕特農神廟的視域之內,幾乎不到305米遠,怎樣處理這種關系并把它表現在設計中?
除了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衛城博物館還牽涉到一些非同尋常的限制因素。這里是地震活躍地帶,博物館底部就是占地4600平方米的考古現場,考古學家正在那里持續發掘1500多年前的城墻和城市遺跡。建筑師能夠從社會、法規、歷史等多重限制中,找到一種包羅矛盾差異的概念嗎?
屈米把他的設計定義為“精心構思的簡單性”,博物館由三個簡單明晰的部分組成,建在考古遺跡上的建筑被抬高,由不規則的混凝土立柱支撐,為了避免觸及下方古城的肌理,每根柱子都仔細定位,透過地面的矩形透明玻璃,能看到下面的考古遺跡場地。
中間一層是大約7.5米高的古文物展廊,用于展示古希臘、古羅馬等幾千件相對普通的藏品,東西立面安裝了不銹鋼鍍層的側翼,保護建筑和藏品不受日光灼曬。最頂端由透明玻璃圍合成頂層展廊,與帕特農神廟遙遙相對,陳列的是帕特農神廟中的大理石石雕及雕塑珍品。
除了混凝土、鋼和大理石的材料,整座博物館沒有任何裝飾。但是,又有什么裝飾能與古希臘雕塑媲美?
博物館的主體部分是東西向的,頂層的矩形展廊相對中間部分和底層卻旋轉了33度。屈米解釋說:“有人認為這樣做,是因為我是一名解構主義者,事實并非如此。下面兩部分的朝向由街道網格決定,而頂層展廊則在方位上與對面的帕特農神廟保持平行,游客在展廊里面可以同時看到神廟中的石雕和對面的帕特農神廟,某種程度上使得三角墻雕塑如原地一般,沐浴在衛城的陽光下。”
一個頗有意趣的巧合是,早年屈米的建筑理論研究著迷于蘇聯早期先鋒派導演愛森斯坦的蒙太奇電影,而愛森斯坦曾經用雅典衛城作為例子,解釋建筑教會了他如何制作電影。他在衛城建筑中徜徉,注意到帕特農神廟在他右邊,丟失的雅典娜雕像基座位于中央,伊瑞克提翁神殿在他的左邊。
新衛城博物館展廊中的古希臘雕塑?
愛森斯坦1937年在《蒙太奇與建筑》中寫道:“希臘人為我們留下了鏡頭設計、切換和長度的典范,雅典衛城可以稱得上是最完美的古代影片之一,很難想象存在著比其結構和順序更加精妙的蒙太奇序列了。”
一直以來,屈米被視為他那一代人中理論成就最高的建筑師,“建筑是概念的實體化”,他的每一次建造都在尋求內在一致的策略以及清晰表達概念的方法。但是涉及到當代城市建設,他認為建筑師在過去15到20年間最激烈的城市化進程中,為今天或明天的城市設計時遭遇了全然失敗。他說:“我認為我們這一代建筑師都應該為此負責,全世界幾百個正在建設的新興城市中,你看不到深入的思考和客觀意義上的實踐。它們看起來都如出一轍,幾乎從中學習不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