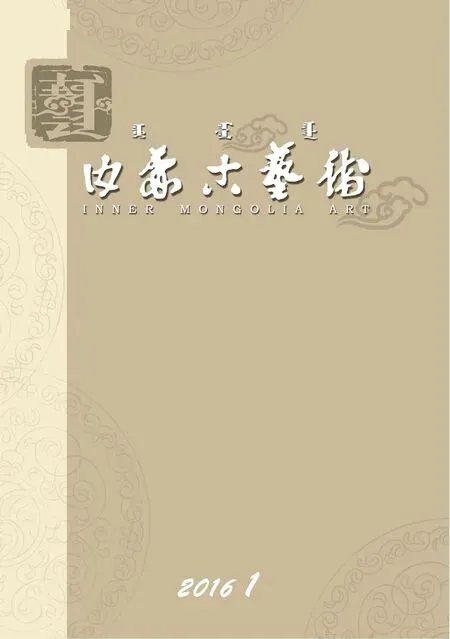論蒙古族神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質
王憲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00)
論蒙古族神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質
王憲昭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00)
神話是人類的口頭傳統,是早期的語言藝術,也是一種綜合性藝術。神話作為人類早期觀察世界、認知世界和反映世界的最經典的文化產品,具有跨文化、跨學科的性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具有其他任何一種文體所難以替代的作用。蒙古族神話作為蒙古族先民生產生活中通過想象或聯想形成的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文化表述,涉及世界萬物的產生、人類與族體的起源、動植物特征的來歷、民間習俗的形成等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問題,成為人們了解蒙古族早期文化的百科全書。因此,蒙古族神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性質是不言而喻的。
一、蒙古族神話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豐富類型
201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是我國關于非遺的首部法律。該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一)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二)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三)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四)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五)傳統體育和游藝;(六)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據此,蒙古族神話應歸屬于第一項的“傳統口頭文學”,同時又與其他類型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從目前見到的蒙古族神話文本看,具有極其豐富的類型。如關于世界產生的創世神話數量眾多,描述的具體創世方式繁多不一。其中,《天地之形成》[1]中說,宇宙在長時間胎動中生出了黑白和清濁,天地便在這樣的混沌世界中形成;《外相世界由三壇而定》中敘述了“風”“水”“土”在世界產生中的作用,解釋了“外部世界”與“內部生靈”的關系;《麥德爾娘娘開天辟地》中說,麥德爾娘娘在大水中馳騁,生出天地、日月、星辰、云雨;《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中說,最早的世界是一片大水,釋迦牟尼把土撒在巨龜身上造出了今天的世界,等等。這類神話不僅產生時間早,流傳時間長,傳播地域廣,而且表現出原始思維的特點,滲透著早期的哲學觀念、宗教信仰,對后世文化的形成影響深遠。
蒙古族大量的英雄與征戰神話同樣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眾多類型。如《天神之戰》,描述了天神派格斯爾·博格多下凡到地上征服魔王、鏟除蟒古思的征戰情形。《烏恩戰妖龍》《烏恩射太陽》《額爾黑莫日根射日》《獵人海力布》《英雄當德巴特爾》《阿勒坦·沙蓋父子戰多頭惡魔》等都以宏大的敘事頌揚了不同時代或不同身份的草原英雄勇猛無畏、懲惡揚善、敢于犧牲的優秀品質和不凡業績。再如,在蒙古族民間廣泛流傳的闡釋自然現象與動植物特征的神話。像《蜘蛛吃日月》中說,一年一次的月食是因為蜘蛛吃月亮形成的;《日食和月食的由來》中說,妖魔吞食日月造成了日全食和月全食;《烏龜馱地球》中說,地震源于馱負大地的烏龜活動身體;《谷子的來歷》中說,燕子給人間帶來了谷種;《冬夏交替是怎么來的》則關注了季節與人類活動的關系,等等。這些神話關于自然現象的解釋表面看有杜撰之嫌,但卻將人類生存的善惡是非融入其中,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先民自覺認識世界、思考生活的積極態度和探索精神。
二、蒙古族神話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態特點
蒙古族神話的產生具有多源性,在其漫長的傳承過程中會發生數量的變化和敘事內容的變異,其中既有神話新母題的出現,也有一些舊母題的消失。從目前留存的內蒙古神話口傳文本與書寫文本兩種主要形態看,表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神話原型與母題的古老性。所謂“神話原型”主要指神話中所塑造的具有民族記憶和原始經驗性質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是可以考察的人類文化敘事中較早出現的觀念或形象。“神話母題”則是神話敘事過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相對于“原型”而言更為靈活和自由,可以存在于神話流傳的各個時期。以蒙古族一些早期部族的族源神話為例,如作為杜爾伯特部落的祖先神話之一的《天女之惠》中敘述,一位年輕獵人在山頂湖岸套住一個天女,結婚生下的一個男孩長大后成為綽羅斯部族的首領和祖先;另一篇名為《綽羅斯準噶爾的起源》(又譯為《錯羅斯的傳說》)的神話則說,一個獵手在一棵大樹的瘤洞中發現一個男嬰,男嬰長大后被推為首領,他的子孫不斷繁衍,發展成為綽羅斯部族。兩篇神話都是敘述綽羅斯部族的起源,但前者突出的是人與天女的關系,意在強調部族祖先的神性;后者則敘述祖先的“樹為母,鳥為父”,更為客觀地表現出始祖源于樹圖騰和鳥圖騰兩個氏族的婚姻結合。同樣,其他如《蒼狼與白鹿》《母雞綿羊》等神話都以圖騰時代的婚姻敘事為主體,描述了早期神話時代的社會事象,也反映出諸類神話母題在歷史文化記憶中的古老性。
二是神話母題的豐富性。從目前采集到的蒙古族神話看,幾乎涵蓋了世界的起源、神的起源、萬物的起源、人的起源、族的起源、自然現象起源、動植物起源、文化起源以及婚姻、戰爭、災難、巫術等所有可以羅列的神話母題類型。以人類起源神話母題為例,如《天地之形成》中說,天上的眾神給地上世界送來與天神一模一樣的人類,屬于“人從天降”母題;《天神造人》中說,天神騰格里用泥土捏出一些男人,屬于“天神造人”母題;《巴巴額吉造人》中說,創世神的母親用羊皮造人;《世界和人類的起源》中說,最早一對男女生的一個肉卵孵育出人類;《青蛙兒子》中說,青蛙變成人;《蒼狼與白鹿》中說狼與鹿結合繁衍蒙古人;《魯俄俄》中說,人與仙女結婚生人;《三個姑娘和天王的兒子》說牧女與天神結婚生人;《蒙古秘史》中說,乞顏部祖先源于感光生子。此外像《魚生祖先》《天鵝始祖》《公牛始祖》《山的兒子》等,都表現出人類起源母題的地域性差異和特定部族產生的多源性。
三是蒙古族神話傳承與保存中的碎片化。蒙古族神話與南方少數民族神話相比有所不同。南方民族由于聚居區人口相對稠密,同一地區民族成分的構成相對多樣化,并且稻作經濟為主體的生產方式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廣泛交流,這就導致每一個民族對民族自識的高度關注,往往以神話這種具有歷史記憶性質的“神圣性”教科書為依托,在重大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中會常常演述神話,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神話特別是“創世神話”敘事的完整性。對作為典型北方民族之一的蒙古族而言,神話傳承場域和敘事內容則相對分散。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總人口為5981840人,分布在我國的多個省市自治區,其中作為主要聚居區的內蒙古自治區面積達到118萬平方公里,由于開闊的草原文化導致的人口聚居地相對分散,這也導致神話流傳的板塊分割和碎片化的特點。特別是游牧的生產方式和遠征尚勇的文化傳統,使大量帶有一定歷史原型性質的英雄史詩和英雄傳說逐漸取代了以想象或虛構方式建立起來的神話系統。即使許多原始部族流傳到后世的神話,也往往帶有較強的區域特色。當然,蒙古族神話的碎片化現象并不是神話的消失,其中大量神話母題會借助于其他文類或文化載體得以保存下來。有些神話與佛經故事、薩滿神歌、民間說唱等結合在一起,有些附著在文化器物中,有些則融入民間祭天、祭火、祭敖包等民俗儀式中。目前許多列入蒙古族各層級非遺名錄的項目都與神話具有不解之緣,且不說突泉縣的《突泉傳說故事》、準格爾旗的《準格爾傳說故事》、敖漢旗《敖漢傳說故事》等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都具有神話母題,眾所周知《江格爾》《格斯爾》等蒙古族英雄史詩都無一例外地吸收了古代神話的經典母題。像江格爾可以進入七層地獄下的紅海底,會用神樹的寶葉救活戰友洪古爾,而洪古爾的未婚妻格蓮金娜能在丈夫危難之際變成一只天鵝出手相救。同樣,在描述格斯爾的出生方面,有的說他是天神騰格里兒子的轉世,有的說他是玉皇大帝次子,是威震十方的圣主。這些敘述直接把神話中的“三界相通”“神的變形”“圣主天降”等母題直接植入到史詩敘事中,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家喻戶曉的英雄。
三、蒙古族神話作為非遺的重要文化價值
蒙古族神話敘事的古老性與文化意蘊的豐富性決定了它的重要文化價值,許多神話深刻影響著蒙古族共同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甚至引導或規范著群體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乃至信仰。
首先,神話是保留蒙古族古老民族記憶的口碑史。國內外的學者對蒙古族的族源提出過不同的說法,諸如匈奴說、突厥說、東胡說、韃靼說、白狄說、蒙兀室韋說等。這從神話中的不同圖騰崇拜也可略見一斑,說明蒙古族與漢族以及其他民族一樣,在形成過程中吸納不同支系或部族的可能性。民族的產生、發展與演變的歷史一般會由集首領、巫師、藝人的傳承人通過具有神圣性的“神話”來記錄和傳承。有研究者認為:“歷史不是客觀經驗的賜予,歷史是神話。神話亦并非杜撰,神話是現實,只不過是在另一序列上,是比所謂客觀經驗的賜予更現實的現實。”[1]這一論斷較好地解釋了神話在許多民族歷史中的載體作用。有些神話還較具體地記錄了民族遷徙的軌跡,如流傳于吉林省前郭縣的《化鐵出山》中記載,以前蒙古部落與突厥部落爭戰時敗北,逃出兩男兩女在大山谷里結為夫妻生兒育女。當山谷難以容納日益增多的人畜時,老人就帶領大家砍樹為柴,用牛馬皮做成風箱,燒爆山石開辟了一條通向深山外部的路。從此蒙古人走出了峽谷和大森林,進入了廣闊肥美的大草原。這類神話保留了蒙古族從山林遷徙到草原的歷史。類似內容在波斯歷史學家拉施特的《額爾古涅·昆傳說》中也有記載,并指出時間發生的時間是約在成吉思汗出生前兩千年。[2]研究實踐表明,神話的“口碑史”傳承功能是其他文化遺產所難以替代的。
其次,神話是護佑草原文化生態的常青樹。草原文化是長期繁衍生息在草原地區的各民族包括歷史上的各族先民所創造的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并具有鮮明地域文化內涵的各類精神產品。對于蒙古族神話而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態為神話敘事打下深深的草原文化烙印,正如恩格斯提出的“在原始人看來自然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經歷的一定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3]蒙古族神話中恰恰凝聚著有關草原生態的最原始古樸自然觀,倡導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天人和諧觀。如神話《保牧樂》中說,一位名叫保如樂岱的單身牧羊老人,因智勝危害羊群的烏鴉、惡狼、紙鬼、黑龍等天帝的使者,最后被蒙古人普遍供奉為“牲畜保護神”;《吉雅其》神話說,勤勞的牧馬人吉雅其被人們當成牲畜保護神,而他的慈善的妻子則成為孩子們的保護神。這些神話把草原的保護者塑造成為蒙古人心目中與生活休戚相關的“神”,這些母題涵納著道德倫理和民俗信仰的正能量,在規范日常行為、調節人際關系中具有積極意義,對維護良好的自然生態和社會和諧同樣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他如《尋找仙丹神藥的狼》《長翅膀的神馬》《馬頭琴的來歷》《金鷹》《松、柏和麻黃為什么常青》等直接表達出草原風情,洋溢著“一草一木皆關情”的草原氣息。
第三,神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溯源的活化石。以往許多學者多把記錄在文字典籍中的人類文化敘事作為主流傳統即“大傳統”,卻往往忽視口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事實上,不僅人類的絕大多數歷史、文化觀念、傳統習俗均孕育、產生并流傳于無文字時代,并且直至當今絕大多數人對歷史和重大事件的認知仍來源于口耳之間,許多口耳相傳的神話母題已積淀為后世人類的生產生活習俗的潛意識。如蒙古族生產生活中常常把數字“九”作為吉祥美好的象征,這種普遍的審美情趣與神話中的“99尊騰格里”“九重天”“九層地”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目前許多被列為非遺的民俗活動,如果缺少神話的解讀也往往會影響內涵的發掘,如烏蘭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廟祭祀、烏拉特中旗的蒙古族剪胎發習俗、烏拉特中旗的蒙古族祝壽儀式、巴林右旗的翁根毛都祭祀等,皆有神話母題作為支撐。如新疆蒙古族在農歷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祖拉節之夜,各家點燃七盤自制的酥油燈,合家圍坐燈旁觀燈、向菩薩像、成吉思汗像磕頭求保佑。這種儀式包含著許多神話母題,如七盞燈象征的七星崇拜母題,祭菩薩像與帝王像既包含佛教神靈母題、祖先崇拜母題、文化英雄崇拜母題,也表現出佛教與民間信仰在蒙古族生活中的有機融合。很多情況下,只有從神話的視野對民間事象加以解讀分析,才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并從中得到優秀文化傳統的熏陶與滋養。
總之,蒙古族神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毋庸諱言,隨著當下生產方式現代化的推進和社會生活信息化的普及,諸如神話、史詩這類口頭文化的生存環境日趨脆弱,其敘事母題的傳承鏈也正走向斷裂的邊緣。這種現象一方面體現了經濟生活對文化形態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也應認識到,人類的今天并非與昨天毫無關聯,而是文化精神的一脈相承和延續。我們只有認識到神話的特質和對其研究保護的重要性,才能不斷發掘這些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代價值,使其在當今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中發揮出應有作用。
注釋:
[1]本文涉及的神話作品較多,具體出處可參見王憲昭《中國神話母題W編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及相關實例索引。本文不再一一標注。
[1][俄]別爾嘉耶夫著,張雅平譯:《歷史的意義》,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2][波斯]拉施特著,于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51-252頁.
[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