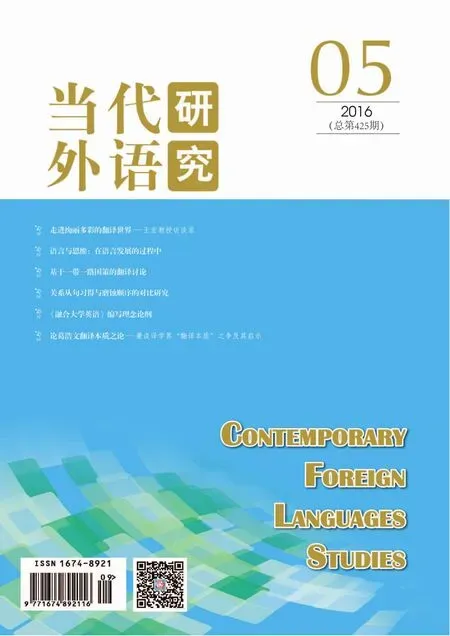走進絢麗多彩的翻譯世界
——王宏教授訪談錄
劉性峰 王 宏
(南京工程學院,南京,211167;蘇州大學,蘇州,215006)
?
走進絢麗多彩的翻譯世界
——王宏教授訪談錄
劉性峰王宏
(南京工程學院,南京,211167;蘇州大學,蘇州,215006)
本文是對王宏教授的訪談錄。訪談從王教授與翻譯的結緣談起,并結合其翻譯與治學的經歷,針對翻譯、翻譯研究、翻譯教學、典籍英譯和漢譯英能力等話題展開討論。這些深刻見解對當下的翻譯研究、典籍英譯,以及青年譯者和學者的成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翻譯,翻譯研究,翻譯教學,典籍英譯,漢譯英能力
劉性峰(以下簡稱“劉”):您好,王教授,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這次訪談。我們都知道,您在翻譯領域,尤其是在中國典籍英譯領域做出了很大貢獻,比如,您主持翻譯的多部中國典籍作品被《大中華文庫》收錄,有的還在國外出版,直接與海外讀者“見面”,這對探索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效傳播途徑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請問您是怎樣與翻譯結緣的?
王宏(以下簡稱“王”):我自幼喜愛文字,我母親是一家省級報社的編輯,一輩子做文字工作,可能我的基因里也有這偏好。我最早與翻譯結緣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我還是武漢大學英文系的一名研究生。有一天我去武大圖書館讀書,讀到一本英文原版書,題目是The Art of Being A Woman,當時就覺得書的選題很好。當讀到作者在“前言”里寫的一句話“The sole purpose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s to light the fire in the darkness”(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黑暗中點燃光明的火焰),青春年少的我更是有了一種沖動,想把全書譯成中文,讓更多的讀者讀到此書。于是我復印了全書并把前言、目錄和第一章譯成中文投寄給國內數家出版社。沒想到,果然有四川文藝出版社表示同意出版。我花了大概一年時間才譯完全書。后來該書取名《女人的奧秘》,于1988年正式出版。順便說一下,雖然出版社給的稿費只有每千字30元,但當時國內物價低,我得到的數千元稿費著實讓我興奮了好一陣子。從1988年到2000年,我陸續出版了九部譯作,多為古典文學作品英譯漢,比如《走進迷宮》、《死者為王》、《茅屋》、《大教堂》、《堅貞不屈的親王》、《布賴頓硬糖》、《金銀島》等。此時,翻譯仍是我的副業,我研究生學的專業是英國文學,后來去英國留學,學的是語言學。我曾在西南師范大學、寧波大學執教,教的課程都是文學和語言學。1996年我調入蘇州大學,仍主講《普通語言學》。
劉:那您是什么時候正式把翻譯作為您的專業的?
王:2002年,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為了加強學院的翻譯隊伍建設,把我正式調入翻譯系和翻譯研究所,翻譯才正式成為我的專業。我的興趣也轉向漢譯英,特別是蘇州地方文化英譯、中國典籍英譯和翻譯理論研究。我最早是與汪榕培教授一起從事蘇州地方文化系列英譯,如《吳歌精華》(2003)、《蘇州古典園林》(2004)、《昆曲精華》(2006)和《昆劇》(2004)。后來,從2004年到2012年,我參加了國家出版重大項目《大中華文庫》,相繼出版了中國典籍英譯作品《墨子》、《夢溪筆談》、《山海經》、《國語》和《明清小品文》等。
劉:您后來的翻譯作品都是漢譯英嗎?
王:不是。我依然從事英譯漢。漢譯英和英譯漢我都熱愛。從2006年到2016年期間,我出版的英譯漢作品有《變形記》(2006)、《辛普森夫人傳記》(2007)、《威廉王子的王妃》(2009)、《刺殺希特勒》(2009)、《我是麥莉》(2009)、《戈登·布朗:過去、現在和將來》(2009)、《民主與教育》(2012)、《人類的故事》(2013)、《民主與教育》(2015)、《房龍地理》(2016)。當然,翻譯成為我的專業以后,我更關注翻譯理論,結合所讀翻譯理論以及自己的翻譯實踐,有了一些自己對翻譯研究的看法和認識,發表了相關學術專著和論文。
劉:您剛才提到對于翻譯的看法。我們都知道,翻譯的屬性、種類和過程都異常復雜。理查茲(I.A.Richards)說過,翻譯“很可能是宇宙演化過程中迄今為止產生的最復雜的事件”。您既有豐富的翻譯實踐,又有深厚的理論涵養。您現在如何看待翻譯?
王:翻譯的確極為復雜。但就具有跨語言、跨文化屬性的語際翻譯而言,其復雜性就源自原文與譯文之間、譯文與譯文之間、作者、譯文發起者、譯者、譯文讀者和譯文審核者之間的多重需求和矛盾。要在諸多矛盾體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極為不易,實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劉:的確是這樣的。王教授,您曾多次提及“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這一提法比較新穎,能請您詳細談一下您的觀點嗎?
王:我曾把具有跨語言、跨文化屬性的翻譯行為細分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王宏 2007)。我提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更多的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意圖為起點,受譯文讀者需求、譯者翻譯目的、譯入語文化等所制約的語言轉換。這種翻譯要以原文為對照,受原文文本限制,這類譯文“既要經得起讀,又要經得起對”,如科技、法律文本的翻譯、參賽譯文等。“寬泛意義上的翻譯”更多的是以原文為參照,受贊助者、譯文讀者需求、譯者翻譯目的、譯入語文化等所制約的跨文化交際活動。與原文文本相比,此類翻譯在內容、長度、文體、語氣等都可能有相當的變異,如某些文學體裁、對外宣傳材料的翻譯。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劃分,是由于我看到譯界“文化學派”和“語言學派”的分歧多源于對翻譯屬性、范圍和過程等不同理解。譯界同仁都在談翻譯,而往往是各執一詞,所指各不相同。
劉:是不是可以這么認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側重于語言轉換的高度對等或相似,同時兼顧原作和作者的意圖、譯文讀者、翻譯目的與譯入語文化。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則以譯文讀者、翻譯目的以及譯入語文化為主要參照系,語言轉換可以有更大的靈活度。
王:是這樣的。
劉:您還提及要從哲學高度認識翻譯研究,您能否談一下為何要從哲學高度研究翻譯?以及如何認識翻譯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王:好的,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比較有意思,也比較有意義。其實,所有學科最終都需要上升到哲學層面進行認識,翻譯學也不例外。這要從哲學的主要問題談起,柏拉圖、奧威爾、笛卡爾和洪堡特等都有過疑問。柏拉圖曾發問:人為啥知道得那么多?奧威爾想知道,人為啥知道得那么少?笛卡爾則問道,我們怎樣解釋那些超越自身認識范圍的奧秘?洪堡特的疑問是:人的知識是怎樣構成的?柏拉圖和奧威爾的疑問看似對立,其實不然。前者是指人類的認知潛能是無限的,后者則指與浩瀚宇宙相比,人類的認知具有相對有限性。以上問題為我們研究翻譯提供了哲學理據,比如,翻譯的可譯性、不可譯性、翻譯的對等與差異等。關于如何從哲學的角度認識翻譯研究,這要從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方面展開。
本體論(ontology)一詞由17世紀的德國經院學者郭克蘭紐(Goclenius,1547~1628)首先使用。此詞由ont(vt)加上表示“學問”、“學說”的詞綴——ology構成,即是關于ont的學問。ont源出希臘文,是on(v)的變式,相當于英文的being;也就是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所說的“存在”。在古希臘羅馬哲學中,本體論主要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質。各派哲學家力圖把世界的存在歸結為某種物質的、精神的實體或某個抽象原則。認識論(epistemology)則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方法論(methodology)指導人們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概括地說,如果世界觀主要解決的是世界“是什么”的問題,方法論主要解決的就是“怎么辦”的問題。
劉:聽上去有些深奧!請您結合翻譯研究具體談一下好嗎?
王:好的。首先需要說明一下,翻譯本質屬性、研究對象、特點規律與學科歸屬的明確與認識是開展翻譯研究的基礎,也是進而確立翻譯研究獨立學科地位的前提,這些恰恰是本體論與認識論需要解答的問題。從另一方面來看,翻譯作為跨語言、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與實現形式,其目的是為了讓語言文化不同的雙方交流信息,溝通心靈,增進了解,促進進步,這就需要方法論提供相應的研究方法和實踐技巧。
何為翻譯研究本體論?我認為,翻譯之在即翻譯活動,翻譯活動即翻譯之在,這兩者原本等義。翻譯正是在這種特殊的人類“生命—精神”的活動中顯現其身。人類“生命—精神”的活動是翻譯作為一種對象存在的終極根據,對此所做的形而上學研究就是“翻譯研究本體論”。本體論的定位促使翻譯形成相應的研究譜系:如對翻譯所做的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文化學、語言符號學的跨學科研究(這些研究從不同學術視角指出了翻譯活動不同的存在本質)。我們還可轉入翻譯活動本身,關注其生成機制、操作表現、運作方式、過程效應及其價值意義等。因此,翻譯研究本體論的構建乃是把“跨語言、跨文化活動”作為翻譯生態的根本性存在,并由此形成豐富的“活動研究系列”,用以完成對于翻譯的最后體認。“何為譯?”是所有從事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我們認為,各種有目的的翻譯活動,各種形式的譯本(包括全譯、摘譯、節譯、編譯、改譯甚至偽譯)都可以成為翻譯研究的對象。翻譯研究范圍的擴大開拓了我們的研究視野,也加深了我們對翻譯本質和屬性的認識。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演出“何在譯、譯何為、為何譯、如何譯”等多個層面,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涉及翻譯研究的過程認識論、主體認識論、相應方法論、目的論與批評觀等。翻譯研究認識論主要圍繞能否認識翻譯以及如何認識翻譯與翻譯研究的問題而展開,涉及翻譯的研究對象、特點要求、原則標準與認識維度等。翻譯研究方法論則應為翻譯理論探索與翻譯實際工作的開展提供可供參考與借鑒的方法。翻譯研究目的論主要解答為何要開展翻譯與翻譯研究,為何需要翻譯的問題。
劉:您從哲學高度的闡釋使我們對翻譯和翻譯研究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您曾說過,翻譯研究的許多課題可圍繞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開展。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關系呢?
王: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是翻譯研究很好的切入點,究其實質,翻譯理論多是依據這個論題展開的,尤其是翻譯定義、翻譯策略、翻譯標準、翻譯批評等。許多翻譯理論家對原文與譯文的關系有過闡述,并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的理論:一種理論偏向于“相似說”,即譯文屈就于原文,以原文為主,考察譯文與它的相似度;另一種理論以描述翻譯學為代表,其研究偏重于目標文本及其在目標系統中的位置。Toury(1995:136)明確建議從譯文出發展開分析而不是從原文出發,并由此開辟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單純地比較不同的譯本,或者對譯本與目標系統中的非譯本進行比較。Toury這種同傳統研究正面抵觸之舉使他成了同時代驚世駭俗的革新者。
英國翻譯理論家Chesterman(1998:7-23)認為,可以從相似性(similarity)的角度來理解原文和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他提出了兩種相似性:第一種叫“發散式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他將其示意為:A → A’,A’’……。這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從源頭導向目標的方向性,就仿佛由父母遺傳給子女那樣,其中蘊含的因果關系是無法顛倒過來的。第二種相似被稱為 “聚合式相似(convergent similarity)”,Chesterman示意為:A ? B。它反映的是譯本接受者觀照翻譯的方式,接受者都期望在A中所尋求的東西在B中同樣能夠找到。“Friday the thirteenth”和“martes 13”的關系就屬于這種相似。
劉:除了相似之外,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是否還有對等和變異關系?
王:Kade在多年前就思考過對等問題。他認為,詞或詞組層級的對等有四種類型:“一對一(one-to-one)”,如固定術語的翻譯;“一對多(one-to-several)”,譯者須在若干備選方案之間進行選擇;“一對部分(one-to-part)”,即可用的等值對象只能達到局部的匹配;“一對零(one-to-none)”,譯者必須新創一個解決方案(杜撰新詞或者借用外語詞)。Kade將“一對一”的對等關系稱為“完全對等(total equivalence)”,他認為專業術語的翻譯是這類對等最典型的例子(以上轉引自Gentzler 2001: 67-68)。需要說明的是,Kade所說的完全對等所涉及的決策過程與其說同翻譯行為相關,不如說同術語學和措辭法相關。這種一對一的關系顯然是雙向的:我們可以將A語言譯入B語言再回譯成A語言,它與自然對等的理想相符。然而,一對多和一對部分的情況在實踐中具有明確的方向性,我們無法保證通過回譯能夠再回到最初的原點。顯然,對等理論均以兩種翻譯方式的對立為基礎,它體現的思維模式是二元對立的。
研究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必須要研究其彼此在意義上對等與差異,在形式和神韻上相似與變異。所謂意義對等,多數只能是相對而言。所謂形似,是指譯文的表達形式和手段與原文相似。所謂神似,是指譯文表達的風格、內涵、意境、氣勢、情調等與原文相似。對于如何處理形式和神韻的關系,古人早就表明各自不同的取向。范縝(約450~515)在《神滅論》中曾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西漢《淮南子》的“君形者論”則強調“神”對“形”的主宰作用,主張神貴于形,形受制于神。翻譯中要達到神形兼備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曾提出,在形神不沖突時,應首先考慮形似,神以形存;在形神沖突時,則需要舍形求神(王宏 2012a:xvi)。我認為,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有:意似形似神似(內容忠實、形式相似、效果對等)、意離形似神似(內容不忠實、形式相似、效果對等)、意似形離神離(內容忠實、形式不相似、效果不對等)。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劉:謝謝王教授,剛才您詳細談論了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令我受益匪淺。翻譯研究關注的另一個維度是否是譯者主體性?
王:翻譯研究除了關注原文與譯文、譯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之外,還需關注翻譯過程中諸者之間的關系和各自發揮的作用與影響。所謂諸者就是原作者、譯文發起者、譯者、譯文讀者和譯文審核者等。譯者無疑是翻譯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員。譯者主體性指譯者作為翻譯主體之一在尊重翻譯客體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和創造意識”。翻譯活動中涉及的人主要有三種: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原作者創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寫作主體;譯者創造了譯作,是翻譯的主體;譯文讀者閱讀、理解譯作并從中獲取自己期待的價值,他們是閱讀的主體。作為翻譯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譯者的主體性體現在對翻譯的總體把握和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上,包括對翻譯文本的選擇、對原作的理解和闡釋、語言轉換的藝術、翻譯目的的定位和由此帶來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的取舍等。譯者的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我們既要關注譯者在翻譯過程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也要關注譯者所受到的不利影響和制約。傳統翻譯研究只注重探索語言轉換層面的活動,認為翻譯沒有創造性,要求譯者對原作亦步亦趨,并對譯文中的“創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貶斥,致使譯者處于尷尬的地位。這導致譯者地位的邊緣化。美國翻譯理論家Venuti(1998:4)撰寫的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一書,就描述了當代英美譯者是如何受到學術界的藐視和出版商的剝削,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處于窘境。
我曾撰文指出,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方面,要作為肩負特殊使命的讀者去理解原作和原作者;另一方面,他又必須作為闡釋者,通過語言轉換,讓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獲得新的生命(王宏 2011)。由此看來,翻譯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結果,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譯者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有不少翻譯理論研究者對譯者的主體性加以關注,譯者主體性的受重視程度大大加強。
劉:是不是我們可以說,譯者主體性與您提出的“嚴格意義的翻譯”和“寬泛意義的翻譯”也有關聯?
王:譯者在從事嚴格意義的翻譯時,只能有限度地彰顯其主體性,有限度地去調控文本,比如,譯者可以決定譯文語氣的輕重、譯文的顯形與隱形、譯文詞語的選擇(褒貶)、譯文語域的選擇(雅俗)、譯文的歸化、異化或雜合化等。譯者還可以決定譯文的透明度、冗余度、結構、語域、褒貶等。只有在從事寬泛意義的翻譯時,譯者的主體性才能得到較充分發揮。從事嚴格意義的翻譯時,譯者需要盡量抵制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等對翻譯的操控,盡力向原文文本靠攏;從事寬泛意義的翻譯,譯者則需順應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等對翻譯的操控,與原文文本拉開距離。
劉:您能舉例說明嗎?
王:比如,《西游記》被亞瑟·韋利譯為《猴》(Monkey),于1942年由倫敦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該譯本在歐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曾多次再版。韋利實際上只選譯了原書的第1至第15回、第18至19回、第22回、第37至39回、第44至第49回、第98至100回,共30回。其譯文均與原文在內容、形式、功能和文體等方面有明顯的變異,可視為寬泛意義的翻譯。再比如,林紓自己不懂英文,他的小說翻譯都是先由一位懂英文的助手口述故事情節,再由他妙筆生花而成。
劉:通過您的闡釋,我們對“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與“寬泛意義上的翻譯”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王教授對翻譯教學有何看法,也請您談一下。
王:我認為,翻譯教學必須注重學生實際翻譯能力的提高。翻譯能力與雙語能力密切相關,但也有區別。學生對原文的理解錯誤以及譯文表達失誤均屬雙語能力不足,而不是真正的翻譯錯誤。學生對翻譯策略、原則、標準的應用不當,表達時的選擇不當才是翻譯錯誤。
劉:學生的翻譯能力是翻譯界比較關注的話題,在您看來,應該如何通過翻譯教學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呢?
王:是的,目前不少專家學者對翻譯專業(MTI)學生的翻譯能力表現出很大的擔憂。我們必須對MTI的翻譯教學進行反思和改革。我們(王宏、張玲 2016)提出,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改革。首先,必須改革教學方法,適應社會對職業翻譯人才的要求。其次,必須改革教學內容,變詞句對比為篇章分析,把教學視角從以句子為中心的翻譯模式轉移到語篇翻譯模式,注重培養學生對語篇整體把握的意識和能力。最后,必須重視網絡等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語料庫和翻譯軟件等現代信息技術的開發和運用給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帶來了挑戰和變化,必須做出調整順應這種變化。
劉:您提的這些建議很具啟發意義,值得高校相關部門和教師參考。我們還想請您談一下與中國典籍英譯相關的話題。能否請您就典籍英譯的定義、分類談談您的看法?
王:謝謝。關于中國典籍英譯的定義,我在2009年主編的《中國典籍英譯》一書中有過探討。我認為,“中國典籍”可界定為“中國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獻和書籍”。所謂重要文獻和書籍是指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典籍作品。這就要求我們在從事典籍英譯時,不但要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還要翻譯中國古典法律、醫藥、經濟、軍事、天文、地理等諸多方面的作品。中國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在中華民族悠久歷史長河里,其他少數民族也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擁有自己的典籍作品。因此,我們不僅要翻譯漢語典籍作品,也要翻譯其他少數民族典籍作品。唯有如此,才能稱得上完整地翻譯中國典籍作品。中國典籍英譯分類不一。根據原作的語言,可以分為漢語典籍英譯和其他少數民族典籍英譯;依據典籍內容,又可以分為文學典籍英譯、哲學典籍英譯、科技典籍英譯和其他題材的典籍英譯;根據翻譯方式,也可以分為典籍全譯本、典籍節譯本和典籍編譯本等。
劉: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典籍英譯可謂成績斐然,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您認為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如何解決?
王:對于中國典籍英譯存在的一些問題,我曾撰文進行專題討論。我認為,目前譯界學者典籍英譯的理論研究多為微觀層面,缺乏具有系統性的理論建構和整體觀照(王宏 2012b)。當然,近十年雖有典籍英譯方向的一些博士論文出版,但是數量仍然太少。典籍英譯的理論探討可以借鑒現有的翻譯理論、相關學科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但必須結合典籍英譯自身的屬性和規律展開。其次,就中國典籍的翻譯實踐而言,目前選材仍比較單一,譯者過多關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較少關注古代科技作品和少數民族的典籍作品。就出版發行來看,目前仍缺乏對外傳播的有效途徑,中國人自己翻譯的典籍作品絕大部分在國內出版,讀者對象多為國內讀者,這些譯作很少“走出國門”,多為“自產自銷”或“自產不銷”,鮮為國外讀者知曉。
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探索中國典籍英譯的對外傳播與接受的有效途徑,采取直接在海外出版發行的方式,或是國內出版社與海外出版社的聯姻,這對中國典籍作品能否走向海外有著重要影響。我翻譯的《夢溪筆談》和《明清小品文》就是由英國帕斯國際出版社購買版權,在海外成功出版發行。要符合國外出版社的出版要求,除了譯文必須是高質量,典籍的選材也非常重要。我翻譯的《夢溪筆談》、《明清小品文》、《墨子》和《國語》都是首次譯成英文。試想如果我去翻譯已經在海外有多個譯本的中國古典小說、詩歌、戲劇等,我的譯本就很難受到國外出版社的青睞了。
最后,我想談一下典籍英譯人才培養方面的問題。典籍英譯是一項高投入、低產出的事業。現在從事典籍英譯的譯者多為“老教授”,年輕譯者極少,這使得典籍英譯事業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建議有關部門大幅提高典籍英譯稿酬支付標準,高校職稱評定要認可高水平的典籍英譯譯作,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輕學子投身到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業中來。
劉:您提到的這些舉措如能落實,必將大大推動中國典籍英譯事業的發展。感謝您提出的寶貴建議!典籍英譯與漢譯英能力密切相關,我們還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漢譯英能力的?
王:譯界同仁楊曉榮(2002)、馬會娟和管興忠(2010)等曾就漢譯英能力進行過探討。我提出將漢譯英能力分為:(1)雙語能力(英語表達能力、漢語理解能力);(2)知識能力(百科知識、相關專業知識);(3)資料查詢能力(利用網絡資源查詢資料的能力);(4)翻譯技能(轉換能力、選擇能力、譯文修訂能力)(王宏 2012c)。英語表達能力具體分為:英語詞語搭配能力、英語造句能力、英語語篇能力。翻譯技能具體分為:轉換能力、選擇能力和譯文修訂能力。英語表達能力是從事漢譯英實踐的基石,轉換能力是漢譯英任務能否得以完成的條件。Pym(1992)曾將翻譯能力簡化為:(1)從一個原文生成為一系列譯文的能力;(2)從一系列譯文中選擇一個符合翻譯目的、適合特定讀者的譯文的能力。Pym對翻譯能力的描述對語言表達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作為非英語母語使用者來說,要具備這樣從一個原文生成為一系列譯文的能力絕非易事,要掌握從一系列譯文中選擇一個符合翻譯目的、適合特定讀者的譯文的能力更是難上加難。由此看來,漢譯英能力與英語表達能力、轉換能力和選擇能力密切相關。除了轉換能力和選擇能力,對譯文的修訂能力也是英譯文質量高低、得體與否的關鍵。
劉:通過您的闡述,我們對于漢譯英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看來要提高漢譯英能力,進而承擔中國典籍英譯的重任,非下苦功不可。
王:確實如此。翻譯的確非常辛苦。但正是由于人類語言、文化、思維、社會、歷史等的不同,我們才透過翻譯看到一個五彩繽紛、多姿多彩的人類社會。《圣經》(1611年欽定本)譯者在序言中對翻譯所做的一番形象比喻:“翻譯好似打開窗戶,讓陽光進入房間;翻譯好似撬開貝殼,讓寶物呈現眼前;翻譯好似拉開窗簾,讓圣潔之處得以展現;翻譯好似揭開井蓋,讓甘甜的水滋潤心田。”翻譯是如此的美好、崇高!我們唯有堅持包容、開放、合作、共生的態度才能更好地走進這如此絢麗多彩的翻譯世界,提升自我,惠及大眾。
劉:感謝王教授與我們分享這么多精彩內容!
王:謝謝你的采訪。
Chesterman,A.1998.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entzler,E.2001.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Pym,A.1992.Translation error analysis and the interface with language teaching [A].In C.Dollerup & A.Loggegaard.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Talent and Experience [C].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iamins.277-288.Toury,G.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Venuti,L.1998.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馬會娟、管興忠.2010.發展學習者的漢譯英能力[J].中國翻譯(5):39-44.
王宏、張玲.2016.中國專業翻譯學位教育:成績、問題與對策[J].上海翻譯(2):13-17.
王宏.2007.對當前翻譯研究幾個熱點問題的思考[J].上海翻譯(2):4-8.
王宏.2011.怎么譯:是操控,還是投降?[J].外國語(2):84-89.
王宏.2012a.走進絢麗多彩的翻譯世界[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王宏.2012b.漢英能力構成因素和發展層次[J].外語研究 (2):72-76.
王宏.2012c.中國典籍英譯:成績、問題及對策[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4):9-14.
楊曉榮.2002.漢英能力解析[J].中國翻譯(6):16-19.
(責任編輯管新潮)
劉性峰,南京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中國典籍英譯。電子郵箱:oliverliu@163.com
王宏,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中國典籍英譯。電子郵箱:hughwang116@163.com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于大中華文庫的中國典籍英譯翻譯策略研究”(編號13BYY034)以及2016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科技典籍英譯詮釋框架構建”(編號2016SJD740008)的資助。
H319
A
1674-8921-(2016)05-0001-05
編碼]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