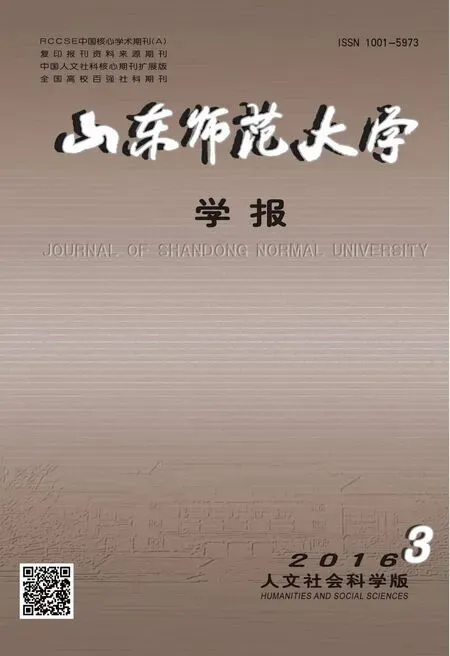靜穆之下:隱匿的狄奧尼索斯——溫克爾曼的《拉奧孔》*
高艷萍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01 )
?
靜穆之下:隱匿的狄奧尼索斯
——溫克爾曼的《拉奧孔》*
高艷萍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01 )
溫克爾曼關于拉奧孔群像的描述,其前后期有所不同。早期強調拉奧孔群像的靜穆的特征,后期則強調它的表現性。但兩者之中,皆可見溫克爾曼關于希臘精神的闡釋中隱而未現的狄奧尼索斯之維。早期溫克爾曼之所以無視拉奧孔群像的表現性特征,是因為他投身于啟蒙運動的德國對抗巴洛克的文化運動之中。
溫克爾曼;拉奧孔;狄奧尼索斯;尼采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8
在1755年出版于德累斯頓的《希臘美術模仿論》(Gedankenüberdie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中,溫克爾曼以“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形容《拉奧孔》*1506年1月14日,一個叫做Felix de Fredis的人在羅馬郊外發(fā)現一座雕像。據判斷,很可能是羅馬皇帝Titus(79-81A.D.)的地下浴室。發(fā)現之初,教皇朱利斯二世攜建筑師Giuliano di Sangallo和米開朗基羅到現場察看,認為正是普林尼所禮贊過的拉奧孔群像。溫克爾曼在德累斯頓初見其石膏復制,到了羅馬之后又見到青銅制作的羅馬復制品。群像(參圖1)的希臘特征。該命題常被視作溫克爾曼之希臘闡釋及其美學精神的特質所在,而事實卻不盡然。溫克爾曼在1764年的《古代藝術史》中,對《拉奧孔》的描敘已有明顯的變化。其一,溫克爾曼認為拉奧孔由于過度炫技而失去了崇高的情韻,從屬于優(yōu)美風格。當美的表象以過度精細的表達為特征,崇高感也就從中滑落。拉奧孔不再是崇高風格的代表。其二,拉奧孔被界定為經過理想化處理的自然肖像。“人們在拉奧孔中發(fā)現由理想和表現所裝飾過的自然。”*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66.其三,《希臘美術模仿論》強調拉奧孔抑制感受的激烈性而欲顯其靜穆的一面,《古代藝術史》則認為《拉奧孔》是表現性的:“拉奧孔表現的是自然間最高的悲哀”*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24.,揭示人的激情與巨大的痛苦。
凡此種種表明,溫克爾曼后期了然于《拉奧孔》的非靜穆特征,發(fā)現了其中關于痛苦的敘述以及自然主義的表現方式。而由此追溯并抉發(fā),可見溫克爾曼的希臘文化闡釋中隱而未現的狄奧尼索斯之維。
一、拉奧孔:作為表象的痛苦
任何一種對視覺作品以文字為媒介的描述都有可能導向新的暗示。溫克爾曼是從拉奧孔的姿勢和表情中讀出了希臘的精神方式——其情感如此敏感、深沉,從而必有痛苦的強烈表征,而其精神又如此超然、沉靜,從而又從痛苦中超逸出去。
“在強烈的痛苦(Leiden)之中……我們無需審視臉和其他部分,而只要在受著疼痛的、收縮的下腹就可以感受到身體的全部肌肉、肌腱以及整個人的疼痛(Schmerz)。”*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Berlin und Weimar:Aufbau-Verlag, 1982, pp.17-18.拉奧孔上身肌肉的收縮表示著遭到劇痛襲擊的跡象。在此,溫克爾曼的語調是暗示的、說服性的、雄辯的,提醒并說服讀者:拉奧孔在遭受痛苦。他同情式的精神方式以及文學性的渲染又使得其闡釋顯得無懈可擊:“拉奧孔受著苦,但是他如同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那樣受苦:他的困苦進入到我們的靈魂之中,但是我們也愿望,我們像這個崇高的人一樣,忍耐這困苦。”*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p.17-18.但是,身體之痛本身并未被具體呈現,而被表示、被指涉的僅僅是溫克爾曼對之的感受。在此,痛苦是作為認識拉奧孔的概念,而且痛苦更是一個中介。《希臘美術模仿論》對《拉奧孔》意在闡說超越痛苦的理性精神,作為障礙的痛苦是理性精神得以考驗自身存在的工具。痛苦的強度也正好用以標示超越的強度,痛苦無論多么強烈,卻是工具性的,是有待克服之物。
在《希臘美術模仿論》中,溫克爾曼對呈現于臉部的痛苦的描述較為簡略,他感興趣的是拉奧孔雕像臉部抵御痛苦的性質以及從中呈現的節(jié)制的心意狀態(tài),有意略去了臉部的痛苦反應的細節(jié)。溫氏又以一種否定性的方式提到尖叫。他說道:“他沒有像維吉爾在他的拉奧孔中所吟唱的那樣發(fā)出可怕的尖叫。嘴之張開在此是不允許的;不如說,這尖叫是一個驚恐的、不安的嘆息。”*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p.17-18.尖叫作為痛苦最強烈的表征,經溫克爾曼的修辭,轉化為與之相異的東西——嘆息。
溫克爾曼時而將拉奧孔比作菲勒克忒忒斯,時而與維吉爾筆下的拉奧孔對峙。無論是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維吉爾的拉奧孔,都在悲劇中、舞臺上、史詩中發(fā)出實質性的尖叫。尖叫是表達痛苦的前語言狀態(tài),它既是身體對痛苦的最直接的回應,本身又具有語言表現的樣態(tài)。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在蛇毒發(fā)作之時,大聲喊叫、咒罵自己的命運,間歇性地昏倒,而維吉爾的拉奧孔放縱哭喊:“他那可怕的呼叫聲直沖云霄,就像一頭神壇前的牛沒有被斧子砍中,它把斧子從頭上甩掉,逃跑時發(fā)出的吼聲。”*維吉爾:《埃涅阿斯紀》,楊周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第33頁。維吉爾這樣寫道:“兩條蛇就直奔拉奧孔而去;先是兩條蛇每條纏住拉奧孔的一個兒子,咬他們可憐的肢體,把他們吞吃掉;然后這兩條蛇把拉奧孔捉住,這時拉奧孔正拿著長矛來救兩個兒子,蛇用它們巨大的身軀把他纏住,攔腰纏了兩遭,它們的披著鱗甲的脊梁在拉奧孔的頸子上也繞了兩圈,它們的頭高高昂起,這時,拉奧孔掙扎著想用手解開蛇打的結,他頭上的彩帶沾滿了血污和黑色的蛇毒,同時他那可怕的呼叫聲直沖云霄,就像一頭神壇前的牛沒有被斧子砍中,它把斧子從頭上甩掉,逃跑時發(fā)出的吼聲。”這個無辜地成為諸神相爭的犧牲品的拉奧孔,其痛苦的丑態(tài)畢露。維吉爾是站在希臘人的角度看待此事,拉奧孔所遭之苦似罪有應得,故而并不憚于讓拉奧孔的形象受損。這其實就是溫克爾曼用其“嘆息”所暗示的身體之痛的極境的另一種表達。
到了《古代藝術史》,對于痛苦反應本身的描述占據了本位。在此,溫克爾曼幾乎是在投入地觀察一具受苦的人體,而不再受其有待發(fā)明的理念所左右。同樣是描述拉奧孔的身體部位的痛苦,《古代藝術史》的描述極其詳盡,雖然充滿同情,語調還是顯出冷靜、客觀與分析性:“拉奧孔是最強烈的痛苦的形象,這顯現于他的肌肉、腱肉、血管之中。因蛇的致死一咬,毒素進入血液,這引起了血液循環(huán)的最強烈刺激,身體的每一部分似乎因為痛苦而緊張著。”*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7.溫克爾曼描述了蛇的毒液在人體上發(fā)作的過程,描述中對肌肉、腱肉、血管的區(qū)分,其本身成為極度自然主義的描摹。此時被痛苦席卷的拉奧孔已不再莊嚴與靜穆,而仿佛是痛苦反應的分析樣本。
尤其是“這引起了血液循環(huán)的最強烈刺激”一句,更令人陡然間感到如此突兀,“血液循環(huán)”、“刺激”一詞的出現,分明是醫(yī)學話語的悄然闖入。這種話語與《希臘美術模仿論》的超越性的精神話語如此不同,一者是自然主義的,一者則是理想主義的、浪漫化的。
醫(yī)學話語與審美話語的結合也許不僅僅是巧合。有人指出,在18世紀,醫(yī)學話語和美學話語共同關注人體并且皆從人體的痛苦下手。*Simon Richter, Laocoon’s Body and the Aesthetics of Pain : Winckelmann, Lessing, Herder, Moritz, Goeth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33.但即便如此,醫(yī)學與美學之間的不同也仍然是明顯的:醫(yī)學揭示可怕的殘酷,而美學則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嘗試對痛苦進行轉喻(trope)。溫克爾曼曾一度立志醫(yī)學,在耶那大學修過醫(yī)學,應該熟悉名為《論人的身體的感受與刺激》(Departibusvorporishumanisensilibusetirritabilibus)的演說,其于1756年譯為德文。該文于1753年(《希臘美術模仿論》出版前兩年)出自一位卓有成就的德國生理學家哈雷(Albrecht von Haller)之手 (據稱, 哈雷之于生理學,相當于牛頓之于物理學領域),總結了幾百年來研究動物各部分如何對痛苦做出反應的實驗。
與此相類,《古代藝術史》中對《拉奧孔》的描述則如同是一樁有關人體如何對痛苦做出反應的研究。溫克爾曼周全地描寫了拉奧孔的臉部,包括上嘴唇、鼻孔、額頭、眉毛、眼皮等臉部各器官的反應:“拉奧孔的樣子是萬分凄楚,下唇沉重地垂著,上唇亦為痛苦所攪擾,有一種不自在所激動,又像是有一種不應當的、不值得的委曲,自然而然地向鼻子上翻去了,因此上唇見得厚重些,寬大些,而上仰的鼻孔,亦隨之特顯。在額下是痛苦與反抗的紋,……因為這時悲哀使眉毛上豎了,那種掙扎又迫得眼旁的筋肉下垂了,于是上眼皮緊縮起來,所以就被上面所聚集的筋肉遮蓋了。”*李長之:《李長之文集》(第10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4-175頁。Cf. 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p.324.在其“佛羅倫薩手稿”中,溫克爾曼更提到拉奧孔臉部因為痛苦而扭曲的鼻子:“臉部的鼻子在表現痛苦之時無法保持直的向上的表面。”*Fcited in John Harry North, Winckelmann’s “Philosophy of Art”:A Prelude to German Classicism,(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2002),p.131.溫克爾曼這種細致的描摹甚至引發(fā)過面相學家J.C.拉維特(Johann Caspar Lavater)的興趣。*Cf. Henry Hatfield,Winckelmann and his German Critics,1775-1781·A Prelude to the Classical Ag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1943 pp.109-110.
溫克爾曼認為,拉奧孔像兼有自然和理想的雙重摹寫,是“理想和表現所并裝飾過的自然”*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66。如果說,《希臘美術模仿論》重于其理想精神的摹寫,《古代藝術史》則多發(fā)掘其人類痛苦反應的自然主義描述。
二、隱匿的狄奧尼索斯
溫氏對痛苦及其痛苦表象具有高度的知覺力。當溫克爾曼描述拉奧孔遭受的痛苦時,幾乎觸及后來為尼采所開掘的希臘酒神的迷狂,但溫氏側身而過。
如果說尼采從悲劇中見到人類在悲劇命運中個體性消亡的過程,那么溫克爾曼的悲劇英雄卻在痛苦中經歷了個體化的最高階段,超越肉體痛苦的個體確立了理性主體,而這個主體一邊受苦,一邊對自己的命運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清晰的覺照。溫克爾曼的拉奧孔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如此。拉奧孔即便處于因肉身之痛而陷入自失的狀態(tài)中,仍保持著理性的內視,從而其外觀(Schein)得以保持平靜,靜穆的表象確立。《希臘美術模仿論》如此描述拉奧孔:“為了將這特別之處(即痛苦的表情)與靈魂的高貴結合在一起,藝術家賦予他一個動作,這動作是在這巨大的疼痛中最接近于寧靜的站相的”*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8.,“仿佛大海雖然表面多么狂濤洶涌,深處卻永遠駐留在寧靜之中”*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溫克爾曼的由拉奧孔所引申的“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的精神其實正與尼采所稱的阿波羅式的理想相關,亦接近叔本華的描述:孤獨的人平靜地置身于苦難世界之中,信賴個體化原理。
即便他在拉奧孔描述中清晰地指向自己的文化理想,赫爾德還是發(fā)現其中對痛苦與死亡的深刻覺知,并從中解讀出“我痛故我在”。布克哈特認為希臘人是對痛苦感受至深的民族。尼采認為希臘人又具有極強的悲劇意識。實際上,這幽暗而生動的部分的關注,并非完全從溫克爾曼的思想中缺席。
尼采在他的一份筆記中說道:“‘古典的’這一概念,當溫克爾曼和歌德形成它的時候,既無法解釋狄奧尼索斯因素,也不能將它從自身中排除出去。”*[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爾的根——尼采,國家社會主義和希臘人》,張志和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38頁。實際上,雖然對靜穆表象投入全部贊美,溫克爾曼并未對表象下面的洶涌視而不見,也未將這種質素從拉奧孔雕像的表征中排除出去。他在描寫《拉奧孔》時,以海作喻,寫道:“仿佛大海雖然表面多么狂濤洶涌,深處卻永遠停留在寧靜之中。”*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7.溫克爾曼對這洶涌的表面的描述,時而又以另一種描述出現:“拉奧孔的肌肉運動被推到了可能性的極限;它們如同山巒描畫自己,為了表達在憤怒和抵抗之中的極端的力。”*Johnann Winckelmann,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s. I&II, translated by G. Henry Lodge, Boston:James R. Osgood and Company,1880, p.338.
溫克爾曼未命名的大海的狂濤,像極了尼采酒神精神的洪波。同樣是以大海作喻,尼采寫道:“為了使形式在這種日神傾向中不致凝固為埃及式的僵硬和冷酷,為了在努力替單片波浪劃定其路徑和范圍時,整個大海不致靜死,酒神精神的洪波隨時重新摧毀日神‘意志’試圖用來片面規(guī)束希臘世界的一切小堤壩。”*[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1頁。溫克爾曼的“拉奧孔”以意志規(guī)束精神的堤壩,但溫克爾曼的希臘精神從未凝固為埃及式的僵硬和冷酷——這也是溫克爾曼本人所批判的——其從一開始就具有了狄奧尼索斯的生動有為。他這樣形容“拉奧孔”:“這靈魂是寧靜的,但同時又是生動有為的,是靜默的,同時又不是冷淡的或是昏沉的。”*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8.因此,既靜默又激烈的“拉奧孔”既具有尼采所言的阿波羅精神,也擁有狄奧尼索斯精神的質素。
實則,溫克爾曼從未視此靜穆超然的品質為希臘人的天然,而是一種屬于智慧的倫理特征。這種阿波羅精神是在與洶涌的情感的洪波的抗爭中掙得。溫克爾曼并非對幽暗的部分視而不見,而是未將之視為希臘人的本質構成。
三、何來靜穆?
正如《古代藝術史》所察見,拉奧孔雕像以精細的手法表現痛苦,而又極富動態(tài)和戲劇性,因此被后世稱作“希臘巴洛克”。那么,德累斯頓的溫克爾曼因何將其作為“靜穆”的集中表征?
現在,不妨回到溫克爾曼在德累斯頓的“大花園”(Gr?sser Garten)的場景。溫氏曾于此間盤桓。在其半暗半明的閣室中,雕像的細節(jié)幾乎難以被真正觀察到,但它足以喚起溫克爾曼的想象以及內藏于心的對古代希臘如同前生般的回憶。可以想見,在他或內視或向雕像周圍的空氣凝視的觀看中,溫克爾曼下意識里關于希臘文化的靜秘、單純、崇高的主要論點浮現了。于是,動蕩、激烈、掙扎的拉奧孔,繁復、精細、自然主義的拉奧孔,在他這里卻倒置般地成為了“靜穆”的集中表征。
溫克爾曼的這種潛意識來自于他早年的閱讀。充滿元音的希臘文曾一度占據著溫克爾曼全部的精神世界。溫克爾曼重荷馬而輕品達,喜愛索福克勒斯,熱愛柏拉圖和色諾芬,視希臘黃金時期的文化、哲學為最佳典范,他同樣心儀斯多亞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不同于同期法國人在希臘悲劇和荷馬史詩中看到殘酷、血腥,溫克爾曼從中發(fā)現的卻是一個光明、節(jié)制、靜穆的世界。荷馬在描寫一切混亂時卻依然讓明喻綻放的文本,其超然笑言、目光遍及一切物事的語調同樣征服了溫克爾曼。
更為關鍵的是,溫克爾曼從希臘藝術中拈出“靜穆”與“單純”,其實是他反對巴洛克的文化策略的一部分。雖然在18世紀中期,對巴洛克和羅可可的反抗已經在法國和意大利展開。羅馬地區(qū)的繪畫已開始從古典尋找資源,而法國似乎從未完全擁抱過巴洛克,在路易十四時期即已發(fā)展出自己的新古典主義形式,如普桑。溫克爾曼理應知道這些變化,然而,當時他所在的德國的薩克森,仍殘留著17世紀的巴洛克趣味。巴洛克藝術多追求自然主義的效果,以激情為表達內容。溫克爾曼對此屢有批評,在《希臘美術模仿論》中,以拉法奇(La Fage)的繪畫為例證,他嘲笑巴洛克藝術中的一切皆在動蕩。他希望引入古代希臘這巴洛克的“他者”,為自己的時代迎來一個莊重的藝術年代。
但略顯反諷的是,17世紀的巴洛克藝術家貝爾尼尼,卻是不折不扣的《拉奧孔》模仿者。他的《圣特雷薩》圣女的姿勢與表情與拉奧孔次子酷似,《月桂樹》的動蕩的姿態(tài)又與拉奧孔雕像整體的構圖近似,他的一些雕像造型甚至被稱為“基督教的拉奧孔”(christian Laocoon)。而從另一方面看,正是在這種顯見的裂縫之中,溫克爾曼試圖為巴洛克文化提供解毒劑的意圖才顯得更為昭著。有意或無意的誤認(misrecognition )正是其文化策略的詭計。
實際上,到了《古代藝術史》,溫克爾曼似乎發(fā)現了更完善的巴洛克的他者。這就是《阿波羅》和《尼俄柏》。他論及貝爾維德爾的阿波羅像,贊其激情的表達被抑制到了最低的限度,憤怒只現于鼻腔,輕蔑只現于嘴唇,因而擁有“崇高的精神,柔和的靈魂。而阿波羅的這種崇高,是拉奧孔所沒有的”*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 p.115.。在尼俄柏及其女兒遭受死亡威脅的場景的雕刻中,溫克爾曼注意到她們的表情,與其說是抗爭的莊嚴,不如說是淡漠:“在這種狀態(tài)中,感受和思考停止了,這就像淡漠,肢體或面部不動。”*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6.淡漠和節(jié)制恰恰是希臘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因而這兩具雕像更進一步擴充了希臘藝術精神中的倫理精神內涵。如是,拉奧孔所指涉的“他者”世界,在阿波羅和尼俄柏的雕像中得到更加完善的具身化。正因如此,在《古代藝術史》中,溫克爾曼已不再需要拉奧孔作為他所要解讀的希臘精神的符碼。《希臘美術模仿論》通過邏輯與修辭的努力而最終論證成功的希臘精神,在羅馬時期歸附于別的偉大的希臘杰作,《拉奧孔》也隨之不再是表述的核心對象,溫克爾曼的觀感反而更為客觀,觀點也更加坦誠。由此可見,溫克爾曼希臘闡釋中的狄奧尼索斯精神的壓抑正是其文化策略的必然結果,及至發(fā)現更為合理的巴洛克的“他者”,他才不憚于道出《拉奧孔》的非靜穆、非理想化的自然主義的一面。
四、溫克爾曼與尼采
尼采心目中的溫克爾曼,停留在《希臘美術模仿論》,沒能注意到《古代藝術史》中對希臘藝術的描述和闡述的變化。這多半是因為《希臘美術模仿論》的觀點和風格幾乎旗幟一般地鮮明。相形之下,《古代藝術史》中的觀點則包裹在混雜的文體中,不易辨識。
尼采被認為是發(fā)現了希臘經驗的古代的、地下性的、迷狂維度的人。“他對溫克爾曼的阿波羅理想(那種帶有寧靜美和靜態(tài)和諧的雕像)的狄奧尼索斯式攻擊,被證明在從一種古典的希臘模式到一種本原的[希臘模式]的轉變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尼采對前蘇格拉底時代的解釋(解釋成‘本原的’)構成了一種反古典主義,一種對德國人關于五世紀雅典的傳統(tǒng)圖景(古希臘文化的最高峰)的無拘無束的攻擊。”*[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爾的根——尼采,國家社會主義和希臘人》,張志和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37-338頁。尼采攻擊溫克爾曼的希臘闡釋,認為溫克爾曼(以及后來的歌德)僅僅見到希臘文化的一半——阿波羅精神,而未能品賞希臘文化的更為本原的一面,即他在《悲劇的誕生》中發(fā)現的酒神精神。他認為,溫克爾曼僅僅強調阿波羅顯示的秩序、和諧和寧靜,但低估了阿波羅精神底下的本能力量,即希臘人以狄奧尼索斯表征之物。
尼采認為,溫克爾曼的“感受性在歷史上的影響,就是阻塞了任何前往蘇格拉底思想之土地性源泉的真正通道。沒有了這種土地方面的聯系,就無法期望任何德國人能把握住真正希臘的古代經驗的種種深層因素了”*[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爾的根——尼采,國家社會主義和希臘人》,張志和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47頁。。溫克爾曼在這隱蔽的地底入口設置的屏障,正好為尼采提示了可能的通道所在,“阻塞”實則構成了道路自身被隱蔽的標記。
在溫克爾曼的感受中,拉奧孔式的靜穆與寧靜并不能掩蓋其深處的激烈情感。溫克爾曼在希臘雕像上所見的自我克制的希臘精神之背后恰恰是人性的沖動和激情的復雜景象。若說中道的力量在于在兩極之間尋找平衡,那么對兩極的深刻意識是其前提。溫克爾曼對所謂希臘經驗的暗面,即不受道德控制的直覺、感受和欲望的一面,并非沒有意識,惟并未命名而已。但,溫克爾曼所見到的希臘經驗的另一面,卻又非尼采的狄奧尼索斯所能涵蓋。除了對狄奧尼索斯式的力量有所暗示之外,溫克爾曼所感知的希臘經驗的土地性的方面,其幽暗的自然涌動的生命活力,還在于其夢幻般的愛欲。在溫克爾曼筆下,少年酒神“踏在生命的春光和豐裕的邊界中,驕奢的情感正如植物的嫩葉在萌芽,他介于睡眠與行走之間,半沉迷在有著劇烈光亮的夢中,開始收集和糾正他的夢里的圖像;他的形象充滿了甜蜜”*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0.。他是輕松、歡樂、甜蜜的,在半明半暗中沉醉或迷狂,其源起并非是痛苦,而是夢幻。
有人指出,溫克爾曼與其說是酒神的信徒,不如說是柏拉圖的第俄提瑪的信徒。*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9,p.194.聽從第俄提瑪,溫克爾曼相信,一切欲望都是愛的形式,一切愛欲源自某種朝向永恒的沖動;美是愛的目標。溫克爾曼所發(fā)現的希臘人的迷狂在于希臘人對愛與美的投身與想象。他自身對美少年的同性之愛使得他與古代希臘人之間建立深刻的同情,也使得他的文化闡釋中明顯地嵌入個人性情的因子(如他對男性雕像的熱情明顯高于女性雕像)。
如果說,尼采是在康德和叔本華的影響下以自然和理性之間的二元論看待日神和酒神的區(qū)別*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194.。在其中,酒神的領域是感性的欲望,欲望和感受是給定的和自然的,不同于或優(yōu)先于理性領域;那么,溫克爾曼的柏拉圖遺產卻在于,他從未在非理性意義上解雇欲望和感受或將其當作盲目的自然力,而將理性和感受視作相粘連的整體。如同柏拉圖《斐德若篇》和《會飲篇》所示,欲望和感受本身是經過理性化了的,是內在精神沖動浮現到形式領域的表征。這即是說,溫克爾曼與尼采是從不同的哲學觀點接近希臘文化的。“不同于尼采以叔本華的意志學說和二元論接近希臘文化,溫克爾曼則以柏拉圖的理智主義和一元論來闡釋希臘文化。”*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9,p.195.溫克爾曼以《拉奧孔》為例證的理性精神(阿波羅精神),從未將狄奧尼索斯從其自身中分離出去。
責任編輯:寇金玲
Hidden Dionysus Element under Stillness:On Wincklemann’sLaocoon
Gao Yanp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001)
Winckelman describeds the Laocoon sculptures in his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as well as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But in the former, he regards it as a property of stillness, while, in the latter, he discovers the pathos expressed in it. Actually, we can find the hidden Dionysus element in both of them. In order to disclose this,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Winckelmann’s description in a close way as well as a necessary comparison between Nietzschze and himself. Besides, mention is to be made that the reason why Wincklemann failes to mention the expressiveness in Laocoon in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lies in his intentional tactics being against Baroque culture in his era.
Winckelmann,Laocoon, Dionysus element , Nietzsche
2016-02-20
高艷萍(1978—),女,浙江寧波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B83-09
A
1001-5973(2016)03-01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