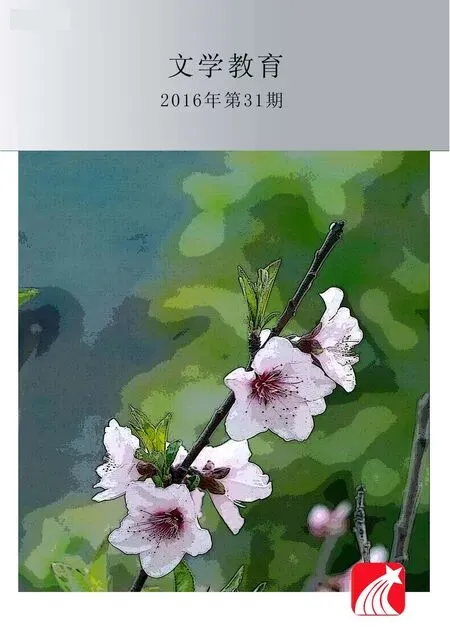豐子愷作品論析
陸煥煥 丁慶玲
豐子愷作品論析
陸煥煥 丁慶玲
豐子愷作品中的城鄉書寫,是在個人情感體驗的基礎之上,以現代為參照的鄉村的視閾所傳達出的精神失落,是豐子愷獨特的人生體驗。通過揭露現代都市的種種“不調和相”,豐子愷展現了他十分具有個人色彩的城鄉心理圖示和價值觀念體系。
文畫 城鄉 書寫
在文學與繪畫之間游戲的豐子愷,洞悉著世間的底色。在他細微平凡的生活意趣中飽含對生活的敬意,盡管他所處的年代,是戰亂頻仍和饑荒遍野的,但在傳統的筆墨中倚賴的是現代的風景靜物。他從鄉村走出,輾轉于現代都市的隘口,飄飄蕩蕩,是手中之筆在記錄和刻畫城鄉之間的風景。比起單獨的藝術載體,在文學與繪畫這種交融和互動關系的之中,更能夠體驗豐富的情感,加深和拓展城鄉的刻畫。
一.文學與繪畫中“鄉”的描寫
豐子愷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鄉市石門灣鎮,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家弟子。這里農田肥美,氣候怡人,豐子愷將它稱為“安樂之鄉”,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辭緣緣堂》中曾這樣描述這個世外桃源:“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漸漸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覺。中產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六套衣服逐漸遞換,不知不覺之間寒來暑往,循環成歲…故自然之美最為豐富;詩趣畫意,俯拾皆是。”[1]豐子愷就成長在這樣富有詩趣畫意得天獨厚的環境中,這里有他封存的記憶,四時佳興的舊事。“故鄉”于豐子愷而言,不僅是生養之地,這里更是他藝術和精神的真正家園。
在豐君的作品中,故鄉總是充滿著濃郁的世風民情,剪紙、花燈、版畫、乃至童年的玩具,皆可入文入畫。他曾在《視覺的糧食》一文中寫到自己對一把彩色紙傘的回憶,說“我由這頂彩傘的欣賞,漸漸轉入創作的要求…于燈會散后在屋里張起這頂自制的小彩傘來,共同欣賞、比較、批評…我的學書學畫的動機,即肇始于此。”[2]《酒令》中記述的是江南文人喝酒獨特的方式,和北方人豪邁吆喝式的方式不同,南方所行酒令多了一股儒雅斯文之氣。至于“清明”、“過年”、“請菩薩”等這種鄉間習俗風物的描寫更是如流水一般自然地蜿蜒在他的文畫里,成為不可多得的民俗史料。甚至這種民俗的書寫呈現了某種地域文化的特征,展現了不同時期的精神變遷,例如他的散文《憶兒時》里就寫了童年時期和家人一起吃蟹賞月時的情景,“積在蟹斗里,剝完之后,放一點姜醋,拌一拌,就作為下飯的菜,此外沒有別的菜了。”他寫飲食、禁忌、節日,都“含蓄著人間的情味”,“老妻忙很著燒素菜,故鄉的臭豆腐干,故鄉的冬菜,故鄉的紅米飯”都紐結著個人的心理圖示,成就了一幅幅故鄉風土圖。在這樣的一方水土里,他用清新趣味的筆調描繪著江南村落的淳樸,民間生活的鮮活,他善于觀察的藝術敏感給以后的藝術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甚至影響了日后創作的整體格調。
豐子愷認為人的“生命情感”是任何藝術創作心理的根源,完成這種本真的追求才是構建人終極價值的體現。其實不管是繪畫還是散文,他的作品大都以生活中的人事為創作對象,表達常情、溫情和真情。先來看一幅豐君早期的鋼筆寫生畫,名為《賣花女》,畫中一位梳著長辮著青衫布衣的女子提著竹籃走在寂寥狹長的小巷里,白墻灰瓦、小巷幽深,畫的右上角還有柳枝掛墻,裊裊炊煙升起,潔白的花朵在恬靜的女子手中,人景和諧,畫面取“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意,營造了一幅寧靜、潮濕的民俗圖。《三眠》也刻畫了家鄉民婦養蠶的場面,深夜提著燭等,小貓依偎在桌腳,取詩《蠶婦吟》:“子規啼血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成歸”,這首詩歌的畫面感在豐子愷的筆下互相為鏡,只不過玉人的綾羅綢緞換成了粗衫,這是姑娘們辛苦勞作所得,畫外之意其實也表達了作者的同情之心。《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和《燕歸人未歸》則是表現了婦人的相思之情,楊柳飛燕,畫中女子發絲凌亂,憑欄遠眺,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人物言之不盡的相思。除了村婦,豐子愷更多地描畫了代表純樸自然的鄉村世界的另一類人物形象,那就是兒童,兒童的純真之心,率性的表達是直觀的,充滿童真的詩意。像最為讀者所熟知的《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只是青山浮云上,教人錯認作山看》、《野渡無人舟自橫》、《幾人相憶在江樓》等都是明顯取自古意,“自然有情化”,以詩言情,蓋豐子愷認為“情”為不朽之物,所創作的自然就是不朽的篇章,而詩意的鄉村理應充滿感情,沐浴恩澤。
二.文學與繪畫中“城”的描寫
在《子愷漫畫全集》中,豐子愷先是將漫畫按照題材劃分為六類,其中描寫都市狀態共六十四幅集合為一冊,名曰《都市相》。他在《都市相》的序言中說道:“吾畫既非裝飾,又非贊美,更不可為娛樂,而皆世間之不調和相、不歡喜相、不可愛相、獨何歟?”此番言論可以看作是豐子愷對都市生活百態的概觀。
1921年豐子愷奔赴日本學畫,短暫的留學生涯讓他接觸到東京這個老牌國際都市。在這個東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和都市,豐子愷接受了不同文化的洗禮,培養了他摩登的都市生活方式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模樣。他致力于融合中西方的藝術實踐,并以現代語言和傳統文藝的方式表現出來。和部分現代派作家一樣,豐子愷在鄉土中國的江浙小城鎮成長,又進入現代的大都市生活,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現都市懷鄉病,這樣就為他的文和畫提供了可供探討的空間。
20世紀30年代之際的上海,被譽為“東方巴黎”[3],是遠東第一大都市,吸引著外地來求學的年輕人和知識分子。豐子愷曾以上海為城市據點創作了一批作品,來展現人們對于大都市生活的渴望和想象。《到上海去的》這幅漫畫是其中的代表作,火車是現代都市的代表,工業文明的產物,這幅畫把環境置于鄉間卻把空間無限延伸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兩個背影相依的人,遙望火車開去的方向,此時的上海猶如一個強大的磁場,吸引著周邊鄉鎮乃至全國的人們,成為他們眼中的“金銀地”。在那時,都市代表著現代文明,正以時髦的元素、金錢的誘惑沖擊著鄉鎮,拾得都市之味的鄉下人,笨拙地將這種陌生的文明融入生活,成了一種“可笑的狀態”。雖然在豐子愷早期的都市題材的作品中,依然保持著他抒情的趣味,但是當那份壓力無法承受時,他也會表現出隱隱的焦慮和恐懼來:“我每入都市,常覺頭痛腦脹。推求其故,知其為嘈雜之音所致。嘈雜之音中最可厭的,莫如汽車鳴笛。我常想,這是市街美的一大破壞者。”[4]噪音對寧靜生活的破壞讓豐子愷不堪城市之擾,創作《病車》也是早期生活在上海的時候,畫中五個勞動者齊心協力推動一輛并不行走的汽車,畫筆之下你能感受到他們腳步沉重、步履蹣跚,豐子愷用“病”這個字當作標題進行嘲諷,他痛苦地發現這個東部沿海城市正迅速擴張,變得兇險和病態,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壓榨大多數人的手段來實現的。如此不和諧的城市諸相,豐子愷用這種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呈現出來,日常生活中的“可驚、可喜、可悲、可哂”都成為他創作的源泉,他的記錄生動地展現了以上海為典型環境場景的樣貌,然而,都市中人民生活的艱辛和苦難,從他初初在上海生活一直延續到離開,都讓他頗感不適。
“五方雜處,良莠不齊”的都市空間里,人們互相防備,但豐子愷并沒有針對人和人的感情溫床做出延展性的書寫,他關心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生存狀態上的改變,城市的變化。我們不得不說豐子愷這種對文化的批判是溫和的,在對城市和鄉村的比較與思考中,這種審判其實是理性和內斂的,雖然他同情勞苦大眾,但當他解除戒備,卻并不從高屋建瓴和政治化的角度來解讀社會中的不平等、不自由的現象。
三.文學與繪畫中的城鄉交融
都市與鄉野之間的對立,其本質在于人性的隔膜,都市人在精神上的漂泊無依,這是豐子愷失落的土壤。現代都市社會被充分物化,商業利益的追逐不停的逼迫人文的氣息,自然的美不復存在,只顯示出都市的“丑”來。不管是從都市到鄉村,還是從鄉村到都市,豐子愷都沒有迷失自己的方向,他懷抱著鄉村的記憶在都市中書寫,回歸的路已斷,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讓他對家園的渴望有增無減。這種濃厚的故園情結卻讓豐子愷保持著一絲難得的清醒,“家”的概念也被無限延伸,它們不再是鄉居六年的緣緣堂,不再是逃難時期的沙坪小屋。和二十世紀中后期尋根文學對鄉村的歷史重塑不同,豐子愷的浪漫記憶不在那一份傳奇和想象性的認同———“他們采用一種雙重視角,在鄉村時懷念城市,回到城市卻又想念鄉村”[5],豐子愷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找到了雙方的共同之處,即使深處城市也能找到自己心靈的居所,在這里他找到了“對話”和“交往”的方式,最終融為一體。
久居都市的豐子愷在這種跨文化的體驗中形成獨特的心態,他以在都市中所感受到的污濁的空氣,冷漠的人性和民俗的匱乏,去觀照農村的貧窮和粗鄙,因而他的筆下就呈現了詩意和失落并存的現象,后者則主要是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對鄉村的浸染,使原本生活在鄉村里的農民和鄉土、土地失去了固有的聯系,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感受到鄉村生活的難能可貴,不管是繪畫還是文學中,都展現了鄉土人民溫暖的生存體驗。時代的進步不能以毀滅珍貴的豐富的民俗文化為前提,所以豐子愷是在記憶里給讀者一個充滿人間煙火氣息的鄉村世界。
注釋
[1]豐子愷.辭緣緣堂.豐子愷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2]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3卷.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3]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2;
[4]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5卷.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6.628.
[5]曾一果.鄉村記憶與城市書寫—當代知青文學的城鄉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6.
(作者介紹:陸煥煥,丁慶玲,浙江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