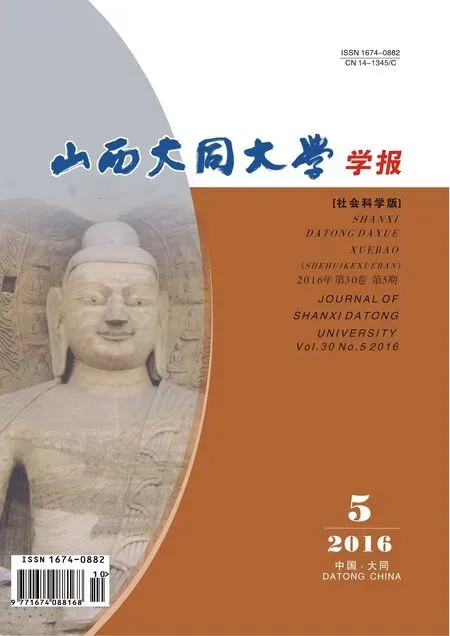歷史轉(zhuǎn)型初期文學(xué)論爭的復(fù)雜性
——以《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為中心
張慎,鐘義榮
(山西大同大學(xué)文學(xué)學(xué)院,山西大同037009)
歷史轉(zhuǎn)型初期文學(xué)論爭的復(fù)雜性
——以《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為中心
張慎,鐘義榮
(山西大同大學(xué)文學(xué)學(xué)院,山西大同037009)
創(chuàng)作于1979年4月的《喬廠長上任記》,呼應(yīng)了從1978年底開始的“全國工作重心轉(zhuǎn)移到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的時代轉(zhuǎn)型。然而,在歷史轉(zhuǎn)型的初期,人們對“揭批查”與“現(xiàn)代化”兩個“時代任務(wù)”之間關(guān)系存在著認(rèn)識分歧,再加上小說敘述的是1978年6月“揭批查”運(yùn)動尚未結(jié)束、時代轉(zhuǎn)型尚未開始時的故事,因此文藝界對蔣子龍?zhí)幚怼敖遗椤钡姆绞疆a(chǎn)生了爭議。受“文革”遺留的種種歷史身份與人事恩怨的影響,小說處理工廠人事問題的方式也引發(fā)了評價分歧。從《喬廠長上任記》評價風(fēng)波,可以了解當(dāng)時文學(xué)論爭、文學(xué)批評的復(fù)雜性。
《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天津日報》;“揭批查”;“現(xiàn)代化”
1978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全國范圍內(nèi)的大規(guī)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yùn)動已經(jīng)基本完成,全黨的著重點應(yīng)該從1979年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既宣告了在“文革”結(jié)束之后歷時兩年多的“揭批查”運(yùn)動的結(jié)束,又明確了歷史轉(zhuǎn)型的“現(xiàn)代化”方向。然而,在具體的歷史實踐過程中,人們對這一轉(zhuǎn)型的理解卻并不一致,形成了種種分歧。創(chuàng)作于1979年4月的《喬廠長上任記》所處理的恰恰是如何認(rèn)識“揭批查”與“現(xiàn)代化”兩個“時代任務(wù)”之間關(guān)系的問題。因此,發(fā)生在1979年下半年的“《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并非僅僅是一場純?nèi)坏奈膶W(xué)事件,而是牽涉著對歷史與現(xiàn)實、政治與社會中諸多問題的不同認(rèn)識和判斷。而且,在小說評價的博弈過程中,“文革”造成的種種歷史身份與人事恩怨也參與其中,使得整場論爭更為復(fù)雜。這里所關(guān)注的是:都有哪些因素、力量參與了、介入了這場文學(xué)博弈?這些因素和力量又體現(xiàn)了歷史轉(zhuǎn)型初期文學(xué)論爭的哪些歷史特點?探究這些問題,對于了解這一時期的文學(xué)論爭、文學(xué)批評的復(fù)雜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從“揭批查”到“現(xiàn)代化”的時代轉(zhuǎn)型
粉碎“四人幫”之后,在中共中央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部署之下“全國廣泛開展了揭發(fā)、批判‘四人幫’,清查幫派體系的群眾運(yùn)動”。[1](P6)運(yùn)動直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宣告“基本完成”。[2]1979年1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提出了“揭批查”掃尾工作應(yīng)該堅持“批判從嚴(yán),處理從寬,抗拒從嚴(yán),坦白從寬,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原則。在對“文革”問題的認(rèn)識上,也開始提出寬容態(tài)度,認(rèn)為“只要把主要問題的基本事實和主要情節(jié)講出來了,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態(tài)度如實說清楚了,對自己的錯誤有了認(rèn)識,愿意改正,就可以了。有些事是‘四人幫’當(dāng)?shù)罆r由他們假借名義,由上面統(tǒng)一布置做的,不少同志執(zhí)行了,責(zé)任不能完全歸咎于這些同志,這類事情就不要再去追查了。”在處理“文革”遺留的人事糾葛時,也提出了“嚴(yán)格區(qū)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的原則:對于極少數(shù)“文革”“首要分子”,“一定要徹底揭發(fā)批判,以致給以黨紀(jì)國法的制裁”;而“對于大多數(shù)由于思想認(rèn)識上的原因,執(zhí)行錯誤路線和上級的錯誤指示,而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的同志,包括犯了嚴(yán)重錯誤的同志,主要是加強(qiáng)思想教育,啟發(fā)他們自覺地進(jìn)行自我批評,認(rèn)真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鼓勵他們努力做好工作。要特別注意保護(hù)那些基本上對黨忠誠,有能力,有干勁,有成績,但又犯了錯誤,甚至犯了嚴(yán)重錯誤的同志。”社論這樣處理“文革”遺留的人事問題,主要是為了“在分清是非的基礎(chǔ)上,團(tuán)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共同為加速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奮發(fā)工作,貢獻(xiàn)力量”。[3]1979年3月10日,《人民日報》再次發(fā)表題為《揭開疙瘩,增強(qiáng)團(tuán)結(jié)》的社論,更為明確地指出,歷史的“帳,只能算在林彪、‘四人幫’身上,……至于同志之間的歷史舊帳,就不要去糾纏了”。[4]
在這樣的歷史轉(zhuǎn)型的背景下,“文革”結(jié)束之后一直呼應(yīng)中共中央“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zhàn)役”部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開始出現(xiàn)新的調(diào)整。創(chuàng)作于1979年4月的《喬廠長上任記》,不僅喬光樸對“時間和速度”的強(qiáng)調(diào)呼應(yīng)了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1976年到1985年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jì)十年規(guī)劃綱要(草案)》、1978年“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中“建設(shè)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jīng)濟(jì)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的論述。而且在“揭批查”運(yùn)動已經(jīng)宣告結(jié)束,全國的工作重心轉(zhuǎn)向“現(xiàn)代化”的1979年,蔣子龍試圖在《喬廠長上任記》中表達(dá)自己對“揭批查”運(yùn)動,更確切地說是對“揭批查”運(yùn)動與“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系的看法。在小說中,不論是喬廠長不計前嫌、放棄私人恩怨重用郗望北,還是處理機(jī)電廠的過去的“三套領(lǐng)導(dǎo)班子”,都體現(xiàn)出以是否有利于“現(xiàn)代化”為解決“文革”所遺留的人事問題的主要原則。蔣子龍后來直接說:“造反派中確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確有和‘四人幫’直接有聯(lián)系的壞分子,但是這類人畢竟是少數(shù)。更多的人是受了騙……當(dāng)時誰如果不參加造反隊,那就像現(xiàn)在不參加揭批‘四人幫’一樣的不得人心,受到孤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提拔的干部全部當(dāng)成‘火箭’干部,當(dāng)成‘雙突’式的干部,一律趕走的話,將給我們國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一律趕下臺,將給生產(chǎn)造成很大影響,加劇新老干部之間的對立。”[5](P58-59)小說中喬光樸調(diào)整機(jī)電廠“文革”遺留的人事班子、提拔“文革”造反頭頭郗望北,都體現(xiàn)了《人民日報》社論所提倡的區(qū)別對待“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在分清是非的基礎(chǔ)上,團(tuán)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共同為加速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奮發(fā)工作,貢獻(xiàn)力量”的精神。
也正是由于小說不僅呼應(yīng)了當(dāng)時意識形態(tài)的調(diào)整,更表達(dá)了當(dāng)時國人對“現(xiàn)代化”渴望、焦灼的情緒,小說在《人民文學(xué)》1979年第7期發(fā)表之后,得到了茅盾、周揚(yáng)、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文藝界領(lǐng)導(dǎo)的稱贊,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在1979年9月3日到12日間(也即在《天津日報》對其展開批判之前)《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軍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先后發(fā)表了大量積極肯定的文章。
二、小說的寫作時間與故事時間
從1979年9月12日開始,《天津日報》卻分別于9月12日、9月19日、10月5日、10月10日各期的“文學(xué)評論”版,連續(xù)四次發(fā)表了“爭鳴”文章。為了突顯四次“文學(xué)評論”板塊的設(shè)計是“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所展開的,四個版面都是批判性文章和肯定文章各一篇。然而,從版面分配來看,四個版面的設(shè)計都是批判性文章的版面是肯定性文章的2-3倍,報紙的傾向性便明確地顯示了出來。因此,當(dāng)時便有學(xué)者指出“這幾版‘爭鳴’文章,壓軸的都是‘批判’的大作,相反的意見則不過是點綴”,“讓人感不到爭鳴的空氣。相反,倒很象是一場有組織的‘批判’”。[6]
細(xì)致分析“嚴(yán)厲批判”《喬廠長上任記》的四篇文章,批判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從小說的細(xì)節(jié)描寫、人物塑造、情節(jié)處理來看,作品反對“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開展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清查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quán)陰謀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揭批查”運(yùn)動。[7]二、對喬廠長“組閣”的新班子、及其“組閣”過程中處理產(chǎn)生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三套”干部班子的方式和結(jié)果表示不滿。認(rèn)為喬廠長同情、“縱容”和重用“造反派派頭頭”、“火箭干部”郗望北是反對“揭批查運(yùn)動”的“捂蓋子”行為。這就涉及到如何處理“文革”遺留的人事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郗望北這樣曾是“造反派”卻又有真才實干的“文革干部”的問題。三、認(rèn)為喬光樸的“改革”不僅“脫離實際”,而且在改革過程中不民主、個人專斷,搞封建家長專制。因此,喬廠長既不是成功的典型形象,更不是“英雄人物”。四、小說藝術(shù)處理中,有“三突出”的痕跡、“神化”人物形象、“從路線出發(fā)”、“圖解政治”等缺失。因此,小說的對“現(xiàn)實主義”的運(yùn)用是失敗的。
如果熟悉當(dāng)時的歷史語境的話,就可發(fā)現(xiàn),在這些否定性意見中,批評小說處理機(jī)電廠的人事方式、認(rèn)為小說反對“揭批查”運(yùn)動等觀點,事實上已經(jīng)將問題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在時代轉(zhuǎn)型初期,人們對新意識形態(tài)走向還有所猶疑、過去的歷史教訓(xùn)依舊余悸未消。這種批評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顯然具有極強(qiáng)的敏感性和威懾性。
問題還在于,小說的寫作時間雖然是1979年4月,然而小說所敘述的故事時間卻是1978年“又過去六個月”。而在1978年6月,國家意識形態(tài)雖然已經(jīng)開始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和速度”問題,但“揭批查”運(yùn)動并沒有宣告結(jié)束,更沒有提出“在分清是非的基礎(chǔ)上,團(tuán)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的處理“文革”人事問題的原則。而這恰恰給《喬廠長上任記》的批判者提供了批判的理由。四篇批判性文章都是緊緊抓住小說的故事時間,認(rèn)為在1978年6月“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全國人民正在黨中央的領(lǐng)導(dǎo)下,深入開展揭批查運(yùn)動”,小說卻批評老干部冀申“每天翻著報刊、文件提口號,搞中心,開展運(yùn)動,領(lǐng)導(dǎo)生產(chǎn)”,這實際上是在批評“揭批查運(yùn)動”;小說同情、“縱容”和重用“造反派頭頭”、“火箭干部”郗望北,實際上正是反對“揭批查運(yùn)動”的“捂蓋子”行為。[7]并由此認(rèn)定:喬光樸的“改革”是對“揭批查”運(yùn)動“大潑冷水,……捂蓋子,壓群眾”。[8]
在論爭發(fā)生的1979年下半年,《喬廠長上任記》的批判者都諱言小說的1979年4月這一寫作時間,更諱言國家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在1978年底宣告“揭批查”運(yùn)動結(jié)束、“全國工作重心轉(zhuǎn)移到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的時代轉(zhuǎn)型,反而都強(qiáng)調(diào)小說的1978年6月這一故事時間,顯然是意在回避小說以是否有利于“現(xiàn)代化”來處理“文革”后人事問題的方式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回避小說的處理實際上是呼應(yīng)了1978年底以來意識形態(tài)從“揭批查”到“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型這一事實。這種有意的批評策略的選擇,無疑體現(xiàn)了這些論者反對蔣子龍及其支持者以“現(xiàn)代化”的需要模糊處理“文革”人事恩怨的方式,而是依舊堅持以嚴(yán)格的“揭批查”原則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態(tài)度。但是否就可以以此來認(rèn)定,這些論者依舊堅持過去“鮮明地區(qū)分?jǐn)澄摇薄ⅰ笆抢^續(xù)革命的邏輯,延續(xù)的仍舊是‘文革’的思路”?是否可以將這些批判者與蔣子龍的分歧認(rèn)定為“反映的是‘四人幫’被打倒后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兩股意識形態(tài)的分野,即繼續(xù)革命和發(fā)展主義的區(qū)分”?[9]事實上還有商榷的余地。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批判文章的發(fā)表還與蔣子龍曾經(jīng)是“揭批查”的對象的特殊歷史身份以及“文革”中的種種私人恩怨有關(guān)。這就使得這一“風(fēng)波”很難完全從純粹的思想分歧的角度來理解。
三、“揭批查”對象與“工人作家”身份
首先來看蔣子龍?zhí)厥獾臍v史身份。
早在1976年鄧小平復(fù)出進(jìn)行全面整頓期間,蔣子龍在《人民文學(xué)》復(fù)刊號上發(fā)表了以鄧小平整頓為大背景、貫徹鄧小平強(qiáng)調(diào)工業(yè)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思想的小說《機(jī)電局長的一天》。其后不久,政治風(fēng)云突變,全國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運(yùn)動,鄧小平再一次從政壇上沉寂下去,《機(jī)電局長的一天》也就成為“反動小說”受到了批判。在政治壓力和《人民文學(xué)》編輯崔道怡兩次到天津的“幫助”之下,蔣子龍不得不寫出“與走資派斗爭”的新小說《鐵锨傳》。[10]而且經(jīng)過《人民文學(xué)》編輯、領(lǐng)導(dǎo)多次與蔣子龍、當(dāng)時天津市委領(lǐng)導(dǎo)王曼恬的交涉、博弈,最終由袁水拍承當(dāng)時文化部部長于會泳之意“定調(diào)”,由李希凡具體“定稿”,“寫下”了題為《努力反映無產(chǎn)階級同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的檢討文章。兩篇文章同時發(fā)表于《人民文學(xué)》1976年第4期。在此期間,蔣子龍還在天津市委領(lǐng)導(dǎo)王曼恬“點名”要求下,參加了“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話劇《紅松堡》的創(chuàng)作組。幾個月之后,“四人幫”被打倒,蔣子龍的遵命文學(xué)《鐵锨傳》等作品,則又被視為“幫文藝”、“反動小說”、“反黨小說”受到嚴(yán)厲批判。由于蔣子龍在此過程中與王曼恬的關(guān)系,[11](P210-213)“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運(yùn)動中,天津有讀者就這篇小說(指《鐵锨傳》)曾給《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和《人民日報》文藝部寫來批判文稿,說他與‘四人幫’在天津的爪牙王曼恬的陰謀活動有牽連”。[12](P342)因此,直到1978年,還有作者給《人民文學(xué)》、《人民日報》內(nèi)參郵寄、發(fā)表批判蔣子龍的文章。[12](P74)到了《喬廠長上任記》所描寫的1978年6月,《天津日報》還在發(fā)表批判蔣子龍“反動小說”的文章。①
因此,論爭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在《喬廠長上任記》的1978年6月這一故事時間中,“揭批查”運(yùn)動并沒有宣告結(jié)束,而且小說的作者蔣子龍在1978年6月還仍然是“揭批查”批判的對象。
正是由于蔣子龍這一特殊的歷史身份,他在小說中對“文革”以來的人事處理的思考,必然帶有自己在“揭批查”運(yùn)動中被批判、被審查遭遇的切實體驗。而蔣子龍的這些思考,也由于其歷史身份的特殊性而顯得特別“敏感”。在四篇批判文章中,批判者對作品中喬廠長反對“揭批查”運(yùn)動、“捂蓋子”的批判,也大都直指作者:“作品從始到終缺乏對林彪、‘四人幫’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滿了對‘揭批查’運(yùn)動的不滿和低毀”,“作者把他的作品中唯一造反派起家、上升到副廠長地位、對揭批查有著嚴(yán)重抵觸情緒的人,描寫成時代英雄,這不能不說是對現(xiàn)實的歪曲。”[13]顯然是認(rèn)為蔣子龍在小說中表達(dá)了對“揭批查”的不滿。甚至認(rèn)為《人民日報》1979年9月3日發(fā)表的重新肯定《機(jī)電局長的一天》的文章是“與事實根本不符的毫無原則的評說,不能不使人啞然失笑!評論者的態(tài)度不能被認(rèn)為是嚴(yán)肅的。對事實真象和我們的觀點將另文論及。”[7]這種曖昧地點出“事實真象”行文方式,事實上也都暗暗指向了蔣子龍的“文革”行為。
有意思的是,在《天津日報》的批判文章大都指向蔣子龍的歷史身份的時候,《文藝報》等《喬廠長上任記》的肯定者,則開始重提蔣子龍“工人業(yè)余作者”的身份。“《文藝報》編輯部對《喬廠長上任記》是肯定和贊賞的,對青年工人作者蔣子龍是持保護(hù)態(tài)度的。”1979年10月6日,馮牧召開《文藝報》編輯部會議,指定要發(fā)表“一篇論述改革題材和改革人物的評論”。1979年10月10日,陳荒煤領(lǐng)導(dǎo)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文學(xué)評論》編輯部和《工人日報》聯(lián)合召開座談會,討論《喬廠長上任記》。在會上馮牧、陳荒煤等人都重新提及蔣子龍的“工人業(yè)余作者”身份,并對其在天津所遭受的批判“表示氣憤”。陳荒煤說:“文藝界有許多爭論,是極左思潮的延續(xù)。經(jīng)過歷次運(yùn)動后,工人作家還剩下幾個?為什么產(chǎn)生了工人作家,又遭到如此命運(yùn)呢?應(yīng)該寫文章指出,《天津日報》的幾篇文章,是打著百家爭鳴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認(rèn)是爭鳴,那就要允許反批評。”[12](P342-346)
可見,蔣子龍的歷史身份問題也是《喬廠長上任記》引發(fā)“風(fēng)波”的重要原因。當(dāng)批判者的批判直指蔣子龍“揭批查”對象的歷史身份之時,馮牧、陳荒煤等支持者又提出了蔣子龍“工人業(yè)余作者”的身份。而這一身份,也是《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向蔣子龍組稿的理由之一,在當(dāng)時無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從而成為支持者肯定其創(chuàng)作合法性的重要“砝碼”。
四、領(lǐng)導(dǎo)層的思想分歧與私人矛盾
《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體現(xiàn)出的思想分歧,主要是在當(dāng)時的文藝領(lǐng)導(dǎo)層。
據(jù)徐慶全考證,面對《天津日報》的批判,“陳荒煤、馮牧等人一方面以座談會的形式力挺,另一方面通過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出面與天津市委打招呼,終止《天津日報》的批判”。主持發(fā)起這場批判的天津市委書記劉剛“對于來自中宣部的指示只好執(zhí)行,但內(nèi)心并不服氣”,于1979年12月25日寫了致朱穆之并轉(zhuǎn)胡耀邦、周揚(yáng)的信,再次指出“這個小說有嚴(yán)重的政治錯誤”,有反對“揭批查”運(yùn)動的傾向。并抱怨說“對于陳荒煤同志這種只準(zhǔn)談好,不準(zhǔn)說有錯誤的看法,我不能理解,不知為了什么?不知要把文藝引導(dǎo)到什么方向?在作風(fēng)上用行政的方法號召出擊等等也覺得不大合適。”最后請示“是否能給天津日報一點民主權(quán)利,準(zhǔn)許其批評這篇小說的缺點和錯誤?實際上也是給文藝評論一點爭鳴的權(quán)利,如可以,請示知。”“12月28日,胡耀邦在信上寫道:周揚(yáng)同志什么時候回來?這個問題需要議一議。劉剛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贊同。”1980年1月12日,周揚(yáng)將信轉(zhuǎn)給陳荒煤和馮牧,要求他們“研究提出意見告我”。1月23日,陳荒煤致信周揚(yáng),將研究結(jié)果告知。陳荒煤的信中除了堅持認(rèn)為“一定要說它反對‘揭批查’,給幫派頭頭翻案,是政治錯誤,是說不通的”之外,還談及“《喬》事涉及文藝界派別爭論,也涉及到劉剛與市委宣傳部白樺同志之間的矛盾,不只是對此小說有分歧的問題。”[14](P375-387)
可見,即使在天津市委與陳荒煤、馮牧等領(lǐng)導(dǎo)層之間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理解分歧中,也糾纏著劉剛與白樺等不同文藝派別之間的矛盾、批評發(fā)起者的私人恩怨。這種矛盾分歧使得所謂的“天津方面”也并非鐵板一塊。在《天津日報》對《喬廠長上任記》展開批判之后,天津的《新港》雜志則召開了該小說的座談會,并在第10、11、12期接連發(fā)表肯定該小說的評論文章和“來稿摘登”,儼然與《天津日報》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同樣,發(fā)表在《新港》上的這些肯定性評論,大都強(qiáng)調(diào)了蔣子龍是“我市工人業(yè)余作者”的身份,以加強(qiáng)其創(chuàng)作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天津日報》的批判平息下來之后,在1979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評獎前后,《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再起。“一股風(fēng)從天津吹過來,說這篇小說帶有‘抄襲之嫌’!”由于沒有具體檢舉,不便正式調(diào)查,《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具體負(fù)責(zé)評選事宜的副主編葛洛,便向天津文學(xué)界的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側(cè)面打探”,后來得到回復(fù)說,“天津這里傳言很多,懷疑成風(fēng)……但又提不出真憑實據(jù)來……有些人的目的,是想把蔣某人搞臭,把支持他的作品的人也搞得灰溜溜的。”并說“有些傳言,不可輕信”。[15](P549-551)1980年3月25日,評選結(jié)果揭曉,《喬廠長上任記》榜上有名。據(jù)說“大約這種活動,又觸及天津方面對此小說敏感的神經(jīng)”,天津方面又給新任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奏上了一本”。王任重在1980年4月23日的回復(fù)中,表達(dá)了對小說基本肯定的包容態(tài)度,認(rèn)為“對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派頭頭,只要不是搞打砸搶有罪行,不是十年一貫制的,則不應(yīng)追究。從郗望北的工作表現(xiàn)來看,這個人是有能力的,工作是積極負(fù)責(zé)的。”顯然體現(xiàn)出與《人民日報》社論《揭批查運(yùn)動要善始善終》相同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方式與態(tài)度。然而,天津方面還沒有罷休,1980年6月,“《文藝報》編輯部又接到了來自天津的有關(guān)蔣子龍的一封告狀信。《文藝報》編輯部只好派人到天津去調(diào)查。”[15](P388-389)
從《喬廠長上任記》的曲折遭遇以及“風(fēng)波”的復(fù)雜歷程來看,歷史轉(zhuǎn)型時期對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理解和認(rèn)同、特定歷史時期造成的私人恩怨糾纏于整場博弈過程之中,都是引發(fā)論爭的重要因素。因此很難單純地從思想觀念分歧的角度來認(rèn)識論爭雙方的思想立場。而這,恰恰體現(xiàn)了歷史轉(zhuǎn)型初期文學(xué)論爭、文學(xué)批評的復(fù)雜性。還應(yīng)注意到的是,在“《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中,蔣子龍的批評者與支持者都曾以“打招呼”、“上書”的方式試圖尋求“政治裁決”的手段解決論爭。這一現(xiàn)象也體現(xiàn)出,在“文革”結(jié)束之后,文學(xué)批評與政治密切關(guān)系的“傳統(tǒng)”依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論爭雙方對歷史、政治認(rèn)識存在分歧,難以達(dá)成一致的情況下,各方都試圖尋求“中央”、“領(lǐng)導(dǎo)”的支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隨著1980年《喬廠長上任記》獲得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風(fēng)波”似乎塵埃落定。對其不滿的意見雖依然存在,卻已少見于批評文章。然而幾年之后,批評界開始反思“改革文學(xué)”的“模式化”、“形象塑造的危機(jī)”,《喬廠長上任記》的批判者曾經(jīng)提到的喬光樸的不民主、個人專斷、搞封建家長專制等問題,以及小說藝術(shù)手法的概念化、模式化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加以批評。②當(dāng)然,事隔多年之后,文學(xué)批評的機(jī)制、形態(tài)已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論爭漸漸走上了思想批評、藝術(shù)批評正常化的軌道。因此,這種“再批評”事實上是試圖在“現(xiàn)代意識”、“現(xiàn)代觀念”的參照之下,推動“改革文學(xué)”在思想上、藝術(shù)上走向深入。
注釋:
①1978年,《天津日報》發(fā)表了三篇批判蔣子龍“反黨小說”的相關(guān)文章。白春生:《一把反革命的大鐵锨——批判宣揚(yáng)反革命政治綱領(lǐng)的反黨小說〈鐵锨傳〉》,《天津日報》,1978年2月12日;楊士剛:《蒼蠅雖死細(xì)菌猶在——反動小說〈不平常的日月〉》,《天津日報》,1978年5月8日;杜哲:《欣賞奇文析疑義——評中篇小說〈不平常的日月〉》,《天津日報》,1978年6月19日。
②相關(guān)文章如吳亮:《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wù)》,《上海文學(xué)》,1981年第2期,第75-79頁;張志忠:《奮戰(zhàn)在經(jīng)濟(jì)改革的戰(zhàn)線上》,《當(dāng)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4期;閻真:《超越觀念——評第一階段改革題材小說的藝術(shù)缺陷》,《當(dāng)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5期;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機(jī)》,《當(dāng)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6期。
[1]李德生等.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N].人民日報,1978-12-24(01).
[3]揭批查運(yùn)動要善始善終[N].人民日報,1979-01-05(01).
[4]揭開疙瘩,增強(qiáng)團(tuán)結(jié)[N].人民日報,1979-03-10(01).
[5]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生活賬[A].不惑文談[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6]楊洪立.爭鳴與批判[J].讀書,1980(02):50-51.
[7]召珂.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N].天津日報,1979-09-12(03).
[8]宋乃謙,滑富強(qiáng).喬廠長能領(lǐng)導(dǎo)工人實現(xiàn)四化嗎?——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N].天津日報,1979-09-19(03).
[9]徐勇.“改革”意識形態(tài)的起源及其困境——對《喬廠長上任記》爭論的考察[J].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4(06):123-133.
[10]涂光群.我和《喬廠長上任記》及其它[J].長城,2012(03):156-163.
[11]吳俊.環(huán)繞文學(xué)的政治博弈——《機(jī)電局長的一天》風(fēng)波始末[A].向著無窮之遠(yuǎn)[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9.
[12]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M].開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4.
[13]王昌定.讓爭鳴的空氣更濃一些——也談《喬廠長上任記》[N].天津日報,1979-10-10(03).
[14]徐慶全.《喬廠長上任記》風(fēng)波及其背后——從兩封未刊信說起[A].名家書札與文壇風(fēng)云[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
[15]崔道怡.方蘋果[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The Complexity of the Literary Controversy in the Early Stage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Taking the Argument aboutDirector Joe Took Officeas the Object
ZHANG Shen,ZHONG Yi-ro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Jang Zilong's novelDirector Joe Took Office,which was Created in April 1979,echoed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the focus of national work has shifted to the“modernization”since the end of 1978.However,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 ideology,and the story's time of novel was June 1978,when the movement of exposing,criticizing and checking the remnants of the Gang of Four had not finished,there had been a controversy about the novel's narration of the national movement.Moreover,because of the various historical identities and personal grudges,which were caused by the“Cultural Revolution”,the adjustment of the Factory personnel in the novel,also triggered heated controversy.To analyse the factors and power in the Comments ofDirector Joe Took Office,can help u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he argument ofDirector Joe Took Office;Tianjin Daily;the movement of exposing,criticizing and checking the remnants of the Gang of Four;modernization
I207.425;I247.5
A
1674-0882(2016)05-0061-05
2016-05-08
山西大同大學(xué)青年基金項目(2011Q22)
張慎(1983-),男,山西渾源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鐘義榮(1981-),女,山西陽高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xué)。
〔責(zé)任編輯 裴興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