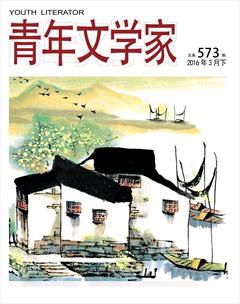建構“話語中國”視域下對漢外翻譯的幾點思考
摘 要:在建構“話語中國”的背景下,本文關注的焦點為文化話語權的建構及漢外翻譯中的策略和實施環節,并結合實例提出了幾點想法。
關鍵詞:話語;漢外翻譯;多元系統;策略;模因
作者簡介:劉沁卉,山東青島人,現為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德語系講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德語翻譯學。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09--03
一、緒言
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話語權利論”自誕生以來,備受關注,“話語權”一詞在人文社科研究當中也越來越多地被提及。下至普通公民的社會生活,上至關乎民生、民族命運的國家大計,“話語”無處不在,話語所承載的建章立制、構建文明、傳播理念的功能在其交際功能之外成為另一個受到關注的焦點。
就“話語中國”而言,它意味著國際社會中中國的聲音,意味著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統中,帶有鮮明傳統特色和獨特時代風貌的中國話語元素逐步由邊緣走向中心。而從目前來看,我們距離這一目標無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中國在過去的三十余年里,通過制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針戰略及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但伴隨而來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即所謂“崛起困境”。“崛起困境”無疑是多方面的,本文關注的焦點是與中國崛起的經濟、軍事實力產生巨大反差的文化、理念輸出困境,及與之相應的薄弱的“話語實力”。因為在應對“既不能不顧及他國顧慮而一味提升自身‘硬實力,又不能為打消他國顧慮而止步不前”這一困境時,著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取得更多的“文化話語權”無疑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與文化輸出關系最為密切的活動恐怕非漢外翻譯莫屬,那么在如今中國已經作為大國和平崛起的時代背景下,漢外翻譯又能夠為促進中國文化產品的輸出、爭取更多的文化軟實力和話語權做些什么呢?本文將試圖結合實例,對這一問題作出幾點思考。
二、近代中國文化話語權的削弱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軍事、科技與現代化的突飛猛進,閉關鎖國、以泱泱大國自居的中國落伍了。從嚴復以文言文體翻譯《天演論》到“白話文運動”中魯迅、瞿秋白等將“德謨克拉西”、“賽恩斯”、“尖頭鰻”等“先生”請進漢語殿堂,短短二十余年,中國文化原本穩定的多元系統在外來沖擊下轟然崩塌,譯介的外來文學和語篇由邊緣迅速進入多元文化系統的中心,以至于中文暫時無對應語匯的概念以純音譯的極端異化方式走進讀者視野。西方列強“擊碎了國人自以為是、孤芳自賞、以世界中心為自詡的夢囈,……國人進而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自卑心理”[1]。中國文化逐漸轉變成了“求教文化”,同時成就了西方對東方居高臨下的“指教文化”,成就了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與之相應,中國文化在他國,尤其是西方各國的多元文化體系中退至絕對邊緣,對歐美國家高達100:1以上的文化貿易(涵蓋書籍與影片的引進與出口)逆差清晰地映出了一個萎縮的中國形象[2]。一方面,歐美等國家的受眾在面對中國文化產品時,或因西方輿論的片面導向而拒絕摘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或因東西文化差異巨大而懷有陌生感、神秘感,造成接受障礙;另一方面,當中國有意識地對外宣傳、譯介自己的文化時,在選題方面缺乏策略與受眾研究,文化自信不足又導致譯介過程無法產出有強感染力、傳播力的中國話語。
以文學譯介為例,2015年12月初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翻譯:現狀與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的德國圖書信息中心主任龔迎新、人民文學出版社外編部歐陽韜等資深出版人及中外著名文學譯者、學者就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德譯介現狀給出了這樣的描述:中國在國際圖書市場上仍未擺脫“文化引進大戶”這一身份,相對于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的迅速崛起,中國顯然還未能為自己的“文化亮相”做好準備,西方的受眾亦是如此。德國出版社受模糊的市場預期影響在中國圖書版權購買方面慎之又慎;而熱愛并有豐富的漢語文學德譯經驗的德國譯者隊伍,也僅有不足十人。我國近年來部分機構策劃的外宣圖書選題,成書后較為普遍地留存于駐外使領館中,真正進入市場銷售、觸及文化消費者的寥寥無幾。可見,至少就德國文化市場而言,中國文化產品仍是掙扎在邊緣的,而整個歐洲范圍內,除法國的情況略好之外,也是大致如此。
三、翻譯與話語權
翻譯與話語權的緊密聯系,在我國近代幾次翻譯“高潮”中已盡顯無疑。西方的話語體系正是在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中堂而皇之地占據了一個個文化及學術領地。而今,當中國的崛起奏響時代強音的時候,我們依然要通過翻譯展示和推進中國理念、中國文化的傳播,逐步構建文化領域的中國話語。然而翻譯是一種有目的性的、牽涉到贊助人、委托人、譯者、讀者等諸多環節、受制于各種錯綜復雜的外在框架制約的、多途徑、多層面的復雜活動;文化話語權的構建也絕非僅憑一廂情愿的盲目呈現與文字表層的簡單操作能夠完成的工程;自“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制定以來,國內已有不少學者撰文闡述中國文化輸出的總體設想以及翻譯中的權利策略[3],卻少有提及宏觀大略之下的具體問題和解決方案,也未明確指出文化話語權建構可行的步驟和實施路徑,這也正是本文從翻譯角度出發試圖關注的焦點。
(一)作為動態進程的翻譯
翻譯是一項創造性活動。對于任何一個文本,都不存在唯一或“最終”的譯文版本。翻譯史上無數的實例證明,越是經典的文本,其譯本版本往往就越多,而當我們將某一作品誕生于不同歷史時代的版本相比較時,往往會看到,各版本所屬時代譯出語與譯入語文化的關系、譯者本人的主體性及歷史局限性對譯文的面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的許多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水滸》、《西游記》、及部分明清小說,自十九世紀初開始便不斷出現各種德譯、英譯本,其中多數為節譯。在這些譯本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作品首先被關注和譯介的是故事情節,甚至只是其中的某個能夠引起西方讀者興趣和共鳴的主題。除此之外,作品在譯者的筆下被刪節、改寫得可謂“面目全非”。以《西游記》為例:在德語區國家,《西游記》先后出版過四個版本,書名分別被譯作“Monkeys Pilgerfahrt”(猴子的朝覲之路,1947)、“Die Pilgerfahrt nach dem Westen”(西行朝覲,1962)、“Der Rebellische Affe”(反叛的猴子,1972)、“Monkeys Pilgerfahrt,1983”(猴子的朝覲之路);2016年,其最新全譯本即將在瑞士面世,定名“Die Reise in den Westen”(西游記)。僅從書名的翻譯就不難看出,各時代譯者的策略在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同時也有從“歸化”逐步走向“異化”,即:從首要考慮譯文讀者的接受、或為契合本國時代背景而“取其所需”片面夸大作品某個主題[4],到更加注重忠實再現漢語原文風貌、保留和傳遞中國文化元素。
也就是說,以翻譯途徑實現中國文化元素的走出去與有效傳播,不是一廂情愿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順應多元文化系統內部運動的規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對外譯介的初期,正如資深出版人、自由文化策展人Jing Batz女士在上文提到的研討會上所言,中國當代文學尚需在德國讀者中建立一種“信任”,需要一位川端康成、村上春樹那樣的為本國文學樹立形象的開路者。在這一階段,翻譯的選題不能急于宣傳我們自己認定的“核心”、“精髓”,而是在研判外國受眾期望值和心理上多下工夫。西方讀者普遍對中國“禁書”的好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帶有“宣傳”和“禁書”標簽的中國文化產品在國外的接受和傳播完全是冰火兩重天。最近,中國青年作家徐則臣的作品《跑步穿過中關村》在德國取得了不俗反響,眾多讀者評論當中紛紛提到了很耐人尋味的一點:該書的主人公乃是一群掙扎在中國社會底層、映射出社會陰暗角落的“京漂”年輕人,這樣題材的作品扉頁上,居然沒有打上“禁書”標記,反而是“鳴謝新聞出版署的翻譯贊助”,這在德國讀者看來是一個亮點。這說明中國官方并非他們想象中的那樣一味宣揚社會的陽光與美好,類似這樣觸及草根和“自曝家丑”的作品同樣被鼓勵譯介到國外。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外國讀者對“中國式宣傳”的偏見和抵觸,而只有逐步建立了信任,作品才能真正得以走入讀者內心,形成話語傳播開來,否則僅在翻譯文字上做文章,恐怕收效有限。待中國文化產品逐漸“叫響”之后,我們可以再進行二次、三次譯介,同時轉變策略,推動越來越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與話語輸出和傳播。
(二)受眾分析研究
要叩開國外讀者的心扉,自然應當對他們的人群組成、心理、閱讀動機、知識背景、 閱讀反饋等等作出一番梳理和考究。然而目前此類研究,在文學、翻譯學、跨文化學各研究領域里都少之又少。誠然,這項調查工作的開展,要做到有普遍代表性、有說服力,是殊為不易的,需要出版、銷售、傳播等各方面的配合;但就目前而言,至少讀者的書評或許能夠成為一個可行的切入點。如果我們對書評進行長期的、細致的、大量的收集與篩選,而后進行分析比較,最終至少能夠生成一個讀者群體概貌,并對各讀者群體的心理預期、審美取向等作出相應的研判。雖然作家不可能為迎合讀者而進行“定制”創作,但這樣的調研結果會為我們在輸出文化產品時的對象遴選提供一個參照依據,而避免盲目的、一廂情愿的輸出。目前,被譯介并在國外贏得讀者的中國文學作品,幾乎都是由外國譯者或出版機構選中的,如在英國首次被納入“企鵝經典文叢”的麥加的《解密》等作品;而我們著意要向外推介的書目,雖可能含有更經典更特色的內容,但在完全不考慮受眾接受意愿的情況下,幾乎都在國外市場上舉步維艱。
(三)譯者隊伍與宏觀策略意識
由外語譯入母語一直是翻譯行業通行的做法。我們的文化產品,從古籍經典到當代文學,被譯介的“命運”也一直掌握在外國漢學家手中。古籍自不必說,筆者單就當代中國文學而言,以上文提到的“不足十人”的德國譯者隊伍成員之一馬海默為例,他是一位廣受好評與認可、經驗豐富的著名譯者、漢學家與文學家,譯介了姜戎、劉震云、徐則臣等中國當代作家的多部作品。而當我們仔細研讀馬海默的譯著,便不難發現他首要考慮的是德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審美預期和文學傳統,因而常會對原著進行局部的、頗有力度的“小手術”:將描寫轉為對話、將環境與心理描寫語句進行大段調整、甚至“補寫”原文沒有的情景。這些翻譯手法的確賦予了德語譯文更高的可讀性,從而贏得更多讀者,但同時仍然不可避免的折損了原文的風格:諸如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借景抒情這樣的常見手法,經譯者的微調之后重組成為符合德文連貫特征的語篇,中國文學特有的手法也便無從體現。如果我們將話語當作某種思維方式、感知和見解的體現,那么經此一譯,中國文學的話語是蕩然無存了。
因此,在我們國家制定“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宏偉戰略、積極鼓勵中華典籍外譯的大背景下,就譯者隊伍而言,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一些新的嘗試。翻譯史上,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翻譯的《易經》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他的背后還有勞乃宣——這位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親自為衛禮賢講授《易經》,從而極大程度上保證了原著思想內涵的正確解讀。勞乃宣雖未直接參與譯本產出,但對衛禮賢每日所做的第一稿譯文回譯漢文進行了嚴格把關和進一步修正,因而說《易經》乃二人合譯實不為過。 這種“一中一外”的譯者“結對”,形成搭檔的工作模式,應當說既能發揮外國譯者的母語表達優勢、又能通過中國譯者的參與產生更多積極對話,促進中國語言文化特色的保留與傳遞。
這一設想將使中國譯者面臨更新的挑戰:首先需要明確的宏觀策略意識。通過譯介來傳播中國文化話語是終極目標,那么按照目的論和功能主義的學說,就應當形成鮮明的策略并使一切語言層面的操作服從于這個目的。兩種差別懸殊的語言文化中,無法找到對應表達的例子比比皆是,對于這些表達,譯者究竟要費盡心思地進行解釋,還是可以有其它更簡潔的選擇?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學習生活會上使用了“不折騰”一詞,口譯員在新聞發布會上將此次直接音譯為“bu zeteng”,這樣的“零翻譯”隨后引來眾家熱議。筆者無意在此評判此種策略的優劣得失,但正如施燕華等所言,“這個口語化的詞,在這里含義深刻,且表現力強。真正從歷史的層面以及當前形勢的需要解釋清楚這個詞的含義,一篇文章甚至更多文章也不為過”[5]。因而“考慮到‘折騰的確切含義并不明確,直接采用音譯作為其正式英譯文似可看作中文政治類詞匯翻譯中的一個策略”[6]。不得不說,譯者們將此種策略納入考慮范圍是需要一番考量和勇氣的,然而與之相對的保守的歸化策略顯然更加無異于中國話語信息的傳遞。其次,如何從文化語篇中識別并聚焦關鍵表述,進而通過與工作伙伴的溝通找到適宜的傳譯方案,也同樣考驗譯者的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四)漢語言文化的模因研究及翻譯中的創造性運用
模因論是一種基于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模因如同基因一樣,是一種表現形式非常豐富的、以非遺傳方式傳播的文化信息單位。在語言的傳播與復制過程中,那些相對穩定、具有可復制、傳播和變異屬性的言語便構成了語言模因。這其中可以包括語言的實體,也可以包括語言使用方式。翻譯屬于語言模因的外部復制形式,與模因的生成和傳播有著直接而緊密的聯系。以漢德兩種語言為例,表層結構雖差異巨大,內部的模因組成、結構也迥異,但基于人對生存環境和大千世界的共同感知、相通的情感共鳴和普世觀念,譯者總能夠找到“以模因譯模因”的操作空間,并在選擇的譯入語模因當中搭載來自源語的新信息,利用模因感染性強、傳播力強的特點,將源語的內涵有效傳遞出去。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漢語言文學與翻譯學關注的研究領域。
四、結語
中國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憑借各族人民的不懈奮斗而走上了今日的騰飛之路。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為“話語中國”的振興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契機。文化話語權作為“潤物細無聲”的軟實力,更能夠于無形處讓世界了解、接納、贊同和仰慕中國,成就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形象。為了有效地進行文化輸出,我們在推動經典外譯或其它漢外翻譯活動時不應一味追求數量、無的放矢,而是應當全面顧及翻譯活動的各個環節,有計劃、有策略地進行挖掘和優化。本文中提出的幾點是筆者主要結合近年來漢德文學翻譯談的幾點粗淺想法,希望對漢外翻譯的策略與步驟實施有所啟發。
注釋: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負與文化自信[J].道德與文明,2011,(4):18-23.
[2]參見馬文麗.傳媒翻譯:把握話語權——再談后殖民主義譯論語境下的翻譯策略[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0(5):687-690.
[3]參見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4]如1972年版的《反叛的猴子》正是一個典型代表。1972年,轟轟烈烈的歐洲大學生運動稍漸平息,其突出主題便是對傳統、權威的質疑與反叛.
[5]施燕華等. "不折騰"英譯大家談[J].中國翻譯,2009(2).
[6]朱純深、張峻峰. "不折騰"的不翻譯:零翻譯、陌生化與話語解釋權[J].中國翻譯,2011(1).
參考文獻: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負與文化自信[J].道德與文明,2011,(4):18-23.
[2]河清.中國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民族真正復興的根本前提[J].美術觀察, 2014, (1):18-19. DOI:10.3969 / j.issn.1006-8899.2014.01.010.
[3]何自然.語言中的模因[J].語言科學, 2005, 4(6):54-64.DOI:10.3969 / j.issn. 1671-9484.2005.06.006.
[4]洪溪珧.多元系統論——翻譯研究的新視野[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 2009, 30(2):169-171. DOI:10.3969 /j.issn.1673-2219.2009.02.054.
[5]蔣朝莉,李凌.以高度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J].探索, 2013, (1):18-20,31.DOI:10.3969/j.issn.1007-5194.2013.01.004.
[6]馬文麗.傳媒翻譯:把握話語權——再談后殖民主義譯論語境下的翻譯策略.[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0(5):687-690.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7.05.025.
[7]施燕華等. "不折騰"英譯大家談[J].中國翻譯,2009(2).
[8]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9]朱純深、張峻峰. "不折騰"的不翻譯:零翻譯、陌生化與話語解釋權[J].中國翻譯,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