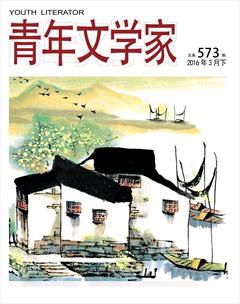論王安憶《荒山之戀》的敘事結構
摘 要:王安憶198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荒山之戀》在敘事結構上別具匠心,雙線交叉對稱敘事,小說的四章有明確主題,可以視作四幕或四折戲劇來看,整個小說呈現出一種精巧的“雙線戲劇式結構”。《荒山之戀》的這種敘事結構,與古典戲曲尤其是宋元南戲(亦稱傳奇)、明清傳奇的敘事結構異曲同工,傳達出深深的古典韻味。
關鍵詞:王安憶;荒山之戀;雙線戲劇式結構;傳奇色彩
作者簡介:宋慶芳(1990-),女,漢族,江蘇南京人,碩士研究生,揚州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09-0-02
王安憶是當代文壇的實力派作家,她緊跟潮流,又具有個人獨特的風格,在新時期以來文壇每一次波動時,這位“海派傳人”都能交出讓讀者和評論家眼前一亮的作品。“三戀”即是王安憶有重大影響的代表之作,轟動一時。與《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相比,發表在《十月》八六年第四期上的《荒山之戀》無論在對現實的透視批判的力度,還是在對性愛的探索思考,作家個人經歷的折射上都容易被忽視,一直以來對它的研究也不夠充分,多停留在傳統的人物分析與主題探討上。筆者認為,《荒山之戀》是一部精巧優美的匠心之作,體現了作家的諸多心血,在人物、思想、語言、結構等方面都具有獨特藝術魅力,本文將從敘事學的角度,剖析《荒山之戀》的敘事結構。在分析研究過程中,筆者將其定義為“雙線戲劇式結構”。
一、雙線敘事
雙線敘事這一特殊的敘事方式在王安憶的小說創作中并不罕見,除《荒山之戀》外,在《大劉莊》、《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等小說里王安憶也運用了這一方式。比較典型的是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在這篇小說中,王安憶“以交叉的形式輪番敘述這兩個虛構世界。我虛構了我的家族,將此視作我的縱向關系,……我還虛構了我的社會,將此視作我的橫向關系”[1],表現了小說家王安憶對于小說敘述的關注和功力。正如她在《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中所說“現代小說非常具有操作性,是一個科學性的過程,它把現實整理歸納,抽象出來,然后找到最具有表現力的情節再組成一個世界。”《荒山之戀》就是王安憶巧手經營的作品,是一個獨特的藝術空間。整部小說圍繞男主人公,一個內向憂郁的音樂家、天才的大提琴手和女主人公,俏麗風流的金谷巷女孩兒,情場高手,雙線交叉并敘。當他們在小城文化宮聚集,相遇、相愛、殉情時,兩條線索合二為一,又分分合合。整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雙線敘事十分明顯,又常常對稱,結構非常精致,體現了小說家王安憶的細致奇妙的構思。這樣精巧的雙線敘事線索對于加強讀者的審美感受,加深小說的意蘊都有很好的效果。它取材于現實又超越于現實,給人以強烈的感染,正如王安憶自己所說,“我從來不期望要寫出任何地方的真正模樣,無論是上海,還是江淮流域的農村,它們都是我小說里的戲劇舞臺,一個空間。我屬于寫實派,我喜歡現實生活的外部狀態,因為存在的合理性,而體現出平衡、對稱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間亦有這樣的美感。”[2]《荒山之戀》的故事空間,呈現出的即是平衡、對稱的美感,也隱喻了男女雙方在愛情上相互平視,聳峙的格局,他們各自成長又隱隱靠近,最終“金風玉露一相逢”,在各自成家立業的情況下走到一起,背叛道德,倫理,社會規則卻忠于內心和身體的真實渴望,演繹了一曲叛逆而又純粹的戀曲,傳達出了無限韻味和對家庭、婚姻、生命、社會等的深深的思索。
同時,伴隨雙線敘事的進行,小說家的“兩副筆墨”也相互映襯,相映成趣。男主人公音樂家,他的不幸的童年,求學期間痛苦的犯罪往事,懷才不遇的遭遇,憂郁懦弱的性格和女主人公金谷巷女孩兒受矚目的出生,被溺愛的成長,眾星捧月的戀情,活潑熱情的性情,一冷一熱,一靜一動,一暗一明,一悲一喜,處處對比,又奇妙地相互鑲嵌,碰撞,有強烈的美感。對讀者的閱讀接受來說,也有調節氛圍和勞逸,引起興趣的作用。
二、戲劇式結構
王安憶的小說往往有很多戲劇化的情節,峰回路轉,跌宕有趣。《荒山之戀》這一曲叛逆而純粹的婚外戀曲也不例外,可以滿足眾多讀者“獵奇”和尋求刺激的心理。與此同時,《荒山之戀》整個故事的結構也耐人尋味,完全可以當成一出四幕或四折戲劇來看。小說的四章各自有十分清晰的主題,依次是第一章的“成長”,第二章的“各自相戀成婚”,第三章的“相遇、孽緣、情死”,第四章的“后事”。每一章集中闡述,界限分明,重重推進,與戲劇沖突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模式正好相符,甚至可以說十分嚴謹。《荒山之戀》的這一結構特點,不僅在王安憶其他“雙線敘事”的小說中是少見的,與同時期其他作家流行一時的作品相比,也很獨特。筆者認為,王安憶在她的創作過程中,流露出對戲劇或舞臺的強烈興趣和某種迷戀,也曾經親自將海派傳奇女作家張愛玲膾炙人口的小說《金鎖記》改編成話劇。《荒山之戀》這樣精致的戲劇結構,與王安憶的這一傾向不無關系。在“三戀”中,也與其他兩篇小說,《小城之戀》和《錦繡谷之戀》稍顯平淡的敘事結構有明顯的不同。
《荒山之戀》中時間和空間的設置和轉換,相對來說是比較固定的,時間處理上基本直敘,很少有插敘和倒敘的內容。筆者認為,如果對《荒山之戀》中的這些情節和空間稍微加以藝術地提煉、精簡、加工,搬上舞臺,可以預見將是一出精彩紛呈,能夠吸引觀眾的好劇目。
鑒于《荒山之戀》鮮明的雙線敘事和戲劇式結構特征,筆者認為不能單一地稱它為“雙線結構”或“戲劇結構”,更傾向于將其定義為“雙線戲劇式”結構。《荒山之戀》這一特殊的“雙線戲劇式”敘事結構,對小說內容的豐富和主旨的揭示無疑有重大的作用。它賦予了小說更多的舞臺意味。
三、傳奇色彩
“雙線戲劇式”的敘事結構在現當代小說創作中并不多見,它提醒讀者,王安憶《荒山之戀》這一小說更多是吸取了古典的敘事方法和寫作特色,尤其是傳統戲曲中宋元南戲(明清時稱之為傳奇)和明清傳奇的敘事結構。
郭英德先生在《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中提到,“生旦俱全、貫穿始終的雙線結構特征,這是南曲戲文的情節結構與北曲雜劇最為顯著的區別,成為戲文敘事結構的核心特征。”[3]以南戲之祖《琵琶記》為例,就是一個雙線敘事結構,全劇共有42出,圍繞男主人公蔡伯喈和女主人公趙五娘雙線交叉敘述;一條線索是蔡伯喈上京趕考,金榜題名,被迫招親入贅相府,生活富貴奢華但因思念在家鄉的父母妻子而有苦難言,一條線索是妻子趙五娘獨自在家中奉養公婆,遭遇饑荒羅裙包土埋葬二老,后又一路乞討進京尋夫。最終趙五娘陰差陽錯尋至相府,相府小姐牛氏深明大義,勸說父親牛丞相迎接趙五娘,夫妻團圓。蔡伯喈得知家中情況后悲痛至極,上書辭官回鄉守孝,夫妻三人同歸故里,后得到皇帝旌表蔡氏一門忠孝節烈。
雖然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所創作的中篇小說《荒山之戀》和宋元時期的南戲《琵琶記》無論是在思想核心還是人物形象上都有很大的差異,但就敘事結構來說,二者卻有絲絲聯系,可以說,《荒山之戀》也是屬于“生旦俱全,貫穿始終的雙線結構”,男主人公音樂家和女主人公金谷巷女孩兒的故事在相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里輪番上演,最終峰回路轉,匯聚一處,在小城無聊的文化宮男女主人公相遇相戀,并最終魂魄同歸于城外的荒山。與南戲《琵琶記》的結局雖然悲喜不同,敘事線索卻不謀而合。
同時,《荒山之戀》伴隨雙線敘事而產生的“兩副筆墨”, 一冷一熱、一靜一動、一暗一明、一悲一喜相互映襯的藝術效果,也可以從南戲《琵琶記》中尋到。《琵琶記》的雙線敘事,圍繞男主人公蔡伯喈和女主人公趙五娘,一生一旦處境截然不同,蔡伯喈進京趕考,金榜題名,意氣風發,趙五娘在家中獨自奉養二老,思念丈夫,苦苦支撐;蔡伯喈奉旨招親,相府成婚,富貴奢華,趙五娘在饑荒中食糠度日,悲痛埋葬二老;蔡伯喈在相府書房彈琴抒發幽思,趙五娘身背琵琶,沿途行乞賣唱,二者強烈的對比,產生了令人動容的戲劇效果。語言上,南戲劇作家高明兼顧男女主人公所處不同階層與環境,一雅一俗,也十分貼切有趣。
此外,《荒山之戀》的四幕或四折戲劇式結構,也與南戲常見的“四折一楔子”結構有某種共通之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王安憶的中篇小說《荒山之戀》,在兩條線索,兩副筆墨,戲劇結構等方面與中國古典戲曲傳奇聯系緊密,異曲同工,更多體現了古典的敘事策略和故事韻味,深具傳奇色彩,可以看作是一曲在特殊年代里上演的精彩的現代傳奇。
王安憶是一位嚴肅而又不斷進步,實力卓越的當代女作家,為讀者和評論家們貢獻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杰出作品,在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她是不斷引領風騷的人物。在小說創作中,她從西方的理論思想中汲取財富,也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吸收借鑒,小說《荒山之戀》在敘事結構,傳奇色彩方面與中國古典戲曲的緊密聯系,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注釋:
[1]王安憶:《故事和講故事》,《漂泊的語言·王安憶自選集之四》(散文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第8頁。
[2]王安憶:《王安憶說》,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第155頁。
[3]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293頁。
參考文獻:
[1]王安憶:《三戀》,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
[2]李舒悅:《王安憶小說的敘事特征》,吉林大學,2009。
[3]佘艷春:《王安憶小說敘事的精神溯源》,《語文學刊》,2002第6期。
[4]姚娜:《王安憶小說敘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8。
[5]薛蓓蓓:《王安憶小說敘述方式述評》,《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第2期。
[6]孟慶蓮:《論王安憶小說的敘事特征》,《作家雜志》,2012第 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