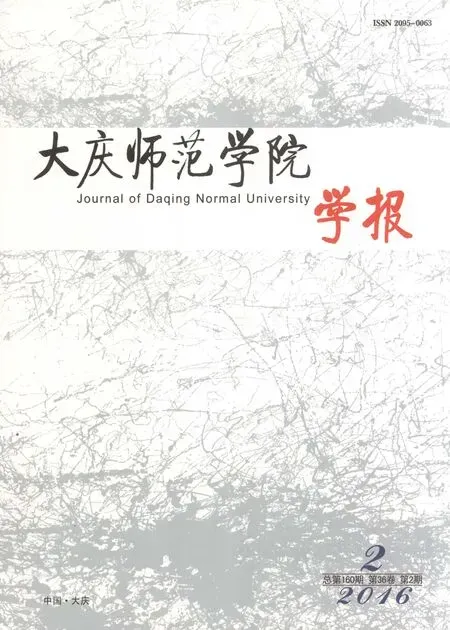交往理性與現代組織的交往困境——基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
顏 冰
(東北石油大學 人文科學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
交往理性與現代組織的交往困境
——基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
顏冰
(東北石油大學 人文科學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摘要: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交往理性作為工具理性的制衡方式,是遏制系統向生活世界入侵、賦予人們交往意義和重建交往秩序的重要前提,這為從微觀組織層面考察交往行為提供了分析工具。出于工具理性目的產生的現代組織,雖然通過內部社會化、權力運行、分工協作等方式得以存在,卻往往由于對目標和權威體系的過度強調,造成功利化交往方式、成員交往主體性喪失以及成員關系疏離等問題。喚醒組織成員交往理性,并使其從日常生活世界滲透到職業領域,恢復成員在組織中的主體地位和身份,是把組織成員從物化目標中解放出來、提高組織活動力和創造力的現實舉措。
關鍵詞: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組織情境;成員主體性
現代社會,人的社會性愈來愈體現為與組織的契合、不可分割性,組織成為個體成長的重要空間。然而組織由于具有一定物理邊界和內部管理控制體系,往往會以內部通行的行為規則屏蔽社會一般道德原則,侵蝕組織成員的思想獨立性或個體道德判斷力。隔絕于社會公共價值評判和監督的組織個體,往往用個體或團體私利綁架內心的道德法則,唯個體私利或組織利益是從,缺乏伸張社會正義或堅持一般倫理準則的意愿和勇氣。現實中,公務人員把腐敗利益作為掌控公共權力“福利”的恣意妄為,員工對企業違背社會道德生產偽劣產品,污染環境,欺騙消費者行為的冷漠和無視,公眾對部分行政人員把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行為的默許和容忍也都源于此。因此,立足現實組織情境,喚醒、發揮人之為人所具有的內在交往理性,充分調動他們的交往潛能,反思、解釋、辯論組織交往理性的內涵與意義,使人成為具有充分價值判斷和道德考量的主體,是規避當前企業、政府乃至社會道德失范的重要選擇。
一、哈貝馬斯與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概念發軔于對韋伯現代社會理性觀的批判。韋伯通過解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關聯,把“事實”與“價值”截然二分,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范疇,強調在價值理性讓位于工具理性過程中,“職業勞動領域內的內部活動,只有在社會行動脫離規范和價值,并能根據有成效的方向、目的合理的結果改變各自特殊的利益時,才會在道德上調合”[1]289。于是,工具理性逐步制度化地走入社會組織與機構,帶來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把人物化為經濟的附庸,導致社會意義和自由的極大喪失。
正是看到理性的工具化將使理性走向自我毀滅的絕境,哈貝馬斯對韋伯的“合理性”理論進行深入挖掘,提出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是所有人或彰顯或潛在具有的、申述意見、進行批判與合理論辯的一種能力,“讓行為主體之間進行沒有任何強制性、誠實的交往與對話,在相互承認基礎上達到‘諒解’與合作”[2]7。作為對工具理性的重要補充,它可以引導具有健全判斷力*哈貝馬斯認為:“具有健全判斷力的人才能合理地行動。”健全判斷力是指人們能夠在工具合理性與交往合理性之間甄別與選擇的能力,可對自身行為進行一定控制。的人合理地行動。而且,交往理性分為表達理性和行動理性,表達理性是指主體運用語言對事件的論證和質疑(說“不”)的能力[3]482-488,有助于交往者之間的互相理解與溝通;行動理性則指行為者按照所論證的合理計劃,實施具體目標的行為。[2]79-80哈貝馬斯在批判基礎上賦予交往豐富的理性內涵,實現了理性與交往的深度結合。
其實,哈貝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植根于交往行為異化的社會場景中。他認為現代社會本是“系統—生活世界”的統一體,卻由于工具理性的泛濫,致使二者發生嚴重分離,而且系統已殖民到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愈來愈喪失自身的價值判斷與標準,為經濟組織的金錢和政治組織的權力熏染,不斷走向工具化。隨著這一價值的普遍化*價值普遍化是美國功能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帕森斯的觀點,是指一種價值目標在社會進化過程中不斷擺脫具體形式,轉向抽象價值的過程,從而成為全社會行為者必須遵守的價值標準。,日常生活的交往行為披上功利外衣,人以物化方式處理主體間的交往關系,造成了道德缺失、私利橫行、文化枯竭等社會危機。因此,亟須“在日常實踐自身中,在交往理性被壓制、被扭曲和被摧毀之處,發現這種理性的頑強聲音”[4]101,以交往理性為核心,喚醒人們參與交往的潛能,鼓勵他們拒絕工具理性的決斷,合理反思、修正引導日常交往的行為規范,在質疑與辯護中實現生活世界的自我復興。在此基礎上,更需要建立主體間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的理性交往模型,倡導社會成員真誠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完成對生活方式的理想設計。
在人類社會存在工具理性與交往理性的緊張對壘,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組織也同樣面對工具理性的侵蝕問題。組織,特別是營利性組織,作為追求績效最大化的功利實體,內部也存在把成員及組織本身視作完成組織目標工具的傾向,進而忽視成員間公平、合理的對話和表達,造成人在組織中存續意義的缺失、組織整體的無凝聚力和無方向感的松散狀態。對組織成員交往理性的關注就是要改變組織情境中工具理性對交往理性的傾軋,強調以一種批判意識和反思精神考察隱匿在合理性背后的“管理與被管理”的矛盾問題。
而且,當金錢和權力作為普遍化的價值觀在生活世界泛濫時,組織境遇也不能幸免。組織同時存在著以交易雙方地位平等為前提的市場關系和以等級化權力結構為要件的層級關系,于是,無論是倡導扁平化還是科層制組織結構,成員都會面對是以平等的交換契約關系,還是以權力為標志的決策服從關系進行交往的問題。然而這二種關系作為組織微觀視域下異化了的社會關系,必需經過適時的合理揚棄才能完成對本真交往關系的復歸。交往理性概念的引入,就可以有效緩解契約關系和權力關系的張力,使成員在組織的層級體系中獲得充分的交往自由和主體性表達。
質言之,交往理性的復蘇最終歸結為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主體間質疑、辯護的交往關系的建立。這是理性完成“以主體為中心”到“以主體間性為中心”的價值轉向,使話語性交往行為深入理性,實現理性交往化的結果。現代組織中尤其存在多元主體雜糅、沖突等問題,諸如主體身份何以取得,主體與他者關系何以確立,主體間交往的組織形式等,都是組織研究一籌莫展的難題。因此,吸納以言語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行動的思想精髓,提升主體的論辯能力,對建構組織內平等、自由的對話氛圍大有裨益。
二、組織本質特征及交往困境
現代社會,組織*組織可從二個層面界定,一是將組織作為一種實體性存在,著重考察組織的結構、機制、效率以及營造的行為環境等問題;二是將組織作為管理的一種職能,強調有目的、系統地對人力資源進行整合,從而保證管理單位內個體活動與關系的有序性。本文采用把組織作為社會實體的釋義。對于人們存在及生活的意義不言而喻,正如帕森斯所說:“組織的發展已成為高度分化社會中的主要機制,通過這個機制,人們才有可能‘完成任務’,達到個人而言無法企及的目標。”[5]41組織雖為集體合作行為的產物,但其一經產生就作為非人格化的機構成為人性化世界的活動形式和背景。它與家庭、鄰里等共同體形式*需要澄清組織與群體的差別:群體往往指具有共同目標和協作意愿,能夠交換信息、溝通情感的個體的集合。組織屬于群體的特殊形式,一般要求具有精心設計的目標、明確的內部結構與人員分工,通過內部協調以及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而得到發展。一道共同構成現代人的主要生活空間,人們在此完成各種社會性功能,例如學習各種行為守則,持續接受社會化洗禮,獲得與他人共存的生活能力,等等。
就現代組織而言,其本質特征主要在于整合性、結構化和權威體系,而后兩者也是保障組織整合性的有力措施。霍曼斯曾經指出,“現代社會的大型企事業組織都是建立在人類團體的意志之上,不僅如此,組織更是這種意志的合理化反映”[6]186-187。這表明組織實際上代表了一種群體意志的整合,這一群體意志雖以個體意識活動為源泉,但已遠遠擺脫了個體自我利益中心的局限,形成關于其獨立存在性的理性認識。也就是說,組織超越了創建之初為組織締造者利益服務的功能性觀念,通過內部社會化、制定與完成目標、溝通、權力運行等方式推進保障自我生存的合理運動。進言之,組織一旦建立,便會獲得生存論上的意義,走向個體的對立面(非矛盾面),成為揚棄個體行動不完滿性的現實存在。不過,組織的整合性并不等于組織內部的均質性。實際上,組織正是通過內部的結構化布局達成表現于外的整體同一性。組織內部依照能力、知識、經歷等個體差異因素對成員進行分工,最大限度地揚棄了個體智力、體力上的局限性,使他們達成優勢整合與重組,共處于追求特定目標的協作體系之中。而且組織的結構化特性也并非來自組織領導者的主觀任性,而是對組織目標的分解和物化。這也是促使成員行為模式化和規范化的有效渠道,當成員嵌入組織結構并作為其組成部分發揮作用時,組織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
既然組織并非群氓的集合,而是目標明確、結構清晰的共同體,那么目標、結構來自何處?這里就必須預設組織內部權威及權力精英的存在。可能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目標、結構應當來自于成員的共同決定。這一觀點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即組織在前結構化時期可以共同參與決策,但組織一旦進入結構化運行軌道后,進行跨結構單元*組織跨越內部結構單元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跨越橫向的結構單元,表現組織內部平行結構之間的整合;二是跨越縱向的結構單元,即為權威等級結構的貫通。的共同決策就成為一項效率極低的不明智之舉,此時組織內部必然產生一種替代策略,即由帶有操控性質的縱向組織結構單元來設定目標,從而保證組織內部的社會控制體系因其合理性而獲生命力。無論如何,組織必然會走上由權威體系操控的道路。而且這種權威體系的存在又進一步推動了組織在意志、資源等方面的博弈與整合。
然而,現代組織愈是基于前面的三大特征不斷發展,愈凸顯出這一結構化實體對組織成員造成的交往困境:
首先,組織情境在建構成員交往現實空間時,也造成他們之間關系的疏離。理論上講,組織界限的確立會使內部成員形成基于共同目的或利益的“內群體”,這一歸屬觀念不僅會增加交往的密度和頻率,也會使交往更為平常化、普遍化和規范化。然而,組織的現實交往狀況遠非如此。雖然組織內部正式及非正式的交往活動頻繁而有序,但成員間心靈的距離并未必然因此親近,反而壁壘高筑、日益疏遠。現代組織中,個體愈來愈被吸納入標準化的生產過程。無論管理者還是普通成員都明顯感到,隨著勞動產品的獨特性在流水線生產模式下的消失殆盡,成員從勞動中獲得的安全感、歸屬感,乃至自我實現的成就感也日漸減少。這種勞動者與直接勞動成果的疏離,直接扼殺了勞動的樂趣。原子式存在的組織成員之間只是基于簡單的工作關系拼插、安置于喧囂的職業空間中,把工作視作組織強制的粗暴干涉而感到厭棄。而且面對與陌生者合作的交往現狀,他們在自保觀念的支配下往往把真誠勞作的愿望審慎隱藏起來,無法敞開心扉、真誠交流,造成交往關系的冷漠和疏遠。
其次,對組織目標的不當強調往往導致功利化交往方式在組織中泛濫。組織存在的依據和理由就在于對組織目標的履行和實現。戰略計劃、機構設置、人員安排等均直接服務和指向組織目標。以目標為核心的組織定位成為組織內合作和效率的源泉。應當看到,目標導向固然是組織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單純以利益最大化為旨歸的目標驅動卻會造成組織內功利性交往方式的盛行。傳統社會和諧共生的家庭、鄰里成員由于抱有一種共同體觀念往往以協作互助方式毫無芥蒂地交往。而在現代組織中以理性、利益為先導的組織行為不大可能延續傳統互相扶持的交往習慣。在工具理性的操控下,互助合作方式被純粹量化的利害考慮所操控,交易、價格成為交往方式的粗鄙描繪。不僅組織工具性地對待成員,成員間也充滿了以物質利益為重心的互相利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采取了像對待機器一樣的物化態度,以競爭者、對手的方式功利性地看待對方,難以再現真誠交往、親密溝通的身影,進而導致組織整體道德水平的滑坡。
再次,組織權力、結構的僵硬束縛導致成員交往活動中主體性喪失。組織總是以集合之力尋求一種穩定、有效的秩序結構。在組織中通常同時存在權力結構、人際關系結構,以及規范結構和行動結構*規范結構與行動結構的劃分來自于斯格特在《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中對戴維斯“規范體系”和“既存秩序”的分析。他把將戴維斯的規范體系稱為“規范結構”,包括價值觀、規章制度和角色期待等,是組織建構過程中一系列指導參與者行為、相對持久的信條和規范;把戴維斯的“既存秩序”解讀為“行為結構”,主要指參與者采取的行為。這種把組織結構區分為“事實”與“應當”的分類方式有助于細化不同結構層次的功能。等多種結構模型*這些結構模型是對組織客觀形態的理論抽象,為從功能主義視角考察組織的結構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框架。。客觀地說,這些組織結構不能憑空建成組織的合理秩序,需要與組織成員能動地結合才能發揮出現實效力。沒有人的參與,就沒有組織的結構秩序,甚至連組織也不會存在。正是在成員的服從、遵循乃至協商對話中,組織及其結構才獲得存在的真實性。這是組織與人內在相關性的集中體現。但是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及在社會中滲透力的增強,組織愈來愈走向形式化成為理性模型,“這個模型是個‘機械’模型,把組織作為可操作部件的結構,每個部件都可以單獨改變,以提高整體效率”[7]5。包含越來越多理性因素的組織像一架精密運轉的機器,不僅要求自身實現標準化、規范化和形式化,也對組織中的人提出理性化要求,即人一旦參與到組織中就需要摒棄情感、偏好與價值觀念,在崗位的甄選下與組織建立契約關系,作為組織部件投入組織的運行過程。此時,組織已逐漸消解了成員的主體性、能動性因素。其實,組織的這一理性運作模式有助于規避個體偏見與非理性情感的消極影響,使組織步入高效運行的軌道。然而更應看到,人在融入組織結構之后,組織的結構秩序實際上造成對人主體性的吞噬,人以物的形式出現時,他們通過交往建構組織生活的愿望也被完全瓦解。
概言之,上述困境實為組織內部目的與手段的倒置。一方面,組織作為超越個體有限性的集合體,本應在創造更大生產效率的同時,也應使人在組織交往中獲得更多支撐和扶持,然而,現代組織僅利用工具性的物質手段不斷驅趕成員每天機械重復工作內容,使他們深陷毫無創造性的勞動中無法自拔,疏離于工作意義和價值的思考,這種組織運作形式極大地異化了成員間的交往關系。另一方面,組織本身也由手段轉化成目的。組織雖作為實現人類更宏大、更復雜目標的理性選擇進入人們視野,卻在獨立后演化為羈絆人性的牢籠。組織要求人在組織生活中采取非情感、非偏見的價值中立態度,即便這對組織效率好處頗豐,卻大大造成了人在組織中的空虛和冷漠,并已滲透、蔓延于整個社會。因此,在審慎考察組織本質的基礎上,更應對組織內交往關系進行深度反思,在鼓勵主體性互動基礎上賦予參與者更多自由和意義,消解組織對人性的壓抑程度,重建組織中成員的主體地位。
三、喚醒組織情境中的交往理性
組織作為以恰當分工和結構為依托建立的合作機制,是一種基于能力差異互補的協作體系,是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等物質交換關系為基礎的集合體*在生產與交往這對范疇的關系問題上,不同學者觀點有所差異。哈貝馬斯在不否定勞動之于人社會性、倫理性作用的基礎上,把交往理論向語言轉向推進一步,將社會性互動與勞動能力并列為人的本質,強調自由、有想象力的勞動必然與語言相伴而生,轉而強調語言對于交往行動的重要意義。而依據馬克思的觀點,生產和交往雖互為前提,相輔形成,但任何時代的意識都反映了這個時代生產力狀況,甚至每個人、每個社會都會帶有鮮明的經濟印記,由此物質交往對精神交往具有決定意義。這從一定角度確證了組織產生于彌補單獨個體能力與創造性不足的觀點。因而充分吸收對這兩種觀點的合理內核可為組織問題分析提供更加有益的理論視角。。它雖依靠代理人運作,卻已成長為獨立擁有權利、承擔責任的實體。同時這一實體性存在也營造了交往活動發生的背景和空間,即組織情境。組織情境中時刻發生著組織實體和個人的相互選擇,成員情感興趣的交流與共享、意見表達、思想溝通等也成為組織行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然而長期以來,在科學主義、工具理性主導下組織過于關注結構和制度等外在約束方式的功用,極大地忽視了組織內交往理性的存在,以及成員對協商對話等交往行為的需求,造成如上諸多交往困境。實際上,交往理性的高揚在組織情境中具有一定合理性,它不僅是規避組織困境的途徑,也是扭轉組織理性工具化趨勢、恢復交往主體性的必然選擇。
第一,交往理性內置于組織及其成員所具有的社會屬性之中,是社會化、組織化進程開啟的理性基礎。無論從邏輯還是歷史角度考察,人都毋庸置疑地具有社會性。人能夠擺脫與動物為伍的自然狀態關鍵在于他們獲得了極具深意的協作勞動、語言溝通等能力。通過勞動實踐建立與自然界的對象化關系,通過言語建立與他者的合作互助關系,個體對自身與自然做出劃分、獲得自主意識的同時,也在勞動和言語交往活動中確證了自我身份[8]291-302。所以,人的社會性很大程度上是人內在交往理性的外在表現。換言之,正因為人具有交往的理性能力和需求,才會擺脫個體獨自生存的境遇,從孤獨走向合作。所以,交往理性并不是人們重新獲得的理性能力,它從人類誕生那一天起就已內置于人的本質之中,建構了人的一切活動和行為。只是它與人的本質如此接近,使得人們往往把其作為天賦能力視為不見。因而,交往是人本能的一種能力,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立足于肯定人具有交往能力的基礎上,人們才能夠學習文化傳統和道德規范,展現其社會性,完成社會化的轉變。
第二,組織情境中的交往行為是交往理性向職業領域滲透的必然結果。人所具有的交往理性必然植根和展現于作為人們職業生活重要載體的組織當中。雖然組織作為人群的集合往往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但組織基于集群和效率優勢的組建初衷,也表明它是人們運用交往理性的產物。然而長期以來,組織中工具理性因其能夠有效地選擇達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而在現代社會大行其道,這極大地掩蓋了組織中成員間的交往需求。實際上,在組織背景下,人不僅要進行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交換與融通,還需要坦誠對話、表達合理意見以及慰藉情感。與工具理性分立的交往理性奠基于生活世界和社會的合理化,通過與工具理性的合題達到“人合理性”的整體構建。
誠然,單純就功能性組織而言,成員往往在表象上僅僅被視作滿足組織及個體需求的功能載體,而對他們是否具有和發揮交往理性不置可否,甚至嗤之以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交往理性內在于人,即便人自身的交往理性暫時受到壓抑可能不會帶來組織利益的損失,反而可能由于成員質疑能力的缺位而提高組織效率,可是,如果長期以往下去,組織將蒙受成員創造性缺乏、主體性淡漠、歸屬感下降等巨大代價,甚至會使人重拾工具性、自我利益為中心等機械定位,最終將造成組織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和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力資源的匱乏。因而,交往理性在組織情境中的彰顯是現代組織保持上升態勢、不斷進步的重要基礎。組織情境中的交往理性的伸張可以重塑組織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打破精英管理層的獨斷格局,使組織成為多元文化碰撞、交鋒的共同體,獲得不斷創新發展的能力。
第三,對組織情境中交往理性的重視是恢復成員主體性地位和身份的必然選擇。就其本質而言,交往理性研究是對從一己之我走向“我—你”互動共生模式的有益探索。在此過程中,他者作為另一主體走入自我的視線,幫助自我實現身份的體認與確證,從而建構出主體之間的交互合作關系。在以理性組建的現代組織情境下,與組織相關的利益相關者、與組織權威相對的普通成員也應進入主體間的世界,成為建構交互主體性的共在主體。應該看到,長期以來組織的主導地位一直由權力精英所把持,外部利益相關者與內部基層參與者往往作為客體處于他們的操控下,管理與被管理、服從與被服從的糾結成為主客二分式哲學理念在組織領域的集中體現。然而,這種單一主體性思維在保持組織同一性方面有一定作用,卻付出了人性壓抑與扭曲的巨大代價。理論界大批學者致力于從組織立場出發建立理論模型,采取多種激勵手段,企圖實現組織與個人融合的理想,可總是差強人意,究其根源就在于他們在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下早就把人作為可操控、可利用的對象之物,又何談人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的發揮呢?改變這一狀況之根本就是要建立一種多元主體并存的組織觀念,擺脫管理者組織權威的壟斷姿態,把成員平等吸納到組織管理體系中,建立知識分享與重塑機制使個體知識匯入組織的集體“智庫”,使他們在組織中獲得同等的參與主體地位。
組織中的交往理性不僅賦予成員表達意見、論證觀點的理性能力,還鼓勵他們的異質性思維,通過組織內部多元的溝通與反饋平臺,使他們能夠對既有的規范體系進行質疑,成為“不僅具有判斷能力和目的合理的行動,具有道德審判力和可信任的實踐,具有敏銳的評價和美學表述能力,而且具有能力針對自己的主觀性進行反思活動,具有能力洞察對自己認識方面、道德實踐方面和美學實踐方面表達的一系列不合理的限制”[1]39的主體。
因此,交往理性及行為并不是對組織情境的牽強嫁接,而是組織及其成員內在本質的再現。組織中管理層與被管理層交往理性的喚醒,會使他們交互成為對方工具化行為掣肘,進而塑造出組織公平、誠信的交往秩序。誠然,敢于承認不同群體的異質意見并賦予他們充分辯論的機會和平臺,是對組織精英提出的重大考驗。換言之,組織精英充分包容下成長起來的交往理性才是組織煥發生命力和創新性的源泉。
[參考文獻]
[1]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M].洪佩郁,藺菁,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2] 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兼論與馬克思學說的相互關聯[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 Thomassenl. Communicative Reason, Deconstruction, and Foundationalism: Reply to White and Farr [J]. Political Theory, 2013(41).
[4] 德特勒夫·霍夫斯特.哈貝馬斯傳[M].章國鋒,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00.
[5] Parsons T R.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M]. Free Press, 1960.
[6] Homans G C. The Human Group [M]. New York: Harcourt, 1950.
[7] W.理查德·斯格特.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M].黃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8] Kieses A. Communication-Centered Approaches in German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J]. SEIDL David.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3, 27(2).
[責任編輯:陸靜]
中圖分類號:C9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063(2016)02-0018-05
收稿日期:2015-12-2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全球化交往視野中的組織文化認同研究”(12YJCZH241)。
作者簡介:顏冰(1976-),女,黑龍江雙城人,博士,教授,從事管理哲學、組織文化與傳播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