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奔
⊙ 文 / 陳 鵬
夜奔
⊙ 文 / 陳 鵬
陳 鵬:一九七五年出生,國家足球二級運動員。作品散見于《十月》《當代》《青年文學》《大家》《山花》《北京文學》等刊,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等選刊選載,曾獲多種獎勵。現(xiàn)居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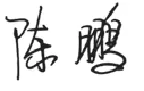
吳糧絕,卒饑,數(shù)挑戰(zhàn),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
——《史記·吳王濞列傳》
一
“是他?”
“是他。”
“大四?”
“剛畢業(yè),二十二。”
“看起來三十。”
我沒感覺。你對大學剛畢業(yè)的菜鳥能有多少感覺?馬馬虎虎吧,能攻善守,技術速度還行。不知上了場,是秘密武器還是銀樣镴槍頭。
“我們就缺一個頭球好、有身體優(yōu)勢的拖后。”本杰說。他每三天跑一趟師大球場,像打了雞血的獵狗追蹤這小子半個月。“關鍵的關鍵,年輕啊!”
“是,嫩泱泱的小鮮肉。”
“你覺得還行?”
“你說呢?”
“還行。”
我沒說話。但年輕就像西門慶褲襠里驢大的行貨。等你年過四十,在球場上再也不能像他們一樣不知疲倦滿場瘋跑的時候,你才發(fā)現(xiàn)年輕有多好。
“像騾子一樣好,”本杰有些著急,“你瞧。你仔細瞧,回身反搶那一下有多快。”
我不是傻子,更不是瞎子。我把滿嘴的煙吐出去,再深吸一口沾著師大熱辣草皮味兒的腥燥空氣,直接由肺部吞入胃底送往全身。血里很快都是這氣味了。
“時間緊任務重。像樣點的都被別的隊伍拉上山啦。”本杰的口吻就像個廳局干部或軍區(qū)政委。
場上的比賽越來越爛。以我的標準,他們除了年輕一無是處。可當你年輕的時候,你哪知道你除了年輕什么也不是呢?我估摸這小子身高一米七八,體重七十五公斤。沒理由不讓他來。
“羅坤知道?”我問。
本杰搖搖頭,說:“你頭一個。”
“他知道了,會咋說?”
本杰還是搖搖頭。
“十八年了。”我說,“羅坤是惠恩鐵打的拖后。巴雷西一樣的拖后。”
“十八年啦。”他說。
“巴雷西終老A米(注:A米,即意甲球隊AC米蘭),場場首發(fā)。”
球場上的喊叫聲奔跑聲喘息聲傳得很遠,塑膠跑道上有幾個特清純的姑娘穿著短裙戴著耳麥捧著書裝模作樣。她們一律營養(yǎng)不良似的瘦瘦高高,皮膚白得發(fā)紫,像結了一層霜花。
“總要有新人進來。”本杰說,“遲早的嘛!”
我一聲不吭。
二
你肯定看出來了,這是一個關于球隊新老交替的故事。沒錯,大概是這意思。但沒把它寫出來之前我也不知道故事會往哪個方向發(fā)展。我真沒譜。說句不負責任的話:寫哪兒算哪兒吧。
但我保證這是一個好故事。你們都是我的朋友。我沒必要瞎編一個故事糊弄朋友,更沒膽子寫一篇糟糕的小說隨便交差。尤其是對百般挑剔的文學雜志主編,我哪兒敢呀!所以……
好,咱們接著講。
三
我和本杰沒想好如何把新人高燁進隊的消息告訴羅坤,似乎合謀干了一件丑事。本杰建議周末野球賽直接把高燁叫上,他來了再說。我設想過最壞的結局:羅坤因為這事砸了球鞋,背起行頭揚長而去,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外面排著隊邀他入伙的球隊多的是,再踢幾年野球賽,甚至四十歲以上中年組業(yè)余聯(lián)賽毫無問題。何必為一個小屁孩子頂替了他而受辱?
這是我絕不想看到的。
那我何必答應本杰跑到師大去找羅坤?
這個鬼迷心竅的大黑胖子最近總在念叨“新老交替”:“世上沒有任何一支球隊不‘新老交替’。巴薩用內馬爾擠走伊布,皇馬王子勞爾也遠走沙爾克,C羅干掉了他;里貝里丟掉拜仁主力,就連瓜迪奧拉也是五冠功勛教頭海因克斯的替代品……”
我說:“那是世界強隊,不換血不行,但惠恩就是惠恩也只是惠恩。一幫老兄弟在昆明業(yè)余賽場摸爬滾打十八年,最大心愿莫過于守著惠恩踢一輩子,踢不動了就在場上遛彎,能遛幾年算幾年。”
“很多隊伍都在換。”本杰說。
“鉆石年代、白馬廣告也換?”
“鉆石換三個中場,白馬換一個前鋒。”
“唉!”
“亞洲展望昆明區(qū)下月開打。”他用牛一樣濕漉漉的大眼珠子看我。他真黑,極像尼日利亞教頭斯蒂芬·凱西。我在一個短篇小說里專門寫過本杰的故事(《清白》),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我保證不會讓你們失望的。那是一個又硬朗又神秘又傷感的好小說。
“你——殺手李,也比過去慢多了,”本杰說,“十年前,你快得像沙塵暴。”
“人終歸要老。偉大的球員馬拉多納、巴喬都沒撐過三十五。我四十啦。羅坤也四十啦。”
周六下午,高燁現(xiàn)身海埂五號場。本杰將他介紹給大家,他一概點點頭。我看他一副穆里尼奧的派頭,就差一件風衣、一根牙簽了。他來到我面前。本杰介紹說:“這是惠恩第一球星李果,綽號殺手李。”他還是點點頭。我低頭穿鞋。不看他。一眼都不看。
隊尾的羅坤小心換上獵鷹9球鞋(注:獵鷹9,為阿迪達斯二〇〇五年推出的專業(yè)戰(zhàn)靴之一),將護腿板塞進干凈的金色球襪。他的衣服襪子永遠干干凈凈,不像桂子、小寶等人的球襪摔地上砰砰響,其濃烈氣味十公里外也能聞見。羅坤的球衣十八年來一直冒著清爽的雕牌洗衣粉香氣,就像他的防守讓人踏實稱心。
本杰向羅坤介紹高燁。
“你好。”羅坤伸出手。
那小子懶洋洋地點頭,懶洋洋地和他握了手。
我一陣難過。
這場球羅坤、高燁各上半場。羅坤坐鎮(zhèn)丟了一球。下半場高燁表現(xiàn)不錯,速度快、反搶也快,但傳球質量和羅坤沒的比。全場3比3平。
“我以為我還有機會再上。”羅坤笑著說。
(注:與正規(guī)比賽不同,在昆明的野球比賽中,被換下場的球員可以再上。)
“讓小高練練。”本杰說。
“他挺好。”
“年輕啊!”
桂子問本杰亞洲展望報上了沒有,本杰說報上了,下月開打。
“小高跟我們?”桂子說。
“是。”
“拖后?”
本杰點頭。
“主力?”
本杰沒說話。大伙都不說話。五號場突然靜下來,能聽見微風掠過草皮的刺啦聲。球場又恢復了蔥郁旺盛的生命力,順滑得像上好的土耳其地毯。
“說話。你說話!小高主力,還是坤哥主力?”
羅坤抽出護腿板,脫掉獵鷹9,再脫下球衣球褲,亮出白花花的肋條和明顯下墜皺縮的小腹。
“到時候看。”本杰說。
“哪樣叫‘到時候看’?”
“到時候看,就是到時候看。”
“首發(fā)只有一個。”
羅坤沉著臉。我能嗅出場上的燥味、血味和海埂早年圍海造田的淤臭味。
“哥幾個,我先走。”羅坤收拾行頭往外走了。沒看高燁,也沒看本杰,他沖我揮揮手。我也沖他揮揮手,眼瞅著他消失不見。
小蔣說:“要我看,還是坤哥首發(fā)。”
高燁說:“我扛得住。”
沒人搭腔。
“每天早上一個雞蛋,就一個,絕對跑得快。”高燁又說話了。
“這幫老倌每天早上干三個。”本杰說。
他們嘿嘿笑。我埋頭喝水。說句公道話,這小子還行。
“吃十個也不行啦。”桂子說,“吃火藥也不行啦。”他笑著拍打肥碩的大肚皮,“你多大?”
“二十二。”
“我二十二的時候一天一場球,一星期六場。一晚上干八次。你行嗎小伙?”
高燁笑得挺傻。
四
我往西站方向開,羅坤的家離那兒不遠,我們通常在“西門驛站”酒吧碰頭。那地方酒很便宜,五塊錢就能要一瓶雪花。
我要了五瓶,坐在露天前廊上等著。天差不多黑了,前廊亮起星星點點的霓虹。我想等他來了再要吃的。西門的酸辣面不錯,我能一氣吃兩碗。他出現(xiàn)的時候滿頭大汗,仍穿著惠恩的5號球服,和場上的羅坤唯一不同的是,他穿了平底膠鞋。
“跑過來的,四公里。”他說。
“你牲口變的嗎?咱剛整完一場球呢!”
“半場。”他拎起雪花咕咚喝下一半。
“每天都跑?”
“想跑就跑。”
“店呢?”
“小許看著。一個版納小傣族。”
“漂亮?”
“九〇后的小姑娘家。”
“你不下家伙別人早晚下家伙。肥水不流外人田。”
“瞎扯。”
“醒醒吧。”
“行啦行啦,莫像我爹一樣。”
一群姑娘小伙迎著彩燈進來,像走在一堆彩色泡沫里。空氣中有法國梧桐的香味。
“你咋想的?”我說。
他抹抹嘴巴,看著我。
“我必須首發(fā)。”
我的心臟怦怦地跳。
“老李,我必須首發(fā)。”他說,“十八年了,哪場球錯過首發(fā)?”
我知道,我根本不用說話了。不用說任何廢話。把面前的酒干掉就行。收銀臺飄出劉德華的老歌《謝謝你的愛》。
當著羅坤的面,我忍不住罵本杰不該這么做,也把自己罵個半死。之后我們回顧了十八年來惠恩的經(jīng)典戰(zhàn)役。
天越來越黑,我們已經(jīng)看不清對方的眼睛。我要了油炸石頭魚和小鍋米線,破例沒要酸辣面條。然后羅坤告訴我說,他爹不行了,胃癌晚期。我問:“哪樣?”他又說一遍。我看了看剛進來的姑娘小伙,抬頭望見鋼藍色天空出現(xiàn)一輪乳白的新月。我問他住哪家醫(yī)院?要不要兄弟們湊錢幫忙?他搖搖頭。
“真正難過的是,”他說,“一點辦法也沒有。醫(yī)生說,最多兩個月。”
我不知該說什么才好。
又進來一堆半大的孩子,都是附近高校的愣頭青。他們將一直喝到后半夜,然后找地方嘔吐蹦迪消夜打炮。
想當年,羅叔駕著巨大的、像匹馬似的“幸福250”摩托,送我們去少體校練球,羅坤坐中間,我斷后。摩托開得飛快,突突突的轟鳴能把人的小雞雞震癟。我和羅坤做了三十年兄弟。十幾歲二十歲的我們,是昆明足球圈的名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沒混上職業(yè)隊只能怪運氣和老天爺不公。人嘛,不是你想干什么都能或必須干成。
“走,帶我看看他。看看羅叔。”我說。
“算啦,算啦!”他說。
“走走走!”我催他。
我硬拽他起來,打車直奔云大醫(yī)院。進入二號住院樓,我酒勁兒醒了一半。我們沒坐電梯,一路小跑直達六樓腫瘤科。羅叔就躺在左手3號床上酣睡。我第一眼沒認出來。——兩三年沒見,他頭發(fā)白了一半,深陷的眼窩和干癟的顴骨像鋼條一樣支棱著。羅坤想叫醒他,我使勁兒擺手。我們抱著胳膊站在床邊瞅他,頭頂白熾燈發(fā)出嘶嘶叫聲。我很難相信眼前木乃伊似的羅叔,就是當年叱咤國防體育場的鐵衛(wèi)。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有他的昆明隊才是正兒八經(jīng)的昆明隊。一九八五年昆明和遼寧踢友誼賽,他一記飛鏟封住快馬李華筠的抽射,全場雷動。那天我和羅坤跑到更衣室去看。他脫下5號球衣,蹬掉金杯皮釘鞋;鞋幫上的皸裂細如發(fā)絲,鞋尖被草皮擦得新嶄嶄的,快得像兩把刀子。
“羅叔要進國家隊咯!”我說。
“哈,那種破隊,去了丟臉。”他說。
他的隊友們咋咋呼呼。
“國家隊連香港隊都整不過。”(注:指一九八五年著名的“5·19”球賽——中國隊在世預賽小組賽中1比2不敵中國香港隊,爆冷出局。)
“換我們上去絕對拿下香港隊。小崽子,你們信嗎?”
“信。”
“你們兩個好好練,將來拿下世界杯。”
“好好練,拿下世界杯!”羅坤大聲附和。
羅坤可是羅叔的種,絕對上乘的足球坯子。
“羅叔,你啥時送給我皮釘鞋?”我問。
“等你長大。”羅叔說。
我長到十七歲,已經(jīng)是少體校主力前鋒,很快有了自己的皮釘鞋。它能帶你滿場飛奔,踢出美妙的弧線球,還能亮出六顆鋼釘廢了別人的腿。我去羅坤家蹭飯時從床底翻出羅叔的金杯鞋。皺得不像話,到處是裂口,像中毒的耗子一樣奄奄一息。我沒法相信它就是我夢寐以求的寶貝。羅叔從昆明隊退役后干了物理研究所伙食團團長。他退役很早,據(jù)說因為廢了別人一條腿。——在一堂稀松平常的訓練課上,他將隊友的脛骨踹成三截。
現(xiàn)在我們安靜地站在病床前,鄰床男人輕輕打鼾,就像皮釘鞋不斷開裂。外面沒有聲音,連腳步聲也沒有。人這輩子,真快。
我們悄悄出來,坐在走廊上。兩排空蕩蕩的綠色塑料椅子癱在燈光下面。到處是臭味、消毒水味、食物殘渣味。
“哪天手術?”我說。
“快了。”羅坤說。
我掏空錢包里的幾百塊錢,卷巴卷巴塞他兜里。他坐著沒動。
夜幕突然打開又重重落下,能看見窗外密集的燈火以及更遠處的山巒和云的影子。
“你走吧。”他說。
“陪你坐會兒?”我說。
“不用。走吧。”
我坐著沒動。我們就這么坐著。不說話更好。在哪兒坐都是一樣的。無論西門還是球場,無論醫(yī)院還是“幸福250”。哪兒都一樣。
五
這場球羅坤早早到了,早早換好行頭熱身跑圈,之后拉上我們玩搶圈、遛猴。高燁很晚才到,和大胖子本杰練長傳,又叫上彭翔練射門。桂子突然指名道姓地說:“你一個拖后射哪樣門,殺手李的專利嘛!”
高燁一聲不吭。說心里話,我不喜歡高燁。
我走過去,將高燁擺好的皮球一記正腳背發(fā)力,彭翔飛身撲救,但破網(wǎng)的聲音又硬又脆,我愛死這聲音了。彭翔起身拍拍巴掌。高燁軟綿綿助跑,射門高得離譜。
“打飛機呀!”桂子說。
高燁茫然地望向本杰。大光頭本杰向他傳球,高聲說:“來來來,你就讓殺手李一個人玩兒去!”
比賽開始了,對方球隊是支從未交過手的球隊,讓我們吃盡苦頭。他們年輕,速度快,體能好,我們隊里除了高燁沒人能跟得上他們。羅坤連續(xù)兩次被對方突破得分。大約第三十分鐘,本杰撤下羅坤換上了高燁,我們的后防才再沒失守。
中場休息時,羅坤脫下獵鷹9,黃色球襪耷拉著,露出護腿板。
高燁氣喘吁吁地說:“對手火力太猛,兩個邊后衛(wèi)不協(xié)防不行啊!”
“羅再上半小時?”我說。
沒人響應。
羅坤說:“我跟不上去。”
“你上去拉拉對方的體能也好啊,要不你上,我歇半小時?”我說。
“你殺手李下了,哪個進球?”
“跑吐血啦!”我想說,上半場沒一次射門,更別說進球了。
“場上,小高表現(xiàn)不錯。”羅坤說。
這時桂子申請下場,羅坤上。于是羅坤被頂?shù)搅撕笱恢谩_^去他不是沒踢過中場,腳法和意識沒的說。但下半場他就跑了二十分鐘,又讓桂子重新上去。
“坤哥你繼續(xù)踢呀!”桂子說。
“我累了。”羅坤說。
羅坤將穿上、脫下、又穿上的獵鷹9脫下來。這回卸了長襪、護腿板,和球衣球褲一起塞進雙肩包。他又是那個穿黑夾克、黑皮鞋的小老板羅坤了。
終場哨響,惠恩1比3敗北。我下場時沒見到羅坤。本杰晃著黑亮的大腦袋說:“走了。我拉不住。”
這么多年,我敢保證羅坤頭一回早退。
“你放他走?”
“他說家里有事。”
“比足球重要?”
“他爹——”
“他爹還沒做手術。”
“老李,你莫激動。坤哥四十一啦。”
“四十。”我說,“比我小五十八天。”
“好好好,四十。”本杰說,“你自己說,還有多少四十的老鳥追得上殺手李?”
“都掛靴算逑。”
我將我的阿迪COURE砸地上,嘭一聲響。高燁收拾東西往外走。
“有意思嗎?”小蔣說。
“有意思嗎?”張勇重復他的話。
“坤哥再踢十年沒問題。”小孫說。
“小高真心不錯。”彭翔說。
“我們究竟要什么?”段凡說,“勝利,還是快樂?”
“沒有勝利,咋有快樂?”桂子說。
“算逑,解散算逑,張勇重新招兵買馬。”小蔣說。
“兄弟們,現(xiàn)在不就換了一個中后衛(wèi),就一個。”本杰說。
我們被一種深深的來自草皮深處的挫敗抓住了。我承認我累得夠嗆。一幫年過四十的老家伙不是想贏哪個就贏得了哪個了;一場九十分鐘的比賽之后,需要三天才能緩過勁兒來。想當年,我的發(fā)小羅坤比巴薩惡霸普約爾還狠,他和彭翔搭檔的后防線一直讓人放心,直到三四年前,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再也干不過年輕小伙們了。干不過了。可為什么每周收到本杰短信,又屁顛屁顛跑來?來了還像騾子一樣較真?
我倒真希望有人接我的班。但那幫小子們各有各的山頭,加入一支老不死的球隊,開什么玩笑?
六
小說寫到這兒我越來越確信它會是一部佳作。你別以為我拉拉雜雜寫的全是雞毛蒜皮。更別以為我寫足球不招人待見。讀我小說的朋友都知道,我寫足球醉翁之意不在酒。小說里踢球的男一號“球星”李果,沒準就是寫小說的陳鵬。沒準。我說的只是沒準。說不定真和陳鵬有什么關系。
重要的是,眼下這故事如何推進。
我承認我有點蒙。再往下必須放狠招了——我指的是事實。絕非虛構的、來自我們惠恩足球隊、千真萬確的事實。我非得征求當事人的同意不可。
好在他們說了——“沒意見”。
那好,先說說我的好兄弟——羅坤。
他直接去了醫(yī)院。
羅叔望著他一步步走進來。
鄰床的那個病友剛下手術臺,鼻子里插著管子,身上裹滿紗布,白得晃眼。
“他運氣好啊。真好。”羅叔說。“他”指的是病友。
“你不會有事。”羅坤說。
“你又不是醫(yī)生。”羅叔說。
“我問過醫(yī)生了,小手術。”羅坤說。
“我也問過了。”
他們半天沒說話。鄰床那位哼都不哼一聲。
“又整一場?”
“輸了。”
“我們昆明隊很少輸。”
“惠恩也很少輸嘛。”羅坤想了想,又說,“四五年前,我們打遍昆明無敵手。”
“你們老咯。”羅叔努力坐起來。羅坤幫他拽了拽枕頭,頂住后背,盡可能讓他舒服些。他能聞見他爹散發(fā)的、難以忍受的臭味。衰敗、腐爛,難以挽回。最可怕的莫過于他爹自己根本察覺不到。
“沒老。還行。”羅坤冒了一句。
“不服老不行。”羅叔說。
“沒老嘛。才四十。”羅坤說。
“我是說,你要服老,就更不行。我退隊之前那場球拼天津,就在拓東。我們先丟一個,下半場硬是打回兩個。2比1。”羅叔豎起食指中指,精瘦的臉閃閃發(fā)亮,“當時天津有左樹聲。國家隊主力啊,上來就進一個,根本不把昆明隊放眼里。我們最后十分鐘搞定兩個。最后十分鐘。他們想扳回來,晚了。”

⊙ 柴春芽·戈麥高地1
攝影手札:
這些照片與一次長久的駐守有關。它摒棄了藝術上的功利主義和攝影上的矯揉造作。它和攝影者個人的生活構成血肉聯(lián)系。二〇〇五年八月,我被迫辭去《南方周末》的記者之職,索性離開都市來到康巴藏區(qū)一處高山牧場義務執(zhí)教。這些照片攝于名為戈麥高地的四季。四季蒼茫,因而這些照片暗含滄桑。十年易逝。我珍存隱匿在這些照片中的苦寒歲月。如今凝視,我知道,我去過,愛過,生活過,痛苦過,然后離開了,懷念著。
本期插圖作者 / 柴春芽:鳳凰網(wǎng)主筆,作家、導演、靜照攝影師。
他聽了不下百遍,都能背出誰犯了規(guī),誰吃到黃牌,三個球都誰進的。
“你煩我了?”羅叔說。
“我不煩。”羅坤說。
“你就是煩了。我認得。早死早了。”
羅坤沒吭聲。
“我小腿咋斷的?”羅叔說。
“不是你的腿。是你把孫杰的腿——”
“我記錯啦?”
“錯啦。”
“嗯,是我把孫杰的腿……他退役,我也退役。”羅叔用力咳嗽,像盯一只螞蟻一樣盯著他,“孫杰剛進隊,才二十三歲。那個球是二分之一球。他年輕我就讓他?憑哪樣?讓了就不是足球,是乒乓球。我迎上去。嘭——”
他微微發(fā)顫,能想見這一腳的慘烈以及小腿脛腓骨涌出的劇痛。那是每一個球員最最害怕的。可足球容不得你害怕。
“我腿斷啦。”羅叔說。
“是孫杰的腿。你又錯咯。”
“是我的腿。”
他望著羅叔。這張臉干癟、蒼白,像拆毀的房子。他想起球賽之后傷痕累累的海埂五號場。
“老子三十四歲就退啦。”
“到底是——”
“你走吧。”羅叔閉上眼睛,又睜開。
他收拾床頭柜上的小東西。猛然傳來咋咋呼呼的歌聲。他們豎起耳朵。是隔壁病房的人用手機聽歌呢。
“我們下個月比賽。”羅坤說。
“多整一天是一天。”羅叔說。
“爹。”他說。
歌聲消失了。
“還沒找著合適的?”羅叔說。
“沒有。”
“我抱不著孫子啦。”
他沒說話。
“球場上有傷停補時。我呢,還有傷停補時?”
“莫亂想。”
“走吧,走吧。”
羅叔生硬地揮揮手,他不讓人陪護。他可是昆明球壇硬邦邦的鐵衛(wèi)啊。羅坤看看窗外,天黑得像一件扔掉的舊衣服。病房黯下來。他沒開燈,轉身走出去。
七
都第七章啦。數(shù)字“7”難免讓人想起小貝,想起C羅,想起菲戈。總之身披7號戰(zhàn)袍的球星大多身手了得,算得上高手中的高手。但我更喜歡數(shù)字“10”。你猜對了,我從小穿10號。前面我說過偉大的馬拉多納、偉大的巴喬都是10號,當然還有偉大的羅納爾多、偉大的貝利、偉大的濟科、偉大的齊達內、偉大的梅西。最偉大的還是10號。
所以你能猜到身披10號的我心里有多拽。
據(jù)說當年被羅叔踢斷腿的孫杰也是10號。一個萬眾期待的未來巨星,一個堪比后來健力寶黃金一代的翹楚和天才。他二十三歲斷腿、退役。十多年后有人在某個停車場見過他,手里拎著酒瓶子跟人討要車錢。誰也看不出來這個胡子拉碴的老家伙究竟幾歲,四十多還是五十多?更沒人能看出他踢過足球。除了那雙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羅圈腿,他與足球運動員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扯遠啦。
到底是羅叔廢了孫杰的腿,還是孫杰廢了羅叔的腿?
如此重大事故,羅叔怎么可能記錯?
八
每周六的野球賽,你到了場邊才知曉對手。全由雄冠公司負責包辦比賽兩隊、三名裁判和一箱礦泉水,場租均攤。此役對手很差勁,羅坤繼續(xù)首發(fā)。上半場我一氣灌了三球。中場休息時高燁想換下羅坤,我告訴他:“再等等。”
高燁看著我,又看看本杰。
“羅再整十分鐘。”我說。
兄弟們都不吱聲。高燁一屁股坐下,抽出護腿板扔進背包。
“你什么意思?”我說。
他腮幫上鼓出一條條肉棱子。
“到底聽哪個的?聽本杰哥的,還是你的?”他說。
本杰笑了,說:“惠恩嘛,哪個說話都要聽。”
但是羅坤踢了三十分鐘時,我讓高燁上,高燁像木樁似的一動不動。羅坤干脆踢滿全場,下來的時候和小蔣勾肩搭背有說有笑,誰都沒料到高燁拋起礦泉水瓶,一個大腳開進球場。噼——啪——,我們眼瞅著它像銀色焰火一樣在空中爆裂。
羅坤向他走去,被本杰一把拖住。混亂之下高燁大聲說:“這是十五分鐘嗎?是他媽十五分鐘嗎?你們瞎了還是傻了?”
桂子和小蔣氣不過。要不是最喜歡打架的小孫拉著,要不是今天贏球了心情不錯,高燁一定會被哥幾個痛扁。本杰一個挨一個搡開他們,像真正的凱西一樣語重心長、絮絮叨叨。我想動手但我知道我動不了。他是我同意挑選來的。那天我去了師大。不管咋說,我去了。
大伙終于散開,場面驟然凝固并傳遞出某種脈脈溫情與自我批判的詩意。但它很快被更深的絕望、嫉妒和虛無的疲乏擊潰了,尤其當我發(fā)現(xiàn)高燁還穿著惠恩的天藍色球衫、白色長襪,卻踩著一雙粉紅耐克的瞬間。——上周明明是草綠色新款F10。太顯擺啦。
他三下兩下脫下行頭。
“小高,這幫兄弟在一起十多年就這爛脾氣。”張勇說。
“行啦小高,我讓桂子、小蔣請你喝酒。”本杰說。
“我退出,”他說話了,“現(xiàn)在就退出。下周來一場。我自己的隊。咋樣?”
長長的沉默。兄弟們互相看著,等著。好幾個光著膀子,挺著懷胎十月般的大肚子。
“行。”我說。
“輸了交場租。不找?guī)褪帧;荻鞑徽遥覀円膊徽摇!?/p>
踢全額場租是二十年前的野球路數(shù)。那時候凡在海埂激戰(zhàn)的球隊,全都為八百元場地費(注:如今已漲到一千八)殺紅了眼;于是四處找?guī)褪郑杭t塔梯隊的朋友啦,老省隊的高手啦……有時候也附帶踢一兩千元賭資,俗稱“打點”,凡打點的比賽必你死我活。我的右肩鎖骨就是在一九九五年一場打點野球中報廢的;我過了門將,他從身后像殺人犯似的將我撂倒。當年的野性早就扔在海埂的臭泥巴下面,越來越規(guī)范的野球賽已不再殺氣騰騰。但現(xiàn)在,我不能不接招。
“不找?guī)褪帧!蔽覕蒯斀罔F。
“下星期六,下午四點,五號場。”高燁脫下40號球衣還給本杰,背起挎包往外走。一只點水雀追在后面,很快消失了。
本杰說:“你們這幫又臭又硬的老東西。”
張勇哈哈大笑。段凡感慨道:“江湖是他們的,還是我們的?說來說去,終究是他們的。”
“做一回‘老炮兒’?”小蔣說。
“你不是六哥,”本杰說,“干不過年輕人不至于送死。”
“要輸了,就地解散。”桂子說。
“我不同意。”張勇繼續(xù)大笑,“輸給一幫小子就不整了?”
“就是,”我來回打量他們,這幫整整踢了十八年的老渾蛋們,“輸了咋地?輸了找一支更老的打回來嘛,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他們嬉皮笑臉。我抬頭望向峰巒似的白云,眼前一片空洞。
九
羅叔想知道川麗是怎么消失的。她說走就走,連一件換洗衣服都沒帶。
“鬼還記得!”羅坤從不擅長縝密嚴謹?shù)倪壿嬐评怼K褪莻€向來認命的爺們;踢球,打工,開小店。不太好也不太差。這就夠啦。日子嘛,咋個過都是過。
羅叔掙扎下床,不讓他攙著,兩腳挨地之后穩(wěn)穩(wěn)坐好。
“那種女人,跑了更好。問題是,你這十年。”
“行啦。”
“她笑話你哩。”
“行啦行啦。”
這些話十年來講了無數(shù)遍。但是現(xiàn)在羅坤必須豎直耳朵仔細聽。也許是他爹最后一次講它了。就算顛來倒去的車轱轆話,也得認認真真聽下去。他爹的嗓音沙啞平穩(wěn)。他想起球場上那個兇悍的爹,不敢相信他就快沒了。好好一個人,一個腰板挺直的、坐在面前說話的大活人,就要沒了。
十年前的六月,店里亮著燈。最后一個進店的小子也就二十出頭,他記得他買了一包三五牌香煙。那天晚上飄著小雨。是他收的錢,川麗取了煙遞給他。那小子縮著肩膀出去時他聽見淅淅瀝瀝的雨聲。次日早上她不見了。第五天他報了警。第十天吧,他被一個陌生電話告知她走了。走了?被綁架了還是被拐賣了?——半個月后他接到川麗本人的電話,嗓音低得像感冒了。
她說:“別擔心,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吧。保重。”
就這么簡單。
“是他。”羅叔說。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川麗跑了。跑就跑吧沒什么大不了。她要覺得跟別人活得痛快那就跟唄,何必在他一棵樹上吊死?沒有她,足球照樣整,日子照樣過。羅叔不斷地詛咒她。
十年來,有零星消息傳進他耳朵里:川麗輾轉從法國去了加拿大,又倒騰去了墨西哥和美國。她的小男人是某個大賭場的發(fā)牌手,因為代人作弊被扔進拉斯維加斯大沙漠。簡直像好萊塢大片。他想象川麗搖身一變成了拉斯維加斯賭城加油站的服務生,每天給美國佬加油、收錢;偶爾找個小混混兒過夜,她就喜歡那類男人。
川麗曾是二〇〇二年的文林街“一球成名”吧的服務生,羅坤和幾個惠恩兄弟跑去看米盧的中國隊征戰(zhàn)韓日世界杯。川麗瘦瘦的,眼睛大而憂傷,染著金發(fā)。那一個月他差不多天天去。反正離家近,離他的小店也近。他后來回憶,川麗身上有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美,仿佛隨時擔心把客人嚇跑。
“大哥,銀子彈買一送一哦。”這是她附在他耳邊說的頭一句話。他還記得她呼吸中的薄荷氣味,記得她單薄高挑的身材和亮出乳溝的淺粉色制服。再后來,他們的戀愛遭到羅叔的反對,羅叔說“那種地方”的姑娘跟窯姐兒差不多,因此連他們的婚禮都沒參加。
半年之后,這個在酒吧站樁賣酒的兒媳,終于站在兒子的柜臺后面幫他收錢了。羅叔做了一大桌子菜請他們回來。難不成把她趕走?
“她在笑話你。她一直躲在暗處笑話你。”羅叔又說。
“行啦。”羅坤說。
“這是命。只有下輩子抱孫子的命咯。”
“莫瞎說。明年就能抱上。”
“明年?”羅叔苦笑。
“爭取嘛。八九不離十。”
“川麗就在昆明哩。就躲在旮旯里瞧你笑話。”羅叔又說。
“我又不是活給別人瞧的。”
“你早這么想,我早抱上孫子啦。”
他不想再談她。十年來談得太多了,大多是無聊的重復重復再重復。他去醫(yī)院食堂打了稀飯、雞蛋羹,外加一點點咸菜。羅叔沒吃幾口,抱怨稀飯?zhí)⑾滩颂玻挥须u蛋羹勉強湊合。窗外很黑,高樓像絕望的病人。羅坤說下周六要和一幫二十郎當?shù)男⊥尥蕖按螯c”。羅叔抽一張紙巾,擦擦嘴。
“干掉他們。”
“太年輕了。”
“干掉。”
“好吧。”
“你不老。除非你躺在這張床上。”
“我認得。”
“要迎上去。你不迎上去你就完蛋了。所以,不如一腳干掉孫杰。”
他又迷糊了。——到底是爹的腿還是孫杰的腿?過去爹掛在嘴邊的是他自己的腿,被二十三歲的孫杰一腳廢掉,從此江湖上少了一道硬邦邦的鐵閘。他老糊涂了還是病得太重?快四十年了,誰廢了誰還重要嗎?
“聽見了?”羅叔冷冷瞅他,“沒價錢可講。你就是太喜歡討價還價啦。”
他一聲不吭。
“我認得你恨我。連你結婚都——”
“不恨。”
“過來,”羅叔說,“你過來,小坤。”
他走過去,羅叔的右手像床架子一樣涼。再也不能將它焐熱了。他有點害怕,也有點厭煩。他突然意識到他們都喪失了太多。從前的鐵衛(wèi),從前的惠恩,從前的“一球成名”,從前的川麗。他們彼此也快喪失了。
他離開醫(yī)院時大約八點半,也許八點四十。前后十分鐘吧。我想象他沿一二一大街走回西站。九點多他穿了運動衣出門,從洪山西路跑到洪山南路,再從洪山東路直達環(huán)城西路,由交林路返回西站立交橋。這一圈大約五公里。路上一次也沒停,速度不快但足夠了。
到了文林街口已渾身大汗。從前的“一球成名”,店名早換了英文洋名,反正看不懂。裝修也比十多年前闊氣得多。一幫九〇后或更小的孩子聚在店里抽煙喝酒。他沿著燈紅酒綠的文林街慢跑回家。他想好了,每天五公里,一百個俯臥撐,一百個仰臥起坐。每三天跑一組樓梯。一樓到七樓,每組十趟。下個月體能絕對上去。就像爹說的,不老,還來得及,更別說他擅長的足球啦。那幫小子不過是烏合之眾,咋可能擊敗大名鼎鼎的惠恩?
十
五號場絕對是海埂最好的場地之一,草皮在太陽下閃閃發(fā)亮,場邊的桉樹列隊排開。下月亞洲展望開打之前你再也找不到這么好的熱身對手了。我們提前半小時到場,高燁那幫小子晚到十分鐘,很快圍住一個白胡子老家伙接受訓話。之后,身披紅色曼聯(lián)3號球衫的高燁朝我們走來。
他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了。桂子、小蔣、段凡笑嘻嘻地回敬他,對上周的事情表示歉意。只有羅坤故意不看他。高燁招呼他的嗓門很小,像桂子主罰的角球一樣敷衍了事。羅坤換了行頭繞場六圈,一臉細汗地回來。我問他還行?他說,行,當然行。
對手真年輕啊,我估摸也就二十歲上下。高燁詢問本杰是否像正式比賽一樣列隊進場。本杰望著我,我大聲回答“行”。
“你們悠著點。”本杰說。
“嘿,該咋踢咋踢。”高燁的目光冷得像冰錐。
我叮囑羅坤:“千萬小心。”
“當心你自己。”
“千萬別對腳。千萬。”
“我爹當年——”
“我有數(shù)。”
“你上去就灌它三個,慢慢打。”
“沒問題。”
“我每天五公里,不帶喘的。”
“那也千萬小心。”
于是我們像正式比賽一樣從中線列隊入場,進去后縱隊變橫隊散開面向替補席抬臂致敬,場下響起寥落的掌聲。高燁居然準備了一面三角小旗交給段凡。我這才注意到他戴了隊長袖標。比賽一上來就激烈兇猛,這幫小屁孩果然跑得飛快。白胡子老家伙在場邊來來回回吆喝,就像踢世界杯一樣。我們很快被壓得喘不上氣來,好在羅坤多次化解了對手強攻。
我很難拿到球。小寶、小蔣和桂子被按在大禁區(qū)前沿無法組織傳遞,也就很難把炮彈輸送過來。我像個傻瓜一樣折返跑。對方10號、9號、7號像牛犢子一樣橫沖直撞。我方中場完全啞火。上半場被對方從中路滲透打進一球。0比1。羅坤撐住膝蓋喘氣。進球的對方7號絕對練過,腳下技術沒的說。中場休息時我覺得我快虛脫了。難就難在你知道你很難撐過高強度的九十分鐘還得咬牙撐下去,就像你明明知道你必死無疑還得在病床上咬牙撐下去。
我們集體表揚羅坤。——他怎么做到的?才短短七天就恢復得這么好。
他大口喝水,湊到我身邊說:“拿回來。”
“拿回來。”我說。
“還行?你很少拿球。”
“球出不來啊。根本沒中場。”
“頂住。”他望著我,仿佛回到十多年前的海埂夏天:一幫三十不到的年輕人所向披靡,任何球隊上來都不怕,就算“打點”也不怕。
“注意7號。”我說。
“下半場不能再丟球啦。”
“不能丟啦,還要想辦法進球。”
“小心高燁。”
下半場全力反撲,終于從王盛所在右路打出像樣的配合突到禁區(qū)了。我貼近高燁。我們絕不看對方。他滿臉大汗,像瘋狗一樣想把我絞殺在大禁區(qū)前沿。
小寶直塞球,我快速前插接球直面高燁。我選擇向左虛晃向右突進,被他猜到了。他以一記兇狠鏟球破壞出底線。
我破口大罵。我罵得相當狠,簡直窮兇極惡。
“你罵誰?”高燁說。
球場爆發(fā)了小規(guī)模騷亂。白胡子老家伙沖上來讓高燁冷靜。高燁知道只要拿我撒氣別人就不敢小瞧他。可他太緊張了。足球不是這么踢的。我會“教教”他怎么踢。騷亂平息后我隱蔽地將他放倒。他捂著小腿肚子嗷嗷叫。
裁判亮了黃牌。
這么整下去我們將輸?shù)粢磺О税賶K錢場租,還將輸?shù)粢恢Ю吓苿怕玫哪樏妗尩摹N艺泻舸蠡飰荷稀W詈笫昼娫俨黄淳蜎]機會了,偉大的惠恩必須向最偉大的德意志戰(zhàn)車學習,全線壓上再壓上……
我們殺紅了眼。只要拿出韌勁和經(jīng)驗總有機會扳平。果然獲得角球,羅坤殺奔小禁區(qū)。我主罰的皮球一出腳就知道有了;羅坤俯搶前點,皮球穿透高燁和兩名小子的后防線直掛左上角。1比1。我們大喊著擁抱羅坤。高燁的臉色比死還難看。最后五分鐘他們瘋狂反撲,要不是彭翔、羅坤打了雞血似的一再救險肯定又丟球了。變故發(fā)生在最后三分鐘,也許最后一分鐘或最后三十秒。事情過去那么久,我真記不住啦。
當時他們也獲得角球,躍起搶點的高燁被羅坤放倒,他大叫著落地、翻滾,像一只垂死的烏鴉。
裁判指向點球點。我們像在夢中一般混沌疲乏地站著,似乎渴望盡快來個了斷。然后,我們瞧著彼此,在高燁一聲高過一聲的慘呼中邁著沉重困惑的步子向他靠近。每走一步,身體就像被他的叫聲幻化的斧頭狠劈一下。我們圍住裁判,想把他趕走。
高燁遲遲沒站起來。
雙方同時罷賽。羅坤想拽高燁起身的舉動招致新的騷亂,很快被本杰和白胡子老家伙鎮(zhèn)壓了。我們回到場下。高燁的慘叫一聲接著一聲。
“去嗎?”羅坤說。
“去看看。”桂子說。
“斷了?”小孫說。
“去吧,坤哥。”小蔣說。
羅坤垂下兩手,低著腦袋曳步過去。短短幾十米仿佛要耗盡他的下半輩子。他走得極慢,像擔心錯過什么。他孤獨的背影穿過空空蕩蕩的只有高燁叫聲充斥的我方半場,草皮綠得能擠出汗來。我們跟上去。高燁仰躺著,白胡子老家伙摸著他的膝蓋說,別看啦。可我們都瞧見了:脛骨明顯斷了,別別扭扭的樣子像一條僵死的蛇。簇新的紅色耐克亮得扎眼。
我招呼本杰:“打120吧。”
十一
我必須告訴你們這場野球賽之后羅坤掛靴了。即便我親自出馬他也絕不回頭。遲早要散的。十八年前哪兒有什么惠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琢磨自己是否也該退啦,周末沒事玩點別的,比如毫無殺傷力的游泳和慢跑,羽毛球或乒乓球。可你真舍得撇下足球?
那天我約他上“西門驛站”小坐,他遲遲沒來。我坐到凌晨一點,看著各式各樣的孩子進進出出,聽著吧臺的歌聲越來越吵。我數(shù)了數(shù)桌上七只空酒瓶,將滿嘴煙霧吐進黑暗。我知道他不會來了。他沒接我電話,也遲遲沒打過來。
起身時忽然天旋地,一個賣啤酒的小妞一把攙住我,問我:“怎么啦,大哥?”
“大哥?”我笑了,“你沒見過喝多了的老男人?”
她笑了:“你不老嘛大哥。”
我瞅見她胸前的“銀子彈”。我問她認識川麗嗎?她想了想,說是不是紅頭發(fā)川麗?這么高,這么瘦?我問她是不是三十出頭,她笑了,說川麗才十七呢。
我使勁搖頭。
“要我?guī)湍愦蜍噯岽蟾纾俊?/p>
“不用,謝謝。”臨行前我買她一瓶銀子彈,像寶貝似的緊緊攥在胸前。
“祝你,祝你嫁個好男人。再見。”我說。
十二
手術定在下禮拜三。羅坤心里清楚,即便一切順利,好轉的可能性也幾近于零。就當傷停補時仍有機會絕殺吧。羅叔要求回家住幾天,整天躺醫(yī)院里哪個受得了?羅坤不能不同意,早早回家給他做好吃的:梅菜扣肉、豆腐腦、蒸南瓜、雞蛋羹。醫(yī)生說過這些東西還能吃。再硬一點就不行了,酒絕不能碰。
羅叔氣色挺好,表揚羅坤廚藝進步很大。
“你一個人也開伙?”羅叔問。
“偶爾。”他說。
“該找個人幫你。”
“一直在找嘛。”
羅坤想說,新來的小許不錯,版納傣族姑娘一向以溫順出名,雜貨店里里外外全靠她。工資不高,包吃住一千六,小許干得不亦樂乎。她說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夠用就行。她就住店面里間的小屋,一張床,一張桌。桌上擺滿叮叮當當?shù)男∑孔有」拮印9媚锛衣铩?/p>
“幾天就搞定的女人不是好女人。”羅叔說。
是啊,當年和川麗好上也就短短幾天。那就慢下來,必須慢下來。小火燉湯才好呢。
他們吃得不多,剛開始的興致莫名消失了。菜一點點變涼,羅坤的心也一點點騰空。突然意識到一頓家常便飯對于馬上手術的爹也是折磨。而意識到它也就成了對自己的折磨。他手里的筷子一個勁兒發(fā)抖。
“我想喝一杯。”羅叔說。
“不行。”他說。
“白酒啤酒葡萄酒,咋個都行。”
“醫(yī)生說了不行。”
“讓我喝點嘛!”
算啦,醫(yī)生的話還需要聽嗎?羅坤倒了四分之一杯紅酒。想喝什么喝什么吧。羅叔一口干了,咂咂嘴巴,沖他勾勾食指說再來再來,至少半杯嘛。他平時很少喝酒。哪兒來喝酒的念頭?他想反對,但還是倒了半杯還多。
“你下個月比賽我看不成咯。”
“好好養(yǎng)病。”
“小坤,我會死?”
“你莫亂說!”
羅叔小心翼翼喝一口。
“醫(yī)生說,頂多兩星期就能下床。”
羅叔笑了:“還能看你比賽?”
“那種破比賽,有哪樣好看。”
“也是。那種破比賽,有哪樣好看。”羅叔握著杯子,輕輕搖晃,“李果還整前鋒?”
“整啊。殺手李嘛。”
“你們兩個,從小到大……”
他到底想說什么?
他抬頭猛喝,杯子見底了。菜涼得真快,畢竟是秋天啦。他喜歡像現(xiàn)在這樣和爹面對面在家里坐著。是啊,這種機會本來就少。他忽然感到害怕,就像地板抽空了,就像還沒熱身就被教練一把推到場上。從小,是爹手把手教他踢球,過去的重要比賽每場必到。直到若干年前再也不看他和李果的業(yè)余表演。爹最大的遺憾是沒進國家隊。他呢,在爹的遺憾之上變本加厲——連省隊都沒進,僅在市體工隊混到二十四歲;到處打零工,后來接下了爹的雜貨店,眨眼混到四十。
“小坤,”羅叔望著他,“我怕連手術臺都下不來啦。”
“瞎說。”
羅叔低頭瞧著空掉的酒杯。沒讓他倒酒,沒任何表示。只是瞧著。
“那天,十年前那天,我往你店里打過電話,接電話的男人不是你。我趕過去,我把他們堵在外面,把他踢個半死。”
羅坤一聲不吭。羅叔又看著他。
“其實,我就站在對面抽了半包煙。天上下著小雨,地上濕漉漉的。后來燈滅了,我走了。”
“莫講啦。”
他們很久沒有說話。七樓窗外傳來汽車聲,走動聲,吵嚷聲。
“帶一個回來。”羅叔揮手扇他腦袋。他一動不動。
羅叔說:“下個月,我去場邊瞧你。”
后來央視直播英超,他們眼瞅著曼聯(lián)輸給阿森納。遠處傳來驢的昂昂叫喚。他知道是收泔水的糟老頭趕著老毛驢來了。他想去一趟店里,羅叔沒說話。他出了門,穿過交林路、西站立交橋來到建設路口。店門開著,小許通常零點打烊。附近新開了一家五星級影院,大大帶動了店里的生意——比從前好太多了。他天真地想,要是換作現(xiàn)在,川麗還會跟一個抽三五煙的愣頭青跑掉?她當然不可能站在拉斯維加斯大沙漠里為各種汽車加油。她就在昆明,錯不了。他的直覺向來很準。
小許坐在深處,柜臺低低的,被各種小食品包圍。他進來時小許有些驚訝。他說他喝杯水就走。小許說沒燒水呢,要不來一瓶脈動?他說隨便。他走進去,店里只有一把圓凳可坐,兩人中間隔著玻璃柜臺,能聞見小許長發(fā)里的清香。
“我累了,”他說,“今天整了一場球,還給老頭子做了晚飯。我把他接回來住兩天。”
小許黑油油的眼睛比頭發(fā)還亮。
“哥,要我做哪樣,你就說。”
“他會死嗎?”
“呸呸呸,烏鴉嘴!”
他什么也說不出來。
“羅叔福大造化大。”
“是啊。我也這么想。”
“好人總有好報。我剛來昆明,就遇著你啦。你是好人。”
他羞赧地避開她的目光,瞧著外面。文林街的柏油路面像冰一樣照出霓虹。
“哥,你喝水。”
他接過脈動,一氣灌下半瓶。
“從前我爹被人踢斷腿。最近他老說是他把別人的腿踢斷了。他老糊涂了?”
“這種事情嘛,我就講不來啦。我們村有個老人從前很正常,后來逢人就講,他上輩子是大象哩。他是大象變的。”
他笑了。
汽車一輛接一輛。安靜的唰唰聲比西門的歌聲好聽多了。
“你踢足球,也受過傷?”
“嗯,踝關節(jié)脫臼。”
“好了嗎?”
“都二十年咯。”
她望向他的腳踝。他覺得她像棵直苗苗的小樹。
“你信命嗎?”
“我信。”他說完就后悔了。其實他也說不太清楚到底信,還是不信,就像他已經(jīng)搞不清楚爹的話是真是假。
“人死了會轉世嗎?”
“會吧。”
“你上輩子是哪樣?”
“可能是,可能是匹馬。”他笑了,她也笑了。
又是長長的像海一樣的沉默。接連駛過七輛車。七輛。他數(shù)著呢。第八輛的時候,他站起來,隔著柜臺抱住小許。她嚇得使勁掙扎。她樹一樣的清香真好聞哪。剛要撒手,她卻不再掙扎了,低頭向他胸前靠近。她的長發(fā)又黑又密。他覺得她才是一匹滾燙的小馬。他喘不上氣來,然后撒開手。
“我明晚再來。”
他跑出去,沿著每晚的必經(jīng)之路向前跑。夜幕像一件干凈的靛藍色球衣展開并籠罩大地,西站附近燈火璀璨。他迎著夜風慢慢跑,不著急,畢竟踢過一場了。五公里,還有五公里。他渾身發(fā)抖,身上胳膊上臉上還能聞見淡淡清香。
回到小區(qū)差不多十一點。老遠看見樓下聚了一大圈人。像被什么東西咬了一口,他停下來,然后搖搖晃晃推開人群。地上躺著羅叔。有人高喊他的名字,說:“你總算回來啦,七樓,他從七樓突然——”
他跪下去,滴滴答答的熱汗敲打地面。劇烈的暈眩仿佛因為運動過度而缺氧。有人又說了什么,過來攙他的手。他聽不見,也感覺不到。他累了,這回是真的累了。他想捧起羅叔的臉跟他說句話,想告訴他說,快了快了你要見的人就快見著了。他還想告訴他們,都走吧,讓我喘口氣。請你們讓我,喘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