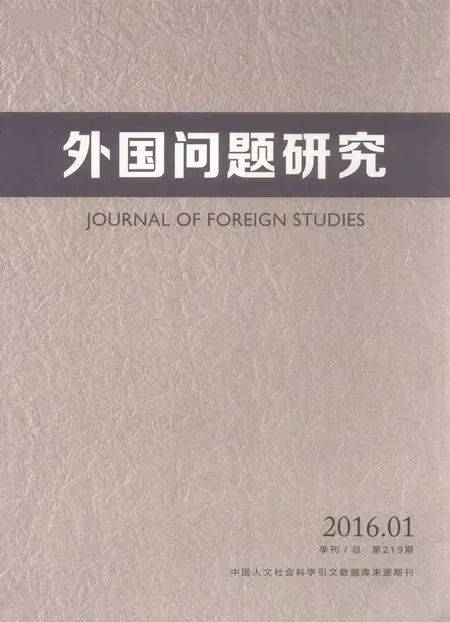朱舜水思想對荻生徂徠影響之再思考
高 悅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
朱舜水思想對荻生徂徠影響之再思考
高悅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內容摘要]荻生徂徠通過吸收朱舜水古學思想中的諸多因素,完成了以“六經”結構為中心、輔以“左國史漢”的學術轉型,真正從學理上完成了對朱子學的框架解構。而這種超越時間、空間的非同步吻合,不僅得益于荻生徂徠與朱舜水弟子的書信往來,同時,深受朱舜水思想影響的加賀藩,也成為徂徠獲取資源的另一有效途徑。
[關鍵詞]荻生徂徠;朱舜水;安積澹泊;加賀藩
荻生徂徠(1666-1728,又名物茂卿)之學問以反朱子學(理學)為基本立場。若分析該學術特質的成因,除了通行于學界的“李王古文辭論”和伊藤仁齋影響說外,新近提出的朱舜水(1600-1682,謚文恭)思想通過安積澹泊間接影響過荻生徂徠的觀點,值得注意。*參見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動及其貢獻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韓東育:《朱舜水在日活動新考》,《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韓東育:《朱舜水在日活動再考》,《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韓東育:《日本近世學界對中國經典結構的改變—兼涉朱舜水的相關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1期。本文擬沿著該理路出發,通過考察荻生徂徠與安積覺的書信交往,來考察徂徠在與安積覺“文通”之前,既已接觸過朱舜水學問的史實經緯。同時,從朱舜水對加賀藩的影響出發,從一個側面論證荻生徂徠對朱舜水古學思想之受容事實,并提出一種可能,即徂徠通過吸收朱舜水思想,完成了以“六經”結構為中心、輔以“左國史漢”的學術轉型,并真正從學理上完成了對朱子學的學理解構。
一、荻生徂徠與安積覺書信始末中的可能性問題
荻生徂徠與朱舜水本人并無直接交集,但通過徂徠與朱舜水弟子安積澹泊之間的書信考察,可以分析出徂徠雖對朱舜水學問有過“誤解”,但他在“文通”之前既已接觸過朱舜水著作一事,應該是事實。
安積覺(1656-1737),號澹泊。十三歲師事文恭先生,“受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句讀”,善通華音,朱舜水曾評價其“吾東渡授句讀者多,皆不可,獨彥六(安積覺乳名——引者注)佳耳。”*[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附錄五《友人弟子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22頁。彥六,安積覺之小字。安積澹泊“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附錄五《友人弟子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19頁。現有資料表明,兩人書信交往集中在享保十年至享保十二年,*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譜考》,東京:平凡社,1984年,第247—251頁。起因是安積覺欲通過友人平野金華向徂徠尋求亭記墨寶,卻遭后者婉拒,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關于文章治學的陳情。關于這一事件的由緒,據《文苑遺談》所載:“晚年與物茂卿書,求作亭記。時物茂卿首唱古學,自樹門戶,視朱學之徒猶仇讐。以澹泊之素尚宋學,故為傲慢不遜之辭以峻拒之。而澹泊不少介于意,屢通書問,質以所疑,禮益恭,辭益溫。茂卿初雖以非己徒而拒之,后稍服其偉度。特加敬重云。”*[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附錄五《友人弟子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24頁。徂徠是否真如文中所言“傲慢不遜”姑且不論,但起源于亭記文章之不悅,復以恭敬友善為結局的六次共計12封書信往來,卻構成了研究荻生徂徠與朱舜水思想之關聯的重要史料。
通過考察兩人間的書信往來,可以發現以下問題,即徂徠在通信前是否真正了解安積澹泊和朱舜水思想特征。而進一步可以追問的是,安積澹泊是否是徂徠獲知舜水學問的唯一途徑。
首先看第一點。在第二書中,徂徠曾說:“不佞之于足下,僅一通書而已,但識其為大藩耆宿碩儒而已。”*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二書,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536頁。可見,徂徠開始對安積澹泊的認識,僅限于“大藩碩儒”之程度。甚至在徂徠嚴詞闡明不為作序緣由的第三書,還有不知文恭先生(朱舜水)學術特色的表述:“足下少服文恭先生之教,意者必習于宋說者,則必以不佞為異端邪說,唾而罵之。”*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三書,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538頁。此言意在表明,徂徠最初對朱舜水的判斷,是“基于”對安積澹泊“素尚宋學”的學術判斷。正是因為上述徂徠對朱舜水的“誤解”,才有了安積澹泊的以下對答:
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為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可征也。當時童蒙,不能知所謂古學為何等事,至今為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后一己之見識耳’云云,今夏偶見隨筆中援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附錄五《友人弟子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19—820頁。
如上文所示,安積澹泊偶然讀到《蘐園隨筆》中援引程、朱之處,誤以為徂徠亦尊信宋儒,躍然自喜。待徂徠澄清后,方知徂徠與業師朱舜水同樣對宋儒進行過非難。又徂徠復第六書言“又近考究歷代度量制,因讀朱氏談綺,載文恭先生論,明三種尺,前后說頗相柢梧,豈記者失邪?”*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六書,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539頁。“朱氏談綺”,為1708(寶永五年)年刊行的《朱氏舜水談綺》,徂徠曾就神主制等家禮祭祀問題就教于該書。徂徠對朱舜水學說的認識,若果真如文字所呈現的那樣,由不熟知(“習于宋儒”)到研習(“問神主制”)且始于寶永五年的話,那么便無法理解“蓋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與六經有不合者”等極具舜水古學特色的論斷了。故而筆者認為,徂徠對朱舜水思想的了解,應在這次“文通”之前。
問題是,荻生徂徠既已了解舜水之學又為何說他“必習于宋說”呢?以下的事實可供參考。徂徠雖盛贊過木下貞干(1621—1698,又名木下順庵)“錦里先生者出,則扶桑之詩皆唐矣”詩文的盛唐風范,*[明]朱舜水著,朱謙之整理:《朱舜水集》附錄五《友人弟子傳記資料》,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07頁。但卻一向視順庵的弟子、朱子學者新井白石為政敵,甚至批評他是“文盲”。徂徠對同為朱子學者的木下順庵和新井白石一揚一抑的評價手段,同樣適用于身為師生關系的朱舜水與安積澹泊,只不過對后者采取的是先抑后揚的態度,這種行文習慣本質上是徂徠對朱子學“痛心疾首”的一種極端表現。徂徠敢于屢屢挑戰權威甚至不惜對“異端者”斥以嚴詞激烈的表達,固然有其學“一時風行于世”的學術自信,但究其根源,實則是對現實學風的無奈與“學問當經世以致用”的強烈呼吁。*事實上,朱舜水也曾惋惜過當時日本社會佛教過盛而儒教不立的現象:“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朱舜水:《答釋斷崖元初書》,《朱舜水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63頁。因此也無需就徂徠言舜水“必習于宋學”的說法做過度解讀。
二、加賀藩儒學:事實受容的一種可能
朱舜水僑居日本22年,除水戶藩外對加賀藩儒學也有諸多影響,主要體現在通過與前田綱紀、木下貞干等人的交往,向他們傳達重教興國、重視人才的治學理念與治邦之道。特別是對儒生五十川剛伯的培養,使后者有能力于元祿十一年奉旨編集《學聚文辨》并《助語集要》,從而對加賀藩的文教普及產生了積極作用。不寧唯是,朱舜水“名教振邦,必從圣賢之學”之理念也向木下貞干做過完整的吐露:“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非欲其文辭遐暢,黼黻皇猷而已,誠欲興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圣之君必以學校為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于圣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朱舜水:《答木下貞干書六首》四,《朱舜水集》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01—202頁。可見,朱舜水曾對加賀藩“崇圣學而振邦,尚仁政興道”的藩政之規定有所嘉譽,認為它已顯示出“實理實學”的特質;而加賀藩明倫堂的設立,又與朱舜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不僅如此,徂徠早在隨父流放的南總時代已經開始對加賀藩所有關注,他曾經稱贊過加賀藩是能夠妥善安置“非人”的仁政大藩:
予十七八之時,聞上總國之事,加賀之國無非人。若出非人則立小屋,作草履、绹繩,吩咐種種事業。加賀守是以養役人,賣其繩、草履。聞于加賀國之逐電、居于上總之人,誠仁政者哉。不知今之如何。*荻生徂徠:《政談》巻一,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287頁。(筆者譯)
特別是原本打算密呈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秘而不刊的《政談》。*尾藤正英:《國家主義の祖型としての徂徠》,日本の名著16《荻生徂徠》,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年,第12頁。其中諸多政見所體現出的文必溯古與古今照合的態度,諸如“古三代之時諸侯國之所關”、“古三代之御代”等言必稱三代的白描,*荻生徂徠:《政談》巻一、巻二,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281、318頁。應是對舜水上述治邦政策之延續。關于荻生徂徠獲取舜水學問的另一重要途徑,韓東育先生的論點值得參考,即“彌漫于加賀藩的朱舜水氛圍,徂徠已不可能全然不知;而如果注意到安積澹泊所謂‘文恭務為古學,不甚尊信宋儒’一語,那么,朱舜水思想對徂徠甚至整個日本‘古學派’的影響,恐怕還是根本性的。”*韓東育:《日本近世學界對中國經典結構的改變—兼涉朱舜水的相關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1期。
另外早于《朱舜水先生文集》(1715年)的“加賀本”《明征君集》(1684年)與1708年刊行的《朱氏舜水談綺》,應當是徂徠接觸朱舜水思想的最早文本。據學者考證,徂徠著手對經子史的系統研究,至晚始于寶永六年(1709年)。“蓋《讀荀子》之成,在《讀韓非子》之前,先生與人書云,韓非子解成,譯筌未就緒,此譯筌以前所著審矣。”*宇佐美灊水:《刻〈読荀子〉序》,《荻生徂徠全集》第三巻,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471頁。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見于今中寛司:《徂徠學の史的研究》,東京:思文閣出版,1992年,第96—99頁。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譜考》,東京:平凡社,1984年,第71頁。考察徂徠歷年出版物,一個顯著的變化是研究對象由“四書”結構轉向“六經”主義的晚期代表作,諸如《學則》(1715年)、《辨道》(1717年)、《辨名》(1717年)、《論語征》(1718年)、《徂來先生答問書》(1727年),時間上均早出于《朱舜水先生文集》且晚于《朱氏舜水談綺》。更為重要的是,徂徠對“李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三書,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537頁。的表達,表明李王二人并非是促使徂徠轉向“六經主義”的根本原因。而加賀藩的儒教方略,或許會為該轉向提供可能。
三、荻生徂徠與朱舜水思想之“契合”
荻生徂徠轉向“古學”的原因,一般認為有兩處值得關注,一是少時困苦經歷,致使其學術造詣“全賴南總之力也”。其二是中年逢遇“天之寵靈”的李、王古文辭學,遂舍“今文”而視“古文”。然而被視為反映徂徠學精髓的“先王之道俱在六經”的依據——從“經典”(圣人之言)再到“治理”(圣人之制)的經世致用之學,卻沒有從上述兩點成因中得到應有的體現,因為前者只能成為徂徠學“務實”的社會背景,后者則多被視為徂徠古文辭學的學術依托。對于面對徂徠是如何一改早年“援朱子以攻仁齋”,又是如何從學理上完成對朱子學全面反攻的發問,載于朱舜水文集中的諸多觀點,應給予過徂徠相當程度的啟示。具體言之,二者在“左國史漢”的治學方略、文章經略的春秋筆法,以及在上述基本治學之道的基礎上推演出的關于宋儒之批判、安天下的經世之學,均有極大的相似處。
首先看治學方略,朱舜水曾在與學生的對答中談及讀書作文之法:“作文以氣骨格局為主。當以先秦、兩漢為宗…讀書作文,以四書、六經為根本,佐之以左、國、子、史,而潤色之以古文。”*朱舜水:《答安東守約問八條》,《朱舜水集》卷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68頁。無獨有偶,徂徠也曾明確表達過“左國史漢”的治學方略,“故初學之人,經書為左、國、史、漢,文章為楚辭文選、韓柳李王,總之漢以前之書,乃人之智見也。”*荻生徂徠:《経子史要覧》,《荻生徂徠全集》第三巻,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364頁。(筆者譯)并且徂徠在給弟子木公達開列的藏書書目中,十三經、諸子、左國史漢等一應俱全,結尾特書“好古之士必須貯置備博”。*荻生徂徠:《物子書示木公達書目》,《荻生徂徠全集》第一巻,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第537頁。具體來說,舜水認為初學者應從易讀易懂的《資治通鑒》入手,而徂徠則最崇《史記》。舜水曰“中年尚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為愈也。《資治通鑒》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于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于事理吻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由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朱舜水:《與奧村庸禮書二十二首》二,《朱舜水集》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56—257頁。徂徠之所以推崇《史記》,是因為在他看來,“歷史者,乃學問之極也。”*《徂來先生答問書》,日本古典文學大系96《近世文學論集》,東京:巖波書店,1966年,第187頁。而且,《史記》不經宋儒染指且最尚存三代遺風:“只史記不經宋儒之手,其時世又與三代相接,風俗氣習,不甚相遠,故不佞教人先讀史記者,亦欲其藉以離宋儒一種惡習也。”*荻生徂徠:《與藪震菴》,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第507頁。
在為學之道上,舜水認為,與宋儒空談心性的扭捏姿態相比,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因為雅尚玄遠畢竟于事無補,故稱“書理只在本文,涵泳深思,自然有會。注腳離他不得,靠他不得。如魚之筌、兔之蹄,筌與蹄卻不便是魚兔。”*朱舜水:《答安東守約問八條》,《朱舜水集》卷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69頁。這與徂徠的“圣人之惡空言也”、“筌乎筌乎,獲魚舍筌”等言論可謂同出一轍。尤為重要的是,徂徠所極力倡導“圣人之道—物—六經”的先王之道邏輯體系,即“夫六經物也,道俱存焉”,與舜水弟子德川光圀的學習心得——“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經,則圣人之道尚矣”,何其逼肖乃爾。*朱舜水:《策問四首》其二,《朱舜水集》卷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43頁。
近世日本思想界始終存在一種“異端排斥”的學術氛圍,這種通過對朱子學的受容而又復以攻堅擊潰的“曲折”歷程,在荻生徂徠的身上表現得異常醒目。通過以上粗淺梳理發現,荻生徂徠對“六經—左國史漢”經典體系的關注與理論展開,明顯區別于當時日本學界的一般認識。從這個意義上,稱徂徠通過對舜水學問之溯源和追尋,在學理和治學方法上完成了對宋學“四書”體系的逸脫與重構并不為過;而朱舜水實學理念的流布,不僅使徂徠學中經典結構的更迭受到影響,更成為長久以來潛伏在德川儒學界“脫儒”現象的原始基因。
(責任編輯:王明兵)
[收稿日期]2015-11-17
[作者簡介]高悅(1988-),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01(2016)01-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