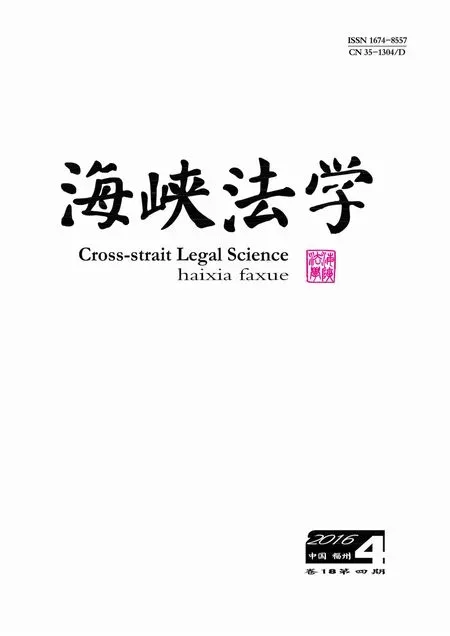“見危不救”犯罪化分析
楊 玲
“見危不救”犯罪化分析
楊 玲
見危不救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僅限于人們心中普遍的善良情感及由這些情感構筑的我國社會公德體系。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分別通過擴張不作為犯的實質作為義務來源和“控制理論”來論證見危不救行為的犯罪化。見危不救行為嚴重違反我國社會主義公德要求,侵蝕我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我國應設立見危不救罪,該罪的設立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見危不救;不作為犯的趨勢;社會公德
一、“見危不救”行為的性質界定
案例一:某市一市場內一名年輕女子,因為受不了被男友拋棄的打擊,想結束生命。當時她爬上3樓,高高地站在陽臺上時,樓下圍觀者數百人。這時候,女子的精神狀態已經很明顯處于崩潰的邊緣。但出人意料的是,圍觀的一婦女突然站出來高喊:“跳下來我給你5000元錢!”另外還有幾個男子也附和:“快跳,跳下來我抱著你!”受到種種言語的刺激,最后女子跳樓自殺。
案例二:日本大審院1917年12月18號的一則判例:被告人殺死養父之后,看到在爭斗時養父投過來的正在燃燒的木棍將院中的茅草點燃,明知放任不管的話就會起火,但為了毀滅罪跡,便放任不管,揚長而去,最終引起熊熊大火。①[日]山口厚著:《刑法總論》,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
案例三:2004年5月19日下午,某縣某村80余名群眾去縣政府上訪,在縣政府二樓被四五名工作人員阻止發生擁擠,16歲的少年陶漢武意外跌倒昏迷。“當時大家向縣政府工作人員請求,讓他們用手機給120打個電話叫救護車來,結果對方回答說‘沒手機’。大家又請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電話叫救護車,他們卻說‘電話不好使’。終于,耽擱半小時后,陶漢武經搶救無效死亡。②王軍榮:《總要有人為“見死不救”付出代價》,http://opinion.people.com.cn/GB/35560/5513664.html,下載日期:2016年11月23日。
上述三個案例基本上概括了當前社會上所存在的見危不救行為的類型,構成了廣義上的見危不救行為,但是筆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見危不救罪所匡正的是第三類行為,可稱之為狹義的見危不救行為。第一類現象其實質在于利用他人的情緒崩潰狀況,用言詞或肢體語言激起或堅定他人自殺、自殘心理的行為。筆者認為這屬于作為的故意犯罪,該種刺激行為不再是一種單純不救助而是超出見危不救范疇以外的加功行為,行為人明知他人情緒處于極端亢奮狀態,稍加刺激就會或可能會發生自殺或自殘的嚴重后果,卻基于心理變態等動機而希望看到血腥結果的發生,進而用言辭或肢體表現進行刺激,最終造成危害結果發生。總之這類現象不屬于本篇文章討論范圍。第二種情況日本法院認為,行為人的消極不救火與主動的放火具有價值的等同性,并且在主觀上有“利用已發生的火災的意思”,因此該判決書認為被告人構成放火罪。①[日]山口厚著:《刑法總論》,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該判例與第三例的區別在于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意利用已有的危險達到自己的其他目的的動機,在筆者看來,見危不救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是缺乏“惡意利用”的意思,筆者認為,見危不救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僅僅限于人們心中普遍的善良情感及由這些情感構筑的我國社會主義重大道德體系,一旦涉及到利用已發生的危險達到其他犯罪目的的情況,所牽涉的刑法關系就不再是單純的不救助與道德體系的關系,因此必須將第二類情況排斥出見危不救行為的范圍。
綜上筆者認為,見危不救罪的表現形式只體現于第三種現象之中。那么如何對這種現象進行法律控制呢?
二、不作為犯罪刑法控制的趨勢與啟發
(一)德日刑法相關理論
眾所周知,成立不真正不作為犯,必須具有避免發生侵害法益結果的法律上的作為義務,因此尋求見危不救的刑法控制必須首先在“作為義務”范圍上尋找答案,自19世紀初開始就不斷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最先費爾巴哈提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僅需法律和契約就足夠了。后來德國學者施邦恩貝格(Spangenberg)和亨克(Henke)將密切的生活關系也納入到作為義務的范圍,而 “密切的生活關系”的具體內涵和外延是帶有模糊性的,應做一種實質性的理解,這就開啟了一種不同于費爾巴哈形式義務來源說的先例,為以后將作為義務擴展到見危不救領域開辟了道路。當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已從形式的作為義務來源說過渡到實質的作為義務來源說,實質的法義務包括:先行行為說、事實上的承擔說、因果過程支配說、機能的二分說等等,以因果過程支配說為例,其中包括“具有支配領域性的場合”,即雖不是基于支配的意思,但事實上支配指向結果的因果過程,例如,建筑物的所有者、租借者、管理人這樣負有社會生活上繼續保護管理義務的情況。②陳家林著:《外國刑法:基礎理論與研究動向》,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這樣,就從實質的支配角度擴展了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主體范圍。另外,為了尋找不作為的結果犯中的因果關系,德國刑法學界根據作為犯的“危險增加理論”即:只要行為人增加了發生結果的危險,便可將結果歸責于行為人。推導出不作為犯的“不積極降低危險的原則”是指:對于不作為犯罪而言,只要為應為之行為就可阻止結果的發生,若結果發生,就可將結果歸責于不作為的行為人。③[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爾·庫倫著:《刑法總論I——犯罪論》,楊萌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日本刑法學界也存在這樣的狀況,日本學界“歷來例舉的作為義務根據有(1)法令、(2)法律行為或者無因管理、(3)一般道理、習慣等一般規范”。而什么是一般的道理和習慣,在教義解釋上就存在很大的彈性,為了對該點進行限制,日本刑法學界提出“主觀的行為無價值”理論,該理論認為在認定違反作為義務的時候,要重視行為人的主觀意思或者人格態度,特別是犯罪動機,即利用至少是有意放任已經發生的危險的意思,日本《修改刑法草案》第12條遵循了該理論,規定:具有防止犯罪事實發生責任的人,盡管能夠防止其發生,卻特意不予防止,以致引起結果發生的時候,和作為引起犯罪事實的場合同樣看待。有學者認為這里的“特意”就是指“對法持有敵對的意思力量”④[日]曾根威彥著:《刑法學基礎》,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但大谷實教授批評道:“根據這種見解的話,就會得出即便具有違反法律上的作為義務的不作為,該不作為即便和作為等價,也不得加以處罰的不合理結論”進而提出“不真正不作為的主觀要件,和作為犯的實行行為的場合一樣,只要具有故意就足夠了”。因此建議,“這一規定(指《修改刑法草案》12條)中,至少應當刪除‘特意’要件”。①[日]大谷實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這樣去除主觀動機的差異后該條就更加接近于真正不作為犯罪性質的見危不救罪。
(二)英美法系的理論
美國刑法學家道格拉斯﹒N﹒胡薩克教授在其《刑法哲學》一書中闡述了他對見危不救理論的構想。他首先引用了傳統理論學者對“人民訴比爾茲利案”(在本案中被告眼看著一名妓女吞食了數克嗎啡而沒有為她呼救,最后該婦女因沒有得到救助而死亡)等案件的評論:“理查德﹒艾伯斯坦的評論是有代表性的:‘人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沒有救助可憐之人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但這并不能推導出一個沒有強制人們履行救助義務的法律體系是無恥的結論’”。接著他從分析傳統刑法因果關系的角度得出上述評論的癥結所在:“比爾茲利案、瓊斯案和奧斯特琳達案都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這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在這些案件中,被告人的行為是否為死亡的一個原因是有爭議的……試圖用因果關系的概念來區分道德義務與法律義務與試圖依靠刑事犯罪的正統模式相比不會有更好的結局。”因此胡薩克提出了“控制理論”來作為因果關系的替代方案。“控制理論”是指:把刑事責任施加于人們無法控制的事態即為不公正,其核心是“一個人,如果他不能防止事情的發生,就是對事態不能控制。如果事態是行為,他應當能不為該行為;如果是后果,他應該能防止其發生;如果是意圖,他應該能不具有這個意圖,等等”。他指出“我認為,控制原則是一個比正統的刑法理論的因果要件更為可取的選擇方案”,“相反,在人們能夠控制并非由他們(也可論證)引起危害的那些案件中,不應當因不公正而不去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不論在這些案件中行為和危害之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系,都不應因不公正而排除刑事責任。我認為這是因為被告人沒有對他們各自的受害人的死亡進行控制,他們的行為在道義上被認為是無恥的。即使人們確信某種因果關系的分析,這種因果關系的分析否定了這些案件中行為和危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我們的憤怒仍將因為這些被告人沒有對危害采取控制而依然存在”。在做出上述闡述之后,胡薩克教授提出兩個“追究不愿施善者”的策略,一是司法的方法,即從現有的關于殺人罪的制定法來尋找根據。二是立法的方法。胡薩克還舉出了弗蒙特州的一個相關法規。相比之下,胡薩克更傾向于立法的方式,因為以不作為方式殺人和以作為方式殺人兩者在“應受處罰性方面的任何差別,都應在一個正義的法律體系中反映出來。”②[美]道格拉斯·N·胡薩克著:《刑法哲學》,謝望原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67頁。
(三)筆者的觀點
必須指出,上述國外的理論雖不能直接用來解釋作為真正不作為犯性質的見危不救罪的合法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對見危不救罪設立合法性理論的建構。上述德日理論中,學者們一直是圍繞著不真正不作為犯理論來探討的。“危險增加”理論和“主觀的行為無價值”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也只是為不真正不作為犯罪尋找合法性依據和限制不真正不作為犯罪中作為義務的泛化弊端,而沒有直接涉及真正不作為犯的見危不救的問題。另外,日本 《修改刑法草案》第12條的規定也并不能作為見危不救罪的立法根據。因為,第一“具有防止犯罪事實發生責任的人”的范圍如何界定,換而言之這里的“責任”具體何指仍未說清楚。第二,這里的“特意”的含義到底是指代某種動機還是僅指必須具有故意還不明確。最后,沒有單獨的責任條款,在刑事責任上“和作為引起犯罪事實的場合同樣看待”則直接表明了該條款指向的是一種不真正不作為犯罪。
但筆者認為這些理論和立法實踐至少表明日本的刑法學界已經在將廣義上的見危不救行為規定為犯罪問題上達成共識,那么再進一步或者說將研究方向稍做調整就能夠觸及狹義的見危不救犯罪了,因為一旦承認了該種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上的義務,就等于承認了廣義見危不救犯罪化的理論建構,只是就構成何罪來說并未明了,例如我國理論通說認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包括法律上規定的義務來源,我國《婚姻法》第15條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但是,即使子女違背該義務將父母遺棄,造成父母死亡的結果,卻并不必然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的,而是構成虐待罪或遺棄罪。因此筆者認為德日的理論等于為不作為的故意殺人行為和狹義的見危不救行為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理論前提,剩下的問題就是為這個理論前提設計一個其外延和內涵能夠表達出見危不救行為犯罪化的歸宿條款。這樣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難題,一是尋求該條款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如何解決該條款的合法性,確切的說是如何解決見危不救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問題。筆者認為在這兩個問題上胡薩克教授的理論值得我們借鑒。雖然胡薩克教授所青睞的“控制理論”連他自己也承認“將控制原則適用于不作為領域是激進的”①[美]道格拉斯·N·胡薩克著:《刑法哲學》,謝望原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頁。,但是其上述理論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思考,一是道德義務的強化,使其直接轉化為法律上的義務來源,這有助于我們解決上述第一個難題。二是放棄傳統因果關系的約束,直接用“控制理論”來代替的構想。雖然筆者認為“控制理論”確是一種大膽的創新,雖然能否使用還有待考證,但卻啟發了我們轉換角度考慮問題。筆者的觀點是,狹義的見危不救行為是一種真正不作為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將狹義上的見危而救的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上的義務有其必要性,不救助行為所侵犯的并不是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而是人們心中普遍的善良情感及由這些情感構筑的我國社會主義重大道德體系。因此,廣義上的“ 因果關系”在這里是指不救助與重大道德體系受損之間的關系。這樣就避免陷入解釋不救助與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受損之間因果關系的泥潭。筆者將在以下第第三、四點中具體進行論述。
三、設立作為真正不作為犯的見危不救罪的必要性
(一)見危不救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這種行為極大地侵蝕了社會主義重大道德體系,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我國刑法通說認為道德義務不能作為義務的來源。但是否違反道德的行為從來不構成犯罪呢?這是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日本著名刑法學家小野清一郎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既不能單純用違反形式的法律規范來說明,也不能用單純的社會有害性或社會的反常規性來說明。法在根本上是國民生活的道義、倫理,同時也是國家的政治的展開、形成,它通過國家的立法在形式上予以確定或創造。”②張明楷著:《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頁。西原春夫教授也認為:“社會性的道義秩序成為獨立的保護權益,國民有遵守這種道義秩序的義務,違反這一義務,就被認為有違法性,構成犯罪”③[日]西原春夫著:《刑法的根基與哲學》,顧肖榮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其實從法理上說,道德與法律并不是絕緣的,法律往往滲透一定的道德同時又是鞏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支柱。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同的規范性命令……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則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④[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頁。如果沒有道德的支撐,法律就不能稱之為法律,或良好的法律。馬克思主義認為,犯罪的本質在于“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傳(中文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9頁。并且只有“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⑥同上,第416頁。可見任何行為只要符合:1.是反對統治關系。2.在量上達到“最明顯、最極端”。即必須符合犯罪的質、量要求,才能進入刑法調整范圍,視為犯罪。那么本罪中的“見危不救”的行為是否達到了犯罪質和量的要求呢?筆者認為從質上看,道德關系明顯屬于統治關系范疇;從量上看該種行為完全達到了犯罪的標準。“成人之美,與人為善”作為我國社會公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倡“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一個人應當與人方便,切勿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或見死不救”,而見危不救行為恰恰是直接違反了社會主義公德的要求,其危害結果是很嚴重的。因為“只有遵守這些社會公共規則,社會生活才能正常進行,社會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社會公德是社會道德的基石和支柱之一,如果社會公德這一道德的基石和支柱垮了,那么整個社會道德體系也就會垮掉,就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①黃娜、何齊宗:《青少年社會公德意識教育》,載《教育學術月刊》2011年第7期,第51頁。可見,見危不救行為侵蝕了我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這是設立本罪的最直接原因。進一步而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質文明就不會進步,甚至已有的物質成果都會喪失,這是設立本罪的深層次原因。
(二)從犯罪學角度看
在“危險”來源是違法犯罪行為造成時,見死不救或見危不救行為等于是幫助了犯罪分子。犯罪情境說認為:“犯罪情境主要是根據與犯罪的實施,有關的不同的人之間互動關系提出的概念,旁觀者的存在及其不同表現會對犯罪行為的實施產生不同的效果”,②肖劍鳴、皮藝軍主編:《罪之鑒》,群眾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頁。一般道德準則要求人們互幫互助與丑惡現象做斗爭,這無疑給犯罪人在犯罪前和犯罪中乃至犯罪后都產生一種威懾作用,或是使其不敢輕易犯罪或是使其不能順利實施犯罪,或是加速刑罰的及時性。在犯罪前,犯罪人一般會顧慮,旁觀者是否會阻礙、遏止自己的犯罪,旁觀者將來是否會成為指認犯罪的證人。在犯罪中,旁觀者罪前威懾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變成現實,形成特殊預防。比如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激起旁觀者的憤怒,使犯罪人不得不停止其犯罪活動,甚至被旁觀者扭送公安機關。在犯罪后,由于自己的犯罪被人親眼目睹,會對犯罪人的心理造成巨大壓力,進而促使其早日投案自首。另外,旁觀者的所見所聞,會給偵察機關提供大量破案線索,從而早日破案。最后,旁觀者可能變成在法庭上指認犯罪的證人。以上可見,旁觀者的存在及其表現,會對犯罪起到巨大的阻礙作用,在現實的犯罪中,犯罪分子一般都盡量避免其犯罪被人目睹,可見旁觀者的存在是犯罪分子所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而當“見危不救”成為一種普遍社會問題時,旁觀者的威懾作用,無疑大打折扣,這等于是減少了犯罪“失”的一面,犯罪分子心理天平自然就會傾向犯罪的一面,使其增強犯罪的決心,并且在犯罪時達到無所顧忌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說見危不救確是幫助了犯罪分子,增大了其犯罪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
(三)設定本罪是解決當前國內相關立法和司法領域混亂的根本手段
目前我國并非沒有關于見危不救的規范,但是其性質過于分散,不成體系并且其處罰和適用的范圍都很有局限性。現有的一些立法例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第32條: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給予處分。其中第(十八)規定:見危不救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罰條例》第153條規定:黨員遇到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能救而不救,依照黨內法規應當受到黨紀追究;《執業醫師法》第37條明確規定:醫師在執業活動中,由于不負責任延誤急危患者的搶救和診治,造成嚴重后果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或者責令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執業活動;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 2004年8月10日公布《檢察人員紀律處分條例(試行)》。該條例明確規定:檢察人員遇到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能救而不救,情節嚴重的,給予降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另外《深圳經濟特區急救醫療條例(征求意見稿)》等一些地方法規也對見危不救行為進行了相關規定。這其中有地方上的條例和部門立法;有執政黨的處罰條例也有軍隊的紀律條令;有醫療行業內部的規定也有司法職業的暫行條例。
這種立法上的混亂直接導致了司法中的混亂,當前我國不同地區的法院,對于性質相同或相當的見危不救行為可能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重刑與輕刑的判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注意到同樣的見危不救的行為在實踐中存在著以下現象:此地法院可能判有罪而彼地法院可能判無罪只承擔行政或民事責任;此地法院可能判故意殺人而彼地可能判玩忽職守罪;此地可能判“有期徒刑六年”,而彼地可能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甚至于行為人是否都被推向被告席也存在疑問(實際上在目前情況下判處見危不救行為人任何罪名都是不合適的,但如果不處罰,則等于放縱犯罪)。這種司法的混亂性無疑破壞了法律的統一,降低了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對我國法治國家的實現很不利。從反面看,在實踐中確有一些見危不救行為人被判刑,且沒有引起惡劣后果,群眾反而拍手稱快,這足以說明把見危不救行為定為犯罪,是有民眾基礎的,是有可行性的。
四、見危不救罪設立的立法與司法可能性分析
(一)立法可能性分析
通過考察外國和我國古代相關的立法可知,本罪并不是一種純理論的探討而早有其立法實踐,設立本罪并不存在立法實踐上的盲區。《法國刑法典》第223-6條第2款規定:“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夠喚起救助行為,且對本人或第三人無顯著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并科五十萬法郎的罰金。”1980年美國《幫助臨險者責任法》規定:“當人們知道他人面臨嚴重的人身危險時,而且沒有相同地位的人可幫助而不具危險,或沒有特定義務人對此負責,此時應給予幫助,除非已有別人給予幫助或關心,否則,處以100美元以下罰款。”《德國刑法典》第330條c規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險或急難之際,有救助之必要,依當時情況又有可能,尤其對其本人并無顯著危險且不違反其他重要義務而不救助者,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罰金。”此外《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條、《日本輕犯罪法》第1條、俄羅斯、奧地利、加拿大、西班牙、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刑法典也有相似條款。我國古代也有豐富的相關立法例:《睡虎地秦墓竹簡》在其中《法律問答》里,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為的懲罰措施。其中規定:“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唐律疏議》卷27中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并須告見在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宋刑統》卷28中見危不救的法律條款與唐代相同。《大清律例》卷24中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者,杖八十”。 可見我國現階段設立見危不救罪并不是毫無先例的嘗試,而有其可能性。
(二)司法可能性分析
有專家認為本罪在實施中缺乏可操作性,借此否認本罪的成立,筆者認為,任何法律在創設之初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借本罪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幾個問題來否認本罪是不成立的,筆者認為所謂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
1. 取證難:由于本罪的特殊構成形式,行為人在不救助現場是不會留下什么有價值的線索,這給偵察機關的調查取證帶來很大的困難,可以肯定在本罪中大量犯罪黑數和死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在任何一種犯罪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完全可以用提高犯罪反應速度和完善犯罪反應機制來減少部分黑數的產生,對于那些毫無頭緒,根本不能證明的見危不救,則不應啟動偵察程序。從另一層意思上講,設立本罪教育意義大于懲罰意義,如果從功利角度出發,投入有限的司法資源就能達到最佳預防效果,那又何必對一些毫無根據的犯罪去遵循嚴格刑罰報應主義而勞民傷財呢?
2. 在本罪的司法實踐中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即一案中多人同時犯本罪該如何處理。外國有學者認為“當很多人袖手旁觀而讓某人死去,我們要么追究眾多人的刑事責任,要么誰也不追究”。這些學者傾向于“誰也不追究”,否則“這樣一來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就太多了”。還有學者認為:“如果有一百個獨立的不作為者……而因為一個人死了,這一百個不作為者就每人承擔百分之一的謀殺罪。”對此觀點胡薩克評論道:“但是,這種責任按罪犯的數量成比例減少的觀點,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奇談怪論,而在法律上絕無任何類似規定。”胡薩克教授認為這種情況下應追究每個見危不救者的責任:“如果行為是應受懲罰的,因為太多的人卷入其中而抵消刑事責任,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①[美]道格拉斯·N·胡薩克著:《刑法哲學》,謝望原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267頁。筆者同意胡薩克教授的評論和方案,第一種方案公然違背了罪刑法定主義,實不足取。雖然胡薩克的方案確有浪費國家司法資源之嫌,但是,其一,這在理論上這是遵循罪刑法定的唯一結果。其二,只有這樣才不至于放縱犯罪并且采取這種措施不僅能對社會上其他成員起到巨大的安慰作用,同時也是一次極好的教育和警示,能更好地達到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其三,這種情況本身少見,在處理中也沒有多大疑難,對于不構成本罪的人調查清楚后盡數釋疑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且隨著本罪的實施,在實踐中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少,完全沒有必要過分擔心。
五、見危不救罪的基本構成
(一)本罪的主體
本罪的主體為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依法應負刑事責任的人,包括一般主體和特殊主體,一般主體是指沒有職務或業務要求的人,特殊主體是指具有職務或業務上救助義務的人。之所以規定特殊主體首先是因為法律上存在漏洞,而做出的權宜之策,比如,我國刑法中的玩忽職守罪,該罪的主觀方面認定為過失,那么行為人故意實施的玩忽職守行為就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例如:一女警眼睜睜的看著歹徒強奸婦女,卻故意不予救助,如果定強奸罪,肯定不合適,實踐中有定玩忽職守罪,但嚴格從理論上說這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其次在客觀方面,玩忽職守罪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與本罪的客觀方面在外表上看是基本一致的,這是本罪可能包括特殊主體的原因之一。
(二)本罪的主觀方面
鑒于本罪的行為特征,本罪主觀方面認定較為復雜,通常認為不包括過失,但到底是只存在直接故意,還是只存在間接故意或是兩者兼而有之,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本罪的故意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認識因素為“明知”,內容包括:1.“明知”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正遭受危險,如果對這種危險沒有認識則不構成本罪。 2.明知有必要且自己有能力救助,如果客觀上自己有能力救助,但卻沒有認識到則不構成本罪。這里“明知必要”可分為“明知相對必要”和“明知絕對必要”。“明知絕對必要”是指,明知只有自己的救助,否則處于危險中的人必不得脫險;“明知相對必要”是指:明知雖沒有自己的救助,但在一定條件下,被害人依靠自身力量或第三者幫助還是可能脫險的。3.明知自己如采取行動對本人或第三人無顯著危險,一般情況下,有無危險及危險大小的判斷是較困難的。如果確實沒有認識到自己救助會給本人或第三人帶來顯著危險,而進行救助,結果使本人陷入危險或造成重大損失,應認定為見義勇為。如果給第三人造成重大損失則可能承擔民事責任但不構成犯罪,如果采取救助對本人或第三人無顯著危險,卻誤以為有顯著危險,而不救助,則成立事實認識錯誤,不構成本罪。
在認識因素為“絕對必要”的情況下而不救助,那么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就不可能存在放縱結果的發生,因為結果是必然發生而不是可能發生或者可能不發生。此種情形只能成立直接故意。
在認識因素為“相對必要”的情況下,區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就存在一定困難。由于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消極的不作為,因此不論是希望還是放縱都表現為消極的不救助。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推定意志因素為放縱,成立間接故意,事實上,實踐中絕大多數行為人也確是放縱而不是希望危害結果發生。綜上,筆者認為在明知內容是絕對必要情況下,行為人主觀狀態為直接故意,在明知內容為相對必要的情況下為間接故意,這樣的劃分也是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因為絕對必要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大于相對必要,而刑法中直接故意的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也是大于間接故意。
(三)本罪的客體
綜覽各國本罪的立法,大多是將其歸入侵犯人身罪的范圍,而德國刑法則將其歸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章節中,①參見賈健:《法益還是規范:見危不助究竟侵害了什么?——以德國刑法典第323條c為基點》,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第209頁。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本罪的客體是不被救助人的具體人身安全或者是抽象的公共安全法益呢?本文認為,這兩種觀點均值得商榷:
首先,以上觀點均自覺不自覺地將本罪當作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為前提處理,將見危不救的行為與以作為的方式實施的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等同起來,因此認為見危不救罪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人身財產安全,但是既然本罪與作為犯罪有等價性,則應該直接適用相關作為犯罪的罪名,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無論是純正不作為還是不純正不作為,都是以違反一定作為義務為前提的。筆者認為,本罪成立的作為義務前提應是我國《憲法》第53條的“公民有遵守社會公德的義務”,所謂“社會公德”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道德,如果行為人犯了本罪,那只能說違反“遵守社會公德”的義務,又怎能說侵害了人身、財產安全呢?
最后,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本罪的設立也正是為了保護因“見危不救”行為所嚴重侵蝕的社會主義重大道德義務,因此,本罪中的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不救助與社會主義重大道德義務受損之間的廣義關系,而不是不救助與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受損之間的關系。實踐中人們譴責的也只是行為人不救助行為,痛斥其良心何在,感嘆世風日下的社會道德,而絕不會把行為人的不救助和造成危險的原因聯系起來,去譴責為什么給受險者造成損害。
綜上,筆者認為,本罪成立的作為義務前提應是我國《憲法》第53條規定的“公民遵守社會公德的義務”,其客體只能是人們心中普遍的善良情感及由這些情感構筑的我國社會主義重大道德體系
(四)本罪客觀方面
1. 必須是國家、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正遭受危險。其來源主要有:(1)自然災害;(2)動物的襲擊;(3)人的生理、病理原因;(4)違法犯罪行為。“正在發生”是指危險已經發生或迫在眉睫并且尚未結束。
2. 依當時情況有救助之必要。“依當時情況”是指以一般大眾正常思維結合當時客觀實際參考行為人實際情況為標準來判斷到底是否有必要,并不是行為人“想當然”認為。“必要”是指除非得到他人救助該遭受危險者必然不能或可能不能擺脫危險。“必要”反映出當時救助的“急迫性”。可分為“相對必要”和“絕對必要”,兩者在量刑時應區別考慮。
3. 能夠采取救助措施且對本人或第三人無顯著危險。“法律并不強人所難”,如果要求行為人冒著對第三人或本人有顯著危險對受險者進行救助,則屬于缺乏期待可能性。有無顯著危險有兩層意思:(1)是指根據社會大眾一般思維結合當時行為人實際情況做出的判斷,而不是行為人任意主觀臆斷,應該注意的是特殊主體在判斷有無顯著危險方面應嚴于一般主體。“無顯著危險”并不意味著毫無危險而是說雖然會遭到一定危險,但從量上看相對于受險者的危險是微不足道的或甚至不能完全排除造成較大的危險,但顯然出現的概率是非常小的。總之,行為人所受危險或可能受的危險明顯處于一般大眾情理所能接受的范圍之內。(2)這里的“危險”取決于救助行為可能給本人和第三人帶來的危險,而不取決于救助對象所正在遭受的危險。救助對象所遭受的危險與救助行為可能給第三人或本人帶來的危險并無絕對必然聯系,而是相對聯系。例如:犯罪人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殺人,這時并不能因為持刀殺人的危險性大而認為如救助則必然遭受重大危險,因此無動于衷、毫無作為。筆者認為,這時法律并不要求勇敢上前與行兇者搏斗,但可以要求在遠處的旁觀者打個報警電話通知警察來救助,否則可能構成本罪。除非有證據表明實施任何的救助行為都將面臨重大危險時,不作為人或者與之關系密切之人才不會因為不實施救助而受處罰。
4. 不予救助,情節嚴重的行為。“不予救助”是指對發生的危險,任其繼續發展甚至造成實在的損害后果,而漠然處之,無動于衷,或雖有救助動作,但顯然不是法律所要求和期待的行為,“情節嚴重”是指其不救助行為在社會上造成非常惡劣影響,嚴重破壞人們的善良情感,侵蝕公民的思想道德并使社會主義道德體系趨于分散和產生離心力。因行為人的不作為使犯罪客體諸如:人身、財產安全持續處于危險狀態而不得脫險甚至造成實際損害后果的,則推定為本罪客體造成侵害。反之,如果對象雖未遭到損害但確實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則也認為對客體造成侵害,仍然成立本罪,但在量刑中可以考慮從輕。
六、見危不救罪的法定刑設置與規范表述
筆者認為,基于對本罪的客體考慮,本罪應列于《刑法》第二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之中,本罪具體的條文設計可分兩款:第一款規定基本犯,第二款規定加重犯,適用于負有救助義務的人,本罪的刑罰設計,筆者認為可借鑒德、法、意三國。《德國刑法典》第330條規定,“……處1年以下人身自由刑或并科罰金”、《法國刑法典》第223-6條規定“……處五年監禁并科50萬法郎罰金”、《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條規定“……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六十萬里拉以下罰款”。可見,通過對三個國家的立法比較可以看出,見危不救罪的立法規定有兩個特點:1.都規定了短期自由刑。2.規定了罰金刑,或得并制或必并制或選科制。結合我國國情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筆者認為在主刑上:一般主體犯本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職務上、業務上負有特定責任的人犯前款罪,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筆者認為,對于一般主體只要規定較輕短期自由刑就足以達到特殊預防作用,同時對于社會上其他人也足以起到教育作用,對于特殊主體規定較重法定刑,主要是適當高于類似“玩忽職守罪”的處罰,以示主觀惡性的差異,另外與司法實踐中對完全符合本罪特征卻定“故意殺人罪”的處罰相當,不至于出現前后刑罰嚴重脫節的問題,是較合適的刑罰。在罰金刑的選擇設置上,采取必并制。在司法實踐中可以適當多判處緩刑只執行罰金刑,以緩解監獄壓力和避免交叉感染并減少行為人的反社會情緒,緩和由設立本罪所可能帶來的社會緊張氣氛。
綜上,其具體表述如下:
第×××條:公共安全,或他人的人身安全遭受正在發生的危險時,依當時情況有救助之必要,能夠采取措施且對本人或第三人無顯著危險,而故意不予救助,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
具有特定職務上、業務上救助責任的人犯前款罪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責任編輯:林貴文)
D914.3
A
1674-8557(2016)04-0092-09
2016-11-30
本文系2014年重慶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犯罪被害人導向的刑事政策研究》(項目編號:2014BS0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楊玲(1988-),女,福建寧德人,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