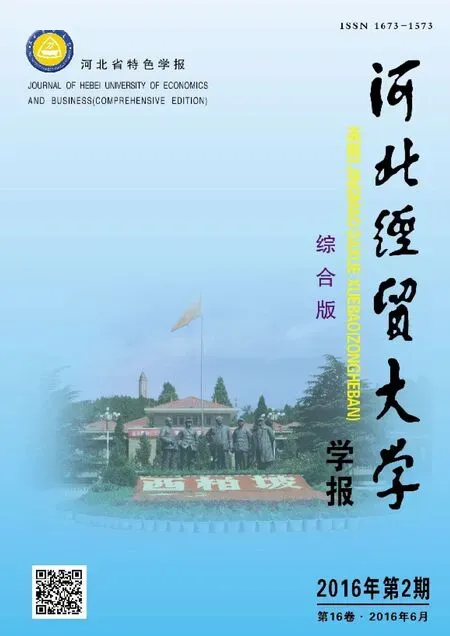民族自治地方司法變通的合理性論證
蒙志敏
(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民族自治地方司法變通的合理性論證
蒙志敏
(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不應享有法律變通權這一命題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這一命題是以現代民主政治理論為基礎的立法權的話語霸權的結果。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應當享有變通法律的權力,以交往行動理性為核心的法律商談理論為民族自治地方司法機關享有法律變通權提供了合理性說明。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司法權;法律變通權;話語霸權;合理性;法律商談理論;現代民主政治理論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建設遇到的突出問題是國家法和民族地區原生態的習慣法之間的沖突問題。對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思路。站在國家法中心主義立場的學者主張以進步的國家法取代民族地區落后的習慣法;以法律多元主義為立場的民間法學者認為,法律多元是當今社會的基本樣態,民間法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習慣法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此國家法應當為民族習慣法保留適當的生存空間。當國家法與民族民間習慣法發生沖突時,不應當一味地強調國家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相反民間法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空間可能更具有合理性。因而為了使國家法律能夠更有效地被貫徹實施,對國家法律進行變通使其與民族地區原生態的習慣法更具有相容性便成為民族自治地方適用國家法律時的重要目標。無論是國家法中心主義者還是法律多元主義者都主張通過法律變通這種技術手段來協調國家法與民族地區習慣法的沖突問題。只是國家法中心主義者僅僅把法律變通尤其是立法變通作為國家協調國家法與民族習慣法之間沖突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還是要實現國家法一統天下的目的。而法律多元主義者認為法律多元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國家法和民族習慣法都是法律多元中的一元,多元的法律之間存在著一種競爭和沖突關系,如何協調國家法和民族習慣法之間的沖突關系是多元法律社會的永恒的主題。因而法律變通作為協調國家法與民族習慣法之間關系的技術性手段將與多元的法律現象共存。法律變通作為協調國家法與民族習慣法沖突的技術手段,究竟該如何變通,即誰可以變通,怎樣變通成為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根本問題所派生出的具體問題。本文僅就誰可以行使變通權問題進行理性的論證,至于如何變通問題留待以后繼續研究。關于誰可以進行變通問題則涉及到變通權行使的主體問題。
一、話語霸權:立法變通權的權威屬性取得
目前國內研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或研究法律變通制度的大多數學者認為,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機關才可以行使法律變通權,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不應當行使法律的變通權。并且這些研究者就民族地區的司法機關為什么不應當行使變通權進行了看似頗為合理的論證。現有的國家正式制度關于法律變通權的規定,也都是對立法變通權的規定,即都規定了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機關才可以享有和行使法律變通權,而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則無權行使法律變通權。學者的言說與國家的正式法律制度互相建構,在這一互相建構的過程中民族地區的立法變通權不僅獲得了一種由國家正式承認的權威性,而且也為其贏得了一種話語權地位。當立法變通權成為一種話語,它就取得了一種天然的正當性,就會被人們不加反思地予以接受。似乎是只有
立法機關才能行使法律變通權成為一種真理。任何允許其他機關行使法律變通權的制度或理論都是對真理的違背。在這種觀念影響下,主張賦予司法機關法律變通權無異于大逆不道。為了論證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應當享有法律變通權,我們不得不打破只有立法機關才可以行使法律變通權的話語霸權地位,揭示出這一話語形成的內在機理。因此我們不得不予以深究的是,什么是話語霸權,立法變通權的話語霸權是如何形成的,這一話語霸權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后果。
(一)對話語霸權的理解
在對話語霸權的研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了。他們的學術貢獻在于關于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以及語言和權力關系的論述。因此,研究他們的理論對于話語霸權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對于話語霸權含義的精準理解對于揭示立法變通權的話語霸權地位的形成機理以及后果具有重要的意義。
福柯認為:“權力制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1]福柯的這段論述揭示了知識和權力之間的相互關系。而話語作為知識載體,當然也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權力關系。布迪厄更進一步揭示出語言和權力的關系。他認為,任何合法語言都是國家體制所擔保的某種符號權力的結果。布迪厄以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語言統一過程來說明,法語上升為官方語言,是通過對其他地方性方言的排斥來實現的,它是社會政治權力運作的結果。[2]福柯和布迪厄的話語言說共同遵循著權力機制,他們都認為,“沒有權力的介入,就沒有話語;反過來,每一種話語的產生和傳播既體現權力,也加強權力。”[3]由此看來,話語霸權體現的是言說者與受眾之間的一種權力與服從的支配關系。話語霸權源自于現實社會中的權力斗爭關系,而話語霸權反過來對現實的權力關系具有一定的建構作用。據此我們可以推斷,立法變通權的話語霸權源自長期以來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權力斗爭關系,反之,關于這種關系的演說的產生和傳播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權力斗爭關系。正是關于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支配關系的言說,使得立法權相對于司法權獲得了一種話語霸權地位。立法權相對于司法權的話語霸權地位,是立法變通權相對于司法變通權獲得話語霸權地位的前提。
(二)立法權話語霸權的取得
那么在我國關于立法變通權的話語霸權地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筆者認為,在我國立法變通權的這種話語霸權地位,源自于在漫長的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斗爭中所形成的權力斗爭關系,而在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立法權對司法權支配地位的取得使得立法權形成了一種話語霸權,這種話語霸權對于立法權在現實權力斗爭關系中的地位獲得具有加強和鞏固作用。
根據我國法律史學者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立法權并非在一開始的時候就相對于司法權具有權威性地位;恰恰相反,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發展的早期階段,居于權威性地位的應當是司法權而不是立法權。①只是到了戰國時代,法治觀念的興起和成文法的誕生,立法權才逐漸取代了司法權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土地私有權和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權利,把自己的意志言說成為反映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正無私的法”,并主張以功利主義的“法治”代替血緣身份的“禮治”。因此,在戰國時期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在權力斗爭中對封建貴族階層的勝利,作為其利益代表的“法治”的話語逐漸取代封建貴族利益代表的“禮治”話語。而法治話語的典型特征就是其對封建等級特權和司法任意與專斷的反對。成文法具備限制特權和專斷的特征,因此,其被新興地主階級作為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地位與司法專斷的有力工具。于是成文法時代,新興統治階層在法治精神的指導下“為了使各級司法官吏能夠明白無誤地依法辦事,以實現司法的統一,故而將法條制定得十分詳細,一覽無余。”[4]法治語境下對成文法的依賴使得立法權獲得了對司法權的權威性支配地位。從此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就進入到立法權居于權威性支配地位的時代,期間雖然出現過為了彌補成文法的缺陷和不足而讓司法機關獲得一定的自主空間,但是相對于立法權而言,司法權仍然處于次要地位,其僅僅是在制定法的空隙處發揮補充作用。立法權權威性地位的獲得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然而卻被封建統治階級言說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維護社會正義的工具,因而其在某種程度上就獲得了某種正當性,并且這種正當性被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的理論言說不斷地強化,以至于成為
那個時代的真理。
到了近代,滿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國內國外形勢下出于變法圖強的政治目的開始了變法修律運動。這場變法修律活動的直接后果就是改變中國既有的法律傳統,引進西方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在這場變法修律活動中,由于大陸法系和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共同的對成文法的尊崇使得中國在這次變法修律活動中以成文法全面取代判例法而告終。成文法對判例法的取代再次將立法權置于權威性支配地位。雖然在這一變法修律的過程中,司法權面對立法權對其全面的排擠也進行了不斷的抗爭,然而由于變法修律活動的主持者沈家本一派手握大權,使得立法權依然戰勝司法權取得了至尊的地位。②北洋政府時期,針對當時成文法典的不完備和成文法典的僵化等方面的缺陷,北洋政府的大理院在審判實踐中大膽采用了判例法,使得司法權在同立法權的斗爭中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③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國民黨當權者為了鞏固國民黨的政治、經濟統治地位,再次舉起了法治的大旗,提出了“從速”“從嚴”地建立一個體制完備、規范周密、人人守法的法治國的主張,在這一主張下,國民政府著手進行法制建設。正是圍繞著法制建設的任務,國民政府制定了中國法制史上數量和規模空前的成文法典。當國民政府在大張旗鼓地創制成文法的同時,一大批法學家和立法、司法實務界有識之士也在呼吁承認判例法的地位。正是這一批具有真知灼見的法學家的呼吁,使得國民黨政府不僅承認了判例法的合法地位,而且還規定了其運行機制。④雖然國民政府時期,成文法與判例法并行的運行機制的確立為司法權贏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但是司法機關的司法權的獨立地位依然是有限的,其在組織上依然受國務會議和國民黨政治會議的指導和監督。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法律制度開始步入到現代化的進程中。根據武樹臣先生的劃分,這一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中國法律制度現代化的探索階段和中國法律制度現代化的實施階段。在這兩個階段,法律制度的運行機制各有特色,與之相應,立法權和司法權在法律運作實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在中國法律制度現代化的探索階段,在階級斗爭擴大化指導思想影響下,出現了“階級本位”的法律觀。在“階級本位”法律觀指導下,法律的運作機制是“政策法”的樣式。政策法作為一種不穩定的、過度的法律實踐狀態,其本身蘊含著兩種發展趨勢:成文法的發展趨勢和判例法的發展趨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政策法”的運行機制,為判例法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土壤和環境。在這一時期,判例法曾獲得了兩次長足的發展契機,⑤然而由于人們偏愛成文法的傳統心理,最終并未確立起“判例法體系”。判例法體系的未能確立,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司法權在爭取權威性地位的斗爭中失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正式步入實施階段,這一階段法律制度的運作機制,正式地由“政策法”轉變為“成文法”。這一時期,由于人們存在一種誤識和偏見,即認為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成文法治理國家,加強法制建設就是加強立法工作,允許判例法存在有可能影響國家法制統一。因此,這一階段黨和國家的主要目的和任務就是立法工作,一直倡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任務,而忽視了法律的實際運作和實現問題。正是由于人們的誤識和偏見加上偏愛成文法的傳統心理,使得立法權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權力場域中的權威地位。
二、立法變通話語霸權對司法變通權合理性的抑制
(一)現代民主政治理論對司法變通權合理性的抑制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差異較大的國家,因此國家在運用法律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治理過程中存在一個突出的難題,即統一的民族國家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統一性、抽象性與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特殊性、差異性和具體性存在沖突。國家為了解決這一突出的矛盾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國家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民族自治機關,并允許自治機關結合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情況行使自治權。自治區少數民族行使自治權實際上就是對國家一般的治理制度、法律、政策的變通。由于法律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因此對國家一般法律制度的變通就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內容。究竟誰可以對國家的法律、政策以及制度進行變通呢?
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治理工具的法律是在民主的基礎上通過合法程序制定的,因而被認為是民族國家內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意志的體現,而體現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意志的法律制度被認為是正當的。因此民族國家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來自于被民主政治承
認的程序規則。由于民族國家的法律制度具有合法性,因而其就對民族國家的成員構成一種規范性導向的命令。民族國家的成員就有義務遵守在這種政治制度基礎上產生的法律制度。司法機關作為民族國家的一種建制,它并不是民意的表達機關,按照民族國家的建制它僅僅是以合法的法律制度對組成民族國家成員的行為進行評判,因此它無權對作為民意表達的法律規范進行變通。如果允許變通有可能導致一種后果,就是允許以少數人的任性、專斷影響多數人的意志。因此,現代民主理論堅持認為,司法機關僅僅是法律(人民意志)的執行機關,它只能嚴格執行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不能對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進行變通。即使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發現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有漏洞或缺陷,或與社會現實有差距時,為了適用的便利也只能按照立法機關的原意對法律作出解釋。這樣立法權就獲得了相對于司法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
(二)我國民主政治實踐對司法變通權合理性的抑制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現代民主政治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傳統的契合,因此伴隨著我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其逐漸成為我國政治制度建設的理論依據,其結果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代表人民行使體現人民意志的國家權力,其中包括立法權。雖然司法機關被譽為人民司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的司法權,但是其作為立法機關的執行機關,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種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本意而言,其僅僅具有執行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因而司法機關僅有執行法律的權力而不具有變通法律的權力。
基于這一理論前提,我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立法法相繼對民族自治地方變通法律的權力做出了規定。除此之外,我國的民法通則、刑法、婚姻家庭法等也授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對于上述法律條文中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可以結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實際情況制定變通規定和補充規定。但是通過對上述憲法、法律中有關法律變通權自治規定的法律條文的分析來看,上述這些條文僅僅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可以對法律條文進行變通規定和補充規定,而按照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僅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權力機關和政府,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因此,從現有的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來看,法律變通權僅僅是立法變通權而不包括司法變通權。國家正式的法律制度的規定奠定了立法變通權的權威性地位。立法變通權這種權威性法律地位的取得使得研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法律變通權的學者內心形成一種確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享有立法變通權是正當的,而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享有法律的變通權是不正當的。因為按照一般的正義觀念,正義就是按照法律規定行為,反之就是不正義的。[5](P49)在這種內心確信的指引下,學者們引證各種材料以證明這種確信是正確的。學者們的各種論說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確信的正確性。但是,立法變通權因其獲得國家正式法律制度的承認因而就具有正當性,而司法機關變通法律的事實因為沒有得到國家正式法律的認可因而不具有正當性究竟是否就是正確的?國家正式法律制度只承認立法變通權而不承認司法變通權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國家正式制度僅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機關法律變通權而未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機關法律變通權并不是客觀真理,其不過是現代民主理論主導現代政治制度的話語權的產物。而民主理論并非是絕對的真理,民主制度也并非是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正如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分析的那樣,“民主的缺點馬上可以察覺——而其優點只有經過長期的觀察才能發現。”[6]民主制度由于賦予多數人無上的權威,而無上的權威在托克維爾看來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所以任何人都不應當被賦予無限的權威。因而如若不對多數人的權威進行適當的限制,它就容易造成多數人的暴政。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代表多數立法機關的無上權威應當受到必要的合理的限制。那么代表多數的立法機關的權威應當受到誰的限制,應當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以及通過何種方式進行限制呢?這種限制是否為司法機關行使法律變通權提供了某種契機呢?如果允許司法機關以變通法律的形式限制立法機關的無上權威,那么這種限制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三、交往行動理性:司法變通的合理性基礎
如前所述,司法變通權行使的目的是為了對立
法機關無上的權威進行適度的限制以便克服由于多數權威的無限行使所可能導致的多數人暴政這一民主制度的缺陷。但是在現代社會,任何制度的存在必須具備合理基礎,這一基礎為這一制度的正當性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這種合理性解釋只有得到人們的認可才能為人們接受。那么司法變通權的合理性基礎是什么呢?
(一)合理性概念的演化
“合理性這一概念來源于理性時代對于一切事物理性化評價的基本愿望和基本要求。”[7]在理性時代,理性成為萬事萬物的評價標準,凡符合理性的事物都被認為是正當的。但是理性的概念是不確定的,隨著理性概念的變化,合理性的要求也不同。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時代理性被分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理論理性是指為人們提供確定原則的知識或者哲學智慧。實踐理性是指在自己所處的具體條件下,為人們的行為提供理性指引。”[8](P49)由于亞里士多德堅信,人性和宇宙存在著某種本體論的結構,這一本體論結構就是事物的本質,所以亞里士多德鼓勵對事物本質的探求。所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的本質就是事物的基本性質,它們存在于事物運作的自然過程中而非存在于超越時間空間的理念世界,因此亞里士多德對事物本質的探尋轉向了周圍世界的運行方式。他假定事物是以可以預見的方式運行的,在這一假定的前提下將自然變化與人的行為變化做了區分。自然變化是對自然實在所具有的內在行為方式的回應;而正是自然物體向其終極目標變遷的過程中,物體和行為的善才得以顯現。每一個具體行為所要達到的終極目的就是善,因此善存在于具體情形之中。但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善雖然存在于人的內心,但我們并不因為某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定達到至善,如果我們不刻意去追求并選擇按照善的要求去行為,善不會出現。前一種關于存在于物體和行為中的善的知識和原則就是理論理性;人們在具體情形下按照善的要求對人的行為發出的規范性指示就是實踐理性。因此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對行為合理性的評價就是事物本身的發展變化是否符合善的規范性命令。這種合理性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實體合理性,這種整體意義上的合理性觀念一直延續到中世紀,說某一法律制度或行為是合理性的,是因為這一制度或行為是符合整體意義上的善的規范性命令的。
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形成于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實體性理性概念發生了分裂。康德(Kant)通過對統一的實體性理性概念的批判奠定了傳統實體性理性概念分裂的基礎。他指出了在三個不同領域三種不同的理性在發揮著不同的作用。⑥理性概念的分化所帶來的好處是,它促使知識結構的分化和學科的專業化。但同時它也帶來了現代性的難以克服的缺陷:即價值的斷裂和現代社會危機的癥候。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為了解決現代社會的這一危機問題,他從社會行為的層面上把握理性的概念,將社會行為分為實質合理性行為和形式合理性行為。韋伯以實質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聯接為出發點提出了一個實踐理性的復合概念來解決由于理性的分裂導致的現代社會的危機問題。但是在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看來,韋伯的這一努力遠未成功。因為“韋伯雖然提出了實踐理性的復合概念,這個復合概念是以目的合理的行動方面與價值合理的行動方面的連接點為出發點的。但是韋伯在另一方面,卻完全按照目的合理性來考察社會合理化。”[9]因此哈貝馬斯在韋伯對理性概念把握的基礎上試圖重建理性的統一性,他提出了交往行動理性概念取代了韋伯的實踐理性概念,交往行動理性概念并不是對前現代具有宗教色彩的實體性理性統一概念簡單恢復,也不是僅僅對實踐理性概念更換了一個標簽。
哈貝馬斯通過對米德(Mead.George.Herbert)和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社會理論的研究,發現了語言和交往在現代社會整合中的意義,由此引申出了交往行為概念實現對社會理論的重構。哈貝馬斯指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10]由于交往中同時包含了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領域三個領域之內有效性的要求,所以交往行為是最具合理性的行為,交往行為中蘊含的理性最能承擔起彌合理性的分裂,促進人類的知識在最具合理的軌道上運行這一重要任務。交往行動理性概念相對于實踐理性概念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征:首先,“交往理性不再被歸諸單個主體或國家或社會層次上的宏觀主體。相反,使交往理性成為可能的,是把諸多互動連成一體、為生活形式賦予結構的語言媒介。”[11](P4)其次,交往行動理性不像古典形式的實踐理性那樣是行動規范的源泉。它只是在如下的意義上才具有規范性的內容。[12](P5)第三,“交往行動理性使得一種對有效性的主張的取向成為可
能,它本身并沒有給實踐性任務的完成提供確定內容的導向——它既不提供具體信息,也不直接具有實踐意義。”[13](P6)因此,交往行動理性概念是在批判實踐理性概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在批判地繼承了實踐理性概念合理性內容的同時發展了實踐理性概念,使得在新的語境下這一概念更加適合重構社會理論的功能。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當我在同重構性社會理論的聯系中堅持使用交往理性概念時,上述區別必須放在心上。在這種新的語境中傳統的實踐理性概念獲得了新的某種程度的啟發價值,它的作用不再是直接引出一個關于法和道德的規范理論。相反,它提供一種導向作用,引導人們對形成意見和準備決策的諸多商談——合法行使之民主統治的基礎就在于此——所構成的網絡進行重構。”[14](P7)因此,在現代社會以重構社會理論為目的的新的語境下,交往理性概念是評價社會行為的最好判準,進而以交往理性概念對作為社會整合的重要行為之一——司法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進行解釋和評價是最恰當不過了。
(二)司法變通的合理性解釋——以交往行動理性為視角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解釋,人類社會由傳統進入現代的過程就是除魅的過程。伴隨著世界的除魅化過程形成于傳統時代的確定性逐漸喪失。一方面人們渴望通過理性認識除魅化了的世界,獲得關于世界的確定性的知識;另一方面由于理性自身的反思性特點決定了知識的不確定性。現代性的危機主要是確定性的需求與不確定性的現實之間的內在張力。現代性的這種危機在法律領域的體現就是:一方面從外在觀察者的視角來看,法律作為現代社會系統中一種社會整合的工具應當具有確定性能夠為人們的行動提供確定的預期;另一方面從內在參與者的視角來看,法律作為人們具體行動的指南能夠滿足不同時空中人們的正義感,即客觀上的法律的確定性與主觀上的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的內在張力。這一張力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也就是在司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為法律理論家而且對法律適用者提出挑戰。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西方的法律理論家們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做出了不同的努力。法律的闡釋理論認為,法律適用的過程就是一個闡釋過程,就是在一種受評價影響的前理解的基礎上,通過在如果—那么、由于—因而之間循環往復的解釋來實現法律的規范與事實之間的統一。法律闡釋理論通過訴諸法律適用者群體共通的前理解,來保障以闡釋的方式實現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之間的統一的過程中不致喪失法律的確定性。然而正如法律實在論所批判的那樣,法律闡釋理論所建構的闡釋過程本身沒什么問題,問題在于法律適用者本身受評價影響的前理解。法律實在論者通過觀察發現法律適用者的前理解受適用者本身的階級地位、生活社會環境、教育狀況甚至適用者本身性格的影響。正如法律實在論者所觀察到的那樣,由于法律適用者群體的前理解本身的不確定性,就有可能出現在通過闡釋過程這一方式實現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正確性之間的統一的過程中降低、削弱甚至喪失法律的確定性。實際上美國現實主義法律運動的出現就是這一理論走向極端的一個例子。與此相反,法律實證主義者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突出強調法律適用者適用法律過程的合法律性,而這個法律被實證主義法律理論家們建構成規則體系的系統結構。這一系統結構包含調整行為的初級規則和用于自我指涉地產生規范的次級承認規則。法律的確定性通過法律系統的封閉性和自主性得以保障,而法律的正確性通過立法程序符合次級的承認規則得以實現。然而正如其批評者所言:“這種把法律的有效性同它的起源綁在一起,合理性問題就只能做一種不對稱解決。理性或道德在某種程度上被置于歷史之下。因此對司法判決的實證主義理解過分重視了確定性保證而忽視了正確性保證。”[15](P250)實際上無論是闡釋學理論、法律實在論還是法律實證主義者依然未能解決事實與規范之間的關系問題。美國新自然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德沃金(Ronald M.Dwokin)為了避免上述三種理論在解決事實與規范之間關系問題方面的缺陷,通過轉向一種義務論的權利概念,建構了一種法律理論,即建構性闡釋理論。建構性闡釋理論將法律解釋成是一個由規則、政策原則構成的法律體系,司法判決過程并非像法律實在論者所宣示的那樣充滿了不確定性,也并非像法律實證主義者那樣為了滿足確定性需求將判決的正確性建立在符合現行有效的法律規定基礎上的形式意義上的合法律性,而是一個受法律理論指導的建構性的詮釋過程,在司法判決的過程中,法官通過建構性的詮釋使得其判決具有符合原則的唯一正確性。建構性詮釋的法律理論所認定的判決的正確性,既不是符合客觀真實的真實性,也不是符合人們正義感的真誠性,而是一種融貫性。
因此,建構性法律闡釋理論克服了法律實在論和法律實證主義在解釋內在于法律有效性之中的確定性與正確性之間張力方面存在的缺陷,闡釋了在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者是如何通過建構性詮釋實現法律的確定性要求和合理可接受性之間的統一的。
然而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那樣,建構性詮釋理論對法律適用者,即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法官的智慧必須像赫拉克勒斯所具有的力量那樣強大,然而這一條件事實上很難滿足,所以德沃金的理論注定只能是一種理想。哈貝馬斯認為,要想使德沃金的建構性闡釋理論成為可能,應當對這種建構性闡釋過程進行一種程序主義的理解,這種理解把對于建構性闡釋形成指導的理論提出的理想化要求轉移到法律商談之必要的語用預設的理想化內容上去。這樣哈貝馬斯以一種建立交往行動合理性基礎之上的法律商談理論為司法機關如何解決司法領域出現的法院判決的正確性與自洽性之間的張力的合理性提供了恰當的解釋。
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社會中法律的合法性與法律的實證性之間的沖突是現代以來由于理性的分化所導致的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內在張力在法律領域的具體體現。要解決這一沖突單純從法律的視角考慮難以找出恰當的方法。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建構的交往行動理性的概念在彌合由于理性的分裂造成的現代性的危機所具有的效果同樣可以應用到法律領域。在法律領域以交往行動理性概念為基礎形成的理論被稱為法的商談理論。法的商談理論對于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協調法律的自洽性和法律的正確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和說明。法的商談理論是在法的商談論視角下提出的一種超越了資產階級形式法和福利國家實質法的第三種法律范式。這種法律范式主張對福利國家的實質法從程序主義的角度加以理解。截至目前,法的商談理論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司法最具說服力的合理性的基礎。
我國目前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傳統的實質合理性觀念和現代的形式合理性觀念并存。以形式合理性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國家正式法律制度在適用的過程中與以實質合理性為基礎的民間非正式制度常常發生沖突,這一沖突在少數民族地區尤其突出。對于這一沖突的解決,我國曾經存在這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認為,以實質合理性為基礎的民間規范是封建迷信,是落后的應當被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法律規范所取代;⑦另一種思路雖然也認為民間規范應當被取代,但是由于人們的思想上的慣性的支持,這種規范在特定的時空中還具有相當的生命力,若簡單粗暴地以現代性的法律取代民間規范所花費的社會成本太大,因此主張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逐步以現代性的法律制度取代民間規范,因而在特定的時空中允許民間規范存在。其具體措施就是我國憲法、法律中規定的法律變通制度以及學者們言說的法律變通的理論。筆者以為,上述兩種解決思路從表面上看似乎不同,事實上二者如出一轍。二者存在一個共同的前提是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正式制度是優于具有實質合理性的非正式制度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使我們認識到,無論是以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范式取代實質合理性的法律范式,還是以實質合理性的法律范式取代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范式都不是解決法律領域的危機癥候的最佳方法,哈貝馬斯的以交往行動理性為基礎的法的商談理論是目前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因此,在我國要解決國家法與民族地區習慣規范沖突的最佳選擇并不是對具有實質合理性的習慣規范回避或簡單粗暴的排除,而是應當對他們在程序主義的角度加以考慮。如果對實質主義的法律規范從程序主義的角度加以考慮可以在兩個層面進行,一是在立法層面,二是在司法層面。如果在立法層面對這些實質性習慣規范進行了程序主義考慮一旦進入國家法律體系,那么毫無疑問作為公民個人和司法機關就應當遵守。如果具有實質合理性的習慣規范并未在立法實踐中進行程序主義的考慮,在司法實踐中又遭遇到,司法機關因而面臨一個問題,要做出一個判決既是正確的,同時又是自洽的。這時司法機關究竟應當如何去行動呢?法律商談理論為司法機關的實踐行為提供了一種思路。這種思路要求,法律以組織規范的形式運用于自身,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創造一種司法權能,而且是為了建立作為法庭程序之組成部分的法律商談。在法律商談過程中,正式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在一種由特別程序支配下進行了充分的論辯。在這一論辯的過程中,程序規則并不對規范性商談本身進行實質上的調節,而只是在時間維度、社會維度和實質維度上為受運用性商談邏輯支配的自由交往過程所需的制度框架。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各方在理想條件下自由交往互動達成無強制的共識。在以法律商談理論為導向的司法實踐過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商談過程中都有可能被變通。因此,以交往行動理性為基礎的法律商談理
論為司法機關的變通行為的合理性提供了有效的解釋和說明。
結語
從前述分析來看,司法機關不應當享有法律變通權,只有立法機關才能享有法律變通權并非是一個客觀真理,它只不過是長期以來立法權所處的話語霸權的一個結果。司法機關可以享有變通權,但是應當對其享有的變通權進行必要的規范。法律商談理論為司法機關的變通權的正當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釋。
注釋:
①根據中國法律史學者武樹臣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被劃分為六個階段:即神本位——任意法階段;家本位——判例法階段;國本位——成文法階段;國、家本位——混合法階段;個人本位的介入——混合法階段;國、社本位——混合法階段。武樹臣先生認為,在任意法階段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文,作為“御廌”具有神權色彩,司法裁判的任意性、隨機性很大。但是隨著法律實踐的連續進行,產生了對任意法的否定因素,出現了參照成例判決,于是就進入判例法時代。在判例法時代,司法審判的典型特征可以用晉卿叔向的一句話來概括: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②清末變法修律過程中關于成文法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判例法即比附援引之爭實際上就是立法權和司法權之爭。以沈家本為首的修律者認為,中國固有的判例法是落后的東西,不符合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應當全面引進成文法取而代之。以成文法取代判例法實際上就是立法權對司法權的戰勝。
③北洋政府時期,其司法領域采用的是雙軌制,司法部門除了以制裁手段維護成文法律的尊嚴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司法機關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積極主動地擔負起寓立法于司法之中的職能和責任。
④國民政府為同一判例的創造與適用,曾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司法院組織法》《司法院處務規程》等。
⑤⑥他指出在以客觀世界為對象的認知領域,起作用的是理論理性;在人類社會實踐領域,人要遵循實踐理性;在思維領域,審美理性起決定作用。
⑦我國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被稱為現代化運動的一系列活動其本質就是這種思路。
[1]【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29.
[2]【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言語意味著什么[M].楮思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0-23.
[3]Sara Mills.Michel Foucault[M].New York:Rout ledge,2003:p.55.
[4]武樹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320.
[5]【英】韋恩·莫里森.法理學[M].李桂林,等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49.
[6]【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國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63.
[7]楊道波.自治條例立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
[8]【英】韋恩·莫里森.法理學[M].李桂林,等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49.
[9]【德】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性(第一卷)[M].洪佩郁,藺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323.
[10]龔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哈貝馬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M].北京:商務出版社,2003:50.
[11][12][13][14][15]【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4,5,6,7,250.
責任編輯、校對:武玲玲
On Rationality of Judicial Adaption in Minority Autonomous Areas
Meng Zhimin
(Law School,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 730020,China)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judicial organ of minority autonomous areas should not have the power of judicial adaption does not have natural rationality.It was the result of legislative discourse hegemony based on modern democracy.This paper points out clearly that the judicial organ of minority autonomous areas should have the power of judicial adaption,which was provided by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based on commutative action theory
minorityautonomousareas,legislativepower,judicialpower,powerofjudicialadaption,discoursehegemony,rationality,discourse theory of law,theory of modern democracy
D927
A
1673-1573(2016)02-0067-08
2015-06-14
教育部項目“法律變通問題研究”(09CFX031)階段性成果
蒙志敏(1975-),女,內蒙古赤峰人,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