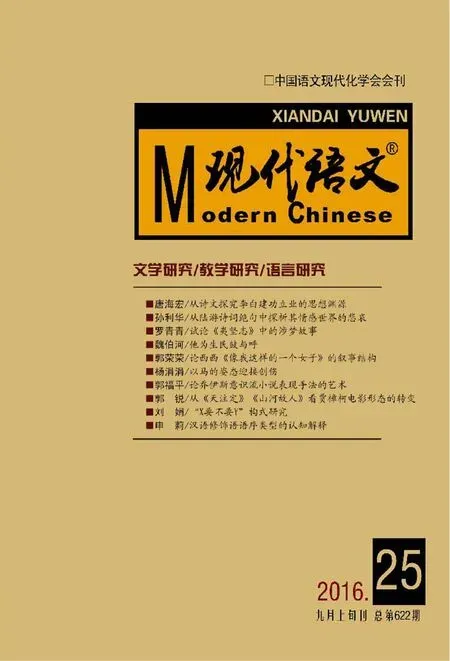接受美學視域下的詩經“興義”淺析
○李鵬飛
接受美學視域下的詩經“興義”淺析
○李鵬飛
首先分析了當代學者們對于詩經“興義”的研究,并對其相關研究進行對比,接著從接受美學的視角入手重新闡釋詩經“興義”,然后對比詩經“比義”和“興義”的關系,最后得出結論:興,本身是一種讀者作為接受主體的審美體驗,在藝術創作中為一種初級的創作狀態,作為“詩經六義”之一的“興義”則是表現出一種原始思維下的簡單的文學創作手法。
詩經 興義 接受美學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自其出世起,就一直存在于人們的視野之中。春秋時期,文人解詩、說詩,《詩經》作為一種話語工具,在文人的生活中、在典籍的記載中屢見不鮮。對于《詩經》的研究更是經久不息,最早的《詩經》研究記載可見于《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中提到的“六詩”在《詩大序》中被稱為“六義”。自此以往,《詩經》“六義”成為各大家研究的重點所在。而詩經“興義”與“比義”的纏雜更使得詩經“興義”變得模糊不堪:漢儒把“興義”附在“比義”之上,劉勰“比”“興”并舉,直到宋代朱熹的“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詩集傳》)才開始區分“比”與“興”的不同含義。后代學者在研究詩經“興義”的時候大多遵循朱熹此意。
本文擬就接受美學的觀點來重新審視詩經“興義”的內涵。
一、詩經“興義”的當代研究
對于詩經“興義”的專門研究文獻,筆者能搜檢到最早的是1980年程俊英的《略談〈詩經〉興的發展》。此篇文章中,對《詩經》的“興義”發展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最終得出結論,興義的發展到了后世成了“比興”這一文學范疇。文中稱“比和興是分不開的,是一種手法,而不是兩種手法。”“比興”是詩歌創作中“比”和“興”融合的最終產物,文中稱“……由《詩經》的興發展為后來的比興,它的含義,是不包含發端,只有兼比義的興才稱為比興,且含有寄托之意,成為形象思維與形象塑造的代稱。”[1]在這里,他把“興義”作為一種“起情”作用的筆法性質消解,而成為一種依附在“比義”之上的托物言志的一種寄托。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欠妥的,詩經“興義”的作用不僅是一種作為詩歌文本寫作的手法,而更多的是一種情感的交流與分享。正因為“興義”的冗雜,使得其在詩歌文本呈現之中更多的和“比義”融契而成為“比義”的附庸,從而有了“比興”一詞。“比興”中的“興”只是“興義”的一部分,而“興義”的其它含義并不能從文本呈現中看到,所以,應該從另外的角度切入來重新審視詩經“興義”的內涵。
與程俊英同時代的學者李湘在其文章《“興”義辨源》中通過對《詩經》興詩本身的解讀并結合歷代對于詩經興義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興’,在《詩經》這部特定的詩集中,乃是以每個詩章的立意構思為基礎,以先言他物引起所詠之事為步驟,從而造成意境和表達情思的一種方法。”[2]此看法對于“興”義的理解還是從文本本身出發,但其已經脫離了如程俊英把“興義”強加到“比義”之中的觀點,從文章的立意出發,從意境論的觀點出發,從而把“興義”的解釋提高了一個層次。
學者對于“興義”的研究不止于對其本意的研究,還有學者對其源頭進行了探究,其中徐元濟在其文章《“興”與原始思維》中,將《詩經》的“興詩”與《周易》卦爻辭結合起來討論,指出,“《周易》卦丈辭中的象占之辭(也稱設象辭、示辭)相當于《詩經》興體詩中的興辭(興句、“他物”),敘事之辭(也稱記事辭、告辭)相當于中心辭(“所詠之辭”)。這種類似的結構形式,前人早已發現……《周易》卦丈辭與《詩經》興體詩的相同的結構,是打開“興”形成之謎的鑰匙。”[3]最終,徐元濟將“興”的源頭定義為原始思維。無獨有偶,2003年楊述的文章《原始宗教——詩經興象建構的觀念平臺》中也提到了原始思維對“興”的影響,楊述從“興”的“隱喻說”和原始宗教的圖騰崇拜之間的關系進行類比分析,認為《詩經》的大部分興詩都帶有原始宗教的觀念痕跡。
當代學者葉嘉瑩對于中國傳統詩歌的研究在國內首屈一指,她對于詩經六義的研究有自己的成果,她認為“‘興’是完全自然的感發,‘比’是經過你自己的理性的安排。”[4]即是說,“興”和“比”的差異在于,“興”是一種由物及心的過程,即創作者看到物以后,內心引起觸動而萌生出感情,從而進行創作;“比”是一種由心及物的過程,即創作者內心有郁結,將自己的郁結附加到物上,這里的“物”已經不單純是自然景物,而更多的是創作者自己安排過的景物。這種說法顯然超越了前人的分析。但仍存在己身的弊端,即將“興”與“比”完全分割開,對于“興義”的闡釋有所缺憾。
綜上所述,誠然,歷史上研究者們對于詩經“興義”的闡釋已經多如牛毛,當代研究者們對于詩經“興義”的研究熱情度不是很高。但學界仍不乏真知灼見,譬如葉嘉瑩的解釋。筆者自接受美學視角入手,力圖重新闡釋詩經“興義”,不僅把詩經“興義”作為一種創作手法來對待,更多的是將其作為一種美學的思維方式來闡釋。
二、接受美學視域下的詩經“興義”
“接受美學”這一范疇是德國文藝學教授姚斯在其作品《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1969)中提出的。接受美學從讀者的視角出發,重新定義了文學文本與文學作品的概念及其關系,指出:文學文本是指作家創造的同讀者發生關系之前的作品本身的自在狀態;文學作品是指與讀者構成對象性關系的東西,它已經突破了孤立的存在,是融會了讀者即審美主體的經驗、情感和藝術趣味的審美對象。文本是一種永久性的存在,它獨立于接受主體的感知之外,其存在不依賴于接受主體的審美經驗,其結構形態也不會因事而發生變化;作品則依賴接受主體的積極介入,它只存在于讀者的審美觀照和感受中,受接受主體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結構的支配,是一種相對的具體的存在。由文本到作品的轉變,是審美感知的結果。也就是說,作品是被審美主體感知、規定和創造的文本。[4]
筆者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來闡釋詩經“興義”。
(一)詩經“興義”的再闡釋
我們把詩經“興詩”的創作者不作為一個作者來看待,而是將其作為接受主體,而他所面對的自然景物,也不是普通的景物,而是作為自然的文本而存在。
《說文解字》中對于“興”字的解釋為“興,起也。從舁從同。同力也。”《文心雕龍·比興》中也提到“興,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據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興”是指文學創作的起步階段,“起情”則是指因為某種感情的觸動而引發“興”這種狀態的出現。創作者,即接受主體,在面對自然景物,即文本的時候,為文本所吸引,接受主體內心的情感郁結被觸動,從而主體的審美經驗、情感和藝術趣味被觸發,審美主體和文本合二為一,達到了我們所說的物我合一的狀態,也就是接受美學所說的文本到作品的轉化。這種“作品”在創作者的口中呼喊而出,變成了我們所看到的《詩經》“興詩”。存在于“興詩”中的景物已然不是自然的景物,而是經過創作者的改造而具有創作者本身情感與審美經驗的“作品”。
據此,“興義”本身并不是作為一種創作手法而存在,而是作為一種審美體驗的方式而存在。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此處的“興”即是我們所說的“審美體驗”。孔子把《詩經》作為文本來對待,提出了“興”的概念,此處“興”的意義絕不止于對兒童的啟蒙,更多的是通過對詩歌文本的閱讀而達到一種融匯的狀態。孔子生活的時代,古典文獻不多,而具有文學氣息的《詩經》儼然成了文人們引經據典的重要來源。孔子此處的“興”是要求《詩經》的讀者們,也就是當時的文人們能夠深入地了解《詩經》,在閱讀的同時能夠感同身受,達到“詩我合一”,從而在以后的交談運用中能夠達到熟練自如的狀態。
(二)詩經“興義”與“比義”的關系
“興義”作為一種審美體驗的方式而存在,那么為什么歷代研究者,總要把它當成一種創作手法呢?這源自“興義”與“比義”的纏雜。如朱熹在《朱子語類卷八十》中說:“說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址》相似,皆似興而兼比,其體卻只是興……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義”很好理解,即是我們當下所說的比喻、類比,等等。漢儒研究《詩經》大多據儒家經典進行論述,故而把“比義”作為諷喻的一種方法。而“比義”的本意則是一種對于自然景物的自我比喻,這和“興義”就有了纏雜,“興義”是物我合一的狀態,這其中就夾帶著自我比喻的色彩。但研究者們沒有看到的是,“興義”的范疇比“比義”要大,可以說“比義”是在“興義”之后產生的:首先要有自身的情感與物的融合,才能把自己和物進行對比。“比義”實則是在“興義”的審美體驗產生之后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創作狀態。
“興義”也可以作為一種創作的狀態,但是是一種初級的創作狀態,即是把自己所見到的景物和自己的情感如實地描繪出來的一種創作手法。譬如《詩經·邶風》中的《燕燕于飛》:“燕燕于飛,參差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創作者在送別時看到了兩只一起飛翔的燕子,如實地在首句把景物記錄下來,這期間創作者是作為接受主體存在的,他相對于燕子是一個讀者,他看到了燕子在結伴飛翔,觸動了內心的離別之情,行諸筆端,故而成了這首詩。從這里也可以看到“比義”的存在,我們能感覺到創作者把自己和送別的人當做了那兩只燕子。可是我們也能明顯地區分出來,“興”是在創作者(接受主體)創作之初看到自然文本就產生的一種審美體驗,而“比”是自然文本經過作者改造以后轉變成的“作品”。
“興義”與“比義”的關系,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可以看出是“文本”與“作品”的區別。
(三)詩經“興義”的美學定義
綜上,筆者對詩經“興義”確定一個接受美學范疇下的定義:
興,本身是一種讀者作為接受主體的審美體驗,在藝術創作中為一種初級的創作狀態,作為“詩經六義”之一的“興義”則是表現出一種原始思維下的簡單的文學創作手法。
在定義中,筆者提到了原始思維,這里借鑒了上文所引述的徐元濟的觀點。《詩經》成書年代較早,與《周易》中的卦爻辭大致一個年代出現,表現出的是一種原始思維控制下的創作者們對于自然景物和內心情感的簡單描述。正如《周易》是一種簡單的哲學觀一樣,《詩經》是一本簡單創作的詩歌集合,它沒有后世復雜的文辭點綴與聲律合成,而僅僅是一種粗糙的“野蠻”的情感宣泄方式。
后世對于“興義”的解釋,大多摻雜了“比義”的自我比喻義在,但是都無出于此處所定義的審美體驗之說。如鐘嶸的《詩品》中提到:“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所謂的“意有余”正是創作者的審美體驗在讀者的心中延宕,“興詩”的創作者們把自己所見到的景物和內心情感進行簡單的描繪,實則是一種大巧若拙的手法,正是這種簡單的表述,把自己的審美體驗完整地保留下來,更能引起讀者們的共鳴,從而達到“意有余”的狀態。
(四)總結
歷代學者對于詩經“興義”的闡釋眾多,筆者此處僅從接受美學角度對“興義”進行了簡單的闡述。興義本身并不復雜,實則從孔子開始就已經有了接受美學的意蘊在。但是歷代學者多拘泥于把“興義”當成文學創作的手法,使得“興義”與“比義”纏雜而變得意義模糊。
興義本身就帶有接受美學的特點,是一種對自然事物的原初的審美體驗,而其作為一種創作手法被大多數人得知,是因為歷代多把“賦、比、興”并舉,從而把“興義”的本意模糊。筆者此處把興義作為創作手法的意義解釋為對于自然景物和內心情感的簡單描述,與“比義”“賦義”實有區別,“賦義”是對自然景物和事件的描寫,摻雜的感情少,而“比義”則是一種摻雜了過多情感的一種寫法。“興義”恰恰在兩者之間,又有啟發自己的景物,又有自己感情的如實描述。
注釋:
[1]程俊英:《略談〈詩經〉興的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0年,第8期。
[2]李湘:《興義辨源》,中州學刊,1984年,第04期。
[3]涂元濟:《“興”與原始思維》,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2期。
[4]葉嘉瑩:《談作詩的三種方法:賦、比、興》,語文學習,2011年,第10期。
[1]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3][日]家井真.《詩經》原意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4][德]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李鵬飛 寧夏銀川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 7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