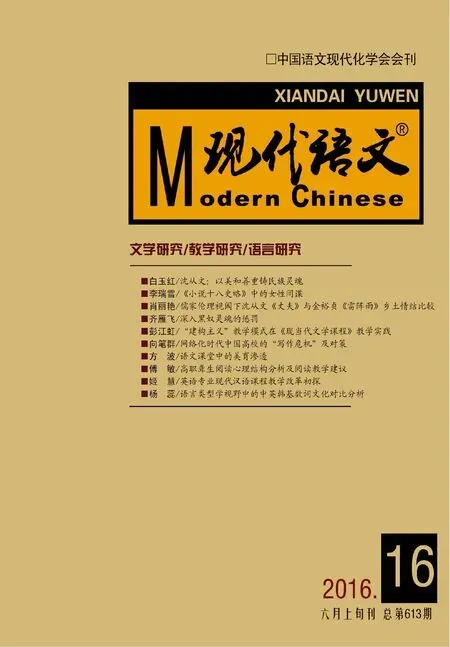沈從文:以美和善重鑄民族靈魂
○白玉紅
?
沈從文:以美和善重鑄民族靈魂
○白玉紅
摘 要:美與善的自覺融合是沈從文作品獨特的文學境界。他希望通過非現實功利性的文學表達來達到改造國民性的功利性目的,文學的功利性與非功利性之間的二元劃分在沈從文這里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它既有現實目的,更有超越現實的指向。沈從文以一種不同于同時代的美學風格,給現代文學提供了一種別樣的選擇,也使其獨特性顯得更加突出。
關鍵詞:沈從文 善 美 重塑民族品格
沈從文攜著以湘西社會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踏進文壇,以美與善筑起其特有的文學境界,極力通過原始、古樸的湘西鄉土文化中僅存的古老的民俗風情,來展現自然和人性美的理想境界,即使面對現代社會潮流沖擊下的湘西,他仍執著地以極大的熱情挖掘“墮落趨勢”中尚未完全喪失的純樸、美好的人性,從而使作品具有引導人心向善的力量,并以審美的方式達到其改造國民性,重塑民族品格的目的。
一
在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中,自然生命的興衰枯榮是有自己的節奏的,自然的就是美好的、無可指責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描繪了極度神奇的夢幻世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環境,原生態的人生形式,同時通過一系列人物表現出純樸善良的人性美。
沈從文用自己的愛心感受自然與人世間的一切,用筆描繪著美麗的湘西世界,那里的山山水水無不讓人心醉:“月光淡淡地灑滿了各處,如一首富于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山寨中、樹林角上、平田的一隅,“飄揚著快樂的火焰”,還有清亮細碎的馬項鈴和沉靜莊嚴的銅缽的聲音。特別是那劃龍船的蓬蓬鼓聲剛剛響起,這邊渡口上的人還反應不過來,那靈性十足的黃狗便“汪汪地吠著,受了驚似的繞尾亂走,有人過渡時,便隨船過河東岸去,且跑到那小山頭向城里一方面吠”……
自然環境是美的,生活于其間的人的生存狀態更是令人驚異的。原生態的人生形式和自然的生命形態是沈從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礎。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閉的湘西大地上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其原始的生活習俗往往帶有人類遠古時期原始文化的印記。沈從文通過創作民間故事和民間傳奇來展現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其目的不僅僅在于獵奇,而在于通過對原始生命形態的玄想來呈現一種美好的人生境界,來展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主觀感情。
沈從文善于將人物放置于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純自然的生存狀態中去刻畫和表現:那里既沒有階級社會中政治經濟的因素,也沒有原始社會中落后、愚昧野蠻的一面,人們如同生活在伊甸園,除卻自我人性的不斷追求和不斷滿足、完善外,沒有任何來自世俗紅塵的人生煩惱。即便《月下小景》中悲劇的制造者是野蠻的原始習俗,作者為了不破壞完美性,在兩個主人公活動空間中也將其隱入幕后,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仍然是月明風清、美人香草、柔情蜜意、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愛與和諧。《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某商會會長的女兒吞金而亡,由于地位懸殊,只能在心里愛著她的豆腐店老板,為了實現自己的愛,根據當地風俗,“吞金而亡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的人,只要有異性伴睡即可復活”,于是將她的尸體從墳中刨出,背到山洞里去“睡尸”,……作者從這看似怪誕的現實生活中找到一種浪漫的精神寄托,一種強悍的靈魂力量,一種超越倫理道德束縛的生命的質樸和真誠。即使描寫土娼制下畸形的男女,他也力避猥褻的場面,而以近乎偏嗜的筆調縱情揮寫那種充滿著原始野性的生命形式。《柏子》里那個拍擊風浪,靈活得像“妖洞里的嘍羅”的水手柏子,為了和吊腳樓上相好的妓女兩月一次的約會,竟可以花去全部積蓄而不留后路……
沈從文用獨特的方式表現其筆下人物美的特質:他不注重人物的外部特征及其形式上雕塑式的完美,而是強調人物性格的發展和命運的沖突,并通過這些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在特定歷史背景和民俗文化氛圍中不同的命運和遭遇,來揭示社會的本來面目。這些特殊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在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上,也許只是一個簡約符號式的速寫,或者“清風般”無典型特征的形象,如翠翠、夭夭、三三、蕭蕭、阿黑、三翠、桂枝……他們在人物的外觀、體態上極為相似,“被山風吹得黝黑的皮膚,水靈靈般鮮活年輕的生命,水晶般清瑩的心靈,一條烏梢蛇般油亮的辮子”,甚至連生存的自然環境也極為相似,翠翠始終與渡船連在一起,三三總離不開她的碾坊,夭夭的時間全部花在桔園里;至于蕭蕭、三翠等童養媳,勞動更成為其生命的全部內容,“喂雞養鴨、挑水種菜、推磨碾米,無事不能亦無事不做”,勞動生產成了她們的本能;她們不僅無好逸惡勞觀念,反而厭惡“戴金穿綢,進城坐轎子,坐在家里打點牌,看看戲,無事可做就吃水煙袋烤火”等鄉下人所說的福氣。
二
沈從文講述的故事無論是喜是悲,其人物形象的性格在本質上都是善良的,他們都保留著湘西世界特有的原始的也是最純樸的善。
然而,沈從文的善的觀念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規范的。道德標準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是具體的,也是變化的,并無固定模式,如果以某種人為的道德模式為標準對我們的生活予以控制,那無異于畫地為牢,特別是對于道德和藝術這一對似乎永遠沖突和敵對的范疇而言。沈從文是立于藝術對道德的超越性一端的。如果說道德試圖以群體的標準對個體進行壓制,那么藝術則恰恰相反,它無視道德對個體的框定,只求個體的審美價值的張揚。在他看來,自然生命本身就是屬于非道德范疇的,其自身就構成了生命自給與滿足,人的生命的自然性與社會倫理的規范性之間的矛盾是無法消除的,對于真正的藝術精神而言,任何世俗的道德是沒有意義的。
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善”是一種終極性的道德指向,超越任何現實目的,是對生命的一種信仰。因此,他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善是一種抽象的善,他反對讀者和批評者在他的作品中尋找確定的思想和意義,用通行的價值標準如進步與落后、現代與傳統、文明與野蠻等去解讀沈從文的思想和作品,勢必出現誤解和偏差。
另外在沈從文的文學觀念中善與美是統一的,不可分離的,美與善的融合是沈從文獨特的文學境界。但與傳統觀念中美對善的依附關系不同,善與美在沈從文這里是鼎足而立并且互相制約的。對于善的超現實目的的理解,就決定了沈從文所追求的審美形式必定是抽象的,因為超越現實性的美必定指向美的形式,善與美在沈從文這里須臾不可分割,或者說他們本來就是同一的。在沈從文這里,美與善統一于一種最高境界的生命形式,在這樣的境界里,美與善是互相包含的。正因如此,在沈從文對生命的信仰、對自然的崇拜這種善中就包含了審美的人生形式,而這種具象而抽象的美又體現了沈從文的一種人文關懷。若沒有這種美反而使善居于文學觀念的中心,或者弱化這種美的含量,沈從文就與主流的文以載道的作家沒有什么不同。同時美的指向又必須是善的,必須給人以精神的提升。
三
沈從文認為,人生是由“生活”和“生命”兩部分構成的。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沒有“生命”。正是基于這種對“生活”與“生命”的理解,沈從文才提出了重塑民族品格的命題。
對于沈從文來說,這種改造必須以審美的方式來完成,與主流作家注重社會改造不同,沈從文看重的是人性的完美和提升。沈從文并不一味地反對文學的功利性,他顯然既不是有直接的現實功利目的的作家,但同時又不完全等同于躲在藝術的象牙塔里的非功利作家。在沈從文看來,文學更高的境界應該是對于抽象的生命和人性的認識,他把他自己的創作就定位于對于普通的人生的認識上。
沈從文堅信,文學具有改造人心的作用,而且堅信這種改造較政治更有效、更長遠。在他看來,人性中存在著一些跨越時空、遠離現實的抽象的精神層面的東西,而對這種人性和抽象精神的表達正是文學本身的訴求。正是因為文學有從深層上改造人性和國民品格的作用,所以沈從文希望通過創作塑造真正健康優美的國民品格。他一面真實、冷靜地攝取變形后湘西林林總總的丑惡社相,一面熱烈而真誠地在扭曲的心靈中抽取美的因素,在尚存的純樸的鄉村文化中打撈屬于重建民族文化的基因,真實的攝取加上想象的作用,使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凸現出一群具有美的素質和品格的鄉下人,形成一種優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把童年時代留在心靈里的湘西民性的美好印象,剪除鄉村宗法社會的黑暗和冷酷,剪除人性中被擠壓而扭曲的部分,升華而起,用幻想加以豐富,用癡情釀成詩,譜成一曲理想人性的夢幻曲,通過對理想人生形式的再現以啟迪人們精神層面上的反思,達到改造國民性的目的。
理想人生形式的再現主要體現在《邊城》和《長河》中。
《邊城》在色彩絢麗的湘西邊城自然景觀的映襯下,在散發著醇厚的人情味的風俗畫面中,所有的人都善良、正直、熱情,從祖父到翠翠,從船總順順到天保、儺送兄弟,他們都有著簡單而執著的信仰,在寧靜純樸的生活中躍動著生命的堅韌活力。作為小說情節核心的是翠翠和儺送兄弟倆的愛情故事,三者都顯示出熱烈、深沉、忠貞、崇高、正直的品質。這是作家理想的地方民族性格的夢幻,也是理想人性的夢幻。很明顯,沈從文是清楚地認識到邊城的理想主義和夢幻特色的。小說描寫的不是湘西邊城的現實而是一種理想的人生形式,是對人類之愛的一種詮釋。這夢蘊含著沈從文對民族性格和人與人關系重造的真摯而熱切的希望。
《長河》是以30年代中期沅水流域的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寫出一群平凡的湘西人民在生活中的“常”與“變”,全篇籠罩著一種風雨欲來的歷史使命感。理想的生命形式在時代風雨的洗禮中走上了更高的階梯,老水手滿滿堅韌開朗、飽嘗人生艱辛而洞悉世情,直面殘暴現實且從不逃避,比起《邊城》中老船工對命運的哀怨和生命的崩潰,他的勇氣和信心要強得多。年輕一代的夭夭,三黑子們一改翠翠的溫柔沉靜,他們活潑機敏、大膽樂觀,就是在“新生活”已經擾亂了鄉村的平靜時,夭夭還能“在船邊伸手玩水,用手撈取水面浮游的瓜藤菜葉,自在從容之至”,面對保安隊長為首的邪惡勢力的壓迫,她有一己之見,她認為“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著,沒理由懼怕”。三黑子也發誓:“沙腦殼、沙腦殼,我總有一天要拿斧頭砍一兩個。”在夭夭和老水手滿滿等人的身上,躍動著生命的神性光彩,理想的生命形式在他們身上得到了現實而深刻的詮釋,他們是湘西世界的希望,也是民族的希望。
四
沈從文希望通過作品中呈現出來的美與善達到改造民族品格,重塑自然、健康、優美的民族品格,要達到這一目的,文學作品本身就必須具有一種超越性的境界。沈從文實際上希望通過非現實功利性的文學寫作來達到改造民族品格的功利性目的。文學的功利性與非功利性(如“為人生”與“為藝術”兩派作家)之間的二元劃分在沈從文這里卻有機地連結在一起,不僅有現實目的,更有超越現實的指向。
對沈從文來說,他既不同于魯迅,又不同于后期的周作人,他試圖以一種個人化的方式得到群體的理解和認同,這樣做似乎冒著更大的風險,也預示著一種不太樂觀的結局。沈從文是一個反叛性很強的作家,一種生命不斷向深處延伸的執著使沈從文無視當前流行的價值觀。但他的文學夢想卻在現實面前步步后退,即使這樣沈從文也沒有違背自己的文學信念,他寧愿放棄文學而轉向文物研究,而他的文學夢想最終也只有淹沒于歷史的滾滾洪流中。
(白玉紅 河南鄭州 鄭州師范學院中文系 45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