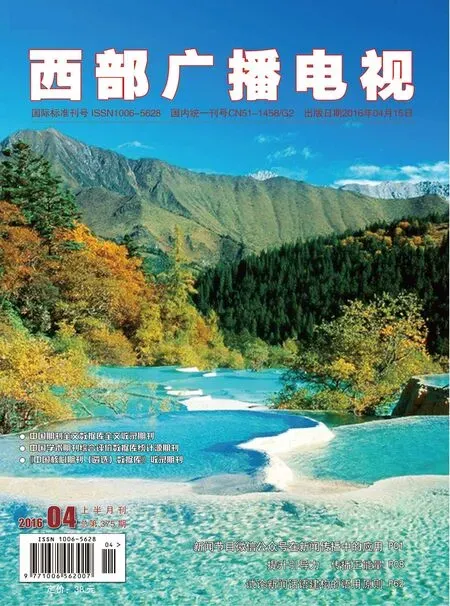跟蹤記錄
——紀錄片創作唯一而獨特的方式
曾志斌
?
跟蹤記錄
——紀錄片創作唯一而獨特的方式
曾志斌
摘 要:跟蹤記錄是紀錄片創作獨有的方式,跟蹤記錄得越久,挖掘得越深入,其內涵越豐厚,其價值就越大。本文探討跟蹤記錄之于紀錄片創作的意義與實踐。
關鍵詞:紀錄片;跟蹤記錄;創作實踐
紀錄片是創作主體對現實生活中有價值、有故事的人物、事件進行記錄和表達的藝術作品,它采用的是真實記錄的方式,不主張人為的導演和安排。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生活運行邏輯,所以創作者只能跟蹤人物、事件的發生、發展而進行記錄,這就決定了紀錄片在拍攝上只能采用跟蹤記錄的方式。跟蹤記錄,這是紀錄片創作獨有的方式,電視劇不具有,電視新聞片不具有,電視專題片也不具有。紀錄片創作跟蹤得越久越深入,就越能發現人物、故事的矛盾和糾結,越能展示人物面對自然或者現實的挑戰時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格,因而就越有價值。可以這么說,紀錄片創作者的藝術功力全在于跟蹤記錄;紀錄片的內涵和價值全在于跟蹤記錄。跟蹤記錄得越久,挖掘得越深入,其內涵越豐厚,其價值就越大;跟蹤記錄得越短,就只能靠拍攝手段和所謂的敘事技巧來湊合。
1 跟蹤記錄之于紀錄片創作的意義
我們說跟蹤記錄是紀錄片創作唯一的、最具特征的方式,是因為這一創作方式具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和任務要求,與其他藝術作品的創作方式有著顯著的區別。
與紀錄片創作具有親緣關系的種類是電視新聞,許多電視新聞的題材就是紀錄片創作的選題來源。從某種情況來說,在題材確定的情況下,電視新聞的落點就是紀錄片創作的起點,比如央視創作的《錢云會之死》、大連電視臺創作的《農夫與野鴨》等作品,電視新聞深度報道也屬于紀錄片的范疇。但是,電視新聞的拍攝方式與紀錄片的創作方式具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是,電視新聞采用的是挑、等、搶的方式,它聚焦新聞事件,很多時候是抓拍。而紀錄片不僅是需要挑、等、搶,更需要跟蹤記錄;不僅對情節事件跟蹤記錄,也要對日常生活景象,比如時序、季節的變化跟蹤記錄。
紀錄片創作與劇情片創作同樣屬于影視創作,需要借助畫面語言來表現被拍攝對象。但是,紀錄片創作與劇情片創作有顯著的區別。劇情片的創作方式是導演,所有的人物、場景、動作、對話等等都是導演藝術構思的外化表現,畫面語言的運用是圍繞著導演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推進故事情節而服務的,所以劇情片創作的拍攝方式就是擺拍,而紀錄片的創作方式是跟拍,這是劇情片與紀錄片創作方式的根本區別。
紀錄片與專題片的創作在很多地方具有相同之處,以至于一些專家認為紀錄片與專題片就是同一個品種的不同名稱。然而,紀錄片的創作方式與專題片也有顯著區別。這就是,專題片是主題先行,是在主題的統率之下各種畫面的集萃,畫面與畫面之間可以沒有聯系,上一個鏡頭可以是泰山日出,下一個鏡頭就可能是北京的長城,他們都為闡釋主題而被選用。而紀錄片的主題是在跟蹤記錄的過程中,經過不斷挖掘反復提煉,甚至有可能在剪輯臺上才最后確定的。它的每一個鏡頭,每一組畫面必須是有聯系的,是關系的組合。
2 紀錄片創作需采用跟蹤記錄
人物、事件、環境、關系——這是構成紀錄片故事化的四大要素,依據這四大要素,紀錄片體現為時間的藝術、空間的藝術和發現的藝術,而這些特征,決定了紀錄片創作只能采取跟蹤記錄的方式來進行。
紀錄片是時間的藝術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紀錄片的記錄形態具有同時性,即創作主體的記錄與人物、事件的發生、發展同時進行,稍縱即逝、不可重復;二是指紀錄片的表達形態具有即時性,即“現在進行時”,人物事件的發生發展只能隨著時間的進程次第展開,不可顛倒。正因為如此,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認為“紀錄片的第一要素是時間”,意思就是說紀錄片人跟蹤記錄的時間長度,決定著作品的內容和價值。
紀錄片是空間的藝術主要體現在環境和關系上。人是環境的產物,這是法國唯物主義學者的觀點,也得到了英國管理學家羅伯特·歐文的證實。紀錄片要立體的表現人物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就要跟蹤記錄人在不同的環境中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的性格特征和行為舉止,就比如《醉翁亭記》中的太守歐陽修一樣。作為滁州太守,歐陽修的性格特征和行為舉止是不一樣的;而在醉翁亭上,他卻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任性不羈的“醉翁”:“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歐陽修是一個有作為的官吏,但是為什么要在醉翁亭上“飲少輒醉”?這是他官場失意寄情山水的表現。顯然,只有在醉翁亭這樣的環境里才能見到歐陽修這個人物的真性情。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馬克思的觀點。這個觀點提示我們,紀錄片中的故事人物一定是能夠反映時代特征,能夠反映各種社會關系的角色,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故事人物一定與社會、環境之間有著相應的關系,也因不同的社會關系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比如《舌尖上的中國》,表現的就是食物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食物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食物與情感之間的關系。跟蹤記錄就是要準確地找準這種關系,并且準確地表現這種關系。
所以,紀錄片還是發現的藝術。跟蹤記錄得越久,越能發現人物、事件、環境、關系之間的聯系,就越能豐厚地表現人物,反映事件。跟蹤記錄就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它的妙處在于,你始終不知道下一分鐘究竟會發生什么事,會出現什么情況,由此形成了紀錄片的“懸念”。所以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是無法導演的,你在拍攝過程中始終得跟著人物和事件走,需要的就是等待的定力和功力。只有這樣,創作者才能真正抓到最有特征、最有趣、最有表現力的東西。
3 跟蹤記錄在紀錄片創作中的實踐
生活中本身充滿了有趣的情節,關鍵是我們要去發現,而跟蹤記錄就是發現情節、挖掘情節唯一的方式。可以說,任何一部優秀的紀錄片,都是長期跟蹤記錄的結果。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的拍攝歷時一年,走訪150多個拍攝地點,行程40多萬公里,主創團隊的足跡遍布包括香港、澳門、臺灣在內的中國大部分地區,歷盡千辛萬苦,給觀眾呈現出了150多個人物,300余種美食,共計七集的系列片。
養蜂人譚光樹和妻子,每年有300天奔波在路上。為了收獲質量上乘的蜂蜜和蜂漿,他們跑遍整個中國,追逐花期。導演李勇也同養蜂人一起,日夜兼程,跟蹤記錄,時間最長的一次行程超過2000公里。
黃土高坡上的小村落里,68歲的張世新老人開始帶領家人制作掛面。50多年的經驗,使他能準確把握面條的制作時間、韌性和口感。分集《心傳》導演陳磊歷時7個月,跨越4個省份才找到張世新老人。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拍攝,攝制組準確地記錄下了張世新老人的絕技和一家人的生活狀態。
在廣州的大都市,遼河邊的小村子,重慶的火鍋店,香港的夜排檔……美食的故事隨著環境的不一樣而不斷展開,香氣四溢,吸引著觀眾追逐的眼光。總導演陳曉卿說:“我們正經歷太多的歡樂與痛苦,但中國人能苦中作樂,把喜悅通過美食呈現。我們在關注生存,同時,更注重人們對生活的熱愛。”
顯然,沒有長時間的跟蹤記錄,沒有全身心投入地體驗和采訪,要揭示出美食如此深厚的內涵是絕對不可能的。跟蹤記錄,是紀錄片創作不斷發現、深入挖掘的唯一利器。許多紀錄片之所以淺薄,靠炫技來博眼球,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跟蹤記錄的定力和功力。
著名紀錄片導演蔣樾在拍攝《幸福生活》時,為了拍攝到主人翁一段有意義的對話,蔣樾整整拍了三盤帶子,到第四盤才拍攝到想要的狀態;為了真實記錄鄭州火車站的擁擠狀態,他一共拍攝了八次,最后剪輯成為一次來表現。段錦川在拍攝《拎起大舌頭》這部紀錄片時,在村子里住了一年半左右,一直跟蹤記錄。他開始以村長為主角,但拍攝了一年以后通過比較判斷,認為另一名村委更有故事,然后馬上進行調整。由于與被拍攝對象成為了朋友,事件的記錄也十分完整,所以故事的改變沒有一點痕跡,主人翁所呈現的狀態非常自然。顯然,沒有充分的跟蹤記錄,就不可能有這部優秀的作品的產生。
4 如何在紀錄片創作中做好跟蹤記錄
跟蹤記錄作為紀錄片創作唯一而獨特的方式,必須明確如何跟蹤,怎樣紀錄的問題,是簡單地跟蹤記錄,還是有追求的發現捕捉?顯然,后者才是我們所提倡的,否則就容易淪為漫無目的的“跟腚派”,或者是監控式的視頻記錄。
跟蹤記錄必須符合生活的邏輯,不干預、不擺拍,忠實記錄事件發展的進程,這是紀錄片創作的重要前提。然而,紀錄片不僅僅是記錄,更是創作。跟蹤記錄現實生活的原汁原貌,不等于漫無目的地無選擇記錄。事實上,跟蹤記錄的創作核心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情節性記錄、故事化敘事。
劇情類作品找的是“戲”,紀錄片作品找的是“事”。事件是故事的基本構成要素。事件中間有故事,故事里面有事件。事件由情節和細節組成,情節和細節經過故事化結構,就成為故事化敘事。
所以,情節是構成故事的鏈條,離開了情節故事就無法展開和進行,“情節性記錄”和“故事化敘事”關鍵是要找準情節點。比如大連電視臺拍攝的《農夫與野鴨》跟蹤記錄了稻谷從播種到收獲的全過程,拍攝了人、鴨兩條線,故事的脈絡也依據事件的時間順序和發生、發展的過程展開。人的活動情節分為育秧、備耕、插秧、收獲5個階段;鴨的活動情節分為覓食、求愛、孵蛋、真假野鴨、掠食5個階段。在敘事上,則以季節不同,相互之間發生的矛盾和沖突的不同作為敘述的主線,構成育秧—覓食;備耕—求愛;插秧—孵蛋;真假野鴨;人鴨再戰五個樂章。一只野鴨和一位農夫,數萬只野鴨和一千畝稻田,是五個樂章的基本內容和結構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礎上,用懸念和意味,將農夫和野鴨之“戲劇沖突”加以真實呈現和放大。不僅呈現野鴨生存境遇的窘迫和農夫勞作的艱辛,更把農夫與野鴨能否共生共存的現實思考作為深沉的主題呈現給觀眾。
所以,情節性記錄主要體現為長鏡頭和同期聲。長鏡頭能夠原汁原貌地記錄故事人物的表現,構成紀錄片獨特的情節,而同期聲也同長鏡頭一樣具有情節性,不可忽視。比如紀錄片《中國儀仗兵》中劉孟子躺在床上回答母親的問話;班長在班務會上批評黃倩倩的長鏡頭記錄,就是典型的案例。在紀錄片創作中,同期聲與畫面一樣重要,就在于同期聲里面也有情節。
5 結語
跟蹤記錄需要我們有發現的眼光,去發現具有戲劇要素的情節,這是構成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跟蹤記錄更需要我們用堅定的毅力,平實的鏡頭,去跟蹤和記錄不平凡的故事。現在,拍攝和制作的技術手段已經越來越先進,這容易引導我們在創作上“討巧”,或者“炫技”,因此,論述跟蹤記錄是紀錄片創作唯一而獨特的方式,在今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四川廣播電視臺總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