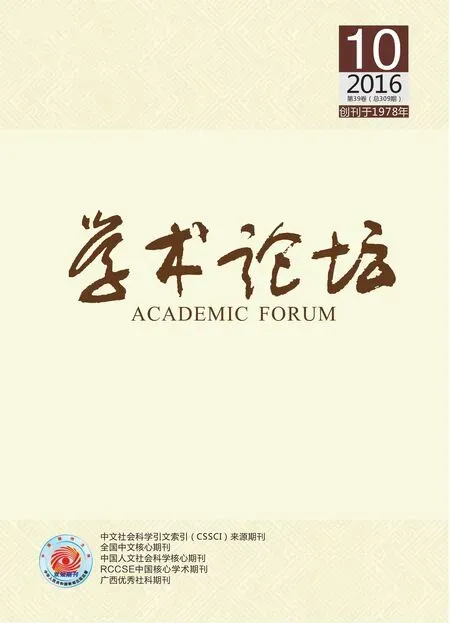中國普通村民的角色變遷:以村落文化傳承為視角
蘭東興
中國普通村民的角色變遷:以村落文化傳承為視角
蘭東興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普通村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村落文化傳承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口語傳播時代,普通村民在相對封閉的村落環境中接受代代相承的地方性文化,并在不自覺的狀態將地方性文化傳承下去。進入電子媒介時代,村落的信息內容和傳播途徑多樣化,普通村民在對待傳統的態度發生改變之時,也改變了自己在文化傳承中的地位。村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需要正確引領,村民傳承村落文化的主體地位不能弱化。
村落文化;村民;文化傳承;鄉村建設;引領
普通村民在村落中沒有任何特殊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他們不是族長、寨老、宗教領袖或舊時代的保甲長,也不是新時期的村委會主任或支書,他們在村落中屬于大多數,但他們一直在影響村落文化的變化方向和發展進程,是村落文化傳承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同的時代,普通村民在村落文化建設和傳承中的地位不同。當代中國的村落社會正在發生劇變,正確認識普通村民在村落文化中的地位并科學引導,顯得非常重要。
一、口語媒介時代普通村民的文化身份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村落的信息交流和文化傳承主要靠口耳相傳。口耳相傳既是傳播方式,也是傳播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與人親密接觸,在傳與受的過程中保持著基本平等的關系。村民不僅認識到知識技能需要口傳心授,而且養成了口耳相傳的習慣,探索出許多傳播的途徑,形成了與環境相對應的傳承機制。
(一)口語傳播時代的村落文化傳承表現為“后喻文化”
中國傳統的鄉村在經濟生活、社會管理、文化傳播等方面都高度自治,體現為“自組織系統”,社會自我運行、自我約束、自我控制、自我完善。維持“自組織系統”的力量是傳統,傳統對每一個村民而言與生俱來,就像自己不可能選擇出身一樣。村民在傳統的環境中出生、成長,接受傳統,延續傳統,繁衍下一代。個人屬于村落,習慣了服從村落,接受村落的集體決議,順應村落多數人的意見;村落屬于傳統,習慣了按照傳統解決問題,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在傳統的框架下運行。
歷史上中國多數村落的內部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沿襲傳統,缺少外部力量的強烈撞擊,長期處于“超穩定”狀態。正是這種“自組織”和“超穩定”,成就了村落的悠久歷史、豐富多彩的古老文化和口耳相傳的文化傳承方式。禮儀人倫幾乎在不自覺狀態代代相承,生活技能和生產技術幾乎在不知不覺地傳授和習得,迎來送往、待人接物的人際關系幾乎不需要專門學習就逐漸掌握,村落歷史和家族源
流在日常講述中嵌入村民的記憶中,關于天地自然的認知和人生態度在一次次的宗教儀式或祭祖敬神活動中悄然滲透到村民的精神世界。
有學者將村落在歷史上的這種文化傳承表述為“后喻文化”,即未來的重復過去的,在生產生活上經驗性的傳遞方式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文化代際傳承中是后人學習前人。這種“后喻文化”對文化的傳承,使農業社會里保存在老一輩手中的寶貴經驗得以傳承下來[1]。每一個普通村民在生產和生活中必然地充當了文化傳承者,同時又作為文化的接受者。生活環境越封閉、村落內部社會結構越緊密,“后喻文化”表現得越突出。
村落是家庭的延伸,是擴大的家庭。村民一方面將家庭的相處之道應用于村落之中,另一方面在村落中學習和檢驗家庭中獲得的禮儀人倫。在家庭接受基本的生產生活技能,然后在村落中展示和進一步豐富。在家庭將迎來送往、待人接物的人際關系形成認識,在村落將這種認識進一步提高和深化。家庭成員講述的家族創業史和村落發展史,在村落的其他人那里得到佐證和補充。村落既是比家庭更廣闊的信息交流和知識傳播舞臺,又對家庭的文化傳承內容、途徑和方法加以規范。
在村落中,傳播有身份關系和場所限定,傳授者對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和信息傳授時通常會有選擇,把個人經驗在生活世界按照社會規范進行有條理的整合,根據傳統整合生活的片段,選擇話題,闡釋現象,呈現符號,強調觀點。接受者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獲取知識和信息,同時又在確定或建立社會關系。村民接受知識、掌握技能和理解信息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建構意義,使自己的認識得到規范并服從傳統。傳播在社會關系中進行,它符合傳統規范,并且在規范中形成和鞏固現實生活的社會關系。傳播在面對面的人際關系中進行,傳授雙方的一切行為舉止都是傳播活動,都會受到傳統影響,歷史上的“自組織”尤其如此。傳統影響著村民的思想和言行,村民的思想言行又在影響他人并受到他人制約。所以,村民的言行舉止看似很自由,其實受到社會制約。這種制約是無形的力量,貫穿于傳播活動的方方面面。
(二)口語傳播環境中普通村民的傳播行為受習俗制約
家庭傳播的主要內容是敘說生活民俗,傳授生產技藝,其傳播方式是口耳相傳,示范演練,其表現形式有兒歌、古歌、故事、諺語、民謠、族規、祖訓以及秘方等。倫理道德傳播在家庭內部呈開放性,每個家庭成員都可以而且應該知曉。而有些技能、秘方則在封閉性的環境中傳播,例如民間醫生傳授醫技、民間工匠傳授制作技巧、村落傳授食物制作的秘密配方等都有傳授的規矩。
制約不是硬性規定,不是來自某個擁有特權的人或某個社會機構,主要來自傳統形成的社會壓力。普通村民生活于這種壓力之中,同時又在給予其他村民這種壓力。壓力體現在生活之中,規范著文化傳播活動。村民在交流中接受制約,又將制約作為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傳承。
制約首先表現為對傳播對象的規定。當本村與其他村在一起參加活動時,有些語言和行為需要注意,村落內部的很多活動排斥其他村落參與。即使在本村落內,傳播對象還有年齡、身份、性別的區分。其次表現為對傳播內容的約束。有些內容不是任何場合或時間都能說能唱能展示的,不同場合有特別的語言和行為忌諱。其三表現在對傳播內容的程度限制。例如各民族青年男女在唱情歌表達愛慕時,不能在私下有身體接觸,不能用下流的語言挑逗對方。村落的水井邊、神樹下都不得有污穢之物和褻瀆的行為。此外表現為村落文化傳播總是和時間密不可分。壯族、水族家里的銅鼓只有特定的時候才能使用,土家族喜愛的儺戲要在開演之前進行一番神圣的儀式,苗族從前每年自插秧至稻禾抽穗這段時間內嚴禁吹奏蘆笙,有些民族的英雄史詩只有在族群的重大儀式上才能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講述。還有,表現為村落文化傳播存在身份問題。在村民看來,口頭傳播不只是傳播“說什么”,還在傳播“由誰說”“對誰說”“怎么說”“在哪說”“為什么說”等社會規范,村民覺得傳播的內容、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也是文化。
村落文化在口耳相傳過程中的習俗制約,本身就具有文化意義。村民的言行舉止是在踐行傳統,遵循規范,他們用符合規范的言行舉止在肯定傳統和傳承傳統。因此可以說,他們既是村落文化的接受者,又是村落文化的繼承人。
二、大眾傳媒時代普通村民在文化傳承中地位的轉變
中國文字的使用時間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而大范圍推廣則在私塾、義學興起以后。普通村民掌握文字則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在鄉村普遍推行義務教育。20世紀70年代,廣大農村開通有線廣播。到世紀之交,國家實施“廣播電
視村村通工程”,無線電傳輸設備建設和小水電站建設全面鋪開,鄉村信息傳播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電腦和手機普及,村落信息環境被徹底顛覆。
(一)村民傳承村落內部文化出現地位變化
大眾媒介廣泛進入鄉村,改變了村民信息接收的內容、途徑和方式,也在改變村民的觀念和生活狀態。村民對外面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對自己的生活開始重新定位和規劃,對村落傳統文化和當前的生活方式有了新的理解。普通村民在村落傳統文化傳承中的地位發生變化,傳統文化的傳承方式以及在村落中的命運也不同從前。
第一,村民獲取信息和知識的途徑改變。村民的信息渠道不再單靠彼此間的口耳相傳,對歷史的認識和知識的儲備不再局限于本村落或本地區,娛樂不再只靠宴會、節日歌舞或游戲,他們可以借助大眾媒介間接地從媒體獲得,交流實現了傳者與受者的分離。這也就意味著在村落的傳播中,媒體擔任了傳播者角色,以前口語傳播中的傳播者失去舍我其誰的地位,接受者淡化了對口語傳播者的依賴,傳者和受者之間缺少了從前面對面的親密關系,傳統歌舞、宴會或娛樂的參與者變少,晚上坐在火塘旁聽故事的人也在減少。
第二,村民在傳播中的地位改變。“傳統路徑是由老人向其兒女傳承,然后兒女再向其晚輩傳承。在日常生活中,則是通過衣食住行這樣的生活行為來傳承傳統文化的。”[2]村民現在可以通過大眾媒介獲得知識和信息,傳統的人際交流方式一部分被取代,因此村民改變了對村落和傳統生活方式的態度,對家庭、村落長老、民俗活動的依賴度降低。而村民比以前眼界更開闊,文化水平更高,對村落歷史的看法和對自然現象、社會問題的認知發生變化,對傳統的信任度降低。年輕的村民從前是村落各種活動的主體,是村落文化的表現者和傳承者,現在他們把文化傳承的任務留給了老人。孩子們從前在不同場合從不同渠道獲得這個年齡階段需要的各類地方性知識和技能,如今要么沒有了傳授的人,要么傳授人的身份改變,要么自己有了新的娛樂手段和接受信息的途徑,因此失去了對村落傳統知識的興趣。
第三,村落文化的傳承關系以及村民對傳承內容的認識改變。以前的傳承者和接受者都生活在村落,使用同樣的語言,處于同樣的生活狀態,傳承者的閱歷和對歷史的了解要更多一些,對村規民俗的認識要更深刻一些。普及義務教育后,家庭的傳統教化功能幾乎被學校所替代,人們通過學校教育擴展了知識面,改變了對村落傳統文化的認識。電視普及后,曾經以村落老人為權威,以火塘為中心的傳播狀態已經不可能維持。有學者在云南布朗山做民族調查時發現,“隨著衛星電視的接入,電視和網絡大多使用漢語和英語等通用語言,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更是充滿了挑戰。尤其對沉迷網絡和電視的年輕一代來說,很多人已不知不覺被流行文化‘格式化’,民族的傳統文化漸漸失去感召力。”[3]在其他少數民族村落和廣大漢族村落,傳統文化傳承現狀也同樣如此。
因此,在村落中,普通村民就有了傳承傳統村落文化的主角與看客雙重身份。所謂主角,就是村民還在從事村落文化傳承,做著許多前輩做過的事,延續著過去的習俗,保留著一些傳統觀念。有些村落的形態依舊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還深烙著歷史的痕跡。所謂看客,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有些村民覺得自己的村落和文化變化都事不關己,做一個旁觀者。他們與外來觀光客不同的是,自己置身于村落,看見了村落的傳統文化傳承過程,對村落的傳統文化不足為奇。二是很多村民將村落文化改編成表演,將互為依存不能分割的村落文化各部分撕裂成若干碎片,表演給他人觀看,撕裂成碎片出售給他人,在表演和售賣村落文化的同時,也和他人一起在觀看。村民和游客一起欣賞著被商業化利用之后的產品,他們和游客不同的是,游客只看到了傳統文化被商業化利用之后的文化產品,以為這就是“原生”的村落文化,而他們要么參與了傳統文化商業化利用的過程,要么清楚這一轉化過程。村民不僅參與村落文化商業化活動,而且成為村落文化商業化的一部分,被他者觀看。
(二)村民接受村落外部文化出現地位變化
村民兼具傳統村落文化傳承主角與作為看客的雙重身份,既是傳統村落文化的傳承人,也是破壞者。村民與生俱來地生活在村落,不可避免地受到村落文化“濡化”。“濡化”就是其他村民在充當村落傳統文化的傳播者,而自己是一個接受者。同樣,受到“濡化”的村民,又在行使傳統文化傳播的職責,影響其他人。生活在村落中的個體,其言語、行為和思想“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4](P2)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落的全體成員都是村落文化的創造者、享用者和傳承者。隨著村落走向開放,“涵化”也在村落發生,村民勢必接觸來自外面世界的文化,并與村落中的傳統文化作比較。因此,今天的
村民不只是村落文化的接受者和傳承者,也在吸收外面的文化,并在村落的生活中產生影響。他們對村落文化的接受就不是不假思索或不加辨別地全盤接受,對村落文化的傳播有了新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對傳承的內容有選擇性。村民或將自己認為落后的、沒有價值的村落文化內容過濾掉,或將村外人認為最具有吸引力的內容強化和包裝。現在的村民也許覺得有些習俗反映了落后,也許覺得對外面的人沒有看點,因此不再要求下一代遵循,甚至自己都排斥。在傳授歌舞的時候,刪減了一些生活化的內容,使之變得簡潔流暢或者更有視聽沖擊力。在對某些傳統技藝傳承中,省略了復雜的工序或者不具備觀賞性、實用性的部分,以實用為原則,追求產品的商業價值。
第二,在傳承的方法上有改進。對于村落或家族的歷史、地方戲曲或民歌、神話和傳說、社會知識和生產生活技能,早期靠口耳相傳,之后用文字做記錄。當錄音、攝像、攝影設備走進普通村民家庭后,村民將民歌錄音,將歌舞、婚慶、喪葬、喬遷以及祭祖等活動用影像記錄,將建筑、服飾、生產工具、生活用具、村落景色等拍攝下來,用播放錄音帶、影像光碟的方式學習或傳授,把音響和影音作品作為資料保存。這種傳授具有可重復的特點,實現了聲音、動作、場景與現實的分離,突破了傳授的時間、空間約束。但是,無論使用錄音帶還是影像光碟進行傳授,它的畫面選擇有角度,它的聲音經過技術處理,從文本而言經過了二度創作。盡管聲音具有真實感,畫面富有形象性,但是傳播活動脫離了具體的場景,傳播者和接受者不是真正的面對面。
第三,傳播目的發生改變。在過去,傳播原本在生活、生產中進行,并不是為了文化傳播才安排生活和生產,而是在生活和生產的過程中實現文化傳播。傳授技藝是為了生產,介紹倫理道德是為了規范生活秩序。所有的傳播活動都充滿生活氣息,保持生活本色,都是村落活動的本來狀態。每一次文化傳承都是村落生活的一個片段,每個村民都經歷無數的生活片段,無數的生活片段構成生活的整體和村落文化的全貌。現在村落打破了封閉,外面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進入村落,影響著村民的生產生活,村民開始將傳播活動從生產生活中剝離出來,專門組織村民學歌舞,專門安排工匠教手藝,專門培訓一幫人攝影、攝像、錄音和剪輯、制作,完整的生活被撕成碎片,互不相連的碎片被拼貼成似是而非的生活圖景。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大眾傳媒時代的村民并非沒有行使傳播村落文化的職能,只是有了更明確的意圖,運用更現代化的手段,并且使村落文化的價值得到延伸,擴大了村落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們傳承的村落文化在內容上已經做了很多改造,改變了村落文化發展的軌跡。他們一方面做了大量文化傳承的事,另一方面也扮演了傳統文化破壞者的角色。
三、社會轉型時期對普通村民文化傳承的引領
在口語傳播時代和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下,貴州少數民族村落文化表現為自發傳承。當外力作用加強后,村落文化自發傳承的軌跡發生改變,村民對村落內部的傳統文化和進入村落的外部文化都需要客觀評價和合理把控。
(一)普通村民的文化思想和行為亟待引領
當代中國的村落出現傳統與現代分野。村民的生活節奏和內容改變,工業化、產業化、現代化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生長。傳統的觀念受到質疑,老一輩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被年輕人拋棄,建筑、服飾、語言、習俗等也分成了傳統與現代兩個部分。時尚文化、官方消息、大眾觀點、前沿科學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村落,村民在傳統生活狀態下所依賴的文化受到現代經濟發展與媒體效應的挑戰,越來越邊緣化。這種變化對村落生存所帶來的壓力絲毫都不比經濟上的壓力小,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三農問題’并不僅僅是來自今日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變化,它也同樣是來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變化。這些變化互相激勵,緊緊地纏繞成一團,共同加劇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的艱難”[5]。村民走出家園,誠然有對外面精彩世界向往的沖動,而更多的是物質欲望增強、生活標準改變之后的一種自我救助。村民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還在經受村落現實與媒介信息環境巨大反差在精神上產生的強烈撞擊。村民無論是走出家園,還是陶醉于媒介,都是向村落文化的告別。村落中的鄉土藝術一步步凋零,傳統文化形式一天天萎縮,遠離農村生活本真狀態的娛樂形式正在占據主流。更重要的是,在社會轉型中,“農村普遍出現了一種無意識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慮”[6]。年青一代幾乎未假思索地接受時尚文化,毫不留戀地放棄村落傳統文化,村落的生活秩序被打破,維系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和道德被拋棄,而另一方面又沒有重建維持村落和諧的文化系
統,社會管理和精神家園出現真空,村落中賭博風氣、偷盜事件、虐待老人的行為、好吃懶做的現象滋長。當這些問題暴露的時候,村落中發出了一聲聲回歸傳統文化的呼喚。
事實上,“回歸傳統文化”已然不可能。村落文化作為農村共同體擁有的“精神家園”,它既是一個自有其存在價值的獨立系統,卻又不可能獨立于村落而存在,總是與村落環境、村落經濟、村落政治、村落社會互為一體。
村民固然是村落文化傳承的主體,但是村落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不能只依靠村民的自發行為。社會轉型時期的村民不可能都具有正確認識村落文化的覺悟,能抗拒充滿誘惑的物質生活和媒介傳播技術。要提高村民傳承村落文化的覺悟和熱情,如果沒有特別的技術、擁有知識的人及有關組織,如果沒有讓村民看到村落文化傳承的實實在在的好處,就不可能達到很好的效果。村民需要社會尊嚴和物質生活,只有讓村民認識到村落文化可以捍衛和展示其社會尊嚴,可以擴大村落的社會影響力,可以把村落文化轉化成村落建設的資本,才可能發揮村民作為傳承村落文化的主體地位的作用。
(二)村民傳承村落文化的主體地位必須落到實處
引領村民發揮村落文化傳承主體地位的作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作為引領者要正確地認識村落文化,否則引領就會偏離方向。現在有一些人習慣于用自以為“文明”的棱鏡透視村落,對居于主流文化邊緣的村落文化作出自以為客觀的評價,貼上“原始”和“現代”、“落后”與“進步”、“迷信”與“科學”、“糟粕”與“精華”等標簽,建議將某一部分剔除而另一部分吸收、某一部分改造而另一部分發揚光大。例如在村落改造和“生態移民”政策實施上,這種凌駕于村落文化之上的傲慢就還明顯存在。對于被改造和建設的村落、被搬遷的村民來說,“鄉村建設”和“生態移民”是“被提出”的概念。所以,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既要充分注意到村民生活環境堪憂、信息閉塞和可支配收入偏低,充分考慮農村的居住安全、飲水衛生、交通方便、生產資料配置以及今后的發展前景等,也要認真傾聽村民對改造或搬遷的意愿,思考村民社會關系變化和村落文化空間變化的問題。
第二,要遵循村落文化傳承的特點。村落中任何一種能被傳承的文化并非是被刻意地創造、維持、繼承的,它具有“生活史”的特點,其文化傳播路徑不像學校講課式的灌輸,全都貫穿于日常生活之中,總是與情境相伴。今天固然應該引入學校教育、現代傳媒等新方法或新途徑,但不能忘記生活永遠是傳承的主要載體。村落生活中包含著豐富的文化,生活為村落文化傳播提供豐富的場合與途徑。通過生活傳承的文化富有情趣和生機,文化在生活中實現價值轉換。當村落傳統生活改變,可能就失去了與之相伴的文化,失去了傳播文化的場合與途徑。因此,從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角度而言,推動村落發展不一定要同時廢除原來的生活方式或民間習俗。既然村落的自然環境、產業結構、人際關系、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千差萬別,就沒有理由將所有的村落生活改變成一樣。只有生活的多樣性,才會有文化的多樣性。
第三,在保護和傳承村落文化中沒有必要糾纏于“保人”還是“保文化”的問題。有人認為:只有生命得到保證,文化才能得到傳承,不能因為要保留傳統文化而生活永遠固定在一種社會形態中。另有人認為:物質生活是多樣的,村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不應該用行政權力來決定村民的生活,更不能因此讓不可修復的村落傳統文化毀于一旦。還有人認為:引導和幫助村民通過發展生產、改造村居的方式來改善生活,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村民應該作出的選擇,村落文化可以采取建立民族博物館、民俗村等方式加以保留。以上幾種觀點都把人和文化割裂開來,似乎提高生活水平總是和保留傳統文化處于對立狀態。在他們看來,人與生態環境的共同作用產生相應的文化形態,任何文化都有與之相適應的生存環境,改變后的生活環境就只能與另一種文化相對應。這種觀點導致現實生活陷入了“保人”還是“保文化”的兩難選擇,而且注定了將原來的“人”與原來的“文化”割裂。事實上,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在人的生活中傳承,文化是人的文化,村落文化是生活中的活態文化。今天在村落看到的文化不是歷史長河中凝固的文化,歷史上的村落文化從來就沒有與村民分離。
任何人都沒有權力苛刻地要求村民被迫忍耐惡劣的自然環境而繼續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也沒有人能夠讓村落文化的現狀永遠保持不變。對村落文化的保護不是使村落文化停滯,而是希望真正認同這種生活方式的人能受到來自外界的一份尊重,不被強制改變原本喜愛的生活。今天在做村落發展規劃的時候,尊重村民,尊重村落中的傳統建筑和習俗,尊重村落中業已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遺產,這就是文化保護。今天在做村落文化保護的時候,不只是為了申報遺產項目或炫耀文化遺產資本,而應把村落文化擺在與其他文化同等的地位,把村民擺在村落文化傳承的主體地位。這既是村落文化保護和傳承的認識論,也是方法論。
作為政府或民間組織,在幫助村民發展的時候,具體操作上一定要把對村民思想和行為的引領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文明的責任意味著引導而不是強制,意味著理性感召而不是標簽化處理,意味著人文關懷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意味著保留選擇多個的自由而不是只有一個選擇,還意味著增進不同文化的了解、欣賞。”[7]村落文化不是外部力量強加的,所以村落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不應該是強加于村民的;村落文化是彌漫于村落生產生活之中的,所以村落文化的保護就是引領村民在村落的生產生活之中健康地、自如地運用和享受本屬于自己的傳統文化;村落文化傳統生生不息傳承下去的原動力就是該村民對自己的區域文化有認同感和自豪感,所以只有當文化擁有者認同和熱愛自己的文化,并把對文化的愛融入“血液”中,這樣的文化才得以實現真正的傳承。
[1]段友文.論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文化建設[J].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
[2]劉金榮.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背景下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J].甘肅農業,2013(11).
[3]黃新炎,戎青,翟青.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芻議——基于布朗山布朗族鄉的調研[J].江蘇科技信息,2012(8).
[4]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何錫章,黃歡,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5]王曉明.L縣見聞:“三農”問題上的文化誘因[J].天涯,2004(6).
[6]石勇.被“文化殖民”的農村[J].天涯,2005(1).
[7]謝元媛.文明責任與文化選擇——對敖魯古雅鄂溫克生態移民事件的一種思考[J].文化藝術研究,2011(2).
[責任編輯:陳梅云]
蘭東興,貴州民族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 貴陽 550025
G122
A
1004-4434(2016)10-0134-06
2012年國家社科規劃基金課題“貴州少數民族村寨文化傳承研究”(12XMZ079);2013年貴州民族大學重點科研項目“貴安新區村寨文化保護和影像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