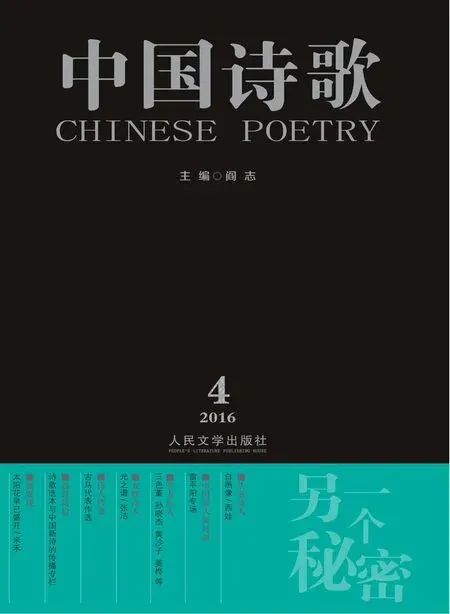邵洵美詩選
邵洵美詩選
序曲
我也知道了,天地間什么都有個結束;
最后,樹葉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著的;但這須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誘惑,聲的慫恿,動的罪惡?
這些摧殘的命運,污濁的墮落的靈魂,
像是遺棄的尸骸亂鋪在凄涼的地心;
將來溺沉在海洋里給魚蟲去咀嚼吧,
啊,不如當柴炭去燃燒那冰冷的人生。
莎茀
蓮葉的香氣散著青的顏色,
太陽的玫瑰畫在天的紙上;
罪惡之爐的炭火的五月嚇,
熱吻著情苗。
莫非不與愛神從夢中相見?
啊盡使是一千一萬里遠嚇,
請立刻回來。
你坐著你底金鸞車而來吧,
來唱你和宇宙同存的頌歌——
像新婚床上處女一般美的,
愛的頌歌嚇。
你坐在蘆蓋艇石上而唱吧,
將洶涌的浪濤唱得都睡眠;
那無情的亂石也許有感呢,
聽得都發呆。
藍笥布的同性愛的女子嚇,
你也逃避不了五月的燒炙!
罪惡之爐已紅得血一般了,
你便進去吧。
你底常濕的眼淚燒不干嗎?
下地的雨都能上天成云呢。
罪惡之爐中豈沒有快樂在?
只須你懂得。
仿佛有個聲音在空中喚著:
說不出不說出當更加苦呢,
還是說了吧!”
海水像白鷗般地向你飛來,
一個個漩渦都對你做眉眼。
你仍坐著不響只是不響嗎?
五月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燒,
罪惡在處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淚汁總引誘著我
將顫抖的唇親她的乳壕。
這里的生命像死般無窮,
像是新婚晚快樂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將比紅的血更紅。
啊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戀愛的靈魂的靈魂;
是我怨恨的仇敵的仇敵。
天堂正開好了兩扇大門,
上帝嚇我不是進去的人。
我在地獄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夢著過醒。
Madonna Mia
啊,月兒樣的眉星般的牙齒,
你迷盡了一世,一世為你癡;
啊,當你開閉你石榴色的嘴唇,
多少有靈魂的,便失去了靈魂。
你是西施,你是浣紗的處女;
你是毒蟒,你是殺人的妖異:
生命消受你,你便消受生命,
啊,他們愿意的愿意為你犧牲。
怕甚,像鋒針般尖利的欲情?
刺著快樂的心兒,流血涔涔?
我有了你,我便要一吻而再吻,
我將忘卻天夜之后,復有天明。
頹加蕩的愛
睡在天床的白云,
伴著他的并不是他的戀人;
許是快樂的慫恿吧,
他們竟也擁抱了緊緊親吻。
啊和這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纏綿地廝混;
在這音韻的色彩里,
便如此嚇消滅了他的靈魂。
上海的靈魂
啊,我站在這七層的樓頂,
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
下面是汽車,電線,跑馬廳,
舞臺的前門,娼妓的后形;
啊,這些便是都會的精神;
啊,這些便是上海的靈魂。
在此地不必怕天雨,天晴;
不必怕死的秋冬,生的春:
火的夏豈熱得過唇的心!
此地有真的幻想,假的情;
此地有醒的黃昏,笑的燈;
來吧,此地是你們的墳塋。
花一般的罪惡
那樹帳內草褥上的甘露,
正像新婚夜處女的蜜淚;
又如淫婦上下體的沸汗,
能使多少靈魂日夜醉迷。
也像這樣個光明的早晨,
有美一人踏斷了花頭頸;
啊,是否天際飛來的女神?
和石像般跪在白云影中,
憊倦地看著青天而祈禱。
她原是上帝的愛女仙妖,
到下界來已二十二年了。
她曾跟隨了東風西方去,
去做過極樂世界的歌妓;
她風吹波面般溫柔的手,
也曾彈過生死人的銅琵。
她咽淚的喉嚨唱的一曲,
曾沖破了夜的靜的寂寞;
曾喊歸了離墳墓的古鬼;
曾使悲哀的人聽之快樂。
她在祈禱了,她在祈禱了,
聲音戰顫著,像抖的月光,
又如那血陽渲染著粉墻,
紅色復上她死白的臉上。
“啊,上帝,我父,請你饒恕我!
你如不饒恕,不妨懲罰我!
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惡,
去將顏色騙人們的愛護。
“人們愛護我復因我昏醉,
將淚兒當水日夜地灌溉;
又賣弄風騷嚇對我獻媚,
幾時曾想到死魔已近來。
“啊死魔的肚腹像片汪洋,
人嚇何異是雨珠的一點;
啊,死魔的咀嚼的齒牙嚇,
仿佛洶涌的浪濤的鋒尖。
“我看著一個個卷進漩渦,
看著一個個懊悔而咒詛,
說我是蛇蝎心腸的狐貍,
啊,我父,這豈是我的罪過?
“但是也有些永遠地愛我,
他們不罵我反為我辯護;
他們到死他們總是歡唱,
聽吧,聽他們可愛的說訴:
“世間原是深黑漆的牢籠,
在牢籠中我猶何妨興濃:
我的眉散亂,我的眼潮潤,
我的臉緋紅,我的口顫動。
“啊,千萬吻曾休息過了的
嫩白的醉香的一塊胸膛,
夜夜總袒開了任我撫摸,
撫摸倦了便睡在她乳上。
“啊,這里有詩,這里又有畫,
這里復有一剎那的永久,
這里有不死的死的快樂,
這里沒有冬夏也沒有秋。
“朋友,你一生有幾次春光,
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蕩漾?
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
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
“四爿的嘴唇中只能產生
甜蜜結婚痛苦分離死亡?
本是不可解也毋庸解釋,
啊,這和味入人生的油醬。”
上帝聽了,吻著仙妖的額,
他說:煩惱是人生的光榮;
啊,一切原是“自己”的幻相,
你還是回你自己的天宮。
仙妖撤脫了上帝的玉臂,
她情愿去做人生的奴隸;
啊,天宮中未必都是快樂,
天宮中仍有天宮的神秘。
季候
初見你時你給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個春天的早晨。
再見你時你給我你的話,
說不出的是熾烈的火夏。
三次見你你給我你的手,
里面藏著個葉落的深秋。
最后見你是我做的短夢,
夢里有你還有一群冬風。
你以為我是什么人
你以為我是什么人?
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
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錯了,你全錯了;
我是個天生的詩人。
我愛金子為了她爍爛的色彩;
我愛珠子為了她晶亮的光芒;
我愛女人為了她們都是詩;
啊,天下的一切我都愛,
只要是不同平常。
但是,有的時候,
極平常的一個肥皂泡,一聲貓叫,
或是在田溝里游泳的蝌蚪,
也會使我醉,使我心跳,
使我把我自己是個詩人忘掉。
是不是把肥皂泡當作了虹,
把貓叫當作了春的笑聲,
把蝌蚪當作了女人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全不知道;
你得去問那個不說誑的詩人。
牡丹
牡丹也是會死的
但是她那童貞般的紅,
淫婦般的搖動,
盡夠你我白日里去發瘋,
黑夜里去做夢。
少的是香氣:
雖然她亦曾在詩句里加進些甜味,
在眼淚里和入些詐欺,
但是我總忘不了那潮潤的肉,
那透紅的皮,
那緊擠出來醉意。
蛇
在宮殿的階下,在廟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軟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褲帶
在等待著男性的顫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紅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哪一邊的嘴唇?
他們都準備著了,準備著
在同一時辰里雙倍的歡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疊的竹節:
我知道了舒服里有傷痛,
我更知道了冰冷里還有火熾。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來箍緊我箍不緊的身體,
當鐘聲偷進云房的紗帳,
溫暖爬滿了冷宮稀薄的繡被!
二百年的老樹
在那廟前,水邊,有棵老樹,
光光的腦袋,皺皺的皮膚,
他張開了手臂遠望青山,
像要說訴他心中的悶苦。
二百年前在這里種了根,
便從未曾動過一寸一分,
他看著一所所村屋砌墻,
他看著一所所村屋變粉;
他看著幾十百對的男女,
最初都睡在母親的懷里,
吮著乳,哭,笑,小眼睛張閉,
不久便離了母親去田里。
待到男的長大,女的長美,
他們便會在樹蔭下相會,
一個忘記了田里的鋤犁,
一個忘記了鍋里的飯菜。
“我騎在黃牛背上吹小笛,
你坐在竹籬邊上制夏衣,
春天快跨上那山頭樹頂,
別忘了今晚上到后園去。”
“我坐在竹籬邊上制夏衣,
你騎在黃牛背上吹小笛,
春天已跨上了山頭樹頂,
別忘了昨晚上在后園里。”
他看著他們的臉兒透紅,
他看著他們彎了腰過冬;
沒多時他們也有了兒女,
重復地扮演他們的祖宗。
他已看厭了,一件件舊套,
山上的老柏,河上的新橋;
他希望有一天不同平常,
有不同平常的一天來到。
女人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詩——
你用溫潤的平聲干脆的仄聲
來捆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彎燦爛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為了我,
還是為了另外一個熱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