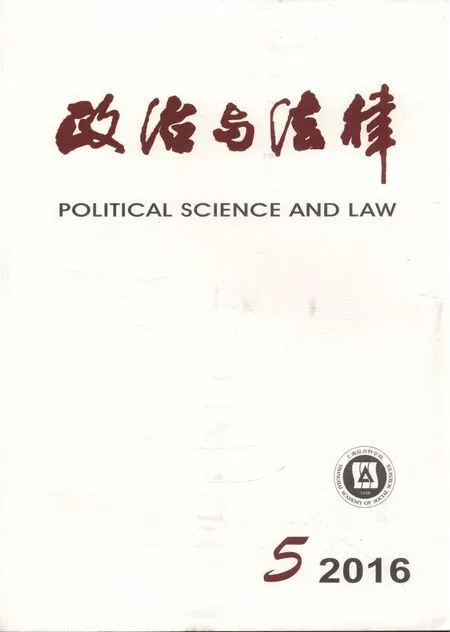論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法理基礎及其完善*
張忠民
(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重慶400067)
論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法理基礎及其完善*
張忠民
(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重慶400067)
轉基因食品自誕生以來就爭議不斷,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享有知情權具有正當性。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與消費者知情權緊密相關,“風險防范原則”并非是轉基因食品標識的法理基礎,消費者知情權才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消費者知情權限制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基礎。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對強制標識范圍與標識豁免范圍的界定不盡科學;對消費者權益與生產者權益的保護有失均衡。我國應當結合實際情況,設定標識閾值、改進標識目錄,對強制標識范圍和標識豁免范圍進行雙向調整,以便充分發揮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功能。
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標識豁免;消費者知情權;權利的限制
轉基因食品自誕生伊始,就爭議不斷,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無所適從,于是對知情權的訴求與日俱增。然而,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使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無法通過市場競爭得以實現,市場調節出現失靈,需要公共權力(政府)進行適度干預,通過在法律上確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強制生產者披露信息,矯正信息偏在,以恢復市場機能。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與消費者知情權緊密相關,其焦點是界定強制標識和標識豁免的范圍,其核心是實現消費者與生產者權益的平衡。我國建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較早,但十多年的法律制度實踐表明,其法律效果并不盡如人意。近年來,我國不少專家學者對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進行研究,但絕大多數研究僅采用消費者保護單向視角,通過對制度設計的比較考察或經濟分析,提出完善制度的建議,鮮有從法理基礎出發論述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完善。法學界一般認為:“法律理論就是對法律產生、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揭示,而法律實踐就是對具體法律理論的直接應用和使用,目的在于產生出被應用的法律理論所預期的現實結果。”①姚建宗:《中國語境中的法律實踐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因此,探討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法理基礎,更有助于理解其立法目標和作用機理,更有利于找到其法律實踐效果不盡如人意的緣由,并提出完善相關法制的建議。
一、消費者知情權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
消費者知情權的產生有著堅實的經濟學和法學理論基礎。“當今社會,消費者知情權已經成為人們生存與發展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首要的基本權利。”②李國光、張嚴方:《網絡維權中消費者基本權利之完善》,《法學》2011年第5期。然而,在轉基因食品市場中,消費者知情權不會自動實現。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是消費者知情權實現的有效保障,消費者知情權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轉基因食品標識與食品安全無關,因而“風險防范原則”并非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
(一)經濟學和法學視域下的消費者知情權
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在轉基因食品市場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生產者沒有披露轉基因食品信息的動力,在轉基因食品爭議不斷的背景下,披露轉基因食品相關信息,會降低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生產者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沒有任何披露信息的內在動力;相反,生產者卻有不予披露信息的充分動機。另一方面,消費者沒有克服信息不對稱的能力,對于消費者而言,轉基因食品具有典型的信用品特性。③Nelson、Darby等學者以消費者對商品的了解程度為依據將所有商品劃分為搜尋品(Search products)、經驗品(Experience products)和信用品(Credit products)三大類。搜尋品是指購買前消費者已掌握充分信息的商品,比如根據產品顏色、光澤、肥瘦、新鮮程度等僅憑感官就能確認其品質的食品。經驗品是指只有購買后才能判斷其質量的商品,比如根據食用后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頭暈、惡心、腹瀉等)來確認其品質的食品。信用品則是指購買后也不能判斷其品質的商品。參見Nelson P.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2):311-329;Darby M R,Karni E.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67-88。轉基因食品與非轉基因食品在物理外觀、營養成分等方面往往具有實質等同性,④目前,世界各國均將“實質等同”作為轉基因食品安全性評估的重要工具。實質等同是指如某個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或食品原料在種屬、來源、生物學特征、主要成分、食用部位、使用量、使用范圍和應用人群等方面比較大體相同,所采用工藝和質量標準基本一致,可視為它們具有實質等同性。消費者無法通過感官確認,也不能通過消費體驗進行識別,從而缺乏克服信息不對稱的能力。因此,市場本身不能克服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權利無從行使。“在那些不能依靠競爭來誘使信息顯示的市場中,可能需要強制的信息披露”,⑤[美]丹尼爾·F.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余暉、何帆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3頁。而“強制要求經營者提供信息是公權對自然人與經營者的交易進行規制的主要信息工具”。⑥應飛虎、涂永前:《公共規制中的信息工具》,《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于是,轉基因食品市場需要政府(代表公共權力)發揮作用,通過制定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強制轉基因食品生產者披露信息,確保消費者知情權的實現。
從實質意義上講,“消費者知情權最初脫胎于民事權利,其關注點最先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誠信告知關系”,“民事法律和規范的變化發展以及局限最能體現消費者知情權產生和發展的邏輯”,⑦王宏:《論消費者知情權產生和發展的三個階段》,《山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而將民法上的知情利益發展成為經濟法權利最能體現消費者知情權的本質。近代民法理論認為,人有著至高無上的理性,消費者的知情利益可以通過主體平等、意思自治及契約自由等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得以自動實現。⑧參見[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闖譯,載梁慧星主編:《為權利而斗爭》,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7頁。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實力、社會勢力、信息收集能力的差異完全沒有被當成重要問題,⑨參見王全興、管斌:《民商法與經濟法關系論綱》,《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因此在法律上沒有出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分野。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信息越來越復雜,交易主體之間的信息掌控能力差距越來越大,“近代民法制度在應對消費者弱勢信息地位問題上表現得軟弱無力,于是促成了現代民法(特別是契約法)的修正”。⑩現代民法通過強化誠實信用原則,不斷擴大生產者的告知義務,以保護消費者的知情利益。然而,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所謂平等性和互換性已經喪失,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對立”,①現代民法試圖將“基于民事主體特殊身份而產生的消費者知情利益”,融入“基于權利對象而確定的民事權利體系”,存在著法理上的障礙。這就意味著“基于傳統的告知義務模式已經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保護消費者的知情利益”。②李友根:《論經濟法權利的生成——以知情權為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6期。于是,面對日益嚴重的消費者問題,政府積極介入,從市場主體視角出發,基于消費者與生產者在經濟能力和信息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在經濟法上確立了消費者知情權。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和第20條分別規定了消費者知情權和生產者告知義務。
轉基因食品是人類利用基因技術改變生物遺傳信息的產物,因而自誕生伊始就爭議不斷。我國對基因技術科學普及不夠,③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15年2月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不僅提出“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還專門提出“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科學普及”。致使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心存顧慮,轉基因食品輿論環境缺乏理性。加之“消費者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其‘弱勢’主要體現為與經營者在交易信息上的不對稱地位”。④陸青:《論消費者保護法上的告知義務——兼評最高人民法院第17號指導性案例》,《清華法學》2014年第4期。由是,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訴求,具有現實性和正當性。⑤政府是否承認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享有知情權,直接決定了實行何種類型的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比如,美國認為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沒有實質區別,據此否認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享有知情權,于是實行轉基因食品自愿標識制度;歐盟認為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不同,消費者有權知悉,于是實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參見張忠民:《美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法律剖析》,《社會科學家》2007年第6期;張忠民:《歐盟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淺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7年第6期。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經確立了消費者知情權,倘若通過該法可以實現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那么就沒有對轉基因食品實行強制標識的必要。遺憾的是,該法難以保障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實現。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生產者提供商品信息“應當真實、全面”是一個范圍非常廣泛、內涵極不確定的概念,商品信息范圍是否包含“轉基因信息”不甚明確,致使消費者與生產者對此存在巨大的認識差異。從消費者角度而言,獲得信息越充分,越能保障其權益,其自然認為上述“應當真實、全面”應當包括“轉基因信息”,而且信息還要盡可能的具體充分。從生產者角度而言,向消費者提供“轉基因信息”,必然增加經營成本,提供的信息越細化,需要的成本越高;而且,還會增加經營風險,因為“轉基因信息”會降低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因此,生產者認為自己無需承擔超越法律明確規定范圍的告知義務,以確保自身利益在合法范圍內最大化。雖然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規定消費者可以向生產者進行詢問,生產者“應當作出真實、明確的答復”,但該規定依然無法讓消費者實現知情權。一方面,基于轉基因食品系信用品的特性,消費者很難在未掌握一定信息情況下向生產者提出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生產者“沒有告知”和經詢問“沒有回答或沒有明確回答”的行為,沒有設置法律責任。可見,無論消費者是否詢問,生產者不予告知(答復)的法律成本極低。于是,當消費者購買到轉基因食品后想要維權時,就不得不回到現代民法的制度框架中,需要證明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舉證責任過于繁重。而且,轉基因食品生產者的侵權方式具有隱蔽性,在眾多受害消費者中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受到了侵害;維權成本高、收益小致使維權行為效益低下,甚至消費者額外受損,知道權益受損者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尋求救濟。當預期救濟成本大于預期救濟獲利時,一個理性的人就沒有動力去尋求救濟,如此狀況可能產生激勵侵權的效果,⑥參見許明月:《普遍性侵權、機會主義與侵權現象的法律控制——對傳統侵權法的反思》,《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致使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受害更為嚴重。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賦予經營者的強制性說明義務”,⑦應飛虎:《從信息視角看經濟法基本功能》,《現代法學》2011年第6期。這就需要政府再次介入,通過制定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強制生產者披露此類信息,以確保消費者知情權的實現。
(二)“風險防范原則”不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
關于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問題,有學者認為“消費者知情權和風險預防原則構成了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標識規制的理論基礎”;⑧付文佚:《轉基因食品標識的比較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頁。還有學者對“消費者知情權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基石”提出異議,認為“作為WTO的成員國,我國有關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國內立法應當盡量避免與WTO規則的沖突”,進而提出以“風險防范原則”為法理基礎的解釋模型。⑨參見竺效:《論轉基因食品之信息敏感風險的強制標識法理基礎》,《法學家》2015年第2期。事實上,且不論“增強與國際法的協調性”能否成為國內法的法理基礎,即便從“避免與WTO規則的沖突”這一目標和“風險防范原則”本身內涵來審視,“風險防范原則”亦不應成為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
“風險防范原則”,又稱風險預防原則或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此后被一系列的國際文件所采用,其中1992年的《里約宣言》最具代表性。《里約宣言》明確提出了預防原則: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按照本國的能力,廣泛適用預防措施;遇有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的威脅時,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確實證據為理由,延遲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環境惡化。⑩參見曾煒:《論國際習慣法在WTO爭端解決中的適用——以預防原則為例》,《法學評論》2015年第4期。“由于預防原則本身的復雜性,加之諸多環境保護公約措辭不統一及法律效力多為宣言和‘軟法’的現狀,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律地位一直存有爭議”,①陳亞蕓:《EU和WTO預防原則解釋和適用比較研究》,《現代法學》2012年第6期。“從1997年的荷爾蒙案到2006年的生物技術產品案的近10年間,關于預防原則的性質、內涵與法律地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部門仍然未達成一致,以致于實踐中對于預防原則的態度仍為保守。”②同前注⑩,曾煒文。因此,“盡管預防原則在許多國際條約及國內法中被宣示,但是,它并沒有成為真正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強制性法律原則”,③李秋高:《論風險管理法律制度的構建——以預防原則為考察中心》,《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3期。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也未得到應用,“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權威性國際法院或法庭承認預防原則為國際習慣法或法律一般原則”。④同前注⑩,曾煒文。所以,即便將“風險防范原則”作為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依據,也無法實現“避免與WTO規則的沖突”的目標。換言之,為“避免與WTO規則的沖突”也就不能成為將“風險防范原則”作為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基石的理由。
那么,拋開“避免與WTO規則的沖突”的考量,“風險防范原則”能否作為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呢?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探討支持者的主張,得出初步結論。其支持者認為:“當有一定科學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可能對生態安全或環境保護具有潛在巨大的、不可逆轉的風險,但尚不具備科學上充足的證據證明該種轉基因食品具有對人體健康的實質風險或對動植物的生命、健康的風險時,可以根據我國國內環境法上的風險防范原則,采取積極防范的措施,包括對該種轉基因食品采取強制標識措施。”⑤同前注⑨,竺效文。此主張至少含有以下三個要點:其一,“風險防范原則”的適用范圍從環境保護領域擴張到食品管理領域;其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不僅要保障消費者知情權,還要防范消費者生命健康權(人身安全權)遭受侵害;其三,“舉證責任轉換”,⑥牛惠之:《預防原則之研究——國際環境法處理欠缺科學證據之環境風險議題之努力與爭議》,《臺大法學論從》2005年第3期。除非生產者有充分科學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無害,否則不得豁免標識。
首先,將“風險防范原則”擴張到食品管理領域特別是轉基因食品管理領域,并無不妥,但其并非適用于轉基因食品管理的所有環節。具體而言,“風險防范原則”可以適用于涉及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轉基因生物研發管理、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等制度,但并不適用于轉基因食品標識管理制度。因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風險問題,屬于轉基因食品研發和安全評價階段的議題,倘若轉基因食品不能通過安全評價并獲得安全證書,就不會被允許上市,也就根本沒有標識制度適用的余地。換言之,轉基因食品標識是上市流通階段的議題,與食品本身的安全性無關。倘若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確實存在問題,則美國、加拿大等國家不可能實行轉基因食品自愿標識制度。質言之,即便采取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也不可能解決轉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性問題。實際上,最先將“風險防范原則”的適用范圍從環境保護領域擴張到食品管理領域的歐盟,也只是將其作為“分析風險的方針”,⑦1996年以來,歐洲接連發生瘋牛病、口蹄疫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由此引發了歐洲消費者的恐慌和對食品安全的信賴危機。面對食品領域出現的科學研究還不能完全解釋的潛在風險,歐盟決策者們決定將風險預防原則引入到食品安全管理的過程之中。1997年,歐盟執委會發布的《消費者健康與食品安全》(Consumer Health and Food Safety)規定,在科學證據不充分或存在某些不確定的情況下,歐盟執委會將以預防原則作為分析風險的方針。參見王傳干:《從“危害治理”到“風險預防”——由預防原則的嬗變檢視我國食品安全管理》,《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第4期。并非作為食品標識的指導原則。
其次,將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保障的消費者權利擴展至生命健康權,有失妥當。通過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避免消費者生命健康權遭受損害,蘊含著轉基因食品存在人體健康安全隱患的前提。轉基因食品是否存在人體健康安全隱患是個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因此只能依據科學技術,且不應有國界之分。倘若轉基因食品確實對人體健康存在安全隱患,那么就關系到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和憲法性權利,⑧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世界衛生組織章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規范,生命健康權屬于一項基本人權,世界各國大都確認其為憲法性權利。參見杜承銘、謝敏賢:《論健康權的憲法權利屬性及實現》,《河北法學》2007年第1期。不得輕易被限制。⑨限制憲法性權利必須遵循法律保留原則、限制條件明確化原則、比例原則、公共利益法則、利益衡量原則和救濟原則。參見高慧銘:《基本權利限制之限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由此,實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采取的標識豁免措施,將失去正當性;而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實行轉基因食品自愿標識制度,將更加無法解釋。另外,“‘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問題為一個公共管理問題,更是公共產品問題”,⑩戴慶華、張云河:《食品安全管理的三維進路研究——基于公共產品視域的闡釋》,《現代管理科學》2015年第12期。應當屬于政府責任。倘若轉基因食品確實存在人體健康安全隱患,政府通過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讓消費者自行選擇是否消費,意味著要消費者自行承擔相關責任,存在國家轉嫁責任之嫌。①Markie Peter.Mandatory Genetic Engineering Labels and Consumer Autonomy.Paul Weirich.Labeling Genetically Modifie Food:The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Deba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7,PP.88-105.因此,結論只能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與食品安全無關,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并沒有防范消費者生命健康權遭受侵害的功能。
最后,舉證責任轉換要求生產者提供充分科學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無害,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盡管“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都認為目前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均是安全的;②FAO/WHO,Safety Aspe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of Plant Origin(Report of a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 on Foods Derived from Biotechnology).2001,PP.20-22;OECD,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for the Safety of Novel Foods and Feeds. 2000,PP.4-6。盡管實踐中,“過去的16年全世界共食用了2萬億份含有轉基因成分的膳食,沒有一例被證明對健康有害”,③[美]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轉基因作物在美國的發展、應用和趨勢》,劉海軍譯,《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但生產者仍d然難以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將來不會產生對人體的損害,事實上這也是轉基因食品之所以存在爭議的根源。因此,倘若要求生產者提供充分科學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體無害才能豁免標識,則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規定和自愿標識制度同樣將失去正當性。不可否認,消費者在轉基因食品知情權訴求中,存在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有所顧慮的因素,但原因在于“轉基因技術的公眾認知與食品安全成負相關”,“食品安全早已觸碰到了公眾最敏感的神經”。④徐振偉、李爽、陳茜:《轉基因技術的公眾認知問題探究》,《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綜上,“風險防范原則”不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
二、消費者知情權限制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基礎
無論是在經濟學視域下還是在法學視域下考量,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均需要予以限制。合理對消費者知情權限制的范圍,就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范圍;法律關于標識豁免的相關規定,就是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限制的表現形式。
(一)經濟學視域下的消費者知情權限制
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需要政府進行干預。然而,“政府并非是具有完全理性的‘超人’,而是具有有限理性的‘常人’,在進行干預決策時,也會面臨如何進行最佳選擇的難題”。⑤應飛虎:《論均衡干預》,《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3期。一方面,政府必須考慮市場的干預需求。政府干預市場的目的是讓市場功能得以發揮,而不是替代市場,市場存在需求是政府干預的前提,因此,政府干預市場時,必須根據消費者對信息的需要程度判斷市場干預需求的大小。另一方面,政府必須考量自身的干預能力。政府干預市場時應當確保干預的效率,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在考量自身干預能力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干預對象和科學的干預方法。總之,政府干預市場追求的是一種動態均衡,“政府有選擇的、恰當的干預可以使市場的運行更為流利”,⑥張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個經濟學說史的考察》,《理論學刊》2014年第11期。若過度干預或過于僵化,均會適得其反。
政府在干預轉基因食品市場時,至少應在以下兩個方面作出抉擇。其一,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范圍。政府需要判斷讓消費者在多大范圍內實現轉基因食品知情權,才可以使市場重新發揮功能,由此來確定干預的程度。其二,政府干預對象的范圍。政府是通過強制生產者披露信息來實現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而生產者又呈現類型多種多樣、能力參差不齊的狀況,政府必須判斷將哪些生產者列為干預對象,既是力所能及,又是效率最高。政府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范圍和干預對象范圍的抉擇,意味著需要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進行限制,也就意味著需要對部分轉基因食品豁免標識。
(二)法學視域下的消費者知情權限制
在法學視域下,“法律始終是保護肯定性自由的力量與限制否定性自由的工具”,⑦[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因而權利限制可界定為“立法機關為界定權利邊界而對權利的客體和內容以及對權利的行使所作的約束性規定”;“權利限制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界定權利邊界,權利限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和擴大權利”。⑧丁文:《權利限制論之疏解》,《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由于權利限制具有普遍性,我國在憲法層面就設有約束性規定。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鑒于法學研究中對權利構成與權利限制問題,存在“外部理論”與“內部理論”之分,⑨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8-179.現筆者擬從“權利的內在限制”和“權利的外在限制”兩個維度,探討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限制問題。
1.消費者知情權的內在限制
正如論者所言,“權利的內在限制理論把權利的構成和權利的限制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該理論認為,權利自始都有其固定范圍,權利的保障范圍并非漫無邊界。相反,按照權利的本質,任何權利都有自然而然的固定范圍”。⑩同前注⑧,丁文文。權利內在限制理論源于權利的相對性理論,權利相對性理論來自于權利限度理論。研究者指出,“所謂權利的限度理論,是指任何一種權利的行使,都有它的合理限度,都存在著一個運用和行使的適當與否的問題”;“權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也是有其限度的。擁有了權利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擁有了限度”,“超越了權利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權利濫用”。①劉作翔:《權利相對性理論及其爭論——以法國若斯蘭的“權利濫用”理論為引據》,《清華法學》2013年第6期。因此,對權利“限度”的確定,成為限制權利的關鍵,否則權利的內在限制在形式上難以實現;而要確定這個“限度”,必須揭示制約權利的因素,否則權利的內在限制在實質上難以實現。關于制約權利的因素,馬克思曾經作出過本質上的揭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換言之,“一切有關自由和權利的法律確認及其實現,都取決于具體的特定的社會條件,離不開社會條件的給予和制約”;③劉作翔:《權利沖突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離開了這種限制,基于這一權利的期待利益就不會轉化為現實”。④劉凱湘:《權利的期盼》,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頁。
根據權利的內在限制理論,消費者的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絕非漫無邊際,消費者在擁有知情權的同時,也受到了知情權的限度的制約,超越限度行使知情權就可能走向權利濫用。法律在確定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限度時,必須考慮我國的經濟社會條件。立法中至少應當考慮以下制約因素。其一,輿論環境。我國轉基因食品輿論環境非常嚴峻,存在明顯的轉基因食品“妖魔化”傾向。其二,共存狀態。隨著轉基因食品產業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轉基因食品與非轉基因食品深度共存的狀態。其三,飲食文化。根據我國的飲食文化傳統,絕大多數食品既有主料又有多種輔料。其四,能力差異。我國食品市場中的生產者數量龐大而又參差不齊,既有大中型企業,又有餐飲業者、零售業者,轉基因食品市場主體之間的能力差異巨大。其五,技術水平。科技具有局限性,轉基因成分檢測技術存在極限檢測值。其六,監管能力。實踐中,含有轉基因成分或者使用轉基因原料的食品種類繁多,比如轉基因食用油加工食品就數不勝數;轉基因食品銷售場所數量龐大,比如餐飲小店即比比皆是。要實現對轉基因食品標識的有效監管,必須考慮我國的監管力量。法律應當在綜合考慮上述制約因素的基礎上,確定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限度;對消費者知情權有所限制的范圍,就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范圍。
2.消費者知情權的外在限制
權利的外在限制理論把“權利的構成”和“權利的限制”分為兩個層次。首先解決“權利的構成”問題,“這時候權利的范圍是寬泛的、沒有邊界的、存在無限可能性的”。⑤張翔:《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權利的邏輯》,《法學論壇》2005年第1期。然后討論“權利的限制”問題,“就是通過衡量公共利益、他人權利、國家功能的實現等因素,從外部去確定什么樣的權利主張不能得到支持的問題”。⑥同前注⑧,丁文文。換言之,當該項權利與其他權益產生沖突時,法律為了平衡權利沖突,必須對該項權利進行限制,以確定權利的邊界。
在法律關系中,一個權利主體享有的權利,必須與義務主體負有的義務相對應,即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⑦參見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頁。與消費者權益對應的是生產者的義務,但生產者并不是純粹的義務主體,他也享有經濟自由的權利。⑧參見錢玉文:《論消費者權之法律邊界》,《現代法學》2012年第4期。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對應的是生產者的信息披露義務,而生產者是否披露信息,屬于其商業言論自由的范疇。一般認為,商業言論主要包括商業廣告、商品標識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傳遞;商業言論自由是指市場主體為商業目的而傳播商品或服務信息的自由(或權利)。⑨參見趙娟:《商業言論自由的憲法學思考》,《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商業言論自由根植于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屬于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⑩目前,學界對商業言論自由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其近兩年才開始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我國生產者的商業言論自由主要體現于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和企業法中的經營自由之中,美國則通過判例將商業言論自由納入其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列。參見趙娟、田雷:《論美國商業言論的憲法地位——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中心》,《法學評論》2005年第6期;蔡祖國、鄭友德:《不正當競爭規制與商業言論自由》,《法律科學》2011年第2期;李一達:《言論抑或利益——美國憲法對商業言論保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法學論壇》2015年第5期。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要擴大范圍,就必須增加生產者的信息披露義務,限制生產者的商業言論自由。因此,在轉基因食品信息披露問題上,消費者知情權與生產者商業言論自由之間存在權利沖突。而且,“如果不加區別,盲目加重經營者的責任,又會阻礙科學技術發展,損害全體消費者的利益”。①楊立新、陶盈:《消費者權益保護中經營者責任的加重與適度》,《清華法學》2011年第5期。可見,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擴張,在影響生產者權益的同時,還影響著轉基因食品的研發,最終影響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有利于提升全體消費者的福祉,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也可能產生沖突。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與生產者的商業言論自由、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權利沖突,需要法律通過合理的權利義務安排來予以平衡;法律平衡權利沖突的過程,就是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限制的過程,也就是確定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范圍的過程。
三、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完善建議
我國政府非常重視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保護,2001年就建立了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根據我國《食品安全法》、《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食品標識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②此外,國家農業部制定了國家標準《農業轉基因生物標簽的標識》(農業部869號公告-1-2007),明確了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的位置、標注方法、文字規格和顏色等要求;國家商業部制定了國內貿易行業標準《餐飲企業經營規范》(SB/T 10426-2007),規定各種經濟類型的餐飲業者“使用轉基因原料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須明示”。我國實行的是以定性為標準的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并采取目錄管理模式。特別是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我國最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不僅將轉基因食品的標識規范提升到法律層面,還在該法第69條、第125條等條文上設置了多種法律責任。以下,筆者基于對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法理基礎的認識,緊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如下完善建議。
(一)規制工具的完善
1.標識閾值
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是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一種規制工具,是立法者設定的一個食品中轉基因成分含量的臨界值,轉基因成分含量超過閾值的食品必須予以標識,轉基因成分含量低于閾值的食品可得到標識豁免。標識閾值越小,對消費者知情權限制越少,消費者知情權范圍就越大,對生產者言論自由限制越大,生產者披露信息責任越重;標識閾值越大,則效果反之。可見,標識閾值的大小,體現了政府干預轉基因食品市場的程度,反映了法律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限制的態度。
⑴標識閾值的缺失
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中沒有設定標識閾值,采取的是以定性為標準的制度設計。食品(含原料,下同)中只要含有標識目錄內轉基因生物成分,無論多少均需標識,③必須明確的是,根據我國法律法規,并非只有標識目錄內列出的產品才需要標識,而是只要食品中含有目錄內列出的轉基因生物,無論多寡,均需標識。比如,我國《食品標識管理規定》第16條規定:“食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在其標識上標注中文說明:……(三)屬于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轉基因原料的;……。”只有食品中標識目錄內轉基因生物成分“零含量”,才可以豁免標識。就標識目錄內的轉基因生物食品而言,消費者知情權得到了極度地擴張,沒有任何限制。這種以定性為標準的制度設計,體現了政府對轉基因食品市場的過度干預。
一方面,其忽略了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實現所依賴的經濟社會條件。第一,忽略了有關的輿論環境。在當前的我國,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報道無不觸動著公眾敏感的神經,“三代絕育”、“致癌致殘”、“滅華陰謀”等各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絕于耳,④參見王揚、劉曉莉:《我國轉基因食品安全社會監管問題研究》,《河北法學》2015年第2期。“隨著越來越多轉基因作物獲得種植許可并進入食品市場,近年來大眾對它的恐慌也愈演愈烈”。⑤戴佳、曾繁旭、郭倩:《風險溝通中的專家依賴:以轉基因技術報道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5期。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的缺失,使得大量食品均需標識,給消費者造成我國轉基因食品已經普遍商業化的假象,對社會輿論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第二,忽略了轉基因食品與非轉基因食品深度共存的狀態。隨著轉基因食品產業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轉基因食品與非轉基因食品深度共存的狀態。在此種狀態下,“轉基因食品在種植養殖、收獲運輸、生產加工、流通消費等環節中,要么基于自然原因,如基因漂移、基因污染等,要么基于人為原因,如有意或無意的混雜、交叉污染等,都可能使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⑥張忠民:《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問題研究》,《食品科學》2015年第9期。因而,要實現轉基因成分“零含量”,客觀上很難做到。第三,忽略了我國的飲食文化傳統。根據我國的飲食文化傳統,絕大多數食品既有主料又有多種輔料,單一原料食品很少,如此,食品中混雜轉基因成分的概率大大增加。第四,忽略了科學技術的局限性。轉基因成分檢測技術具有局限性,存在極限檢測值,所謂轉基因成分“零含量”,只能表示現有檢測技術無法檢出,并不意味著其確定不含轉基因成分,只會使標識內容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誤導消費者。⑦Yu Zhuang,Wenxuan Yu.Improving the Enforceability of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Labeling Law in China with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Vt.J.Envtl.L.,Spring,2013(15):465-492.第五,忽略了政府的監管能力。實踐中,含有少量轉基因成分的食品種類繁多,經營主體數量龐大,以我國現有執法力量不可能監管到位。第六,我國轉基因食品豁免標識的“零含量”要求,必然造成經濟性差的后果。從微觀上看,增加了轉基因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負擔;從宏觀上看,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以檢測成本為例,轉基因食品檢測實驗室建設需要經費近千萬元,每年運轉經費需要近百萬元。⑧參見胡璇子、郭爽:《轉基因標識:知情權的成本》,《中國科學報》2015年6月24日,第5版。
另一方面,其忽略了消費者知情權與生產者商業言論自由、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法律置消費者知情權實現的經濟社會條件于不顧,嚴重脫離國內實際情況,過度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過分增加生產者信息披露責任,會引起生產者的對策行為。“對策行為是指被規制者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對公權規制作出對抗其效果的行為。”⑨應飛虎:《弱者保護的路徑、問題與對策》,《河北法學》2011年第7期。參見祁瀟哲、賀曉云、黃昆侖:《中國和巴西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比較》,《農業生物技術學報》2013年第12期。生產者是理性的經濟人,面對如此繁重的披露義務,巨額的經濟成本和激烈的市場競爭,會產生機會主義傾向,普遍采取規避標識規定的行為。這種行為是由于制度的不當而導致的對策行為,屬于制度性對策行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生產者也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最終使得社會公共利益遭受損害。而且,“制度性對策行為對制度的消極影響是徹底的、致命的”,⑩應飛虎:《權利傾斜性配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參見張忠民:《我國臺灣地區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變革淺析》,《食品工業科技》2015年第23期。以至于有學者發出疑問:“為什么中國有關轉基因食品標識的律令法條看似不少,卻在市場經濟的大浪淘沙中名存實亡呢?”①李響:《比較法視野下的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研究》,《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7期。參見許明月:《市場、政府與經濟法——對經濟法幾個流行觀點的質疑與反思》,《中國法學》2004年第6期。
⑵標識閾值的完善
標識閾值作為一種重要的規制工具,在實踐中已被實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廣泛采用。比如,歐盟的標識閾值為0.9%(轉基因成分來源獲得歐盟批準)和0.5%(轉基因成分來源未獲歐盟批準),②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Regulation(EC)No 1829/200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September 2003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feed.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3(L268):11,22.應飛虎:《為什么“需要”干預?》,《法律科學》2005年第2期。巴西、澳大利亞、新西蘭、捷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的標識閾值為1%,瑞士、韓國的標識閾值為3%,日本、俄羅斯、泰國的標識閾值為5%等。③參見金蕪軍、賈士榮、彭于發:《不同國家和地區轉基因產品標識管理政策的比較》,《農業生物技術學報》2004年第1期。
關于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的設定,有學者提出應設定為10%,④參見盧長明:《我國實施轉基因產品定量標識的對策與建議》,《科技導報》2011年第24期。有學者提出應設定為0.9%。⑤參見孟繁華、李清:《歐美轉基因農業發展的兩重性》,《世界農業》2014年第6期。筆者認為,綜合考慮我國轉基因食品市場干預需求和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利益平衡,我國的標識閾值設定為5%比較合適。另外,考慮到我國轉基因食品的種類和數量日趨增多的事實,相對較高的閾值能夠更加科學地認定標識對象,增加執法的可行性。⑥參見喬雄兵、連俊雅:《論轉基因食品標識的國際法規制——以〈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為視角》,《河北法學》2014第1期。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的內涵應當是,以核酸為計算基準,食品中前三種含量最高的任何原料品種的轉基因成分含量達到或超過5%的,必須進行標識;低于5%的,可得豁免標識。⑦參見張忠民:《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問題研究》,《食品科學》2015年第9期。同時,根據轉基因食品市場干預需求的變化情況,適時對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進行動態調整。實踐中,動態調整標識閾值已不乏先例,比如,2003年,歐盟將標識閾值從1%調整為0.9%,⑧參見張忠民:《歐盟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淺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7年第6期。巴西將標識閾值從4%調整為1%;⑨參見祁瀟哲、賀曉云、黃昆侖:《中國和巴西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比較》,《農業生物技術學報》2013 年第12 期。2015年,我國臺灣地區將標識閾值從5%調整為3%。⑩參見張忠民:《我國臺灣地區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變革淺析》,《食品工業科技》2015 年第23 期。
2.標識目錄
從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法理基礎來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屬于經濟法的范疇。經濟法是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對經濟生活進行強度干預的法律,其功能在于創造條件使市場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①參見許明月:《市場、政府與經濟法———對經濟法幾個流行觀點的質疑與反思》,《中國法學》2004 年第6 期。因此,“與其他規范相比,經濟法的規范更追求效率”。②應飛虎:《為什么“需要”干預?》,《法律科學》2005 年第2 期。標識目錄作為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規制工具,承載著政府對轉基因食品標識進行動態管理,從而提高規制效率的職能。鑒于此,筆者對有學者提出的“廢除轉基因產品標識目錄制”的主張并不贊同,③付文佚:《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困境的立法破解》,《中州學刊》2015第9期。而是認為應當堅持目錄制并加以改進完善。
⑴標識目錄的缺陷
2002年,我國制定了《第一批實施標識管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標識目錄內轉基因生物有五類十七種,具體為大豆種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玉米種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油菜種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棉花種子、番茄種子、鮮番茄、番茄醬。只要食品中含有標識目錄內轉基因生物成分,無論多寡,均需標識;標識目錄外的轉基因生物食品,屬于標識豁免對象,含量多少,在所不問。④參見張忠民:《轉基因食品法律規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235頁。
從提高規制效率視角審視,我國的標識目錄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項目不全。對所有已經獲得國家批準的轉基因食品,政府均有責任讓消費者知悉,目前,我國僅有“實施標識管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一個項目,造成消費者對哪些轉基因食品屬于標識豁免范圍,不甚清晰,因此標識目錄項目有待完善。第二,協調性差。標識目錄不能與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有效銜接,致使規制效果大打折扣。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頒發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是以原料品種為對象,而標識目錄卻以產品為標識對象;審批以原料為視角,目錄就不宜以產品為視角。二是我國頒發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均是以轉基因生物的具體品種為對象,即便是同類轉基因生物,倘若具體品種不同,仍然需要另行申請安全證書,標識目錄卻以轉基因生物的種類為對象進行羅列。可見,轉基因食品標識目錄與轉基因生物安全審批制度之間協調性很差,法律效果自然不盡人意。第三,缺乏動態調整。審批的動態性決定了標識目錄不能一成不變,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實踐中,盡管近年來我國轉基因食品市場發展迅速,轉基因食品種類和數量俱增,但我國自《第一批實施標識管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出臺以來,十多年未進行任何調整,動態性近乎喪失。
⑵標識目錄的完善
為充分發揮標識目錄的功能,我國應當將《實施標識管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改名為《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目錄》,并從以下四個方面改進完善。第一,增加項目。《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目錄》中,除了“實施標識管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外,還應增加“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豁免目錄”,以便讓消費者全面了解市場中轉基因食品的概況,同時為動態調整目錄提供基礎條件。第二,以原料替代產品作為標識管理對象。無論實施標識管理目錄還是標識豁免目錄,均應只列出原料品種,不羅列產品形態。以轉基因玉米為例,只列出轉基因玉米品種即可,其產品玉米粉、玉米油等,無需逐一列出,否則無法窮盡。第三,細化品種。目錄中列出的原料不應概括表述,而應細化明確到品種,具體名稱以安全證書為準。以轉基因大豆為例,不應概括表述為“轉基因大豆”,應當表述為“抗除草劑大豆GTS40-3-2”、“抗除草劑大豆CV127”、“抗蟲大豆MON87701”等。細化品種是目錄動態更新的前提,否則即便有新的轉基因品種獲得批準,目錄也無法更新。第四,動態更新。根據轉基因生物審批和市場干預需求變化等情況,定期更新目錄。對于獲得安全證書且認為應當實行標識管理的轉基因生物,應及時列入實施標識管理目錄;對于認為沒有必要實行標識管理的轉基因生物,或者消費者認可、市場表現良好、已經沒有市場干預需求的轉基因生物,應及時列入標識豁免目錄。
(二)標識范圍的完善
由于標識閾值的缺失和標識目錄的缺陷,使得我國政府對標識目錄內外產品市場的干預非常不均衡,導致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對強制標識范圍與標識豁免范圍的界定,科學性不足。為充分發揮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功能,實現政府對轉基因食品市場的均衡干預,我國應當對強制標識范圍和標識豁免范圍進行雙向調整,對轉基因食品標識范圍進行完善。
1.強制標識范圍
消費者知情權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因此,只要市場上存在的轉基因食品,除基于消費者知情權限制予以標識豁免外,均應納入強制標識范圍。目前,除目錄內轉基因食品外,我國已經形成了轉基因棉籽油及其制品、轉基因木瓜及其制品、轉基因甜菜及其制品的龐大市場。
⑴轉基因棉籽油及其制品
自1995年引入美國保鈴棉以來,我國種植轉基因棉花已經20年。⑤參見郭三堆、王遠、孫國清:《中國轉基因棉花研發應用二十年》,《中國農業科學》2015年第17期。2014年我國有710萬小農戶種植了390萬公頃轉基因棉花,占當年棉花種植總面積的93%。⑥參見Clive James:《2014年全球生物技術/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態勢》,《中國生物工程雜志》2015年第1期。“轉基因棉籽在各地都普遍用于榨油,并在市場上銷售為人類食用,根據實地調查,農民普遍食用這種棉籽油。”⑦環境保護部:《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與風險管理》,中國環境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頁。轉基因棉籽油還可用于加工種類多樣的食品,可見轉基因棉籽油及其制品的市場已經形成。
⑵轉基因木瓜及其制品
轉番木瓜環斑病毒復制基因的番木瓜華農1號由華南農業大學研發成功,于2006年獲得在廣東省生產應用的安全證書(農基安證字2006第001號),并于2010年獲得在華南地區生產應用的安全證書(農基安證字2010第056號)。⑧該轉基因生物獲得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編號。參見農業部官方網站“轉基因權威關注”網頁“審批信息”欄目,http: //www.moa.gov.cn/ztzl/zjyqwgz/spxx/,2015年7月18日訪問。轉基因木瓜在我國種植發展迅速,廣東省的種植比例由2007年的70%很快上升到2012年的95%,全國轉基因木瓜的種植面積至少達到了6275公頃。⑨參見吳孔明:《中國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安全評介與風險管理》,《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實際上,“目前國內市場上銷售的木瓜基本上都是轉基因品種(包括從美國進口的轉基因品種)。”⑩羅云波、賀曉云:《中國轉基因作物產業發展概述》,《中國食品學報》2014年第8期。
⑶轉基因甜菜及其制品
我國沒有批準轉基因甜菜在國內種植,但批準了進口轉基因甜菜及其制品。近年來,批準進口了轉基因抗農達甜菜H7-1(農基安證字2009第031號)及其糖、糖漿制品(農基安證字2011第026號)。由于以糖、糖漿為原料的食品種類繁多,我國轉基因甜菜及其制品的市場已經形成。
這些食品與轉基因大豆及其制品、轉基因玉米及其制品以及轉基因油菜及其制品,從市場干預需求和消費者知情權實現的視角審視,并無區別。然而,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并未將這些食品列入強制標識范圍。這反映出政府干預的極度不均衡,應當予以矯正。因此,我國應當將這些轉基因食品列入強制標識的范圍。當然,倘若這些轉基因食品符合標識豁免條件,仍然可得豁免標識。
2.標識豁免范圍
為實現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市場需要政府適當的干預,但政府干預應以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為限。法律賦予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同時,也就設定了知情權的邊界。消費者知情權的實現受限于經濟社會條件,還須兼顧與生產者權益的平衡。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的限制,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法理基礎。目前,實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制度的歐盟、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日本、韓國等60多個國家或地區,①Laura Murphy, Jillian Bernstein, Adam Fryska. More Than Curiosity: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Labeling Requirements for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Vt. L. Rev., Winter,2013(38): 477-553.都對部分轉基因食品實行了標識豁免。②比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規定最終產品中不含新的DNA或蛋白質的食品、食品添加劑或加工輔助物質以及在加工點銷售(如餐館等)的食品可不進行標識;俄羅斯規定由轉基因原料生產的食品,若不含外源基因及外源蛋白,且在營養價值方面與其傳統產品具有實質等同性,則不需要標識;韓國規定只要終產品中不含外源DNA或蛋白質,就無需標識,如轉基因大豆醬油和食用油等。參見陳超、展進濤:《國外轉基因標識政策的比較及其對中國轉基因標識政策制定的思考》,《世界農業》2007 年第11 期。豁免對象主要是轉基因成分含量較少或者已經不含轉基因成分的食品、轉基因飼料飼養的動物及其產品,以及特殊生產者銷售的食品等。③參見徐琳杰、劉培磊、熊鸝:《國際上主要國家和地區農業轉基因產品的標識制度》,《生物安全學報》2014年第3期。從消費者知情權實現的經濟社會條件出發,兼顧消費者知情權與生產者權益之間的平衡,筆者建議我國將以下轉基因食品列入標識豁免范圍。
⑴轉基因成分含量低于標識閾值的轉基因食品
轉基因成分含量低于標識閾值的轉基因食品,應當豁免標識。前已論及,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實現的限制因素,即轉基因食品輿論環境、共存狀態、飲食文化傳統、政府監管能力等經濟社會條件,決定了我國應當對轉基因食品標識實行閾值管理。而且,轉基因食品標識閾值的設定還有助于實現消費者知情權與生產者商業言論自由、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
⑵使用轉基因疫苗的動物及其產品
動物飼養過程中,為預防疾病或者實現特定目的,會使用轉基因疫苗,由于轉基因疫苗在動物體內殘留量極低,應當豁免標識。動物使用轉基因疫苗有兩種情況,一是注射疫苗,比如注射重組桿狀病毒AcMNPV表達的豬圓環病毒2型ORF2基因工程亞單位疫苗(農基安證字2012第005號)、重組LHRH(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融合蛋白(農基安證字2005第245號)去勢疫苗等;④參見沈育華、陳志遠、魯江陵:《重組“LHRH融合蛋白去勢注射液”對豬的促生長試驗》,《福建畜牧獸醫》2013年第4期。二是食用疫苗,比如動物食用轉基因植物中表達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諾沃克病毒外殼蛋白、口蹄疫病毒、變異鏈球菌表面蛋白等疫苗。⑤參見周巖、趙茜、何男男:《轉基因植物疫苗的最新研究進展》,《中國畜牧獸醫》2013年第1期。
⑶轉基因微生物為媒介制造的食品
有些發酵食品在加工中會使用轉基因微生物,但終產品中不再或極少含有轉基因成分,因而應當豁免標識。比如,使用轉抗菌肽CAD基因啤酒酵母CAD-1(農基安證字2004第027號、第028號、第029號)生產的啤酒,以及未來可能使用轉基因乳酸桿菌(目前尚未獲得我國安全證書)生產的酸奶等。
⑷添加轉基因食品添加劑的食品
食品添加劑在現代食品工業中應用十分廣泛,目前我國市場中已經存在多種的轉基因食品添加劑。比如,食品中加入由轉基因大腸桿菌發酵生產的阿斯巴甜(主要從德國進口),或者重組畢赤酵母GS115生產的葡聚糖酶(農基安證字2011第069號)、葡萄糖氧化酶(農基安證字2013第012號)、果膠酶(農基安證字2013第013號)等。倘若要求使用轉基因食品添加劑的食品必須標識,那么強制標識對象范圍將會非常寬泛。食品中添加劑含量很少,消費者對食品是否使用轉基因添加劑并不關注,因而并無市場干預需求,應當豁免標識。
⑸特殊市場主體銷售的轉基因食品
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對市場主體能力上的巨大差異重視不足,將數量龐大而又參差不齊的餐飲業者、農貿市場個體戶、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農戶等市場主體,也列為轉基因食品標識義務的主體。這種制度安排嚴重脫離我國國情,不切合實際,實踐中引起了制度性對策行為。這些主體基本無人履行此項法定義務,所以人們在餐飲店、農貿市場幾乎看不到轉基因食品標識。與其漠視法律規定和有法不依的狀況使得法律形同虛設,不如結合實際,認可這類市場主體能力上的不足,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進行必要限制,將這些特殊主體銷售的轉基因食品列入標識豁免范圍。值得注意的是,只要轉基因食品符合上述豁免條件之一,即可豁免標識。
四、小結
轉基因食品自誕生以來就爭議不斷,消費者對知情權的訴求與日俱增。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使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無法通過市場競爭得以實現,需要公共權力(政府)進行適度干預,通過制定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矯正信息偏在,以恢復市場機能。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與消費者知情權緊密相關,其焦點是界定強制標識和標識豁免的范圍,核心是實現消費者與生產者權益的平衡。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是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實現的有效保障,消費者知情權是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基石。轉基因食品標識與食品安全無關,因而“風險防范原則”不能成為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的法理基礎。無論從經濟學視域還是法學視域下考量,消費者轉基因食品知情權均需要予以限制。消費者知情權限制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基礎,對消費者知情權限制的范圍,就是轉基因食品標識豁免的范圍。我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對強制標識范圍與標識豁免范圍的界定有失科學,對消費者權益與生產者權益的保護有失均衡,十多年的法律實踐表明,其法律效果不盡如人意。基于對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法理基礎的認識,應緊密結合我國實際,在法律上通過設定標識閾值、改進標識目錄來完善標識規制工具,通過對強制標識范圍和標識豁免范圍進行雙向調整來完善標識范圍,以便充分發揮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的功能。
(責任編輯:徐瀾波)
D F529
A
1005-9512(2016)05-0118-14
張忠民,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1X FX 02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轉基因食品法律規制研究”(項目編號:10Y JC820165),教育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改革試點項目(項目編號:教高函[2014]7號),重慶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轉基因生物標識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1SK H 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