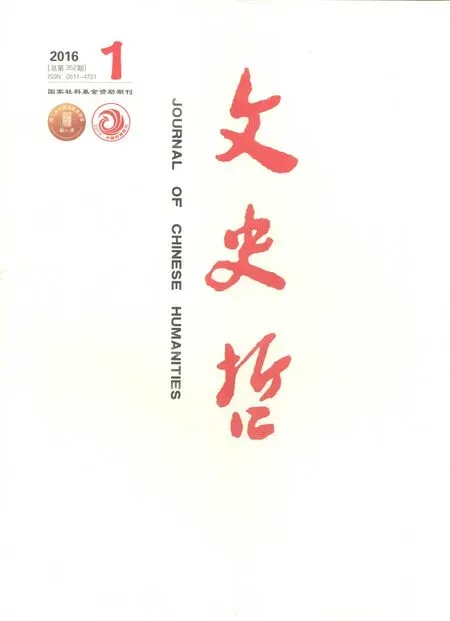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學術史——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為中心
左東嶺
?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學術史
——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為中心
左東嶺
摘要:中國近二十年的學術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存在著種種缺陷,需要進行系統的理論反思。要撰寫出為學界所真正需要的學術史著作,應遵循《明儒學案》所提出的“明宗旨”與“別源流”的基本原則,具備“宗旨”明確、評價允當與預測學術增長點的基本內涵,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研究者應具有較高的學術素養與豐富的專業研究經驗。
關鍵詞:學術史研究;撰寫原則;基本內涵;作者資質
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學術界,編寫各種各樣的學術史成為近二十年來的流行學術操作。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各種學科由于受到西方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的影響,紛紛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并運行了近百年,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但也存在著種種的問題與缺陷,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總結與檢討,以便完善學科建設與提升研究的水平。從這一角度看,學術史寫作的流行便是可以理解的一種學術選擇。然而,在這二十多年的學術史編寫中,到底對于學術研究提供了何種幫助,又存在著哪些問題,或者說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學術史,似乎還較少有人關注。我們認為,總結學術史的寫作就像學術史寫作同樣重要,因為及時檢討我們所從事的學術工作,會使后來者少走彎路,從而提升研究水平。
一、近二十年學術史寫作的檢討
學術史的清理其實是學術研究的常規工作,任何一個領域的問題研究,都必須首先從學術史的清理做起,否則便無法展開自己的研究。中國學術界大規模、有意識的專門學術史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其標志性成果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組織編輯出版的“學術研究指南叢書”,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該叢書出版了數十種學術史“概述”類著作。現在回頭來看這套大型研究史叢書,我們依然應該對其表示敬意,因為它的確對當時及后來的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貢獻與推進。總結起來說,它具有以下幾方面的主要特點。
一是起點較高。作為一套大型的研究指南叢書,其著眼點主要是為研究者提供入門的方法以便能夠領會本領域的基本學術狀況及研究方法,該叢書的“出版說明”就開宗明義地指出:
這套叢書將分門別類介紹哲學和社會科學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對各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分析;對各學派或不同觀點進行評介;對當前的研究動態及未來研究趨勢進行預測;還要介紹各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為了便于研究者檢索,書后還附上該學科的基本資料書目及其提要和重要論文索引。這樣,本書便是集學術性、資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冊在手,即可對某一學科研究的基本情況一覽無遺,足供學人參考、咨詢、備覽,對需要深入研究的內容,也可按圖索驥,省卻“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煩惱。*羅宗強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頁。
從這一說明中不難看出,該叢書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其宗旨是作為研究的入門書,學術史研究當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內容,這不僅從其書后附錄的“基本資料書目”這些非學術史的板塊可以看出,更可以從其撰寫的方式顯示出來。比如關于近代史的研究,該叢書既包括學術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要》(陳振江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同時也收入了《習史啟示錄》(中國史學學會《中國歷史年鑒》編輯組編,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這類談治學經驗的著作。而且在體例上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古代文學領域,該叢書共收了9種著作:趙霈霖的《詩經研究反思》和《屈賦研究論衡》、劉揚忠的《宋詞研究之路》、寧宗一的《元雜劇研究概述》和《明代戲劇研究概述》、金寧芬的《南戲研究變遷》、李漢秋的《儒林外史研究縱覽》、羅宗強等人的《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袁健的《晚清小說研究概說》等。將作為學科的古代文學理論和作為文體的詩詞小說戲劇以及古典名著的《儒林外史》并列,頗顯體例的凌亂。盡管存在這些不足,但其中有兩點是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這就是一方面要“對各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分析;對各學派或不同觀點進行評介”的學術史清理,另一方面還要“對當前的研究動態及未來研究趨勢進行預測”的研究瞻望。這兩方面的要求應該說是很高的,尤其是對于研究趨勢的預測就絕非一般學者所能輕易做到。
二是作者隊伍選擇比較嚴格。從該叢書呈現的實際成果來看,其作者一般都具備兩個條件:在某領域已經具有較大成就的學者和當時依然處于研究狀態的學者。仍以古代文學為例,其中的六位學者都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較為突出的研究業績,但在當時又都還是中年學者,正處于學術生命的旺盛期。這或許與這套叢書的“指南”性質相關,因為初入門者缺乏研究經驗,而已經退出研究前沿的年長學者又難以跟上學術發展潮流。這種選擇其實也反映在上述所言的體例凌亂上,因為是以有成就的中年學者為選擇對象,當然就不能追求體例的統一與均衡,可以說這犧牲了體例的完整性而保證了叢書的質量。當然,從八種學術史著作居然有兩位作者一人呈現兩種的情況看,還是包含著地域性的局限與叢書組織者學界統合力的不足。
三是叢書質量較高。由于具有較高的立意與作者隊伍選擇的嚴格,從而在總體上保證了叢書的基本質量。比如在羅宗強等人撰寫的《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的第一編,分四個小節對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歷史”和“資料載籍”進行系統的介紹,使讀者完整地了解該學科的基本性質與歷史發展,同時還提出了自己的獨立見解,認為“弄清古代文學理論的歷史面貌本身,也可說就是研究的目的”*羅宗強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第7頁。。自建國以來,古代文論的研究一直追求“古為今用”的實用目的,從而嚴重影響了對于其真實內涵的發掘,當時提出弄清歷史面貌的研究目的,可以說是一種撥亂反正的主張。正是由于擁有這樣的眼光,也就保證了學術史清理中的學術判斷,從而保證了該書的質量。
自這套叢書出版之后,便持續掀起了學術史寫作的熱潮,僅以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為例,其中冠以20世紀學術史名稱的便有:趙敏俐、楊樹增的《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張燕瑾、呂薇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蔣述卓等人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黃霖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傅璇琮主編的《20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文學專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春青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等。有的著作雖未以此為名,其實亦屬于同類性質的著作,如: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均包含有對20世紀學術史梳理的內容。還有以經典作家作品為對象的專門研究史,如以《文心雕龍》研究為題的張少康等撰寫的《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張文勛《文心雕龍研究史》(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李平《文心雕龍研究史論》(黃山書社,2009年)等,以杜甫為題的吳中勝的《杜詩批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以蘇軾為題的曾棗莊的《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紅樓夢》為題的白盾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陳維昭的《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至于在此期間以綜述文章形式發表的學術史研究成果,更是難以一一列舉。
與該叢書相比,后來的學術史研究無疑有了長足的進展,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更加系統而規范。比如張燕瑾、呂薇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共10卷,不僅包括了古代文學的各個朝代,而且還增添了近現代和當代,應該說這才是真正完整的學術史;又如傅璇琮主編的《20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文學專輯》,內容更為完整豐富,共由8種構成:《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國戲劇研究》、《中國詞學研究》、《中國詩學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西方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等,文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全都囊括進來了,而且分類也比較合理;再如黃霖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共7卷,除了以分體所構成的“詩歌卷”、“小說卷”、“戲曲卷”、“散文卷”、“詞學卷”、“文論卷”外,還由主編黃霖執筆撰寫了“總論卷”,對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總體狀況與重要理論問題進行歸納與評述,從而與其他分卷一起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系統。這些大型的學術史叢書,較之以前那些零打碎敲而互不統屬的研究已經顯示出明確的優勢。

三是對于學術史認識的深化。學術史的研究對象是相當駁雜凌亂的,如何選擇與評價取決于研究者的知識構成與學術素養,即使面對相同的研究對象,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學術背景,也會呈現較大的差異。比如對于“新紅學”的態度,早期多從政治的角度加以解讀、批判,而近來則更多從學理的層面進行清理。比如郭豫適在評價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研究方法時說:“胡適雖然在具體進行作者、版本問題的考證中,得出了一些比較合乎實際的、可取的看法,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肯定他那實驗主義的真理論和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44頁。很明顯,這是對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方法的關注與批判。而陳維昭在評價胡適時也說:“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的最本質的錯誤在于無視文本的創造過程和文本的閱讀的不可逆性,無視敘述行為和閱讀行為的解釋性。”*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如果沒有接觸過新批評的文本理論與接受美學等開放性闡釋新理論,作者不可能進行此種學理性的批評。郭豫適在傳統理論的層面研究胡適,而陳維昭則是用新的理論視角審視胡適,二人的評價有深淺的差異,但并無高低的可比性。
指出上述學術史研究的新進展并不意味著目前的學界不存在問題,其實在學術史研究局面繁榮的背后,潛存著許多必須關注和可以引起討論的問題。這種情況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大批貌似學術史研究而實則僅僅是成果的羅列,作者既未能全面搜羅成果,也缺乏鑒別揀擇的能力。此類成果對于學術研究幾乎毫無貢獻,故不在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另一個是許多嚴肅性的學術史著作與論文,對學界的進一步研究影響較大,但也存在著種種的問題,這就不能不引起足夠的重視。就筆者所看到的學術史論著,大致存在著以下應該引起注意的現象。
首先是資料的完整性問題。竭澤而漁式的網羅全部資料是學術史研究的前提,然后才能從中篩選出有價值的成果進行分析評價。然而目前的學術史著作中卻很少有人將學術史資料搜集齊備的。盡管目前電腦網絡的搜集手段已經足夠的先進便捷,但也恰恰由于過分依賴網絡檢索而忽視了其他檢索的途徑。比如目前網絡數據庫的內容基本上是經過授權的期刊,而在此之外卻存在大量的盲點,論其大者便有未上期刊網的地方刊物成果、叢刊及論文集中的成果以及通史類中所包含的成果三種,均時常被學者所忽略。且不說那些以舉例為寫作方式的論著,即使那些專門提供成果索引的學術史著作,也存在此類問題。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纂的《百年明史論著目錄》(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一書,搜集了自1979至2005年的明史研究成果,應該有足夠的權威性,但筆者在翻檢自己的成果時卻吃驚地發現有大量的遺漏。其中共收筆者7篇論文和3部著作,但那一時期作者共發表有關明史研究的論文20篇,也就是說遺漏了將近三分之二的論文。遺漏部分有些是上述所言的盲區,如《陽明心學與馮夢龍的請教說》(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3年)屬于論文集所收成果,《明代心學與文學》(傅璇琮、蔣寅總主編,郭英德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屬于論著中所包含成果。而《童心說與李贄的人生價值取向》(《朱子學刊》第8輯,1998年)、《陽明心學與唐順之的學術思想、文學思想與人格心態》(《文學與文化》第1輯,2003年)、《論王陽明的審美情趣與文學思想》(《文藝研究》1999年增刊)屬于增刊或叢刊類成果。但不知是何原因,在知網中所收錄的8篇論文竟然也被遺漏,似乎令人有些費解*這8篇文章是:《耿李之爭與李贄晚年的人格心態巨變》(《北方論叢》1994年第5期),《禪學思想與李贄的童心說》(《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從良知到性靈:明代文學思想的流變》(《南開學報》1995年第4期),《陽明心學與湯顯祖的言情說》(《文藝研究》2000年第3期),《從本色論到性靈說:明代性靈文學思想的流變》(《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6期),《內在超越與江門心學的價值取向》(《南昌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李贄文學思想與心學關系及其影響研究綜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20世紀以來心學與明代戲曲小說關系研究綜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該索引查找筆者有關明史的研究成果,其學術史的研究將會與實際狀況有較大的出入。
其次是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盡管在搜集研究成果時力求其全,但除了索引類著作外,誰也無法且亦無必要將所收集到的成果全部羅列出來,作者必須進行選擇,何者須重點介紹,何者須歸類介紹,何者可歸為存目。選擇工作需要的是作者的學養、眼光以及對該研究領域的熟悉程度。比如同樣是對明代詩歌研究史的梳理,余恕誠《中國詩學研究》用了“百年明詩研究歷程”、“高啟詩歌研究”和“前后七子詩歌研究”三個小節予以論述,而羊列榮《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詩歌卷》卻僅用“關于明詩的敘述狀況”一節進行介紹,而且重點敘述“公安派的現代發現”。這種選擇的不同就有二人學術判斷的差異,也存在是否對明代詩歌研究具有實際研究經驗的問題。其實,就研究史本身看,現代學術史上的明詩研究都比較偏重一首一尾,高啟與陳子龍乃是其重要研究對象。從學術的誤區來看,傳統的研究比較重視復古派的創作而輕視性靈派的創作。二人的選擇都存在一定的問題。
三是體例的統一性問題。就近幾年來的學術史研究看,由于規模越來越大,很難由一人單獨完成,因此組織隊伍進行合作研究就成為常見的方式。合作研究的模式大致有兩種,導師帶學生與學科老師合作,或者兩種模式相結合也很常見。如果導師認真負責地制定體例與審定文稿,統一性也許可以基本得到保障。如果僅僅是匯集眾人文稿而成,就不僅是體例統一的問題,還會具有種種漏洞,諸如資料不全、選擇不當、評價偏頗乃至文句錯訛的存在。而學者之間的合作往往會存在體例不一的問題,因為每人的學術背景、研究習慣及文章風格多有不同,難免會有所出入。《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是由蔣述卓、劉紹瑾、程國賦、魏中林等同仁合著的,其主要特點是將研究的歷史階段與專題研究結合起來進行論述,雖然部頭不大但卻將20世紀古代文論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是一部簡明而系統的學術史著作。但如果細讀,還是會發現作者之間的行文差異。蔣述卓長期從事古代文論的研究,不僅對材料相當熟悉,而且對許多專題有自己的思考,所以采用“述”與“論”相結合的方式,為此他還在“80至90年代中西比較文論研究的發展”一章里專門寫了“中西比較文論研究的總體評價與展望”一節,暢談自己的看法與設想。而在程國賦等人所撰寫的“專題研究回顧”部分,卻很少發表評價性的意見,尤其是《文心雕龍》研究部分,幾乎就是研究成果的客觀介紹。這樣做當然是一種嚴肅的學術態度,與其因不熟悉而評價失當,倒不如客觀敘述介紹,遺憾的是在體例上不免有些出入,與理想的學術史研究還有一定差距。
除了上述的種種不足之處外,還存在著分析的深入性,評價的公正性,預測的先見性等方面的問題。但歸結起來說,學術史的研究其實就是兩個主要方面:是否準確揭示了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是否通過學術史的梳理尋找出了新的學術增長點與研究空間。退一步說,即使不能指出以后的學術方向,起碼也要傳達與揭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在這一方面,目前的問題最為嚴重,羅列成果、分類介紹與泛泛而談幾乎成為學術史寫作的基本套路。而對于研究者的獨特發現、獨特方法與鮮明風格則往往付之闕如。
二、《明儒學案》的啟示:學術史研究的原則
學案體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編撰的一種寫作模式,曾以其鮮明的特點長期被學界所關注。史學家陳祖武概括說:“學案體史籍,是我國古代史學家記述學術發展歷史的一種獨特編纂形式。其雛形肇始于南宋初葉朱熹著《伊洛淵源錄》,而完善和定型則是數百年后。清朝康熙初葉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它源于傳統的紀傳體史籍,系變通《儒林傳》(《儒學傳》)、《藝文志》(《經籍志》),兼取佛家燈錄體史籍之所長,經過長期醞釀演化而成。這一特殊體裁的史書,以學者論學資料的輯錄為主體,合案主生平傳略及學術總論為一堂,據以反映一個學者、一個學派,乃至一個時代的學術風貌,從而具備了晚近所謂學術史的意義。”*陳祖武:《學案再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在中國古代,接近于陳先生所說的這種學案體著作,大致有朱熹《伊洛淵源錄》、耿定向《陸楊學案》、劉元卿《諸儒學案》、周汝登《圣學宗傳》、劉宗周《論語學案》、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等。盡管在學案體的起源與名稱內涵上目前學界尚有爭議,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作為學案體的代表性著作則是毫無爭議的。梁啟超就曾說:“中國有完善的學術史,自梨洲之著學案始。”并且從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總結出編撰學術史的幾個條件:
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個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學案》,總算具備這四個條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58頁。

就黃宗羲本人在《明儒學案》的“序”及“發凡”中所重點強調的看,“分其宗旨,別其源流”*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頁。乃是其主要著眼點。也就是說,《明儒學案》所體現的學術原則與學術精神,主要由“明宗旨”與“別源流”兩個方面所構成,而且這兩點也對當今學術史的研究最具啟發價值。
“明宗旨”是黃宗羲《明儒學案》最鮮明的特色之一,但其究竟有何內涵,學界看法卻不盡一致。筆者通過對該書的“序”、“發凡”及相關表述的細致解讀,認為它具有三個層面的含義。
首先是對最能體現思想家或學派特征、為學方法及學說價值的高度凝練的概括。黃宗羲說: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第17頁。
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學者為學需有自己的宗旨,而且用簡短的語句將其概括出來,以便體現自我的為學原則;二是了解這種學說也要抓住此一宗旨,才能得其精要,領會實質;三是介紹這種學說,也要能夠用“一二字”概括出其為學宗旨,以便把握準確。從學術史研究的角度講,如果研究對象本身宗旨明確,那當然對研究者是很有利的。但實際情況往往并非如此,越是大思想家和大學者,其思想越是豐富復雜,如何在這包羅萬象的學說體系中提煉出為學宗旨,那是需要經過研究者的認真思考與歸納的。黃宗羲的可貴之處是他能夠遍讀原始文獻,經由認真斟酌,然后高度凝練地提取出各家之宗旨。正如其本人所言:“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襲前人之舊本也。”*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第18頁。也就是說,提煉宗旨的前提是廣泛閱讀研究對象的全部文獻,真正尋找出其為學宗旨,而不是將自我意志強加給對象,他之所以不滿意周海門的《圣學宗傳》,其原因就在于:“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第17頁。對此已有許多學者進行過考察,大都得出了肯定的結論。從這一角度出發,可知學術史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真正從研究對象所有成果的研讀中,高度概括出其學術的宗旨與精神,讓人一看即可辨別出其學術的特色。
其次,宗旨是思想家或學派獨創性的體現。黃宗羲認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第18頁。學術的精髓在于有思想的創造,而不在于求全穩妥,因而在《明儒學案》中,就特別重視“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的學者,而對那些“倚門傍戶,依樣葫蘆”陳陳相因的“流俗”、“經生”之見,則一概予以祛除。如果說提煉宗旨是學術史研究的第一步,那么辨別各家宗旨有無創造性從而決定是否納入學術史的敘述則是其第二步。在當代學術史研究中,并不是都能做到這一點的,許多學者為了體現求全的原則,常常采取羅列成果、全面介紹的方式,結果學術史成了記述論著的流水賬,其中既無宗旨之提煉,亦無宗旨之辨析。黃宗羲的這種觀點,體現了明代重個性、重創造的學術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其三,宗旨是為學精神與生命價值追求的結合。此點與其“自得”的看法密切相關。在“發凡”中,黃宗羲除了提出宗旨的見解外,又提出“自得”的看法。何為“自得”?有學者認為:“‘自得’堅持的是一種獨立的政治精神,強調的是一種自由的心理意識。”并認為“自得”與“宗旨”的關系是:“在黃宗羲的視野中,只有走向陽明心學的‘自得’才可以稱為‘宗旨’,否則,不是‘宗旨不明’,就是‘沒有宗旨’。”*姚文永、宋曉伶:《“自得”和“宗旨”——〈明儒學案〉一個重要的編撰方法與原則》,《大連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自得”固然與獨立思考的學術精神密切相關,但這并非其全部內涵,而且“自得”與“宗旨”也不能完全等同。比如黃宗羲認為,王陽明之前的明代學術,“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9頁。。可見他們缺乏思想的創造性,當然也就沒有“自得”,但并不妨礙其學說亦有其宗旨,黃宗羲曾經將明前期同倡朱子學的吳與弼和薛瑄的不同宗旨概括為:康齋重“涵養”而文清重“踐履”。當然,有“自得”之宗旨優于無“自得”之宗旨亦為黃宗羲所認可,但不能說無自得便無宗旨。其實,黃宗羲所言的“自得”,除了具有獨立自由的精神意識外,還有兩種更重要的內涵。一是自我的真切體悟而非流于口頭的言說,其《明儒學案發凡》說: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于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做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做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于天下后世也。*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第18頁。
此處的“自得”便是由自身思考體悟而來的真切感受與認知,而且按照知行合一的觀念,真正的“知”就包括了踐履的“行”,黃宗羲稱之為“切實工夫”。與此相反的是,停留于言說的表面而無體驗與行動,那便叫做“玩弄光景”。正如黃氏批評北方王學“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36頁。。“跡象聞見”便是停留于語言知識的層面而無真切的體驗,也就是沒有“自得”。二是自我境界的提升與人格的完善,也就是心學所言的自我“受用”。正如黃氏所言:“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后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黃宗羲:《黃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學案》,第9頁。在此,語錄與受用、講學與修德都是通過“自得”而聯系起來的。這也難怪,心學本身就是修身成圣的學問,如果不能實現修身成圣的“受用”,便是“玩弄光景”的假道學。所以黃宗羲在概括陽明心學時才會說:“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做圣之路。”*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9頁。
將為學宗旨的鮮明特征、思想創造和自得受用結合起來,便是心學所說的“有切于身心”,也就是有益于身心修為,有益于砥礪人格,有益于提升境界,有益于圣學追求。這既是其為學宗旨,也是其為學目標。黃宗羲以此作為《明儒學案》衡量學派的標準,既合乎其作為心學后勁的身份,也符合明代心學的學術品格。以此反觀現代的學術史研究,就會發現存在的明顯缺失。也許我們并不缺乏對學者思想特征與學術創造的歸納論述,但大都將其作為一種專業的操作進行衡量平說,而很少關注其是否“有切于身心”,也就是對學者的學術追求和社會責任、人文關懷以及性情人格之間的關系極少留意。筆者認為在人格境界與社會關懷方面,也許我們真的趕不上黃宗羲。
“別源流”是黃宗羲《明儒學案》第二個要實現的目標。所謂“別源流”,就是要理清學派的傳承與思想的流變。從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實際操作上看,其“別源流”分為四個層面:一是梳理有明一代學術源流,二是尋覓明代心學學脈,三是陽明心學本身的學脈關系,四是學者個人思想的演變過程。關于黃宗羲考鏡源流的業績,賈潤在其《明儒學案序》中指出:
蓋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余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途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有此書,而分支派別,條理粲然。其于諸儒也,先為敘傳,以紀其行,后采語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無師承者,亦皆廣為羅列,靡所遺失。論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后已。*賈潤:《明儒學案序》,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2頁。
“分支派別,條理粲然”八個字,可以說高度概括了《明儒學案》在別源流方面的特點。黃宗羲在別源流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兩點,即兼綜百家的包容性和兼顧優劣的公正性。盡管他是王門后學,但并不忽視其他學派的論述,這便是其巨大的包容性;而對于他最為看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既贊譽其“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同時又指出:“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后來門下各以意見摻合,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本意。”*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9頁。以會合朱陸的方式以糾正陽明及其后學的偏差,乃是劉宗周為學之核心,黃宗羲對陽明的批評顯然也受到其師劉宗周的影響,但同時也是他本人的真實看法與辨析源流的基本學術原則。
當然,學界也有對黃宗羲《明儒學案》的負面評價,比如錢穆就對黃宗羲在選取諸家言論的“取舍之未當”深致不滿,并認為其“于每一家學術淵源,及其獨特精神所在,指點未臻確切”。至于造成如此弊端之原因,錢穆則認為是黃宗羲“乃復時參以門戶之見,意氣之爭。劉蕺山乃梨洲所親授業,亦不免此病”*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0頁。。至于《明儒學案》是否真的存在如錢穆所言缺陷,以及錢穆對黃宗羲之詬病是否恰當,均可進一步進行深入的討論。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黃宗羲別源流的原則及其依據。
黃宗羲之所以重視“分其宗旨,別其源流”,是他認為明代思想界最為獨特的乃是學者之趨異傾向,也就是表達自我的真實見解與學術個性。他說:“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每久而一變。……諸先生不肯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略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于道者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第7頁。從橫的一面,同一師門的宗旨可以分化為數家;從縱的一面,時間長了必然會發生變化。學術的活力就在于這種差異性和變動不居。這些不同派別與見解也許有“淺深詳略之不同”,但其可貴之處在于不肯重復前人的陳詞濫調而勇于表達自我對“道”的真知灼見。所以他反復強調:“羲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后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何為“懵懂精神”?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人云亦云,就是“倚門傍戶,依樣葫蘆”的迷信盲從。只有那些“竭其心”的有得之言,盡管可能“醇疵互見”,卻足以成家。黃宗羲所要表彰的,正是這些所謂的“一偏之見”、“相反之論”。黃宗羲這種求真尚異的觀念,是明代心學流行的必然結果,是學者崇尚自我和挑戰權威精神的延續,所以他才會如此說:“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于出于一途,使厥美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黃宗羲:《黃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學案》,第10頁。思想的創獲來自艱辛的探索與思考,猶如開山鑿道之不易。而如果使所有的學者均納入同一模式的思想,就只能導致“焦芽絕港”的思想枯竭。學術的多樣性乃是探索真理的必要性所決定的,因為“學術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第7頁。。堅持思想探索,倡導獨立精神,贊賞學術個性,鼓勵流派紛爭,這是黃宗羲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思想啟示。
自黃宗羲之后,以學案體撰寫學術史者雖然不少,但能夠與其比肩者卻絕無僅有。且不說清人徐世昌《清儒學案》和唐鑒《清學案小識》這類以堆積資料為目的的著作,它們既無宗旨之精煉提取,又無學脈之總體把握,即令是今人錢穆之《朱子新學案》、陸復初之《王船山學案》、楊向奎之《新編清儒學案》、張豈之之《民國學案》等現代學術史著作,雖在思想評說、范疇辨析、問題論述及資料編選諸方面各有優長,但在學脈梳理及論述深度上皆難以達到《明儒學案》的高度。
在文學領域的學術史研究中,有兩套叢書近于學案體的特征,它們是陳平原主持的“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陳文新主持的“中國學術檔案大系”(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前者共擬出版20種,自21世紀初至今已基本完成;后者動議于十年之前,如今也已出版有10余種。從編寫目的看,二者都重視文獻的保存,都以選擇優秀成果作為主體部分,這可視為是對《明儒學案》原著摘編方式之繼承。從編寫體例上看,“文存”由導論、文選和目錄索引三個部分組成,“學術檔案”則由導論、文選、論著提要和大事記四部分構成。導論相當于《明儒學案》的總論部分,但由于是針對一代學術而言,不如《明儒學案》的簡要精煉。目錄索引與大事記是受現代學術觀念影響的結果,故可存而不論。至于論著提要則須視各書作者之學術眼光與概括能力而定,大致以截取各書之內容提要而來。如果以“明宗旨”與“別源流”的標準來衡量這兩套叢書,它們遠遠沒有達到《明儒學案》的水平。因為文選部分盡管通過選優而保存了名家的代表作,卻必須通過每位讀者自己的閱讀體味來了解其學術特色。“學術檔案”的情況略有改變,其選文之后附有作者生平、學術背景、內容簡介與評述、作者著述情況等,但大多是情況介紹而乏精深之論。至于別源流更是這兩套叢書的短板,就筆者所接觸到的導論部分而言,只有王小盾在《詞曲研究》的導論中簡略提及了任二北的師承關系及臺灣高校的注重師承傳授,其他著作則蓋付闕如,似乎別源流已經被置于學術史研究之外。當然,在此需說明兩點:一是在此并沒有責備叢書主持人和各書作者之意,因為其他的學術史著作也都沒有關注此一問題;二是別源流的問題之所以被現代學術史研究所遮蔽,是因為學術研究中的師承觀念與學派意識逐漸趨于淡化,從而難以為學術史研究提供豐富的研究案例與內容。但還必須指出,學術研究中師承觀念與學派意識的缺位并不能完全成為學界忽視該問題的借口,因為尋找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缺陷同樣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學術史研究的三個層面:提煉“宗旨”、檢討缺陷與學術預測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明儒學案》是中國歷史上的經典學術史著作,所以應該對其進行認真研究,從中受到有益的啟示。但是,學案體畢竟是古代的產物,面對更為豐富復雜的研究對象,就不必從體例上再去刻意模仿這樣的著作,而是要吸取其學術思想與撰寫原則,從而彌補當今學界學術史研究之不足。對此我們認為有三個層面的內容必須具備并對其內涵進行認真的辨析。
首先是所謂的提煉“宗旨”。這是黃宗羲最為強調的學術史研究原則,也應該是當代學術史最基礎的工作,其實也就是通過對學術研究過程的清理使讀者明白前人提出了何種獨特的觀點,運用了什么獨特的方法,形成過哪些獨特的學風與學派等等。既然是學術史,就需要具備“史”的品格,也就是必須寫出歷史的真實內涵,包括歷史現象的真實反映和歷史發展過程中關聯性的揭示。其實,黃宗羲所歸納的“明宗旨”和“別源流”兩個原則正是反映真實與揭示歷史關聯性的精煉表述。需要指出的是,《明儒學案》只是明代儒學發展的學術史,屬于思想史的范疇,因此其主要目的便是總結提煉各家的主要思想創獲以及學派之間的關系。而現代學術史所面對的研究對象要更加豐富,因而對其歷史真實內涵的把握與關聯性的揭示也更為復雜。
就現代學術史寫作的一般情況看,學界大都采取縱向以時間為坐標而分期敘述,橫向則以地域、學者或問題作為基本單元進行分類介紹。這種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結構方式乃是學術史寫作的主要套路,基本能夠承擔提煉“宗旨”的敘述功能。但也并非不存在問題,因為無論采取哪種角度,都需要經過作者的篩選與揀擇,什么能夠進入學術史的敘述框架就成為作者所操持的話語權力,那么不同立場、不同眼光、不同標準,甚至不同師承與學派,就會有理解判斷的差異,爭議的產生也就在所難免。于是,便有了學術編年史的出現。編年史的好處在于以編年的方式將與學術相關的內容巨細無遺的網羅其中,能夠全面展示學術發展的過程。只不過這種學術編年史的寫作目前還僅限于中國古代,而且也只有梅新林等人的《中國學術編年》這一部書。能否用編年史的方式進行現代學術史的寫作,當然可以繼續進行討論與實驗,但可以肯定的是,編年史無論如何也不能代替傳統的學術史研究,因為它無法承擔“明宗旨”的學術功能,不能體現作者發現學術獨創性的眼光。盡管展示全面與突出重點同等的重要,但黃宗羲以突出主要學脈的《明儒學案》之所以會受到學界的廣為贊譽,就是由于他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慧眼與提煉工夫。
從提煉“宗旨”的角度看,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問題不在于學術史的編寫體例,而是對于“明宗旨”與“別源流”的把握是否到位。從“明宗旨”的角度,存在著一個突出主要特征與全面反映真實的問題。無論是一個歷史時期、一個流派還是一位學者,其學術研究都會存在這樣的矛盾。作為學術史研究,就既要抓住主要特征以顯示其學術觀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結論的獨特貢獻,又要照顧到其他方面以顧及其完整面貌。比如在研究民國時期現代文學觀念的形成時,人們自然會更多關注受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影響較深的那些學者,以探索中國現代學術史是如何從中國傳統的文章觀念轉向現代純文學觀念的學術操作的。但是同時又不能忽視,當時還有許多學者依然在運用傳統的文章觀進行研究。那時既有劉經庵只把詩歌、戲曲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純文學史》,因為作者的文學觀念是“單指描寫人生,發表情感,且帶有美的色彩,使讀者能與之共鳴共感的作品”*劉經庵:《中國純文學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頁。。但也有陳柱收有駢文甚至八股文的《中國散文史》,因為作者的文學觀念是“文學者治化學術之華實也”*陳柱:《中國散文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頁。。從當時的學術觀念看,劉經庵是進步與時髦的,但從今天的學術觀念看,陳柱也未必沒有自己的道理。如果從提供歷史經驗上看,二者都有其學術價值;如果從展現歷史真實上看,就更不能忽視非主流聲音的存在。從“別源流”的角度,目前的學術史研究可能存在的問題更大。盡管現代學術史上真正形成學術流派的不多,但卻不能忽視學術思想的傳承與分化,甚至一個學者也會有學術思想形成、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學術思想的變化往往會導致其研究對象的選擇、學術方法的使用以及學術立場的改變等等變化。只有把這些變化過程交代清楚了,才能從中總結學術研究與時代政治、環境風氣、研究條件之間的復雜關系等歷史經驗,同時也才能把歷史發展的過程性梳理清楚。無論是在所接受的學術訓練的系統性上,還是所擁有的研究條件上,我們的時代都要更優于黃宗羲,理應在明宗旨和別源流上比他做得更好,但遺憾的是,在許多方面黃宗羲依然是我們無法超越的楷模。
在提煉“宗旨”的學術操作中上,目前的學術史研究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誤區,這便是對于歷史教訓的忽視。幾乎所有的學術史在寫到“文革”十年時,都用了“空白”二字來概括本時期的特征,內容上更是一筆帶過。有不少學者甚至在處理建國后十七年的學術史時,也采取了類似的態度。從成果選優的角度,這樣做當然有其道理,因為你無法在此時找到值得后人學習與參考的獨特學術理念與學術方法。然而,學術史研究不同于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上沒有價值的東西未必在歷史經驗的總結上也毫無價值。學術史研究中要淘汰和忽略的是大量平庸重復、缺乏創造力的書籍文章,也就是黃宗羲所說的“倚門傍戶”、“依樣葫蘆”的低劣制作,而不是缺陷和錯誤。歷史乃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時間鏈條所構成的,如果失去其中的一個鏈條,哪怕是一個有問題的鏈條,也將會破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錯誤的“宗旨”也是一種宗旨。一位新詩研究專家在談到自己的研究經驗時說:
在撰寫《中國新詩編年史》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到,面對20世紀的新詩,只是從藝術和詩的角度進入會感到資源十分匱乏,像新民歌運動、“文革”詩歌等,20世紀很大一部分新詩作品并不是藝術或詩的,但如果站在問題的角度加以審視,其獨特和復雜怕是中國詩歌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不能相比的。我力求這部編年史能更多地包含和揭示近一個世紀新詩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及問題的復雜性。*劉福春:《還原歷史的豐富與復雜》,《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
這是就文學史研究而言的,其實學術史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站在學術價值的立場看“文革”或“十七年”,固然是研究史的低谷甚至“空白”,但站在總結教訓與探索問題的立場上,也許包含著繁榮期難以具備的研究價值。比如說建國后一直以極大的聲勢批判胡適的新紅學,可是新紅學所確立的自傳說與兩個版本系統的學術范式卻始終左右著《紅樓夢》研究界,最后反倒是新紅學的主要成員俞平伯對其研究范式提出了顛覆性的看法。這其中所包含的政治與學術研究的關系到底有何價值?又比如在所謂“浩劫”的年代,許多學者輟筆不作或跟風趨時,錢鐘書卻能沉潛學問,寫出廣征博引、新見時出的百余萬言的《管錐編》,這是他個人例外呢,還是其他人定力不夠?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人文學科研究中,閉門造車固然封閉保守,趨炎附勢肯定喪失品格,那么在社會關懷與學術獨立的關系中學者到底如何拿捏才是恰當?這些都是研究學術中的重大問題,也是至今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從這一角度講,對于歷史教訓研究的價值決不低于對于研究成績的表彰。可惜在這方面我們以前的關注實在太少。
其次是檢討缺陷。所謂檢討缺陷就是檢點現代學術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中大到研究范式的運用、研究價值的定位、學術盲點的尋找,小到某個命題的把握、某一材料的安排、某一術語的使用等等。目前,無論是對學術史的研究還是當今的學術批評,往往是贊賞多而批評少,總結經驗多而尋找缺陷少。究其原因,其中既有水平問題,也有學風問題。但是對于學術史研究來說,尋找缺陷的意義絕不低于總結經驗,因為尋找不出缺陷就不能提出新的路徑,也就不能進一步提升水平。
其實在學術史研究中確實還存在著很多需要糾正的弊端與不足,就其大者而言便有以下數種。
(一)研究模式的缺陷。比如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模式是建立在西方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的學理基礎上,從根本上說是西方近代以來理性主義思潮的產物。這種理性主義的研究范式以邏輯的思維與證據的原則作為其核心支撐,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叫做“言之成理”與“持之有故”。沒有這樣的研究范式,中國的學術研究就不能從傳統的評點鑒賞轉向現代的理論思辨與邏輯論證,也就不能具備現代學術品格。然而,這種理性主義思潮基本是以自然科學為依托的,所以帶有濃厚的科學色彩。其中有兩點對現代學術研究具有根深蒂固的負面影響,這便是生物學上的進化論與物理學上的規律論。表現在歷史研究中,就構成以文體創造為演進模式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史理論,而表現在研究目的上則是尋找各種各樣的文學史規律,諸如唐詩繁榮規律、《紅樓夢》創作規律、舊文學衰亡規律等等。直至今日,這種研究模式依然在發揮巨大的影響力而左右著學者的思維方式。其實,自然科學的理論在進入人文學科領域時,是需要進行檢驗和調整的,否則就會傷害到學科自身。因為文學史研究不能以尋找規律為研究目的,他必須以總結歷史上人們如何以審美的方式滿足其精神需求作為探索的目標,然后才可能對當今的精神生活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同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線性進化理論也不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因為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日益豐富的生活帶來人們更為豐富的情感世界,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文學樣式與方法來滿足其精神需求,那么文學史的發展過程就只能呈現為文體如滾雪球般的日益復雜多樣,而不是進化論式的相互替代。不改變這種研究范式,我們只能依然沿著馮沅君的老路,把詩歌史只寫到宋代,而永遠找不到明清詩文研究的合法性來。
(二)流派研究的缺失。學術史研究是對學術研究實踐的描述與歸納,這乃是學界的常識。從這一角度說,現代學術史研究中流派觀念的淡漠與研究的弱化似乎是必然的。黃宗羲《明儒學案》在別源流方面之所以做得足夠出色,是因為思想界學派林立、論爭激烈,從而保持了巨大的思維活力,黃氏面對如此活躍的學術實踐,當然將之作為自己的主要特色。清代缺乏這種思想活力,建國伊始便禁止文人結社講學,當然也形不成學界的流派。研究清代的學術史,似乎也理所當然地寫不出《明儒學案》那樣的著作。那么,現代學術研究是否也可以因學術流派的缺少而走清人的老路,自動放棄流派的研究?這里又是一個誤區。學術研究實踐中流派的缺乏只能導致經驗總結的缺位,因為沒有這樣的實踐當然無法去歸納與描述。然而,正因為研究實踐中缺乏流派的意識與現實,學術史研究才更應該去指出這種致命的缺陷。思想創造的動力來自于流派的競爭,學術研究的活力也來自于流派的論爭,缺乏流派的學術研究是沒有活力、沒有個性的研究。學術史研究,理應去發掘珍貴的流派史實,探討流派缺失的原因,并強調形成新的流派之于學術研究的重要。因此,學術史研究不僅僅是學術實踐經驗的反映與總結,也應該肩負起糾正學術研究弊端的重要職責。
(三)人文精神的缺失。自現代學科建立以來,追求科學化與客觀化一直成為學界的目標,這既與科學主義的影響有關,也與建國后政治時常干預學術的現實環境有關,更與研究手段的日益技術化有關。學術研究的這種科學化傾向也深深影響了學術史的研究,使得研究不僅未能糾正這一缺陷,反而變本加厲地強化了這種傾向。其實,以人文學科的研究屬性去追求科學性與客觀性,本身就陷入一種尷尬的悖論。反思一下中國的歷史,哪一種重要的思想流派不具備經國濟世的人文關懷?就拿最為后人所詬病的強調思辨性的程朱理學與偏于名物訓詁考證的乾嘉漢學來說,其實也并不缺乏社會的使命感。理學固然重視修身,但《大學》的八條目依然從格物致知通向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乾嘉學派固然重視名物的考證,但其大前提依然是“反經”以崇尚實學的濟世胸懷。從現代史學理論看,科學性與客觀性受到日益巨大的挑戰,正如海登·懷特所言:“近來的‘回歸敘事’表明,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地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歷史學處理。”*[美]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5頁。無論從歷史的事實還是學科的屬性,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應該擁有區別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特征。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面對20世紀以來日益嚴重的科學化與技術化傾向,學術史的研究并沒能盡到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在文學研究領域,本來是最具有情感內涵和人文精神的學科,如今卻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運用變成了靠數理統計與堆砌材料以顯示其客觀獨立的冷學科。我們認為,如果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既缺乏理性思辨的智慧之光,又沒有打動人的人文精神,更沒有流暢生動的閱讀效果,而只是造就了一大批頭腦僵硬的教授與目光呆滯的博士,這樣的古代文學研究不要也罷。不過,要真正糾正這種人文精神的缺失,尚需整個學界的努力,尤其是學術史研究的努力。
以上三點只是作為例子來說明學術史研究中尋找缺陷的重要,至于更多更具體的研究缺陷,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重要的是學術史研究者在進行學術評估時既需要挑剔的眼光,也需要批評的勇氣,他理應將學術史研究視為推動學科發展的動力而不是表彰優秀分子的光榮榜。
其三是學術預測。從近二十年來所呈現的學術史研究成果來看,其主體部分大都是對已有成果的介紹與評價,一般也都會在最后有一部分文字表達對未來的瞻望,但對于現存問題的檢討就要明顯薄弱一些。正是由于對現存問題的分析認識不夠具體深入,因而對學術發展趨勢的預測也大多流于浮泛。其實,學術預測包括未來瞻望與提出新的學術增長點兩個層面,而且是并不相同的兩個相同層面。未來瞻望具有全局性與宏觀性,表達了學術史研究者的一種愿望或理想;提出學術新增長點則是對下一步研究的觀念、方法與路徑的認真思考,因而必須與當前的研究緊密銜接。

從以上這些學術史著作寫作經驗的總結中,可以歸納出以下關于提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一些原則:第一,學術增長點的提出范圍應該是專業的學術問題,而且必須有很強的敘述針對性。所謂針對性,乃是建立在對前人學術研究中所存留問題的清醒認識之上的。沒有對前人研究缺陷的發現與反思,就不可能提出有價值的學術增長點。第二,提出新的學術增長點必須對于當前的學術發展大勢具有清醒的判斷與認識。就拿《文心雕龍》研究來說,它理應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緊密關聯。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必須首先借鑒西方的理論方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體系,而西方理論方法也會留下與中國古代研究對象不能完全融合的弊端。因此,近二十年來的學術轉型就是要回歸中國文論本體,尋找到適合中國古代研究對象的理論方法。在《文心雕龍》研究中,幾十年來一直運用西方的純文學觀念去解讀歸納劉勰的文章觀。如此研究,可能會導致越精細而距離劉勰越遠的尷尬局面。從專業研究的層面講,所謂國際化、世界化的提法都是與此學術轉型背道而馳的。《文心雕龍》首先要解決的乃是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的問題,這一點不解決,《文心雕龍》研究不可能走出誤區。第三,新的學術增長點的提出必須具有實際可操作性。對于那些無法實現或者過于高遠的希望,最好不要在學術增長點里提出來,因為這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比如要解決《文心雕龍》研究中以現代文學理論觀念比附劉勰文章觀的問題,僅僅倡導回歸中國本體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更要提出回歸的具體方法與路徑。筆者曾經在《文體意識、創作經驗與文心雕龍研究》(《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對于像“神思”這一類談創作構思的理論范疇,最好能夠結合中國古代相關的文體和劉勰本人的創作經驗進行討論,方可能揭示其真實的內涵。筆者認為這是研究《文心雕龍》的基本路徑,因為劉勰的理論觀點是以其自我的創作經驗和熟悉的文章體裁作為思考對象的,離開這些而妄加比附就會流于不著邊際。如果用以上這些原則來衡量目前的學術史研究,可能大多數成果還不夠盡如人意。當然,學術史研究是很復雜的學術領域,所以很難要求每位從事該領域的研究者對其所有研究對象均具備實際的研究經驗。如果對個別問題不能準確地提出新的學術增長點,也可以作出一般瞻望性的預測,而絕不要勉為其難,以免拿捏不準而誤導了后人。
提煉“宗旨”、檢討缺陷與學術預測,這是互為關聯的三個基本層面。盡管由于學術史寫作的目的、規模與專業不同,或許會在三者的比例上多少有所出入,但如果缺乏任何一個層面,都不能稱得上是嚴肅的學術史研究,或者說就會成為對于推動學術發展起不到應有作用的研究。
四、學術史研究者的基本資質:學術素養與研究經驗
目前學界關于學術史的研究存在著兩種流行的誤解。一是認為學術史研究的價值低于專業問題的研究,二是認為學術史研究相對比較容易。而且二者互為因果,造成了許多混亂。比如博士論文的選題,近年來許多人都選擇了研究史、接受史及影響史方面的題目,其中原因固然復雜,但重要原因之一乃是認為學術史研究較之本體研究相對容易一些。就目前所呈現的成果而言,學術史類的博士學位論文的確顯得較為淺顯易做,很多人也以此取得了學位。但筆者認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依然不宜選研究史方面的題目,原因便是其選題動機是建立在以上兩點誤解之上的。討論學術史研究與專題研究價值的高低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不同性質的研究所體現的價值是完全無法放在同一層面比較高下的。專題研究從解決某領域的學術問題上是學術史研究無法相比的,而學術史研究對于學科的自覺、觀念方法的總結與初學者的入門等方面,又是專題研究所無法做到的。從這一角度說,兩類選題的難易程度也難以一概而論,專題研究需要的是研究深度,而學術史研究需要的是綜合系統。因此,筆者一直認為博士論文選題不宜選擇學術史方面的題目,原因就是博士生最重要的目標乃是對專業研究能力的培養,這種培養當然也離不開學術史的清理工作,但其主要精力要放在文獻解讀、問題發現、論題設計與系統論證上。而且博士生屬于剛入學術門徑階段,他們無論其專業修養還是學術眼界,都還缺乏駕馭全局的能力,使其無法寫出真正合格的學術史論著。筆者想借此說明的是,學術史研究并不是什么人和什么學術階段都可以隨便涉足的,它需要具備應有的基本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學術素養與研究經驗兩個方面。
先說學術素養。所謂學術素養簡單地說就是學養,也就是長期的學術積累所形成的專業知識,認識能力,學術視野以及學術判斷力等等。因為在從事學術史研究時,研究者必須要面對兩類強勁的對手,一類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一類是學術實力雄厚的學界前輩或同仁。學術史研究者必須要具備與之接近的學養,才有資格與之進行學術對話并加以評說。所謂學術研究的對象,就是指歷史上那些杰出的思想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批評家等等,他們無論是思想的深邃性、知識的豐富性乃至感覺的敏銳性上大都是一流的人物。如果學術研究者要判斷其他學者對這些人物的研究評說是否合適到位,首先自身必須對這些歷史人物有基本的理解與認識,否則便只能人云亦云。比如說《文心雕龍》一書,歷來被稱為體大思精的中國古代文論名著,研究這部著作的論文已有近萬篇,論著數百部,其中存在許多爭論的問題。如果要作《文心雕龍》的學術史研究,需要什么樣的學養呢?這就要看作者劉勰擁有何種學養才能寫出《文心雕龍》,我們又需要何種學養才能閱讀和認識《文心雕龍》。羅宗強曾寫過一篇《從文心雕龍看劉勰的知識積累》的文章,專門探討劉勰讀過什么書,構成了什么樣的學養。文章認為,劉勰幾乎讀遍了他之前和同時的所有經、史、子、集的著作,并能夠融會貫通,從而形成了自己豐富的思想體系與敏銳的審美感受力,所以能夠對前人的著作理解準確、評價精當。其中舉了關于劉勰“折中”思想的例子,學界對此曾展開過學術爭議,先后發表了周勛初《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說述評》(《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張少康《擘肌分理,惟務折中——論劉勰〈文心雕龍〉的研究方法》(《學術月刊》1986年第2期),陶禮天《試論〈文心雕龍〉“折中”精神的主要體現》(《鎮江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高華平《也談“惟務折中”——劉勰〈文心雕龍〉的研究方法新論》(《齊魯學刊》2003年第1期)等論文,或言崇儒,或言重道,或言近佛,各執己見,難以歸一。羅宗強在詳細考察了劉勰的知識涉獵與思想構成后說:“我以為周先生的分析抓住了劉勰思想的核心。我是同意的。同時,我也注意到其他學者的分析在結論之外,實際上接觸到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復雜現象。諸種思想在劉勰知識積累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交融形成了他自己的見解。正因為此一種交融,才為學術界對《文心》的許多理論觀點做出不同的解讀提供了可能。”*羅宗強:《晚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頁。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史修養,是無法對學界的不同觀點作出這種圓融的評判的。中國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大家,像杜甫、蘇軾,以及《紅樓夢》等等,都不是可以輕易對其擁有發言權的。既然對研究對象沒有發言權,那又有何權力對研究他們的學者說三道四呢!

學養是任何一個專業研究領域都需要具備的,作為學術史研究的學者,需要更為寬廣的知識背景與學術視野,因為他會面對更多的一流研究對象與一流學者,如果不具備相應的學養,就會缺乏與之進行平等交流的資格,更不要說去評價他們。沒有一流的學養,就不會是一流的學術史研究者。也正是在這一角度,筆者認為剛進入學術門徑的年輕學者不宜單獨進行學術史的研究。
再說研究經驗。所謂的研究經驗,是指凡是要從事某個學術領域學術史研究的學者,應該對該領域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研究體驗及成果,尤其是對本領域的學術理念與學術進展有較為深切的把握與體會。研究經驗與學術素養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學術素養是學術史研究的基礎,主要體現為對于研究對象的理解能力與概括能力。研究經驗則是對某研究領域的熟悉程度與參與過程,主要體現為對于本領域學術重點與研究難度的深刻認識,尤其是對于其學理性與前沿問題的把握。之所以要求學術史研究者擁有一定的研究經驗,是由下面兩個主要原因所決定的。
第一,只有擁有研究經驗,才能具有提煉“宗旨”與學術評估的資格,將該領域中有創造性的成果與觀點選擇出來并作出恰當評價。比如唐代文學的研究,已經具有悠久的歷史與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依然會有大量的成果不斷涌現。目前學術界最大的問題,也是學術史研究的最大難度,乃是對于重復平庸研究成果的淘汰,以及對于有創造性成果的推薦。這些工作都不是僅靠一般的材料是否可靠與文字論證水平的高低可以輕易識別的,而必須對該領域具有長期的沉潛研究的經驗,才能沙里淘金般地識別出那些有貢獻的優秀成果。這就是黃宗羲所說的明宗旨的環節,有無宗旨可以靠學養去提煉概括,而宗旨之有無獨創性則要靠所擁有的學術前沿領域的研究經驗來加以辨認。關于此一點,可以從目前學界名人寫序這種現象中得到說明。現在的學術著作序言近于學術評價,可以視為是該書最早的學術史研究成果。但遺憾的是,真正評價恰當者卻寥寥無幾,溢美之詞倒是比比皆是。更嚴重的是,在以后的學術史研究中,許多缺乏研究經驗者又會以這些“學術大佬”的評價為依據,去為這些著作進行學術定位,從而造成積重難返的學術虛假評價。為什么會造成此種“諛序”的現象?其中除了人情因素之外,筆者認為作序者缺乏該領域的研究經驗乃是主因。當年李贄曾諷刺其論爭對手耿定向是“學問隨著官位長”,現在則是學問隨著職稱長或曰學問隨著年齡長,以為成了博導和大佬就什么都懂,于是就到處寫序。殊不知術業有專攻,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域,離開自己熟悉的專業領域而去評價其他學術著作,自然不能真正認識該書的學術創獲。但“學術大佬”畢竟是有學養的,可以駕輕就熟地說一些雖不準確但又不大離譜的門面話,于是似是而非的序言也便就此誕生。缺乏研究經驗的學術史研究就像名人作序一樣,看似頭頭是道,實則言不及義。
第二,只有擁有研究經驗,才能真正了解該領域的學術難點,并提出新的學術研究方向。按照上節所言的學術史研究的總結經驗、尋找缺陷與提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三個層面,缺乏研究經驗的學者在提煉“宗旨”的層面或許可以勉為其難地進行操作,但一旦進入第二、三層面,就會陷入茫然無知的境地。比如關于明代詩歌史的研究,明清兩代學者始終處于如何復古的討論之中,而進入現代學術史之后,依然在沿襲明清詩評家的傳統思路,圍繞復古與反復古的論題展開論述。豈不知明詩研究的最大問題是,幾乎所有人都在按照一個凝固的標準也就是唐代詩歌的標準來衡量明詩創作,而忽視了自晚唐以來產生的性靈詩學實踐與理論,明清詩論家視性靈詩為野狐禪,而現代研究人員也深受《四庫全書提要》以來傳統觀念的影響,只把性靈詩學觀念作為反復古的一端加以肯定,而對其建設性的一面卻多有忽視。其實,從中國詩歌發展的全過程以及與現代詩歌的關聯性看,性靈詩學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正面價值,是以后應該大力加強研究的學術空間。筆者認為,只有真正從事過明代詩歌研究的人,才會具有這樣的體驗,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才能開辟出新的學術研究空間。其實,豈止明詩研究如此,看一看目前的幾部詩歌研究史,幾乎都將敘述的重點集中在漢魏唐宋,而到了元明清多是略而論之,草草了事。我們不能說這些作者缺乏學養,而是缺乏元明清詩歌史的研究經驗。因為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這些領域從事專業的研究,所以無論是在對該時期詩歌史的價值判斷,還是研究難度,都不甚了了,當然會作出大而化之的處理。因此,在筆者看來,要成為合格的學術史研究者,既要有足夠的學養,又要有足夠的研究經驗,而且經驗比學養更重要。
在目前的學術史研究中,情況相當復雜。從作者身份看,既有著名學者領銜的大型學術史寫作,也有專題研究者在科研項目、學位論文研究中的學術史梳理,更有一些初學者無知者無畏的試筆之作;從成果形式看,既有多卷本的大型叢書,也有各領域的專門學術史論著,更有形形色色的綜述、述略及史論的論文。這些研究除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復之作外,應該說對于各領域的學術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但是,在筆者看來,我們真正需要的學術史是:研究者需要具有明確的學術原則與研究目的,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應對各領域的學術研究的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學術貢獻及發展過程作出客觀清晰的描述,對學術研究中存在的方向偏差、理論缺陷、不良學風及學術盲點進行清楚的揭示,對將來的學術研究中可能解決的問題、采用的方法及拓展的新空間進行符合學理的預測,從而可以將后來的研究提升至一個新的層面。而要實現這樣一種目標,學術史的研究者就必須擁有足夠的學術素養與豐富的研究經驗。
[責任編輯劉培]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詩歌研究史”(05JJD750.114401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左東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中心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