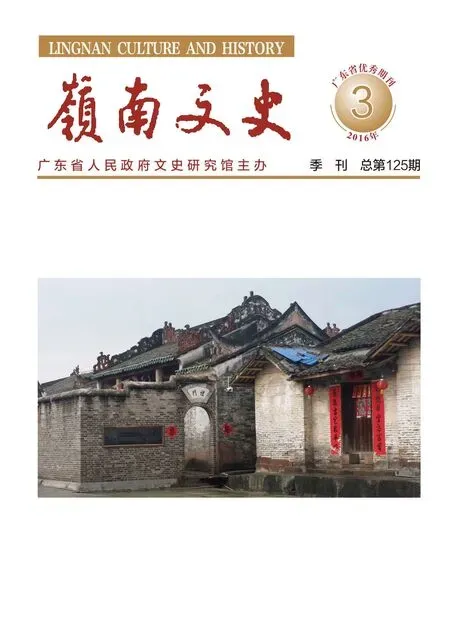“廣府”與“廣州”關系辨析
金峰
“廣府”與“廣州”關系辨析
金峰
20世紀30年代,羅香林提出廣東“三大民系”及“廣府人”的概念。因潮汕和客家人在語言、價值觀念及行為習俗等方面的文化特征十分顯著,形成了自我認同感十分強烈的亞文化圈,加以“潮汕人”、“客家人”等概念范疇十分明晰,“潮學”、“客家學”研究得以在有明確研究對象的基礎上順利展開。但“廣府學”研究則遲至90年代才有重要成果出現,且“廣府人”、“廣府文化”等基本概念仍是歧義紛呈,“廣府學”研究面臨著研究對象缺乏嚴謹和普遍接受的定義,以及被界定為“廣府人”的族群缺乏自我認同等問題。本文擬從有關“廣府人”概念的界定入手,探討廣府與廣府人、廣府文化以及廣州之間的關系。
一、“廣府”界說
有論者指出在定義“廣府人”時,面臨著粵語與白話、廣府與廣州之間關系難以厘清,以及廣府人概念多在通俗層面使用,但缺乏學術性細致界定等問題。理論上“廣府”系指“廣府人”生存活動的地理空間,“廣府人”系指一個特定族群,而“廣府文化”則是指一種亞文化圈,分別涉及地方學、民族學和文化學三個不同領域。有關“廣府人”概念分歧的產生,實因上述三領域的“廣府”未能和諧融通所致。
1.“廣府”概念分歧
首先,關于“廣府”的概念范疇,研究者往往根據需要各自界定。大多數研究者將“廣府人”定義為生活在嶺南地區、使用粵語的漢民族的一個民系。但因粵語在嶺南地區分布極為廣泛,[1]理論上被認為系屬廣府人的族群人口眾多、分布零散,既超出廣府行政區劃范圍,又存在地域文化差異性,使“廣府人”概念能否包容如此大范圍族群成為問題。因此陳澤泓即主張以明代廣州府政區作為“廣府”界限,甘于恩也將廣府文化定義為“以廣州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為通行范圍的粵語文化”。[2]由此造成“廣府”概念出現了廣義和狹義兩個范疇,廣義的“廣府”系粵語覆蓋區,狹義的“廣府”則是指明清廣州府轄境,即以廣州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為主體的地理空間。
第二個是“廣府”古今名實的混淆。地理上的“廣府”秦稱“番禺”,三國時的孫吳黃武五年(226)始有“廣州”之名。唐武德四年(621)設軍事鎮撫機構“廣州總管府”(后改稱“廣州都督府”),唐人漸有“廣府”稱謂。10世紀時來華阿拉伯人也稱廣州為“廣府”(khānfū),[3]說明唐稱“廣府”已極為常見。明清時置“廣州府”,“廣府人”的說法更是普遍流行。然須指出,古稱“廣府”或“廣府人”,系政區概念或系代稱此政區轄下居民,而羅香林襲用“廣府”之名,但此“廣府”已系文化地理概念,即被賦予文化學和民族學的內涵。即是說,古今“廣府”名同實異,但頗有論者對之未能明辨而常有混淆。
第三是早被研究者所指出的“廣府人”自我認同感的缺乏,[4]亦即在沒有客觀主體自我認同的情況下,如何界定“廣府人”的問題。
2.“廣府”界說
筆者支持采用粵語覆蓋區界定“廣府”的主張,原因如下:
其一,“粵語”及其他“文化核”的形成。盡管“廣州話”具有特殊性且與其他片區粵語交流中時有障礙,但并不影響粵語作為更高層級方言的存在,各片區粵語雖有語音差異,但在語法、句法和詞匯等方面的共性更加明顯。更重要的是,由于語言在人類認知構建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操同一語言的族群能夠形成相近的文化心理,使粵語人群在以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以及強烈的宗族和宗法觀念、依托于水路交通的宗族聚居的村落形態、濃烈的民俗信仰等方面,都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正如客家人的活動空間雖小于廣府人,但其范圍更為廣大,客家文化也存在諸多地方特色但共性特質并未削弱。由于粵語的紐帶作用,粵語使用者的核心文化要素具有諸多共性,使得超出珠三角范圍的粵語人群理應被納入廣府民系。
其二,基于基因技術的人類學考察。徐杰舜等指出,廣府民系的父系血統漢族略超50%、母系越族超過80%。[5]此一比例顯然與中原移民南遷史相符。而生物學基因技術也反映出嶺南地區的廣府人作為漢民族的一個亞群,在群體遺傳學方面具有諸多共同特征,并且與潮汕人、客家人之間出現了符合歷史學、文化學一般認知的遺傳距離。[6]也就是說,“廣府人”作為一個民系,其民族特質和生物學共性業已形成,這不僅是歷史文化傳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生物遺傳的結果。
其三,關于認同感問題。有論者指出:“某一民系的誕生傳說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該民系產生之際的背景及誕生的意義”。[7]“珠璣巷傳說”無疑應當被視作“廣府人”自我身份認同的開端。盡管這種認同不是對于文化共性,而是對于血統來源——“中原漢族”的認同。亦即廣府人在自我意識產生之初,主要是關乎“來自中原”和“僑居于此”的共同信念。鴉片戰爭后,近代民族意識推動產生的地方意識,也使“我粵人”的地方認同取代了文化認同,而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廣東社會經濟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同樣更有助于強化 “粵人”意識而非“廣府人”認同。還須指出,相對于潮汕人和客家人,廣府人因遷徙至嶺南地區較早,生存空間的自然地理條件優于后來者,具有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等各方面優勢,因而明顯自居于強勢或主體的地位,也非常有利于“廣東人”或“東莞人”意識的產生,即其心理體驗已由最初的“外來客人”轉而變成“本地主人”。也就是說,“廣府人”作為獨立群體的自我認同在“珠璣巷傳說”以后即已產生,只是始終未能自認為是“廣府人”而已。但缺乏自我意識并不代表廣府人客觀上不存在。如元代新會人與廣府人合作生意的故事,即反映出周邊的“他者”已有明確的“廣府人”意識。民國時南番順及中山被稱為“上四府”,稍遠的臺山、開平、恩平、新會被稱為“下四府”的習慣稱呼,也是“廣府人”自我認同的潛意識表現。因此,缺乏自我認同并不能否認“廣府人”存在的事實,以及現代意義上“廣府”概念的確立和傳播。
二、“廣府”與“廣州”
府、州均系中國古代地方一級行政區劃,在不同時期品級和轄區范圍大小不一。漢代以后多行三級制,府州系省、縣中間一級政區。狹義的“廣府”,秦以南海郡下轄番禺縣治其地,漢代南海郡轄區縮小而上以交州刺史部統領,三國時東吳將“海東四郡”(南海、蒼梧、郁林、高涼)并為“廣州”,此后唐宋均有“廣州”政區,元有“廣州路”,明清有“廣州府”。作為行政區劃,“廣府”大體同于“廣州”。
然而“廣府”的復雜性在于,歷史時期其轄區始終是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所在,古稱“番禺”、“南海”的縣即今廣州市區也往往是嶺南省級機構治地,與一般“府縣”大有不同,即不因行政上不能涵蓋廣義的“廣府”而將之判然兩別。此外,今稱“廣州市”的政區范圍也與古“廣府”有較大變化。因此“廣府”與“廣州”需要辨析者,一在“廣府”能否代稱粵語區,二在舊“廣府”與新“廣州”之間的關系。
1.嶺南地域空間
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廣府”,都處在地域范圍更大且較為獨立“嶺南”地區之中。盡管廣府人并未占據整個嶺南,但其繁衍生存以此特定空間范圍為基礎,史料文獻也無法將“廣府”從“嶺南”中剝離而加獨立討論。也就是說,整個嶺南地區為廣府人和廣府文化的生成、發展及特質的形成,提供了相對獨立、統一、共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其主要影響表現在:(1)因南嶺阻隔,嶺南地區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空間;(2)珠江河谷特別是三角洲優越的水、土、熱條件,是廣府稻作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基礎;(3)珠江水系為廣府先民的內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4)嶺南別有特產且面朝大海,廣州更有開展外貿的區位優勢,使廣府文化別具海洋商貿文化特色。
2.“廣府”核心地區的多維發展演變
明清時期的“廣州府”所轄州縣的地理范圍,主要包括今廣州、東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江門等市所轄各區縣,清遠市轄各區及清新縣、惠州市轄龍門縣和港澳地區,即大珠三角地區,總面積約3.5萬平方公里。[8]值得注意的是,廣府政區地理沿革與嶺南自然地理變遷和社會經濟開發,是一個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相輔相成的發展過程。
自然地理上的珠三角,以西江的三榕峽、北江的飛來峽和東江的田螺峽為各江三角洲的頂點,歷史上海潮曾到達上述地點,這是珠江成陸作用的起點。從新石器時代人類遺址的分布情況,可大致判斷出約6000年前珠三角海岸線,是從羅浮山南端西南至佛山、西樵山一線。[9]出土陶片證明漢代海岸線已推進至番禺、順德一線,并維持至唐代。宋元以后因海平面降低及珠江堆積,海岸線不斷向東南推進。唐宋時珠江中游的河谷地帶基本成陸,宋以后主要在下游發展沖積平原。明清廣州府的陸界與珠三角大致吻合,潛在的自然地理原因是當時珠江下游的成陸過程已基本完成,此后三角洲主要在海岸線發展。
與自然地理變遷相同,嶺南社會經濟開發也以唐宋為分野。宋代珠三角沖積平原大面積形成,同時開始大量修筑捍海及沿江堤壩,[10]不僅有利于防洪、灌溉,更使大量肥沃的湖沼和濱江低地變成易耕高產的“圩田”,加上掌握先進技術的北方移民大批南遷,以及統治者對嶺南著力經營,更兼宋元時中國水稻種植技術趨于成熟,從選種、育秧到大田管理等精耕細作技術都基本成型,[11]并在嶺南大面積推廣,[12]使得宋以后嶺南社會經濟已從相對落后一躍而為較為發達。
嶺南政區沿革與自然和經濟地理的階段性特征相一致,以唐宋為界,前此開發不足而統治者重在軍事撫馭,后此則重在開發。其政區設置在此前系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拓展,[13]此后則以珠三角為核心向周邊輻射。特別是在明清時期,新增縣多系從舊縣析出而非辟地新置,且所置縣逐漸沿珠江向上游擴展。[14]
綜上可知,“廣府”政區是在自然地理和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地域范圍在自然地理上系位于嶺南地區精華地帶的珠江三角洲,在語言地理上大致相當于粵語廣府片區,從文化學上可以視作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三者邊界高度重疊,亦即是廣府民系和廣府文化孳息生長的核心地區。
3.“廣府”的特殊地位
其一,在廣義廣府乃至在整個嶺南地區,狹義“廣府”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是最為先進發達,地位也最為重要。珠三角廣府文化對周邊具有強烈的向心吸引和輻射作用,如粵語廣府片與其他片區及粵語周邊方言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隨距離遠近而相似度、滲透程度不同的關系。[15]而在遠離廣州但與廣州間交通便捷且農耕條件優越的嶺南地區,星散出現使用廣府粵語的亞文化區,并以之為亞中心向周邊輻射,[16]充分說明廣府片粵語在整個粵語區的核心地位,也從側面證明了廣府人和廣府文化是在以廣州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孕育和成長起來,并以此為中心向周邊地區拓展。
其二,“廣府”特別是廣州在嶺南交通地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歷代中原政治中心通往嶺南的交通,越南嶺后往往以珠三角亦即廣州為目的地,復以廣州為核心輻射周邊。如秦所鑿通越“新道”均系溯湘江或贛江支流而上,越五嶺后復順北江支流而下者。[17]漢代越萌渚嶺和都龐嶺間谷地、溝通瀟水和賀江的“瀟賀古道”地位上升,[18]漢統轄嶺南的交阯刺史部治設在廣信,系因其居至廣州干道之上。唐代大力疏通嶺南與周邊的交通,其東北向福建、西經廣西至云南,以及南向粵西、海南島等地的陸上通道均加經營。但上述地方均遠離政治中心且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其與嶺南核心地帶聯系的重要性及交通條件均遠遜北路。[19]開元四年(716),較為平易的大庾嶺梅關道經張九拓修后,成為南北往來的咽喉要道,此后歷代王朝均將之定為中原通嶺南的官道干線并沿途置驛,且不斷加以修繕。[20]
嶺南內部的交通也以廣州為核心,但與北向中原的水陸兼施不同,嶺南內部交通對珠江水系十分依賴,特別是唐以后,隨著造船和航運技術的突飛猛進,珠江河運快速發展。[21]元代以廣州為樞紐、通往珠江流域各地的水運網絡趨于成型;[22]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珠江水系交通更顯繁密,不斷有大規模河道整治,[23]津渡和水陸驛站設置更加密集,沿河廣府村落也大量出現。[24]兩廣各府縣間鋪驛、站線的設置不僅充分利用水道,珠江干支流所到之處的陸上驛道也基本沿江而修,[25]水路驛運極為發達便捷。[26]
其三,嶺南地區的交通地理格局,對于中原文化傳播和廣府文化的擴散,特別是廣府民系的地理空間分布,發揮著重要影響。漢以前湘江聯西江一路最為重要,嶺南文化即以廣信最為發達。唐以后大庾嶺路地位上升,粵北的曲江等縣即成文教興盛之區。宋代廣府民系開始成型,三大民系的地域分野也漸有雛形。如有論者指出,“宋代廣東……三大方言區已經形成,它們的分布區域與這時政區界線部分重合,其中粵語和客家語分界線北段和南段與宋代政區界線完全一致,……客家語和閩南語的分界線……跟梅州和潮州的政區分界線相吻合,不吻合部分界線則是后來移民的結果”。[27]三大民系地理分布表現上看是行政區劃的規定,但實際隱含著自然地理因素的潛在作用。明清時珠江水系的交能孔道作用、沿珠江而設的水陸鋪驛網絡與廣府族群地理分布的高度契合,與珠江水系稻作宜耕地帶、粵語方言區,以及行政區劃的廣府地區的邊界重疊,有著相互關聯的內在成因。
4.廣州的特殊地位
廣州府城,即今廣州中心市區或古代廣東乃至嶺南的省治所在,因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成為汲取嶺南大地及南海精華的一顆璀璨明珠,是當之無愧的嶺南首府。
廣州背山面海,處海陸交會之所。珠三角繁榮的農業經濟及便利的內外交通,為其開展內外貿易提供了重要條件。如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滅南越國,焚番禺城,但僅僅20年后的《史記》中即指出番禺已復為漢19個最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漢書》、《后漢書》均稱廣州物產豐富、貿易興盛。三種史料在檢討嶺南商業都會時均盛贊廣州而不及廣信。漢以后廣州自然地發展成為嶺南內外貿易的重鎮,并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始終是中外貿易最為重要的口岸。此外,除兩漢三百年間統治者有意貶抑而將政治重心北移外,其他時候廣州始終是嶺南政治中心,如秦任囂即稱其“可以立國”。[28]行政中心的角色也不斷地強化了廣州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
三、結論
其一,“廣府”、“廣府人”和“廣府文化”所代表的學術領域不同,其內在一致性系以在共同地理空間的基礎上形成,即粵語與廣府族群的分布在自然地理方面依賴于珠江水系交通和適宜精耕稻作等條件,并在基礎上形成廣府文化的分布區。
其二,“廣府”名詞所涵蓋的地域范圍小于廣府地區,但因其在廣府地區所處核心地位及在廣府文化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以“廣府”代稱以粵語來界定的廣府文化區是最為恰當的選擇。
其三,今所稱“廣州”地理空間大于古稱“番禺”或“南海”的縣級行政轄區,但又小于古稱“廣府”。從地方學角度而言,“廣州學”涵蓋了地方歷史、文化領域,其地理范圍應以明清“廣州府”范圍為主,但在實際研究工作中,超出此空間而以“嶺南地區”為范圍勢不可免。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B13—B14頁。
[2]甘于恩等:《20世紀90年代廣府文化研究概述》,《學術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5頁
[3](法)費瑯輯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14頁。
[4]陳澤泓:《廣府文化》,邱捷序,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5]徐杰舜:《嶺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0頁。
[6]李曉昀等:《潮汕人與廣府、客家人母系遺傳背景差異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0第6期,第664—668頁;王琳凱:《基于15個STR基因座的廣府、客家、潮汕族群遺傳多態性研究和罕見嵌合體案例報道》,暨南大學2014碩士學位論文,第25頁。
[7]片山剛著,朱海濱譯:《“廣東人誕生之謎”——從傳說和史實之間來考察》,《歷史地理》2006第21輯,第417頁。
[8]、[9]曾昭璇、曾憲紅:《珠江三角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頁。
[10]、[21]郎國華:《宋代廣東經濟發展研究》,暨南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41—44、41—51頁。
[11]陳偉明:《宋元水稻栽培技術的發展與定型》,《中國農史》1988年第3期,第31—35頁。
[12]謝敏、李春華:《論北宋嶺南謫宦對嶺南農業的影響》,《農業考古》2007年第6期,第16—18頁。
[13]許桂靈、司徒尚紀:《泛珠三角經濟區政區建置沿革的空間關系演變透視》,《熱帶地理》2005第2期,第101頁。
[14]王榮、吳宏岐:《.明清廣州府土地開發特征研究》,《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7期,第145頁。
[15]熊正輝:《廣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7第3期,第161—162頁;龍慶榮:《漢越語與粵語和平話語音對應關系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第130—132頁。
[16]粟春兵、王文勝:《梧州粵語和周邊勾漏粵語詞匯相似度的計量分析》,《梧州學院學報》2011第5期,第7—13頁。
[17]余天熾:《秦通南越“新道”考》,《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第104—108頁;王元林:《秦漢時期南嶺交通的開發與南北交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4期,第46—47頁。
[18]韋浩明:《秦漢時期的“瀟賀古道”》,《廣西梧州師范學校學報》2005年第1期,第86—89頁。
[19]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學術研究》1987年第1期,第53—58頁。
[20]詹瑞祥:《韶關古道沿革考》,《九江師專學報》1988第1期,第95—99頁。
[22]司徒尚紀:《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的歷史變遷》,《熱帶地理》1991年第6期,第114頁。
[23]蔣祖緣:《明代廣東水陸交通建設及對商貿發展的作用》,《廣東史志》2001年第3期,第3—6頁。
[24]朱光文:《明清廣府古村落文化景觀初探》,《嶺南文史》2001年第3期,第15—19頁;馮志豐:《基于文化地理學的廣州地區傳統村落與民居研究》,華南理工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1頁。
[25]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頁。
[26]葉顯恩《廣東航運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頁。
[27]司徒尚紀《廣東地名的歷史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期,第23頁。
[28](漢)司馬遷:《史記》卷113《南越列傳》。
注釋:
[1]陳澤泓即認為社會活動對“廣府人”作出了各種詮釋,但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什么是廣府人,“真的是個令人糾結的問題”。參看陳澤泓:《糾結的“廣府人”》,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第1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3頁。
[2]以粵語方言界定廣府民系的研究者包括李權時、司徒尚紀、徐杰舜、王杰等人(參看李權時:《嶺南文化·修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頁;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344頁;徐杰舜、李輝:《嶺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460頁;王杰:《廣府文化概念不斷延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27日。
[3]陳澤泓:《廣府文化》,敘言,第7—8頁。當然,此后陳澤泓可能意識到這樣就無法明確指稱“廣州府”以外的族群,因此他又修正上述見解,提出兼用使用粵語方言且有心理認同感,以及歷史上的廣州府地域范圍兩種界定方法,但他仍指出兩種定義并不包容(參看陳澤泓:《糾結的“廣府人”》,第33頁)。
[4]沃爾夫的語言相對性假說主張,“我們所能具備的各種概念和知覺都受我們所說的語言的影響”(見[美]R.L.Atkinson等著,車文博審訂,孫名之等譯:《心理學導論》上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頁),認為話語通過理論、概念等,直接影響認知的方式和水平。喬納森等還指出:“話語與行為、主體、社會過程……都是不可分割的。……話語實際有著種種行動取向時,話語的生產者就不僅僅是‘主體’(subjects),而且是‘行動者’(agents)。”(見[英]喬納森·波特、瑪格麗特·韋斯雷爾著,肖文明等譯《話語和社會心理學——超越態度與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即認為語言不僅構建成認知,而且會指導行動。由于語言對認知及文化構建提供了基本建材并直接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其面貌,因此斯大林在定義“民族”的概念時即將語言列為四項基本條件之一。
[5]此傳說稱:“(梁之攀)壯歲服賈黔省,往來歲以為常。某年,之攀由粵赴黔,在樂昌舟中,與廣府人共一艙,詢其姓名為陳亮。”見同治《新會縣續志》卷6《列傳·人物》。
[6]其中明代廣州府地域較大,北及今清遠市除英德外的陽山、連州、連山各市縣。參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年版,元明時期第30—31頁、清時期第44—45頁。
[7]如宋祝穆引《海嶠志》稱:“中宿峽(即飛來峽)……二月、五月、八月,有潮上此峽,逐浪返五羊。”見[宋]祝穆撰,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06頁。
[8]如明代《一統路程圖記》即記京師至廣州的官道亦即兩地交通干道,至江西后系溯贛江而上至贛州、南安過大庾嶺一線。參看[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卷1,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刻本影印本,史166,第486—487頁。
(作者單位:廣州大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