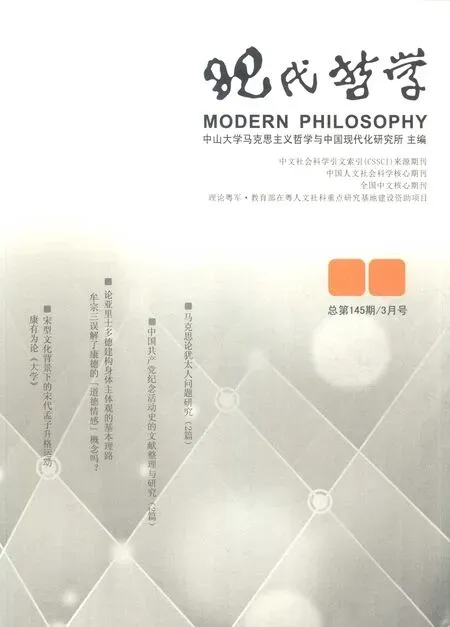現象學心理學與經驗的世界*
游淙祺
?
現象學心理學與經驗的世界*
游淙祺
【摘要】本文闡釋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在胡塞爾現象學中不明確的定位,說明它如何銜接超越論現象學和經驗科學,并特別凸顯經驗的世界這個概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論文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探究現象學心理學和超越論現象學之間的關系,說明“現象學心理學如何是超越論現象學的預備”,以及“現象學心理學如何平行于超越論現象學”這兩個問題;第二部分闡述胡塞爾如何藉由經驗的世界此概念來為事實科學奠定基礎。
【關鍵詞】胡塞爾;現象學心理學;超越論現象學;經驗的世界;自然態度
前言
現象學心理學(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在胡塞爾的整體現象學中定位是曖昧不明的。它被呈現為現象學,但卻立基于自然的態度。它與超越論現象學有所不同,但卻接近超越論現象學(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它連接著經驗科學,因為它與經驗科學分享自然態度的共同基礎,但作為本質科學它也有別于經驗研究。從不同的角度看,它既不是超越觀想的,也不是經驗的,但分別連接了超越論現象學和經驗研究。由于帶著這種混亂的特質,現象學心理學通常被忽視。另一方面,來自經驗心理學的陣營似乎有更多的學者比哲學家對現象學心理學更感興趣。然而,專業的心理學家更多把現象學心理學看成他們的質性研究的一種方法論,而非胡塞爾所理解的那般。(Davidson, 1988; Ashworth, 2003; Davidson/Cosgrove, 2003; Finlay, 2008)就其介于超越論現象學和經驗研究之間的現象學心理學的曖昧狀態而言,胡塞爾把現象學心理學更看作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基礎,而不僅僅是經驗心理學的方法論而已。在此脈絡下,經驗的世界這個概念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本文中,我的目標是藉著經驗世界(Erfahrungswelt)的概念來幫助闡述胡塞爾如何制定出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為此,我的論文將分成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現象學心理學的基本特性,探究現象學心理學和超越論現象學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闡述“現象學心理學如何是超越論現象學的預備”,以及“現象學心理學如何平行于超越論現象學”這兩個問題。然后,我將在第二部分闡述胡塞爾的經驗世界概念,以便探討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如何藉著經驗世界的概念來為事實科學奠定基礎。
一、現象學心理學和超越論現象學
胡塞爾在處理現象學心理學的文本中區分了兩種意義的現象學。早在1925年夏季學期現象學心理學講座的一段話中,他已經提到這樣的區分(Hua IX: 188/ Scanlon, 144),但直到阿姆斯特丹講座(1929)中,他才公開地帶出這樣的區分,甚至以如下方式介紹他的現象學:
在其發展的進一步過程中,它[現象學]向我們提出了它的雙重意義:一方面,作為心理學現象學,它是作為基本科學,是心理學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作為超越論現象學,就其與哲學的連接中而言,有第一哲學的巨大作用;這是說,作為哲學的科學,哲學從源頭涌出。(Hua IX, 303/Sheehan eds., 214)
很顯然,對胡塞爾而言,現象學與哲學并非完全等同。哲學可以看作僅是他的整個現象學計劃的一部分。相對于哲學家集中在自我反思(Selbstbesinnung),探究意義、有效性和各種存在者的構造之起源,現象學心理學家關注那些深入參與世界的人之心理過程,對之進行本質描述。在胡塞爾眼中,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關注是不同的,然而非常明顯地,他們卻共享現象學,這是耐人尋味的一個情況。
我們都知道,胡塞爾以其超越論現象學而聞名,在超越論現象學中他為哲學奠定最終基礎。這樣一來,他的目標是提供方法給哲學以克服所有種類的反論——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存有學主義與超驗主義、實證主義對形上學等等。(Hua IX, 300/McCormick eds., 34)在胡塞爾的觀念中,具有完整形式的現象學無非是普遍的哲學,而這是一個源自于根本的自我反思所導致的嚴謹科學。只有超越論現象學是合法地滿足這一要求。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塞爾把“最終和最高的”的問題看成是現象學的問題。所以,他解釋說:
在其普遍的連接回到自己中,現象學在人類的可能生活當中認識其在超越觀想層面的特定功能。(Hua IX, 299/McCormick eds., 33)
我們對于胡塞爾的這一特征是再熟悉不過了,不過胡塞爾還有另一張面孔,披露他關注所有事實性科學的基礎,這并不亞于他對哲學終極基礎之關注。亦即,他講到一個經驗現象的理念,這是相同于“實證科學的完整系統化領域”。((Hua IX, 298/McCormick eds., 33)而這種現象學當然是方法論地建基于本質現象學。通過本質現象學的奠基,經驗現象學方能被確定,而胡塞爾認為事實性科學的基礎危機在這樣的方式下也才得以被克服。(Hua IX, 297/McCormick eds., 32)
胡塞爾交替使用心理學現象學或現象學心理學術語,而我自己更喜歡前者甚于后者,因為實證心理學家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現象學心理學是為了心理學作為一門特殊科學而有的質性方法論。但對于胡塞爾來說,非常清楚的是,現象學心理學比心理學包含更多的內涵,也就是說,它是關系到所有人文社會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或譯精神科學),甚至各種科學。胡塞爾指出,只要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涉及到精神層面的東西(das Geistige),它們都可以被看作是屬于心理學(Hua IX, 221/Scanlon, 169)。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被視為普全的精神科學(universale Wissenschaft vom Geistigen)。(Hua IX, 91/Scanlon, 68)
胡塞爾一方面定位心理學現象學或現象學心理學是作為超越論現象學的前導或預備;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前者是平行于后者的。由于超越論現象學對于平常人是極其陌生的,胡塞爾就把現象學心理學看成是有用的設置以提升到超越論現象學。藉著現象學心理學的幫助,人們得以一步一步地熟悉現象學,然后就準備好走向超越論現象學。(Hua IX, 296/McCormick eds., 31-32)最后一步需要“其學說內容的僅僅回轉”(Hua IX, 296/McCormick eds., 32),其中涉及態度的轉變。對此,胡塞爾解釋說:
相對于心理學家在他自己所自然接受的世界中運作,把發生在那里的主體性(但仍在世界內)化約成純心理的主體性,超越論現象學家通過他無所不包的懸擱,把這個心理學的純粹因素化約成超越觀想的純粹主體性。(Hua IX, 293/McCormick eds., 30)
具體來說,它涉及世界的統覺(Weltapperzeption)及其轉型。心理學家,無論是經驗的心理學家或現象學的心理學家,永遠不會停止他們對這種統覺的依賴,所以純心理的主體性也是如此。(Hua IX, 340-341/Sheehan eds. 246)世界的統覺不只是包括對象的統覺,還包括他們自己的統覺,藉由它,世間我(Mensch-Ich)乃被構成。這種自我是在世界中被客觀化。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哥白尼式轉向,以便達到超越觀想的層次。(Hua IX, 341/Sheehan eds. 248)超越觀想的純主體性在其自身內設定這種統覺的有效性。胡塞爾描繪這樣轉化過程的過程如下:
它們蛻變成我的超越觀想心理過程,如果通過一個根本的懸擱,我設定作為世界的單純現象,包括我自己的人存在,而現在跟進意向的生命過程,在其中整個世界“的”統覺,特別是我的腦海、我心理真正的感知過程的統覺等等就被形成了。(Hua IX, 293/McCormick eds., 30)
這些過程的內容被保存下來。也就是說,所有被包含在純心理主體性的心理過程被保留在超越觀想的純主體性;而所有這些內容則變成了“超越觀想的內心體驗”。因此,這種新型的超越觀想領域是平行于純心理領域。
胡塞爾主張沒有兩個分開的自我(即世間我和超越觀想我),但同樣的我在不同的態度中運作。就內容而言他們彼此平行,僅就態度而言,一個是世俗的,而另一個是超越觀想的。由于這種平行,“超越觀想自我體驗的領域……可以僅僅通過態度的改變而轉變為心理上的自我體驗”(Hua IX, 294/McCormick eds., 31)。
這意味著,反過來說,凡是在超越觀想領域的研究結果都有可能被應用到世俗的層次。而每當一個人是非常熟悉現象學心理學的還原做法時,也因此能知道心理的主體性,他可說是做好超越觀想還原的準備,去達到了解超越觀想的純主體性。如同胡塞爾所說的那般:
一旦這種心理學已經變成清楚,至少根據其清晰的思路,那么只有超越觀想哲學領域的問題和超越觀想還原的真正意義之說明是必需的,以便它進入超越論現象學的擁有,作為其學說內容納入超越觀想語詞的單純回轉。(Hua IX, 296/McCormick eds., 32)
在這里,我們察覺到胡塞爾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還原:現象學心理學的還原和超越觀想的還原。這種區分首次是在《第一哲學》(1923年至1924年)被介紹,但沒有取得清楚的定位,直到1927年在關于現象學心理學的文章,如《大英百科全書文章》、《阿姆斯特丹講座》(1929年),最后在《危機》(1936年)的第三部分才有明確闡釋。
一般來說,胡塞爾把現象學心理學放在經驗心理學和超越論現象學之間。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也將它定位成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心科學。此外,因其先驗性,它對人類現象的所有經驗研究也是普全科學。(Hua IX, 127, 128/Scanlon, 96, 97)這是非常接近超越論現象學的,但它卻仍然只是實證科學,因為它處于自然的態度。有鑒于此一學科的這些特性,人們可以看到它在超越論現象學和經驗研究之間扮演了橋梁的作用,但它也涉及表面上的矛盾。它是本質的科學,也是積極的科學。它實行懸擱而獲得進入心理主體的純粹性,但它也保留了世界的預設。如果我們看胡塞爾如何談論人類的雙重性——他是活在世界上的人,同時也是使得世界獲得有效性的超越觀想自我(Hua IX, 294/McCormick ed., 31 ; see also Hua VI, §53),那么心理學現象學可以被看成是在考慮到世界的狀態時最適切地反映出這種雙重性。胡塞爾一方面通過還原來排除世界的預設,另一方面他則堅持認為世界由于其連接到自然態度而從來沒有完全被排除,而自然態度顯然地是對立于超越觀想態度。
在胡塞爾的觀念里,心理學不應該只限于經驗心理學。心理學也可以被理解為針對心理現象的重要部分之研究,即意向性。在這個意義上,現象學心理學是一門先驗的、本質的、直觀的、并且是純粹性描述領域的研究。這種心理學是以存在于世界中的個人或社群的意識生活(Bewuβtseinsleben)為研究對象的。(Hua XXVII, 213-214; Hua IX, 335; Hua XV, 142)
為了使研究成為可能,現象學心理學家需要操作還原,使得他們可以成為“非參與的旁觀者”(unbeteiligte Zuschauer)(Hua IX, 313/Sheehan eds., 222)和意識到研究對象的意識生活。心理學家必須放棄他們在自然態度中所堅持的一切,并藉著制定出他們自己主體性的純粹性來準備研究的工作。(Hua IX, 312/Sheehan eds., 222)他們還需要排除對世界存在的信念,而所剩下的就是各種的意識,例如:知覺、記憶、判斷等(Hua IX, 282/McCormick, 24)。藉著所有這些做法,他們就不同于他們所研究的對象。還原要求凡與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無關的東西被括號起來。研究者僅專注在心理活動及其意識對象之間的相關性。
如前所言,心理學現象學針對在世界中的個人或社群進行研究。這些種類的主體深入地參與世界,以致于若沒有世界的相關部分,主體的心理現象可能是難以解釋的。在這個意義上,研究必須預設世界。而這導致關于世界狀態的矛盾,也就是說,一方面世界是通過還原的操作而被懸擱起來,另一方面它卻又為了研究的緣故而被保留下來,只要他們所研究的對象是深入參與世界的。這種矛盾在超越論現象學中被克服,因為整個世界已經變成現象。因此,與哲學家相比較,由心理學家所實行的還原可說是不完整及矛盾的,從而在其中所獲得的純粹性也只有相對的純粹性。(Hua IX, 225/Scanlon, 172)
二、現象學心理學和經驗世界
不過,是否因為這種矛盾便可貶低現象學心理學的價值?只要這門學科著力于從“超越因素”的解放,即心理現象的心理和身體方面,它就抓住基礎來制定出心理現象的本質。而這導致了“整全的經驗世界”(einheitliche Erfahrungswelt)的研究,這是自然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所包羅萬象的世界。(Hua IX, 232/Scanlon, 178)
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需要處理在人們精神層面(das Geistige)所進行的東西,他們所想的東西以及他們如何思考。但只要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中,世俗的層面便需要被考慮到。傳統上,物質性和心理性之間的關系自從笛卡爾17世紀初以來便受到哲學家和科學家的關注。雖然胡塞爾提出了類似的問題,但他拒絕把“自然”或“精神”看成是不容置疑的概念,以之作為我們處理這個問題的開始之處。事實上,這兩個概念產生于我們的理論思維,而不是我們原初的經驗。只要“自然”和“精神”的概念是理論思考的結果,它們在這樣的背景下就不應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通過前理論的經驗所表明的世界從來不是世界本身,即那種純物質性的世界,相反地它關連于主體。胡塞爾描繪這樣一個世界為周遭世界(Umwelt)。這是經驗的一個前科學、前理論的世界,涉及到主觀方面。即使每個主觀經驗都有其特定的、具體的內容,它仍然包含了穩定的意義(fester Sinn),即世界中不變的東西(das Invariante)。(Hua IX, 225/Scanlon, 172)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的目的,恰好要對世界中不變的東西做出澄清。只要它涉及主觀的時刻,它便沒有缺少心靈或精神的層面。此外,人們必須補充的是,主體是與世界緊密相連的。它是“在世界的主體”。那么,這樣一個主體如何被理解?
主體是帶有心靈與精神的存有者,但它不是純粹的精神而已,它也是帶有身體的。主體參與了空間,與物理現象和物質密切相關。那么,這樣的連接如何被解釋?胡塞爾以新的方式來處理這個老問題。
基本上,胡塞爾認為在對人類的定義中精神比身體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精神不能自身存在的程度而言,精神不是與空間無關的。精神是通過身體而參與空間,藉由這種參與,精神可以說定位在空間中,雖然是間接地。胡塞爾認為這是精神在空間中的原初被給予。當我們確定精神不能沒有物理維持而存在時,后者可以說是構成前者的預設。其結果是,當身體被消滅時,精神或心靈也隨之消滅。這是胡塞爾之所以認為死亡是在世界中的一個真實事件之緣故。(Hua IX, 109/Scanlon, 82)因此,胡塞爾并不支持靈魂可以超出身體的毀壞而生存的想法。他堅持精神要有身體存在的必要前提。然而,他也沒有按照自然主義觀點認為精神或心靈可以只被視為物理身體的副產品。借用自然科學的設置來研究精神或心靈,對他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對他來說,這樣的做法構成了恰當理解精神或心靈的最大障礙。他解釋說:
在一個完全一邊倒的方式中,人們總是試圖完全以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繼續進行,并把所有關于現實的研究化約成歸納研究。對許多人而言,歸納科學和經驗科學直到現在仍然代表著等同的表達。與那連接的就是從自然的科學理念到精神本質暨心理自身的科學之不清楚的轉移,這作為一項規則甚至在原則上是錯誤的。(Hua IX, 142/Scanlon, 108)
在自然科學家眼中,精神或心靈只不過是基于生理基礎所發生的現象而已。因而,精神被解釋為在自然世界中的客觀現象。人類通常被理解成這樣,而自我基本上則被看成是空間的存在。但胡塞爾拒絕這樣的自我概念。他主張純粹的自我是遠遠超過了身體現象所能揭示的。
胡塞爾藉著這般的詢問重新詮釋了傳統的精神/身體哲學問題:精神如何參與空間的世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激活(Beseelung),它可以在胡塞爾稱為人格態度的背景下顯得更清楚。
作為世界中的主體,人類以胡塞爾稱之為人格態度來處理周遭世界的事情。這種態度意謂著攸關于事物的意義和價值。而在這樣的態度中,“我的身體……是在周遭世界中給予我,作為其他周遭世界的中心,作為一個擁有軀體性的周遭世界的空間事物,我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甚至作為我在其他周遭世界行使影響力”(Hua IX, 228/Scanlon, 175)。這種態度是明確地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態度,后者的興趣在于完全被剝奪了價值與意義的純自然。對于胡塞爾,周遭世界關系到人格態度,而純自然則源自人格態度的闕如。
原初上,世界從來都不是獨立于我們的經驗,我們所遇到的事物從來都不只是自然的材料,但始終涉及某種超出純粹自然的意義,更何況我們所遇到的人。作為世間我(Mensch-Ich),我正住在世界上,與所有這些事物和其他人一起。而這是人文社會科學所要處理個人生活在他周圍的、文化的世界。(Hua XXVII, 211)在這種情況下,他周圍的事都是富有意義的(bedeutsam)。(Hua IX, 111/ Scanlon, 84)胡塞爾甚至注意到個人與其對象之間有相互交織的關系。(Hua IX, 226/ Scanlon, 173)簡言之,基于某些用途或目的,事物的意義和價值故而產生,文化之物(Kultur objekt)也因此形成。
關于純自然的知識是絕然不同于對世界的理解。周遭世界中的事物是充滿意義和價值,它們是文物。雖然文物有天然材料的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是自然的對象而已。胡塞爾認為“在其原有的生產中被添加到對象上的工作目的和意義是永久地歸屬于物質的對象”(Hua IX, 115/Scanlon, 87)。價值和意義是附著于文物,作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箭頭為例,胡塞爾解釋:
物理上,箭頭是感官地被看到,并在同一時間,如我們所說,在其最終意義被理解為箭頭。它本身顯示出,在可能和實際經驗中,只要它被顯示出并被證明為由于這個意義并作為對應于它而已產生了。(Hua IX, 115/Scanlon, 87)
依此看來,人格態度的本質描述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認識世界。胡塞爾也稱這個世界的研究為“自然經驗世界的本質研究”(die Eidetik der natürlichen Erfahrungswelt)。只要這門科學的目的是描述經驗世界的先驗性,它事實上是等同于上述的現象學心理學和普全的世界科學(universal Weltwissenschaft)。
現象學心理學,普全的世界科學,或“自然經驗世界的本質研究”,所有這些都被確定為先驗的、本質的、直觀的、描述的和意向的。除此之外,它仍然是在自然的態度中,而不是在超越觀想的態度中。先天意味著主體與世界之間存在著一個普遍結構,它通過持續的風格和種類顯現出來。這樣先天普遍的結構是日常生活的預設。然而,這些預設都沒有被察覺到。即使是參與的主體也沒有察覺到。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關心所有關乎他們生活的各種對象。一個人必須后退一步,以便與這些預設以及不斷在發揮作用的主體取得聯系。它是胡塞爾所謂的還原。
通過還原我們察覺到日常生活的預設以及接觸到經驗世界,胡塞爾解釋:
通過“經驗世界”的標題,我們清楚地意指所構成的和諧總實體,它是在我們經驗的過程中不斷地重新被建立。(Hua IX, 59/Scanlon, 44)
如前所述,世界是連接于主體的世界,不僅是世界本身而已。而這樣的經驗世界具有一個普遍結構,在穩定的類型和風格中被揭示。該結構一方面是連接于主體,另一方面是連接于世界。主體和世界恰好是彼此相關。
胡塞爾進一步指出,擁有本質結構的經驗世界是“自然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所包羅萬象的世界”(Hua IX, 232/Scanlon, 178)。它包含了世界的真理(Weltwahrheit)((Hua IX, 63/Scanlon 47),而世界的真理構成了事實性(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文化的)科學的全部真理之基礎。在原初經驗世界所揭示的真理意味著這樣一個真理世界不是一個沒有內容的世界。正是因為其卓有成效的內容,它可以成為所有科學的基礎。基于這樣一個世界的真理,我們可以確定在科學知識的真理。世界是前科學的經驗領域,其結構將反映在其他科學領域中。(Hua IX, 64, 46, 232/Scanlon, 33, 47, 178)
因此,經驗世界是所有科學研究的基礎。經驗擁有它,作為人類生活在自然態度中,我們持有大量的不可動搖的信念,這涉及到世界的現實和整體。它是被我們盡可能堅定地接受。但是對胡塞爾來說,在原初經驗所揭示的有太多被科學文化所污染,以致于我們幾乎無法重返世界的原初經驗,并且完全承認它。為此,胡塞爾建議通過現象學還原,特別是心理學現象學還原來克服這些困難。
結論
在我的論文的第一部分,我探討了現象學心理學和超越論現象學之間的關系。當胡塞爾在說明現象學心理學時,他自己不斷觸及這個主題。然而,當處理現象學心理學時,這樣的關系不應該是我們唯一關心的部份,相反地,現象學心理學和事實性科學、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也應被考慮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驗的世界方被引入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在我的論文的第二部分,我藉著指涉我們經驗和世界的相關性來凸顯現象學心理學的重要性。在處理自然世界的概念時,現象學心理學相當于普全的世界科學。如果,作為心靈的自我認識,現象學心理學側重于主體這一面,那么普全的世界科學便側重于世界這一面。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這兩個學科都彼此屬于對方,它們都符合“自然經驗世界的本質研究”,只要它們是本質的科學。
世界不斷地對我們顯露它自己,它從來沒有被打亂。世界的經驗構成了一個和諧的流動,而世界無非是經驗所給予我們的那一切。(Hua IX, 326/Sheehan eds., 234)胡塞爾一再表明,如果世界沒有在原初經驗中預先給予我們,沒有科學活動是可能的,因為沒有基礎可提供給我們。((Hua IX, 56, 62-63/Scanlon, 41, 45-46)這個世界不是世界在其自身,即純粹的自然。相反地,只要世界在我們的經驗中被揭示,它便是與我們相互關連的世界。
在這個前理論的世界中有著一般的、系統的結構,它滲透和規定事實性科學的系統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對于經驗世界的科學便是世界的普全科學。通過對于預先給定世界的描述,這門科學提供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沒有哪一門科學是可以沒有經驗世界的本質結構作為其基礎的。以此來看,對于經驗世界的科學,無論是現象學心理學、普全的世界科學、或是“自然科學世界的本質研究”都構成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
參考文獻:
[1]Ashworth, Peter. (2003) An Approach to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Contingencies of the Lifeworld,Journal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 34:2, 145-156.
[2]Davidson, Larry and Lisa Cosgrove. (2003) Psychologism a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Revisited, Part II: The Return to Positivity,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33, 141-177.
[3]Davidson, Larry. (1988) Husserl’s Refutation of Psycholog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Journal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19:1, 1-17.
[4]Finlay, Linda. (2008) A Dance Between the Reduction and Reflexivity: Explicat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Journal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39, 1-32.
[5]Giorgi, Amedeo. (2012) The Descriptiv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ical Method,Journal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43, 3-12.
[6]Husserl, Edmund. (1962) 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 Semester 192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Lecture Summer Semester 1925: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r. by John Scanl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7]Kern, Iso. (1977) The Three Ways to th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Husserl, in F. Elliston & P. Mccormick(eds.), Husserl: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8]Kockelman, Joseph J. (1967)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A Critical-historical Study,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9]Lohmar, Dieter. (2012) Husserl’s Psychology: A Conribution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manities, in Investigationg Subjectivity: Classical and New Perspectives, ed. by Gert-Jan van der Heiden et al, Leiden/Boston: Brill.
[10]McCormick, Peter and Frederick A. Elliston(eds.). (1981) “Phenomenology: Edmund Husserl’s Article for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27)” (revised translation by Richard E. Palmer), in Husserl: Shorter Work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The Harvester Press.
[11]Sheehan, Thomas and Richard E. Palmer (eds.). (1997) Psychological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Heidegger (1927-1931),Dordrecht/Boston/Lond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2]Sheehan, Thomas and Richard E. Palmer (eds.). (1997) “Edmund Husserl’s Amsterdam Lectures (1929)” in Psychological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Heidegger (1927-1931),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3]Str?ker, Elisabeth. (1997) The Husserlia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Dordrecht/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責任編輯任之)
*作者簡介:游淙祺,臺灣人,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中圖分類號:B516.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6)03-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