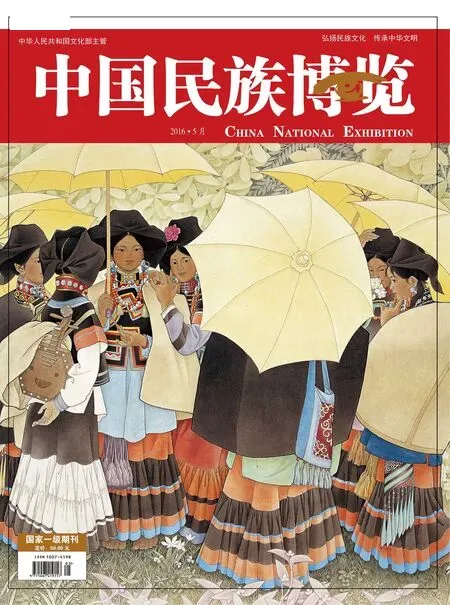從《尤利西斯》看英雄本色
張瀚文
(甘肅省蘭州市蘭州交通大學文學與國際漢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
從《尤利西斯》看英雄本色
張瀚文
(甘肅省蘭州市蘭州交通大學文學與國際漢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摘要】通過對《尤利西斯》中主要男性人物進行分析,探討作品中人物的“英雄特性”,以此進一步探尋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深度意義,獲得對蘊藏在人類文化深處的人類靈魂的認識。
【關鍵詞】英雄;英雄生存模式
一、《尤利西斯》與英雄概說
《尤利西斯》是20世紀初歐美杰出的現代主義意識流長篇小說。小說塑造的布魯姆、斯蒂芬等人形象鮮明。喬伊斯塑造奧德修斯等的理由是20世紀初人們不再相信傳統意義的上帝與諸神,而罹難于現實的人類仍需要被拯救,因而必須誕生時代性英雄。
二、西方文學作品中的英雄及英雄形象
(一)布魯姆:奧德修斯人文精神的完善
布魯姆出身卑微工作平凡,膝下無子又遭紅杏出墻。他對妻子的關愛不必言說,小說第四章講“它們懂我們說的話,比我們懂它們的多”,這是布魯姆在觀察貓后得到的結論,可見他尊重每一個生命、每一個靈魂。第八章他對代答勒斯妻子的被迫多產、皮尤福依的三天難產的憐憫“這可受罪了”以及“朦朧入睡法”的設想,都見其對生命與女性的尊重和愛。“倒不如把錢花在為活人辦點慈善事業上更明智哩。”表明他關心普通大眾的生活,有社會責任感與道德意識,能夠清醒地辨認出宗教騙局。這也與斯蒂芬的精神上有共鳴。布魯姆與瑪莎的通信、對妓女以及海邊姑娘的幻想,是在自己的婚姻失敗時渴望得到異性的愛慕,從而重新獲得男人的情感與人格上的被認可。
奧德修斯集偉大、智慧、勇敢、忠誠、正直的特征,有神助之愛之,成功得無可挑剔。布魯姆又給原來的奧德賽增加了血肉情感,不再戰無不敗,卻又可親可近,這是對奧德修斯人格的完善。
(二)斯蒂芬:顯性的忒勒馬克斯,隱性的哈姆萊特
斯蒂芬與忒勒馬克思前人已做詳較,此處談后者。嚴格來說,斯蒂芬與哈姆萊特較無相關。哈姆萊特亦是西方文學作品的悲劇式英雄。他沒有尋父,而在尋仇;他被剝奪了本應有的權利、家庭,是一個寧可死去也要為失去的一切找回答案的英雄。生存還是毀滅?——他最后的死宣告他尋找的是答案、交代。
《尤利西斯》小說中引用了大量的《哈姆萊特》中的臺詞。第八章中“哈姆萊特,我是你父親的陰魂/被判決若干時在地面上游蕩”。
斯蒂芬作為小說中的知識青年,對于人們盲從教會的苦悶與尋找精神上的父親,是作者刻畫的青年人在缺失信仰的社會中彷徨、苦苦尋找答案的形象。
“斯蒂芬伸直脖子,指著鏡子辛酸地說:‘一面仆人用的破鏡子,這就是愛爾蘭藝術的象征’。”認為愛爾蘭藝術如破鏡子般不堪、最終被廢棄,顯示了青年關心社會關注民族文化的擔當意識,這種悲劇意識與哈姆萊特在裝瘋時看弒父戲劇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者如是描寫斯蒂芬與穆力根關于母親死后的一次見面的爭吵:“斯蒂芬捂著那句話在他的心靈上留下的傷口,冷冷地說:‘我并不是考慮你對我母親的侮辱’,”——“ 對我的侮辱”。可見,斯蒂芬方面堅持著自己對真理的執著,一方面也苦于現實的無奈。這種復雜、矛盾的心理狀態與哈姆萊特放棄殺死叔父的機會的心理較為相似。
“一個有天才的人是不會失策的,他的差錯正通向新發現的門戶,這也是他自愿。”斯蒂芬認為《李爾王》中“她”的死是是在她出生六七十年之后,她給他生兒育女,陪伴他度過余生。這與約翰·埃格林頓所認為的“莎士比亞是一步失策,然后盡其所能地用最好、最快的辦法脫離了它。”這里的“最好、最快的方法”無疑是指死亡。此處作者又寫了一段關于斯蒂芬的內心獨白——“我獨自哭泣”。再一次地表現斯蒂芬即使再讓他選擇,他還是內心堅持不進行祈禱,但同時他的善心又被母親死時的絕望所圍困,自己陷入無奈的兩難境地。所以談及母親的死,無論是誰的母親,他都會很敏感地聯想到自身,不斷地傷心無奈。他便具有和哈姆萊特一樣的糾結不清的苦惱:一方面渴望改變現狀,為父報仇,一方面自己又被糾纏在自己與母親及叔父的錯綜關系里面難以下手。
斯蒂芬在海灘上思考生命“我也在罪孽黑暗中被孕育,由他們制成而非生成一個眼睛與我相同的男人,而另一個則是和我相得益彰……這就是圣父圣子一體性所在的神圣實體了”這都體現了他對自我人格的思考、對命運發展的探索,這是與處于糾結中的哈姆萊特尋找“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的答案有相通之處。在第十五章中作者寫斯蒂芬與母親的亡魂對話,暗藏著哈姆萊特的靈魂和思考生命的方式。
(三)壯鹿馬利根與西西弗
壯鹿馬利根的身上典型地流淌著西西弗的血液。
因被天神處罰要永遠地、并且沒有任何希望地重復往山頂滾石的動作。在諸多人心里,西西弗是極其可憐、無聊、荒謬的。但也是一個具有“荒謬”人性的英雄。壯鹿馬利根亦如此。
《尤里西斯》開篇描寫馬利根“儀表堂堂,結實豐滿”作者對他進行了外貌、動作、語言的描寫,用“莊嚴、肅穆”來形容他,這些就具備了與西西弗一樣機智聰明、熱情活潑的性格特點。接著又描寫馬利根“布道”,從其言語見其表面自娛自樂、詼諧。
書中作者通過對馬利根神態的描寫也向讀者展現了其善于言談、富于變化、粗獷狂放的秉性。他給斯蒂芬起外號“金赤”,和斯蒂芬說話更是一語多腔。第一章中馬利根刮胡子時與斯蒂芬的對話中,先有“回到營房去,他厲聲說”,卻馬上又開始虔誠“布道”,然后又“精神抖擻地大聲說”,在發現自己沒有手帕后又“甕聲甕氣地嚷”,用完斯蒂芬的手帕后,他“柔聲”地稱斯蒂芬小狗,并要給斯蒂芬幾塊鼻涕布。著實荒誕,明明缺手帕的是自己。當他意識到自己言語過失又“親切地”說斯蒂芬“比他們當中的任何人都有骨氣”。這些與西西弗在第一次被判入地獄欺騙冥后時的“詭詐”實為相似。馬力根言語暗喻性極強,第一章和第九章中馬利根出現的次數最多,他的言語引用作品或是名人話語分別有48 和38處。《圣經》及宗教禱文引用最多;葉芝、惠特曼、阿諾德等詩人的詩句;《暴風雨》、《麥克白》和《哈姆雷特》等戲劇中人物的對白,以及關于王爾德的《意圖》和《奧義書》等書中一些哲學觀點的引用,此外還有對當時名人海軍統帥納尓遜等的話語引用,以此暗諷世風。
其實馬利根是有理想的,當他面對都柏林愛爾蘭文化與異族文化互相排斥、缺乏發展出路時,主張推動愛爾蘭文化的希臘化。但這在都柏林是更難行得通的。這番主張連斯蒂芬都覺得有些難度,可見其理想的荒誕性。
三、《尤利西斯》中的古典式英雄與“拜倫式”英雄的結合
傳統西方文學塑造出奧德賽、阿基琉斯和阿伽門農等古典式英雄作為西方人的精神楷模深入人心。到近現代“拜倫式”英雄更加真實地表現出人類成長歷程中的性格特征與人性需求。
“拜倫式英雄”是個人主義反叛者,才能出眾,反抗國家強權、社會秩序和宗教道德而無明確斗爭目的;追求個人自由卻孤芳自賞,斗爭總以失敗告終。
《尤利西斯》中的青年,斯蒂芬與馬利根就是更為典型的既具有古典式英雄的特征,又具有拜倫式英雄的特征。他們有先進思想而被大多數人所不容。第六章中代答勒斯辱罵馬利根,憎恨他“帶壞”了兒子,也不待見兒子。斯蒂芬與馬利根作為當時的知識青年,極具才華。在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五章等他們探討詩歌、哲學以及對民族文化的主張等都表現出博學多才的特征。
內心具有反抗、孤傲而又浪漫的特征。斯蒂芬面對母親臨死時的要求堅持自我主張,反對跟風于教會神學。在被稱是“杰菲特尋父”后,小說對斯蒂芬漫步海灘的敘寫,以及他對愛爾蘭民族文化發展的淡然態度、截然不同于馬利根企圖“希臘化”的主張,都表現出他內心的孤傲。而他對小學生的鼓勵教育、對給他力量、支持他前進的父親的渴求,都是他作為真實人的追求美好的真實性格。
馬利根也在其話語中展現了他的反抗性,只是因性格不同,他的意志的表達往往是通過調侃與戲謔。而他的玩笑又是很富有浪漫主義特征的。貫穿小說始終的,有斯蒂芬對虛偽的宗教神學的反抗、馬利根等青年對社會文化企圖改變的欲求,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斗爭對象,抑或缺乏足夠的力量來與敵對勢力抗衡。他們的斗爭或許不是以失敗告終,或許是不了了之,如小說最后對于母親的死與斯蒂芬自身的關系又能得出什么結果呢?或許是以自己的內心得到充實來作為最后的慘淡收尾。馬利根這樣的不滿于現實渴望有一番作為的熱血青年最終慘淡收場,也是很遺憾的悲劇。這兩個代表性青年通過反映自我更反映出了人類命運的悲劇性。正是古典式英雄成長、發現自我個性、企圖主宰自我命運的個體表現,而這恰趨于拜倫式英雄。
四、英雄的生存模式
假設《尤利西斯》是作者企圖在20世紀初的現代社會中塑造新一輪的英雄,那么他們又符合了自古以來的英雄的生存模式。于是可追溯出這些英雄的共同的生存模式。
(一)天降大任于斯人
首先,這些能夠成為英雄或是擁有英雄情操的人是和普通人一樣,處于蒙昧狀態的。他們關心自己的物質生活與身心需求。如海子所說“砍柴、喂馬,關心糧食和蔬菜”。神話中的奧德賽起初就是無憂而權力至高的國王;小說中的布魯姆是一個平淡安然的工薪階級、斯蒂芬與馬利根亦是剛步入社會的知識青年,這在當時都是社會中的大群體,不足為奇。
但不同的是,這些人身上隱藏著先賢時期的靈魂基因,一種集體無意識——關注人類命運的走向、守衛人類的靈魂。他們因各種遭遇輾轉被動或主動承擔起改變現狀的使命:奧德修斯肩負著結束特洛伊戰爭、重整家鄉的使命;布魯姆肩負著重新關注民族發展、提高女性平等意識的使命;而斯蒂芬、馬利根年輕一派肩負著從苦難中尋找自我、尋找文明發展之路的使命。
(二)為使命而“漂泊”
不論中西方的現實或文學作品,自古英雄都是要經歷漫長漂泊才能被稱為英雄。漂泊即是人物的受難期與英雄塑造期,英雄為完成使命而漂泊。孔子漂泊數年,最終其思想主張成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千年不衰;但丁的《神曲》,經歷地獄、煉獄及天堂,促使人們自我發現與覺醒,為文藝復興唱響了基調。奧德修斯的受難期即是他十年的海上漂泊。這種苦難的歷程是被他人談論時的英雄的體現。斯帝芬與布魯姆的思想的游走也正是一種靈魂的漂泊,他們被“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困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三)反抗性
“士可殺不可辱”,是對英雄的寧死不屈反抗性的高歌。當肩負著重大使命而在受苦受難的英雄,其信念往往與所受磨難成正比。最鮮明的如斯蒂芬與母親亡靈對話時的話語,他做出了最后的、最堅決的反抗。正是由于他反抗到底了,最終才找到了精神上的父親。而換作馬力根,面對母親死前的要求,他是不會拒絕的——對現實的屈服。馬力根不完全是正面人物,也恰因為他過于圓滑、不夠全力以赴地堅持自己的主張,因而他多次與他人的談笑風生,也是掩蓋追求理想的荒誕虛無。
(四)悲劇性
悲劇性需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命運悲劇,在古典式英雄與拜倫式英雄的身上都有;另一種是英雄回歸平凡、回歸現實后適應生存的悲劇性。
命運的悲劇性在俄狄普斯、西西弗身上實為明顯,永遠在反抗卻永遠逃不出命運的手心。如果按照亞里士多德“悲劇是對一定長度的情節的模仿”進行分析,奧德修斯的一生正是悲劇,史詩中的他始終處于斗爭之中:為戰勝與人斗,為歸鄉與神斗,為私有財產與搶奪者斗。而所有斗爭解決之后史詩也旋即結束。
布魯姆與斯蒂芬的悲劇在于他們如何適應社會的生存、在不合時宜、不合群的狀態下安身立命。這表現在布魯姆對母性的尊重與對猶太文化的認同而被人嘲笑、排擠;斯蒂芬明顯地反對神學也被看為異類。這些人的思想高度與卑微處境成反比,這是悲劇。
(五)回歸現實
《尤利西斯》展現的是活在俗世中的英雄的生活,也就是英雄回歸現實。喬依斯通過這部小說告訴大眾:再平凡卑微的生活與處境,都要保持高風亮節的英雄本色,這樣的人生不平庸。
薩特在《文字生涯》中講述自己童年時渴望成為英雄拯救人類,但是當他發現現實難以改變,于是轉變方式——為理想而寫作“我決心為上帝寫作,目的在于解救同胞”。真正擁有英雄本色的人,不論處境如何讓他失望,他都不會徹底絕望,而會繼續為目標堅持。
《尤利西斯》是作者對19世紀末以來,人類歷史現代化進程中人心發展變化的思考,并為處于彷徨、失望、痛苦中的人做出了選擇與解答。敢于堅守信念、不忘初心的人,是在所有善心、勇敢的心被物質社會殺害時堅持到最后的而保衛住靈魂、從而獲勝的英雄。
千百年來,英雄本色不變,永遠流淌在人類靈魂的深處。
參考文獻:
[1]金堤譯.尤利西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7.
[2]蕭乾,文潔若譯.尤利西斯[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3]章影光譯.尤利西斯[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4]荷馬著,陳中梅譯.奧德賽[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5]阿爾貝·加繆著,沈志明譯.西西弗神話[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6]讓·保爾·薩特著,沈志明譯.文字生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