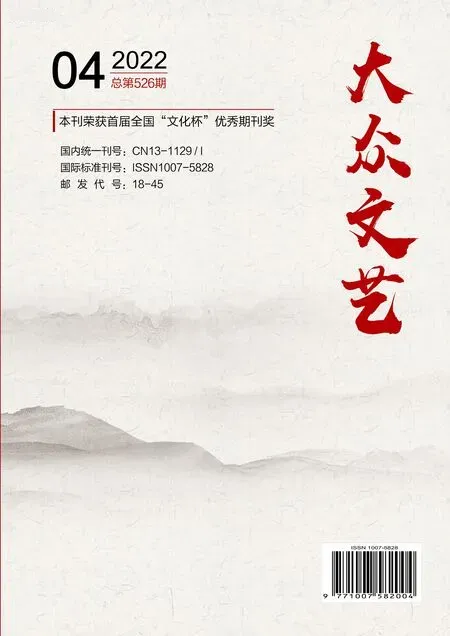淺談“音樂學”
梁 靜 羅冬芹 (武漢音樂學院 430000)
?
淺談“音樂學”
梁靜羅冬芹(武漢音樂學院430000)
音樂學(musicology),是通過與音樂有關的各種現象來闡明它們本質及其規律的一門學科。關于音樂學學科的定義,《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提供了三條定義:1.從傳統觀點看,音樂學是一種知識理論;2.一個以音樂藝術作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學科;3.音樂學的研究包括音樂本身及社會與文化環境中的音樂人。從其他音樂辭書對音樂學學科的闡述來看,盡管就學科的研究領域和方法上存在著一定差別,但可以肯定的共識是:音樂學是具有學術性質的音樂研究。學科的確立和最初的發展得益于德國音樂學家圭多?阿德勒,他創造性的將學科劃分為歷史音樂學(historical musicology)和體系音樂學(systematical musicology)兩大類,前者主要研究西方藝術音樂及其歷史,包括古譜收集,記譜法研究和對作曲家、作品的分析、歷史分期、風格歸納等內容;后者則偏向于音樂技術理論,音樂美學,民族音樂學方面,借用文學、文獻學、訓詁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運用于音樂當中。
音樂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始于19世紀的歐洲,但人們對音樂研究的歷史卻可追溯到世紀之前。早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對音樂的興趣產生于對美的頂禮膜拜中,將音樂看成哲學的一種現象,畢達哥拉斯更是以數的和諧來作為評判音樂美的標準。這一觀念得以傳承,并影響了整個中世紀,伴隨著“大學”的誕生,Quadriviu學科(包括音樂、算數、幾何、天文學)成為其中重要的課程,這為音樂研究走向學術化,日后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埋下了萌芽的種子。在往后的歲月里,不斷有學者從聲學、物理學、哲學、心理學等角度探索音樂的奧妙,終于在19世紀下半葉,對音樂的研究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稱之為“音樂學”。
由于受到“實證主義”精神的影響,長久以來,歷史音樂學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學者們熱衷與文獻整理研究、歷史資料發掘及對樂譜手稿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體系音樂學,也別是民族音樂學,使之一直處于對歷史音樂學的從屬地位。自二戰結束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的衰落和其他人文學科的進步,則開啟了“新音樂學”時代,它平衡了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的地位,是二者相互補充、影響。與此同時,激發了學者對以往研究手段與成果的深刻反思,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卡爾?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他在《音樂史學原理》中指出,音樂史不應該僅僅只是一部風格史,而應包括結構史、接受史和文化史,在他的研究中,更多地將歷史與審美結合在一起,以新視角審視音樂。80年代,約瑟夫?科爾曼(Joseph Kerman)作為英美音樂學的領軍人物,在其《沉思音樂-挑戰音樂學》中提出了對音樂學學科走向的看法,他認為音樂應借用文學中“批評”的形式,以更廣闊的文化,用客觀批判的眼光思考音樂。在隨后的幾十年間,這一觀點成為了學科發展的風向標。
誠然,20世紀后半葉的音樂更多地從文化角度進行詮釋,于是產生了音樂人類學,著重對文化中的音樂研究。民族音樂學家進行大量田野,積極參與民族民間音樂的手機,試圖從中尋找到歐洲藝術音樂與之的關聯。這一過程顯示出音樂研究的多元化趨勢,許多新興的研究領域開始出現,如蘇珊?麥克拉瑞(Susan Maclary)出版的《陰性終止——音樂、性征與性別》就首次關注了音樂和音樂史中的女性地位、角色等內容,從性征角度論述音樂。薩波奇?本采(Szabolcsi Bence)在他的《旋律史》中有史以來第一次從地理、地貌環境方面論述對旋律形成、傳承的影響。這些作品愈發體現出學科交融的特點,也為音樂的研究打開了新思維。
音樂學作為舶來品,在中國從真正意義上確立到發展亦已有百余年光景,但這期間所經歷的又豈非曲折二字所能涵括。音樂學的在最應該迅速發展時遭遇了日本侵華,然后國共內戰,好不容易共和國成立,后來又發生了“文革”……所以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系統地研究與發展音樂學,也只是“文革”結束后開始的幾十年而已。從第一代中國音樂學學者起,歷經百余年的努力,我國現今已建立了專業音樂教育機構,并設置了合理的教育體系及課程,先后培養了一批為音樂學與音樂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人才。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學科相繼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開始走向世界舞臺。在面對西方音樂的研究中,中央音樂學院的于潤洋先生曾告誡廣大中國音樂學學者,要看清自我的立場,作為東方人,以東方的視野觀察西方音樂喜憂參半。喜于我們能更清晰、客觀地觀察到西方學者在司空見慣中易于忽略之處,憂于缺少大量原始資料和研究氛圍。縱觀西方音樂學學科的發展歷程,有大量需要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在吸收西學文化同時要兼顧中國的民族的特色,以確保中國音樂學良好的發展趨勢。就學科建設的問題,許多學者都給予了善意的批評和誠摯的建議,如郭乃安先生的《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楊燕迪先生的《論西方音樂在我國的重建》和《作為人文學科的音樂學》等。
另外,音樂學流傳到中國除了平常意義上的“音樂”,更多了一分“民族”。也就是說作為中國的音樂學家,除了廣泛意義的音樂之外,還必須對本土的民族音樂進行挖掘和研究,這是中國學者的職責所在,更是得天獨厚的條件。比如早期的中國音樂學開拓者,蕭友梅與王光祈作為中國最早的音樂學科留學生,他們在德國的博士論文皆以中國音樂為題材,王光祈更是寫作了國內第一本《中國音樂史》。美國卓越的中國文學史專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說過一番話:“在學習和感受中國語言方面,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無論下多大工夫,也無法與最優秀的中國學者相并肩;我們惟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于(中國)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這段話的要義可以幾乎原封不動地適用于中國的音樂學人。我們的出路就在于“中國立場”和“中國視角”——“我們處于西方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音樂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僅僅跟隨“傳統的”音樂學方法,中國人很難有什么出路。“新音樂學”盡管有許多問題,但恰恰在方法論上對國人有很多啟示。所以,我們絕不能在發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情況了。
對音樂學術研究的目的,理應是為求更深刻地理解音樂,從而更全面地理解人性,這應當是學科的崇高目的,體現出人們對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追求。錢仁康先生認為,音樂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創新,符合人們對音樂的理解,并提倡音樂的創作應更多地貼近生活。據此,對音樂的研究也理應根植于生活,以對人性的理解為其目的,正如阿倫?瑞德萊(Aron Ridley)在《音樂哲學》中的敘述:萬不可將音樂當成火星來客。
參考文獻:
[1]參見楊燕迪主編.音樂學新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2](美)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初唐詩[M].三聯書店,2004:1.
梁靜/羅冬芹,武漢音樂學院在讀研究生。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