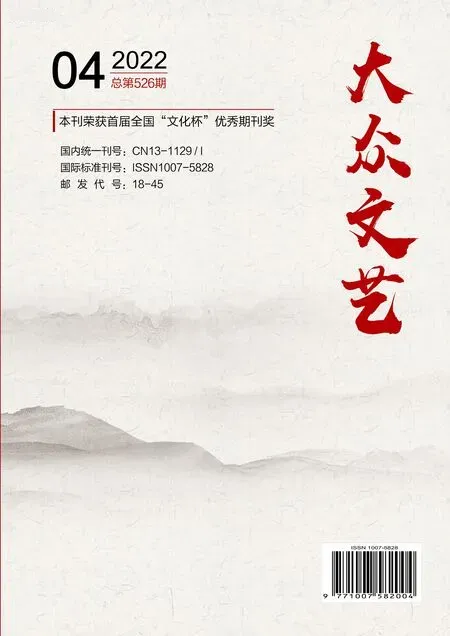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體例的獨特性研究
郭名峰 (海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571158)湯慧蘭 (海南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 571158)
?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體例的獨特性研究
郭名峰(海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571158)
湯慧蘭(海南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571158)
摘要:清代戴震在其重要的義理著作《孟子字義疏證》中,通過對《孟子》中的“理”“天道”等幾個字進行疏證來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并以此對程朱理學進行批判。本書重視義理,在文獻訓詁和考證的基礎上進行義理闡發,呈現出體例的獨特性。
關鍵詞:疏證;體例獨特性;文獻學研究
本文系2015年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青年課題,項目《〈孟子字義疏證〉之文獻學研究》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HNSK(QN)15-125
戴震是乾嘉時期考據學派的重要代表,以其考據學的擅長在文獻學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戴震也主張在文獻訓詁和考證的基礎上闡發義理,“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實行以故訓以明理義的治學方法,避免漢學家只專注于現有文獻考據的狀態和宋儒學家的空發義理的現象。其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就是源于這一主張而產生的文獻學成果,該書以義理與考證結合起來,而又以義理為根本的考證方法,通過疏證《孟子》來批判理學的“得于天而具于心”思想,進而闡發不同于理學思想的新的哲學思想。這種疏證方式使其明顯有別于其他人對《孟子》進行逐句逐篇的訓詁考證的注疏之作,體現了文獻學體例上的獨特性。
一、列舉重要字眼進行新解
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每卷都有若干要進行疏證的字,這樣的創作體例和以往儒家經典的疏證之作有很大不同,它不像以往那樣專門疏通文字,解讀章句,像趙歧《孟子章句》、焦循《孟子正義》、朱熹《孟子集注》等,都是對孟子當中的每一句話進行疏證,其分卷也是按照孟子原文的分卷劃分,都是從卷一“梁惠王章句”到卷十四“盡心章句下”,而本書在分卷的時候則是按照概念范疇劃分然后對相應的重要字眼進行疏證,這樣的創作體例頗利于戴震對其義理之學的闡釋。
在此書的每卷中戴震都分別列出“理”“天道”“性”等字眼進行義理考據而形成新的解釋。這種體例方式在以往的注疏之作中非常少見,特別是在對《孟子》進行注疏的著作中是沒有出現過的。如,在此書上卷開篇中對“理”所做的新的解釋,“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見《孟子字義疏證上?理》)在中卷“天道”篇中對“道”做出了不同于他人所做的解釋:“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見《孟子字義疏證中?天道》)這種獨特的體式在本書的其他篇章中同樣都實行和體現著。
我們可以從這種體例的分析中看到,每篇開頭便預設該篇所要論述的中心議題,接下來的疏證則是為了提供支持該中心議題的依據,而在自問自答的過程中則更加深入地展開批駁,最后得出結論。這種形式非常類似于現在的議論文的寫作格式,戴震采用這種方式無疑是為了便于闡發義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疏證的體例并非戴震首創,如南宋朱熹弟子陳淳的《北溪字義》已開先河,朱熹另外一位弟子程端蒙(與陳淳同時)所作《性理字訓》一卷,體例也與《北溪字義》相同,戴震之后,類似體例的著作較多,如焦循《論語通釋》、阮元《性命古訓》、陳澧《漢儒通義》、黃以周《經義比訓》、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但是即便如此,本書在疏證過程中的具體方式與思路并不一樣,特別是沒有他們那種以訓詁考據為工具建構義理之學的方式,其獲得的學術效果是很不一樣的。
二、引據經書對所列字眼進行互相疏通印證
著者在書中為了達到心中所需表達之義,不惜引據大量經書中對相關字眼進行解釋,這個引用和相互印證的過程是本書論證的主體部分,在此過程中其深厚而靈活的義理考據功底發揮著重大的作用,而這些新的解釋使作者最終水到渠成地闡發了自己的哲學思想,這種方式的采用使此書已在實際上相異于以往注疏體例的引據經言的做法。
如,在上卷對“理”以己意下定義之后,遂大量引用《周易》《孟子》《中庸》《樂記》以及鄭康成的注和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中的相關內容進行互相疏通印證。具體如:“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如此前后相扣,相互疏證,始終緊貼經典,以經書文獻為原理,最終確定“理”解釋為“分理”“條理”的依據。其他在對“道”“性”“才”“仁義禮智”“誠”“權”等的釋義中亦同樣使用這種援據經言以疏通印證的方式。
雖然曾有當世和后世的部分學者,對戴震的這種疏證做法提出過異議,質疑其對原理解釋的正確性和疏證過程的嚴密性、合理性,甚至認為這種疏證在內在本質上帶有很濃的附會色彩,值得斟酌和商榷。但盡管如此,作為戴震此書文獻學方面的體例特征,似乎絲毫也沒有阻礙更多人對它的關注和欣賞,這也許恰恰是其在客觀上不可忽視的文獻學價值吧。
三、采用問答體亦批亦證闡發己意
全書以“問”和“曰”為標志,在對所疏證的字眼下完定義之后,便在一問一答中貫穿著對程朱理學的批駁,這種新穎的疏證形式有利于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以激發讀者思考的興趣,并伴隨著閱讀和著者所闡述之理而逐漸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層層深入地揭露程朱理學在概念和思想上的偏差。
如,對“理”的疏證。先對“理”下定義,即分理、條理之義,立“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謂理者”之論。緊接著“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之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挈之人,則理明。……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謂天理者矣。”……(見《孟子字義疏證上?理》)經過連續三次的“問”“曰”,深究窮索,戴震將自己對“理”義之解釋表達得明確無疑,他認為,古人所言天理就是“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的分理,并強調須通過做為善去惡的工夫以克服情欲之偏私,即“以我之情挈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最終落實到批駁宋明理學之目標上。
戴震的此種以自問自答的方式立論并展開分析的方式在以往他人的注疏體例中是未出現過的,可以看做其文獻學體例上的首創,具有創新的疏證方法論價值。有學者認為,這種獨具個性的語言詮釋方法本身并不具有獨立性,而是與其以“一本論”(以人的自然情欲的實現為本)為基礎的思想相結合的,而這種自問自答形式特別有利于戴震結合特定的時代思想背景和自身人生經驗進行具體闡述的需要,最終在學術上將議題闡釋清楚,達到疏證的目的。
四、論證過程極富思辨色彩
全書所采用的問答體本身就是極具思辨色彩的行文方式,使整個論證過程極富有思辨色彩,戴震使用這種方式是由其為批判程朱理學來闡發哲學思想的目的所決定的,客觀上突出體現了本書在義理疏證體例上不可忽視的獨特性。
戴震非常有針對性地選取理學家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概念“理”“天道”“性”等作為全書的疏證對象時,便開啟了批判的入口。如,戴震為了批判程朱對于“理”所言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在開篇便強調“理”指的應該是“分理”、“條理”,并引據經言,疏通印證,從而歸納出“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后儒所謂理者矣。”(《孟子字義疏證上?理》)在此基礎上,緊接著立即以“問”的形式提出“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接下來又以一連串的自問自答形式援據經言、疏通印證出“情”與“理”的關系,指出真正的理應當是“心之所同然”。接下來,問:“宋以來儒書之言,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今釋孟子,乃曰‘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非‘如有物焉具于心矣’。……”又說:“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群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由此可見,整個論證的過程以及逐步達到的效果都在以問答為形式的行文中蘊含著濃厚的思辨色彩,體現了犀利的思維剖析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在總體氣勢上即顯示穩健有力、勢不可擋,實為本書不可忽視的一大精彩之處。這些在嚴密邏輯之下富有思辨色彩的精彩語言表述,根源當然是有賴于戴震自身敏銳的思想和批判朱理學的強烈需要,在客觀上使本書具有了一種鮮明的體例特征。
五、以考據為器達義理之的
作為文獻學界的重要著述,《孟子字義疏證》本應以考據為主體而以義理作為考據所需之器(工具)用,但實際上是有些反其道而行,我們從本書引據經書互相疏通印證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戴震并沒有把疏證擺在一個獨立的位置上,即并不是純粹為經典疏證,疏證的目的是為批判程朱理學尋找到文獻上的依據,這在客觀上必然造成為義理而疏證的事實,即以義理為根本,疏證成了闡發義理的工具。正如戴震所直言此書就是“講理學一書”,而且是以批判程朱理學為目的的,因為這是“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孟子字義疏證》不得不作”,并強調此書為其“生平著述最大者”,可見,本書在客觀上便是以考據為工具以達到疏證義理之目的,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文獻學體例特征。
因此,戴震在本書的體例安排上把“理”列為首篇,作為最重要部分,目的就在于直指程朱理學“理”之要害。《孟子字義疏證》中重點所列并引經疏證之“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字眼,便是“程朱”等理學家經常提及并引證的非常重要的理學概念,在《孟子》中亦出現過,戴震正是目光敏銳地看到了這一情況,遂以疏證《孟子》字義而從概念的根本意義上來批駁程朱理學的概念體系和思想體系,可見,戴震在體例上如此精心安排,取決于其為批判宋明理學而闡發義理的目的。
綜上可知,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采用了明顯不同于其他文獻學著作的方式,先羅列出程朱等理學家在著述中經常使用的重要概念作為字眼,對它們進行新的解釋后用疏證的方法來相互疏通證明,疏證過程中采用自問自答形式與著者本身的高超的思辨能力相結合,體現出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理直氣壯的行文氣勢,水到渠成地歸納總結出這些字眼在儒家原始典籍中的用法和意義,再將這些用法和意義用來批駁程朱理學著述不符合儒家經典所蘊含的原始教義,從而達到批判宋明理學思想的最終目的。因此,疏證方式在本書中成為證明義理的手段和工具,是為證明義理而服務的,這種特征使本書的體例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不了重蹈“六經注我”的嫌疑,但畢竟并未影響到本書在眾多同類文獻學著作中獨樹一幟、備受關注和享有盛譽的現實。
參考文獻:
[1]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轉引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戴震.《戴震集?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