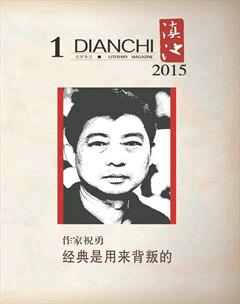昆明記(散文)
姚霏
追憶茶館花燈
二十多年前,昆明的茶館不像今天這樣,招展在熱鬧繁華的地界,供人們談生意、斗地主。那時候喝茶,也不像如今動不動就數十數百元一泡,進茶館類似有節制的顯擺。二十多年前的昆明茶館,一般蟄伏在老城的社區,場子都很蒼老,像不景氣的草臺班子的營盤,有戲臺和破鑼二胡等家什。茶是三毛錢一杯,還有茶官兒隨時續水,一杯茶泡一天也沒人白眼。場面不清雅,鬧哄哄的——戲臺上唱花燈的人,有時粉墨有時不粉墨,總之,是你方唱罷我登臺。
最當初不喜歡花燈,因為我覺得昆明話是拿給人說的,拿來唱就別扭了。甚至,某些說出來很好聽的昆明方言詞匯,被唱出來,感覺很是拿腔拿調,好像自己某種羞于示人的隱私被抖露了,尷尬,不自在,因此那時候,如果不是百無聊賴,我一般不往茶室里湊。
后來有個在社科院供職的朋友,是民俗文化專家,他對我說,作為昆明人,你不理解花燈,就相當于維也納人不聽歌劇,永遠都是個俗不可耐的局外人——這么說吧,如果京劇是中國的國粹,那么花燈就是昆明的“市粹”,以花燈在昆明的生成源起、發展流變和受眾之廣而論,作為地方劇種,它已經在這塊地盤上,深深地扎下了自己的根,成為了一種發端于斯并成長成熟于斯的傳統文化了。他還說,你揚言自己是搞文學的,但知道最高境界的文學是什么嗎?是那種能夠讓人獲得大悲憫大感動的作品,而地方戲曲,從越劇、粵劇、豫劇、川劇、評彈、秦腔、京韻大鼓、東北二人轉直至我們的花燈,原本都是直指人性、關注民間、能夠給人帶來大感動的藝術,你為什么要小視甚至排斥?
我凜然,但不置可否。直到商品經濟大潮把文化沖刷得七零八落,文學逐漸喪失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并日益與生活的源頭活水隔離和斷絕,最終淪為一種無病呻吟、把玩和擺設的時候,我才猛然警醒,開始關注被“正統文學”一貫不齒的戲曲,最終發現,戲曲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從來沒有真正斷絕過它內含的民間氣韻。
回頭尋找那種類似草臺班子營盤的社區茶室,卻再也不見蹤跡。漫步老城區,要么滿目青磚碎瓦,要么高樓林立,咿咿呀呀的花燈唱腔,像嵇康死后的廣陵散,早已成為昆明新城的絕響。
無奈在鬧市的茶館里翻書,讀到清末民初著名學者何海鳴的這樣一段話:“舊劇為詞不雅馴,然其始創,一舉一動、一發吭一案板有法則,要亦非易。要之,創始者之苦心不可泯也。”他所說的“苦心”,該當類似賈島“推敲”之嘔心瀝血吧?問題是,如今賈島不再,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淚”也已不再,那么花燈這種理應受到關注和尊敬的“昆明氣韻”,注定也將淪為追憶。
無處不飛花
在入選《全唐詩》的2529位唐代詩人中,韓翃的名氣不大不小,作品不好不壞,連個生死年月也不清不楚,所以一輩子的官兒,也做得不小不大。但在總計900卷的《全唐詩》中,他一人獨占第243、244和245三卷,卻也令人稱奇。
現在我們僅僅知道,韓翃字君平,出生在諸葛亮曾經隱居的南陽,雖然在天寶十三年就考中了進士,但平生干的卻大多是秘書工作,比如肅宗時,他曾經當過淄青節度使的幕府從事,說白了那就是私人秘書。都老朽了,才得到德宗賞識,最終官至中書舍人。唐代的中書舍人,雖說在皇帝身邊工作,干的還是“知制誥”、為天子擬寫昭告詔曰之類的文書,并無什么實權。不過,既然做的是秘書,就少不了迎來送往,所以后人在評價他的作品時,幾乎是眾口一詞:其詩多送行贈別之作,善寫離人旅途景色,發調警拔,節奏瑯然,但乏情思,亦無深致。真不知道韓翃那“大歷十才子之一”的名頭是怎么混出來的。據我推測,韓翃被列入“大歷十才子”,應該與唐德宗賞識其《寒食》一詩有關,據史載,正是該詩起首那句“春城無處不飛花”,讓德宗心花怒放,才立馬把他提拔到了身邊。
《寒食》后來當然也被收入《全唐詩》里了,但排名不理想,居然是他第三卷的第44首(全卷共62首)。全詩如此:“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用白話說就是:春天的長安城中,熱鬧繁華,處處飛花,寒食節了,東風吹拂著御柳。傍晚漢宮傳送蠟燭賞賜王侯近臣,裊裊的輕煙隨風飄散。
坦率地說,在韓翃的所有詩作中,這首詩應該是他的上等貨,但讓它的排名如此靠后,毫無疑問,清代奉敕編纂《全唐詩》的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楊中訥等大儒,是看出這首詩的味道不對了——這分明是一首政治諷刺詩!只不過韓翃的構思精妙,委婉含蓄,筆觸輕靈活潑,沒讓德宗皇帝看出來他是在影射肅宗、代宗以來宦官專權的腐敗和朝政的黑暗。
曹寅他們是怎么看出來的呢?這得從寒食節說起。
那寒食節,是為紀念春秋時期的介子推。時間是在每年清明節的前一天,節日那天,必須禁火、吃冷食。介子推是春秋時期的晉國人,又名介之推,后人尊為介子。在春秋那個亂世,晉獻公因為寵幸驪姬,就廢掉了太子申生,改立驪姬之子奚齊為太子。隨后申生被驪姬害死,公子重耳畏懼逃亡,先遭父親獻公圍堵,后被兄弟惠公追殺。介子作為隨行護駕的5人之一,沒少遭罪,比如重耳快被餓死的時候,介子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來熬湯給他喝,是為“割股奉君”……重耳在外逃亡19年,備受風餐饑寒與生死磨難,終于苦盡甘來,重返故國做了晉文公之后,發誓要好好報答介子。誰知介子不是戒指,他不愿顯赫,就跑到綿山躲了起來。晉文公鐵了心要介子出山共享榮華,于是下令放火焚山逼他出來,但同樣鐵了心的介子卻寧愿抱著樹被燒死。晉文公重耳深感愧疚,遂改綿山為介山,并立廟祭祀,由此產生了“寒食節”。對于介子“割股奉君”而隱居“不言祿”之壯舉,后人深為贊嘆,故而歷代詩家文人,都留有大量吟詠緬懷的詩篇——對于曹寅他們而言,當時許多有骨氣有節操而且聲名顯赫的漢人,都不愿出仕清廷為官,寧愿像介子那樣隱居深山,你說他們又怎么敢把韓翃的《寒食》排在其作品集的顯眼位置呢?
這么一解釋,大家也就明白了,我說《寒食》是一首徹頭徹尾的政治諷刺詩,那可不是無稽之談:此詩短短四句,其中的“春城”指春天的長安城,“御柳”是御苑里的柳樹,“漢宮”當然說的是皇宮,“五侯”即宦官寵臣。既然這天是寒食節,必須的禁煙火吃冷食,宮外一片漆黑,為什么宮里卻能“傳蠟燭”給“五侯”家,以使他們燭光亮堂,而且還可以輕煙裊裊地熱炒爆烹?這不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又是什么?
據唐詩研究專家考證,此詩是寒食節那天,韓翃在長安街頭漫游,暮色降臨時,被宮里閃出的燭光和官宦寵臣之家的煙火給刺激了,突然想起早年的楊貴妃和她哥哥楊國忠倚仗皇帝的恩寵,作威作福禍害天下,受不了啦才憤而提筆一氣呵成的。可笑的是,這層并不深奧的意思,唐德宗愣沒給看出來,反而給其作者韓翃升了官。還有野史杜撰,說曹寅曾與同僚戲言:“春城無處不飛花?楊花乎?柳絮乎?無非殘花敗柳,礙人吐納觀瞻,何美來哉!”
如果說野史戲言不足為憑,那么唐詩研究專家根據韓翃的生平及創作年表考證出來的結論,應該靠譜。也就是說,韓翃的這首以“春城無處不飛花”開頭的詩,與楊貴妃和她哥哥楊國忠海水間接有關。所以,在“春城”一詞事實上已成為昆明特指的現在當今眼目下,每每艱難行走于昆明街道,看到藍色圍擋上寫著這樣的標語,“春城無處不飛花 美麗昆明是我家”,我都會忍不住哈哈大笑:還以為你們都是楊貴妃的娘家啊?
龍頭村的哭腔與呻吟
我不應該寫這篇文章。倒不是我與時俱進了,而是往事不堪回首。我寫過蔡鍔將軍故居,寫過王九齡(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故居,以及袁嘉谷(清末云南唯一狀元)故居,結果,它們現在都成了高檔飯館,每日肥頭大耳的狐朋滿座。我還寫過一篇題名為《回望昆明老街》的文字,但沒過幾年,那些青石板鋪就的老街就沒有了,要么變成了錦繡大道,要么矗立起了高樓大廈。一支筆肯定干不過推土機和挖掘機,所以對昆明的文化古跡而言,我即便不是螳螂,那也是不祥之身。
那么就不要把我以下的文字當作文章,甚至不要當成文字,且當呻吟。
因為這涉及到昆明龍頭村,涉及到西南聯大,涉及到朱自清、聞一多、金岳霖、馮友蘭、吳大猷、陳夢家、趙蘿蕤、梁思成、林徽因等文化大家,他們都曾經被我們當成神一樣的人物。我可以自作孽不可活,但不能禍害人家。我的意思是,不能因為貪圖自己痛快,就真把人家的老屋給毀了。雖然眼下國人對什么都已經喪失了敬畏之心,我也從小就會高歌“從來就沒有什么神仙皇帝”,但馮友蘭、梁思成、吳大猷們的確不是“神仙皇帝”,他們只不過是延續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血脈的前輩先人。對神你可以不敬畏,但對先人就不可以,否則依照泱泱華夏幾千年的遺訓和傳統,不敬先人,我們就連人都不能算。而毀掉人家的老屋,從“憑吊”的角度說,類似于河南某地的平墳事件。這么樣子干,就算不是有意而為之,或者被迫而為之,你說咱還算個什么東西?
所以誰要說我這是一篇文章,我就真有可能去刨他家的祖墳。
或曰:那你就呻吟成個調調唄。好吧,這個可以有。
林徽因小姐1940年9月20日給好友費正清寫信,說:“我們正在一個新建的農舍中安下家來。它位于昆明市東北八公里處一個小村邊上,風景優美而沒有軍事目標。鄰接一條長堤,堤上長滿如古畫中那種高大筆直的松樹。我們的房子有三個大一點的房間,一間原則上歸我用的廚房和一間空著的傭人房……這個春天,老金在我們房子的一邊添蓋了一間‘耳房。”沒想到吧,70多年后,你和夫君梁思成親自設計并參與建設的老屋,當年的確沒有軍事目標,但眼下馬上就要成為拆毀目標了!
情圣金岳霖啊,你作為中國現代哲學和邏輯學的創始人,不會不明白老子所云,“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建筑的靈魂在于劃分空間,而空間的合理規劃才能使人與環境有了和諧統一,使人能在空間里有了安心的家的感覺。可你為了一段絕望的愛情,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不遠千里追隨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林徽因而來,還在人家的“一顆印”旁違章搭建了一個低矮的偏廈,并且故意不設獨立外開的門——其門設在梁家的客廳內——每次出入,必須穿過梁家的主客廳,這在外人看來,你其實是與梁氏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君子相攜,共度亂世,你的曠世真情固然令人唏噓,但你終身未娶,又何苦來哉!過不多久,當大型挖掘機轟然而至,歷史價值也好,情感價值也罷,都將化為一縷黃霧,隨風飄散,連你們的游魂也追趕不上。
梁思成大師啊,作為上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建筑學泰斗,你深知建筑里寫滿了歷史,建筑里勾勒著民族的文化,建筑就是一個活化石,是一座城市的博物館。當年,為保護北京的古建筑,你上下游說,八方奔走,終于使包括天安門、故宮在內的許多不可復制的中華古建筑得以有效保護。但你能否料到,70多年后,你親手設計的昆明龍頭村小屋,將在拆遷大潮的滾滾洪流中,變成一片凋謝的殘落,連你那名垂千古的老爸梁啟超也保佑不了你啦,世事難料吧?
馮友蘭先生啊,你在《三松堂自序》里是這樣寫道:“在昆明受到的戰爭直接威脅是空襲。于是人們開始考慮到選擇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遠離軍事目標。人們就開始向城外遷移,用當時的話說,叫‘疏散……后來又疏散到離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龍頭村。這個村子是昆明郊區比較大一點的集鎮,又叫‘龍泉鎮。”你一代大哲,怎么就沒料到今日的“地襲”遠比當年的“空襲”強悍!
羅常培所長啊,1941年8月26日老舍從重慶飛抵昆明講學,你為什么要陪同他到龍頭村居住,讓昆明北郊的山水把一代文豪搞得像情癡那念茲在茲,還寫了系列散文《滇行短記》……當然,后來老舍先生投昆明湖自盡,與你無關,更不是昆明的過錯,名稱相同而已,但你敢肯定“昆明”二字,沒有在老舍先生縱身一躍的那一刻,在其內心里激蕩起了一絲絲的漣漪么?
還有朱自清先生,我們從小背誦你的《背影》,但現在,在昆明龍頭村,我們或許又將只能最后再看一眼你故居的背影了。從你父親的背影上,我們讀出了磨難,但從你故居的背影上,我們將親眼目睹一種難以抗拒的災難。當然,你故居的災難并不孤單,因為所謂的“修舊如舊”的“龍泉古鎮”一旦破土動工,你的鄰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址(含馮友蘭舊居)和中國營造學社舊址等等,都將與你同行,或者淪落成泥,或者云散煙消。
惜乎!悲乎!據不完全記載,在西南聯大遷入昆明的8年時間里,為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居于城內的聯大教授不得不疏散至城郊的龍頭村、司家營、車家壁等處。這里的呻吟不涉其他,僅一個小小的龍頭村,就先后居住過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金岳霖、馮友蘭、吳大猷、陳夢家、趙蘿蕤、李濟、梁思永、李方桂、董作賓、吳定良、丁聲樹等35位院士。他們暫居于此的象征意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魂魄曾經在這里留存。一旦“龍泉古鎮”華麗誕生,那么昆明的文化記憶,注定將被徹底抹去——豪華的招魂,向來都只能招來更貪婪的商客。
最后再鄭重聲明:上面的文字不是文章,甚至不是文字,只是呻吟,也可以稱之為哭腔。因為近年看多了“修舊如舊”的新造古跡,活像一片片人工修復的堅硬的處女膜,還都能招致大批生猛的回頭之客,我每每就有欲哭無淚的沖動。又怕不祥之文將給龍頭村以及曾經居住在那里的先賢大德們招致禍端,所以哀哀地發點兒嗚咽之聲,如此而已。
街名奇味
我說過,街道是有記憶的,有的時候,它的記憶或許比人類的記憶更加具象和久遠。以昆明為例,盡管它直到民國初年才有自己獨立的第一部地方志——《民國昆明市志》,但打那以后,昆明便以文字的方式,不僅自己記住了自己,還隨著歲月的流逝,在后人的心里日漸豐滿和親切。
據《民國昆明市志》載:民國初期的昆明“東至東莊,界大波村大樹三營等處;南至土橋村螺螄灣,界豆腐營何家營等處;西至三分寺,界黃土坡;北至蓮花池,界北校場;西南至潘家灣、瓦倉莊、大觀樓;東南至滇越鐵路總車站,地藏寺。東西廣5.4里,南北袤6.3里……行政上分為第一區、第二區、第三區、第四區及商埠第一區、商埠第二區,共計六區。”
參看志書可知,上述六區各分若干段,各段又下轄街巷若干,由此構成了一個形象、富于文化意味并洋溢著濃烈的人情味兒的觸手可及的昆明。試列第一區和商埠第一區、第二區所轄街巷如下——
第一區分十二段轄街巷103條。第一段轄正義東街、正義西街、南月城、南大街、高山鋪、天寧寺巷、永升巷、清真寺巷、康齡巷、小火巷。第二段轄文廟街、景星上街、甬道街、文明街、甬道橫街、東捲洞巷、西捲洞巷、海天閣巷、慶余巷、郭家曙光巷、質當巷、草紙巷、玉泉巷。第三段轄龍王廟街、景星下街、萬鐘街、通城巷、吉祥庵巷、石灰巷、耳巷、尤家巷。第四段轄南城廟、龍井街、華興巷、龔家屯巷、呂祖巷、華陽巷、小土主廟巷、龍井巷、涌泉巷。第五段轄光華街、甘公祠巷街、興隆街、沙脂巷、石板巷。第六段轄西院街、如安街、五福巷、大廠巷、升平巷、石門坎巷、月宮巷、高石坎巷、圍桿巷。第七段轄菜市街、東院街、三牌坊、南正街、宏昌街、慶余巷、居仁巷、四知巷、邱家巷、孝子坊巷、大銀柜巷、小銀柜巷。第八段轄象眼街、威遠街、勸學巷、大樹巷、六合巷、小柳樹巷、三臺巷。第九段轄青龍巷、財神巷、白鶴巷、雙水塘、石門坎巷、豆豉巷、火腿巷、水井巷。第十段轄繡衣上街、東城腳、穿城巷、啟文巷、福昌巷、豆角巷、汲泉巷。第十一段轄南昌街、繡(素)衣下街、團城角、白果樹巷、新平巷、財神宮前巷、財神宮后巷。第十二段轄登什街、慶云街、端士街、大柳樹巷、云興巷、太平巷、翠花巷、際春巷、豆菜巷。
商埠第一區分十六段轄街巷72條。第一段:珠市下街、祥云上街、氈子街、氈子橫街、寶善西街、廉泉巷、福生巷、崇德巷。第二段:珠市上街、同仁巷、三市街、鳳凰橋、玉溪商業場、銀珠巷、胭脂巷、鹽店巷。第三段:順城街、打帶巷、崇仁街、云龍巷、孚佑宮、靜地庵。第四段:燒珠橋。第五段:敦義下街、雞鳴橋、北岳廟、大梵宮、三益里。第六段:敦義上街、羊市街、金碧街、教子巷、知化巷、金馬巷、碧雞巷。第七段:東四上街、魚課司街、花椒巷。第八段:東四下街、西寺街、石板(?)鋪。第九段:書林街、奏功橋、司馬第巷。第十段:云津市場。第十一段:廣聚街、崇善巷、德磬巷、香油巷、陜西巷。第十二段:巡津下街、后新街。第十三段:新成鋪、三義鋪、巡津上街、護國下街、泰安巷。第十四段:木行街、維新街、護國上街。第十五段:翠花街、頭道巷、二道巷、寶善東街。第十六段:營門口、北后街、端仁巷、履善巷、祥云下街、南強街、正義街、鼎新街。
商埠第二區分十段轄街巷41條。分別是第一段:岔街、后岔街、重關。第二段:聚奎街、三元上街。第三段:三元下街、鹽行下街、白塔巷、石家庵巷。第四段:云津街、鹽行上街、塘子巷、太和上街、得勝橋北岸。第五段:太和下街、福德街、咸和下街、交三橋、楊家莊。第六段:咸和上街、吹簫巷、賣米巷、打草巷。第七段:東正街、金牛街、豬集下街。第八段:豬集上街、丁字街、敷潤上街、米廠心。第九段:桃園街、敷潤下街、靈光下街、薛家巷、南河埂、豆腐巷、米線廠。第十段:靈光上街、羊塢里、北河埂。
其他,第二區分十九段下轄160條街巷,第三區十八段下轄91條街巷,第四區六段下轄21條街巷。
我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地羅列這些街巷及其名稱,是因為即便你什么都不說,僅就這些街名,都已經呈現和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充滿人世情懷的立體的昆明了。
這些街還告訴我,當時昆明已經是個擁有488條街道的大城,而且各街巷自有歸屬,和諧有序,無論精神物質,市民但有所需,總有一條“望文生義”的街巷在等著你。比如,你想買什么?草紙?胭脂?石灰?豆豉?火腿?氈子?珠寶?食鹽?花椒?香油?米線?豆腐?……不都有以這些物什命名的街巷么?盡管直奔那兒,準保你錯不了。要買豬雞牛羊,只需上豬集街、馬市口、羊市街、三市街去也就是了。要典當什么,則徑投第一區第二段的質當巷去。甚至,賣魚、賣鹽的人,也都明白自己應該去什么地方納稅:魚課司街和鹽行街。
至于精神方面,無論需要心靈的洗滌還是尋找靈魂的依歸,節孝巷、敦義街、教子巷、知化巷、德磬巷、康齡巷、慶余巷、勸學巷、四知巷、孝子坊巷和清真寺巷、文廟街、龍王廟街、靜地庵、呂祖巷、華陽巷、小土主廟巷、甘公祠巷、財神宮巷、北岳廟、大梵宮……等各街巷,你去造訪不去,它們都在那兒。
剪徑之城
很久以前,因為不知道自己是個被蒙在鼓里的納稅人,感覺相當羞愧。后來知道了,其實無論消費什么,只要不以偷搶為生,想活著就得花自己掙的錢去購物,那么我就是個光榮的納稅人,從此很為自己自豪和驕傲。然而,在8月14日這天,我的自豪和驕傲,被昆明某報頭版頭條的新聞給徹底毀了,整整一個下午,我都沉浸在詫異和辛酸里,備受煎熬。
這個新聞的標題是:《時機成熟漲停車費收擁堵費》。字體非常的粗黑壯大,尤其后面8個字,每個都有我的眼珠子那么大!而前面4字,是把“時機”摞在“成熟”之上,疊合起來與“漲”字一般大小。也就是說,“時機成熟”那4個字的組合,略等于我的一顆眼球。
原本,這種新聞不應該影響我的心情,因為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學了車準備領本駕照炫耀一回時,就被當時相當負責任的車管所領導判了極刑:終生不能駕車!那領導原也是一個哥們,可他說我患有一種似病非病的病,名稱很古怪很難記,大意是約十萬個人中,就可能有一個人會出現“間歇性思維停頓”,短的1-2秒,最長可達5-8秒。“以后的道路會越來越寬廣,高速公路也將越來越多,車速必然也越來越快。如果正開著車的時候你的大腦突然出現空白,1秒鐘都會要你的命。”沉重的他說得很鄭重,年輕的我聽了很憂傷,因為那是實情,我的確具有突然成為一個白癡的潛質……很多年之后,正如那哥們所言,咱們城市的道路是越來越寬廣,高速公路也越來越多了,但我始終沒敢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比如自駕出游,甚至開車上班——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打算買車。
然而8月14日昆明某報公布,漲停車費和收擁堵費,預計于10月份向社會公布實施,那就意味著,一個多月之后,我將喪失繳納上述兩項費用的資格!這就像一個練成了好武藝的人,沒人愿意與你切磋,或者一位開了悟的和尚,卻無前輩高僧給予印可,這樣的被剔除,是多么的郁悶與難堪?
于是我把這條被歸置在另一個整版上的頭條新聞逐字逐句鉆研,結果發現,雖然主題還是《云南省“十二五”節能減排規劃》出臺了,為降低能耗和解堵,是到該考慮收取擁堵費和提高停車費的時候了。但通篇要點卻是:怎樣利用陽光發電?廢舊物品回收后該如何利用?為什么公共機構必須一律“拋棄”白熾燈?以及以后每年建設10條公路ETC收費系統……顛來倒去地看,總感覺這里面很有點李逵與李鬼的意思,不由人不浮想聯翩。
為什么不是張三和李四而是李逵與李鬼呢?那得扯到施耐庵的《水滸傳》——作為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該書里有個詞語出現的頻率之高令人動容,那就是“剪徑”。
“剪徑”的意思是攔路搶劫,本來相當令人不齒,但施耐庵大約是為了塑造梁山好漢們的豪邁威武,就對它特別寬容,比如第43回的回目就叫《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說的是李逵從梁山回家,要接自己的母親上山享福,不料半道上殺出個叫李鬼的,假扮他黑旋風在山道上劫財。假李逵哪是真李逵的菜,只三兩下,李鬼就跪地求饒,說他尚有九十歲的老母,殺他就是把他和他的老母也一塊殺了。李逵憐其孝心,便饒了他,而且還給了他一錠銀子讓他走……至于后來李鬼及其妻皆被李逵所殺,那是因為這兩口子太過歹毒,其中另有曲折,在這里我無暇分解,因為我必須把自己讀新聞而聯想到李逵與李鬼的緣由說出來:所謂“交擁堵費”,實乃本人平生聞所未聞,按正常邏輯,你把路挖爛了、圍窄了,給弄擁堵了,耽誤了我的時間,影響了我的工作與生活,那應該是“發擁堵費”予以補貼安慰才對。現在倒好,把正常邏輯完全扭反過來,聽上去就奇了,感覺那收擁堵費基本就等同于剪徑,并且還是像書里虛構出來的那樣,李鬼假冒李逵之后,還公然“剪”李逵的“徑”,其間的無知無畏與無厘頭,恐怕也只有施耐庵才幽默得出來。
眾所周知,古人稱大道為路,小道為徑。所以“剪徑”這種行為只可能發生在偏僻的小道上,剪徑者的規范用語是:呔!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打此路過,留下買路財!在《水滸傳》第六回《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罐寺》中,瀟灑帥氣并且已經在身上紋了九條龍的史進,因為這句話沒練順溜,加之赤松林那個地方,像一個多月以前的昆明一樣,雖然道旁的樹不少,但論寬度,好歹也不能稱之為徑,所以九紋龍史進的剪徑行動相當失敗,連規范用語都沒說全乎就動上了手。
要說赤松林這個地方還真有特色,除了九紋龍,連威猛過人的行者武松,也在那里干過剪徑的勾當,應該是出于同樣的原因,武二郎同樣也沒有完成剪徑的全套動作。不過無論如何,在施耐庵筆下,所有梁山好漢的剪徑行為,都是可圈可點毫無瑕疵的。就像昆明現在先在媒體上公布要漲停車費和收擁堵費那樣,武松史進等無所顧忌的好漢,都是先自報家門,然后才開始剪徑,這讓幾百年之后的我們都覺得他們很拉風。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大家都向施耐庵老前輩學習,端正態度,不以褒貶論漢語(比如不要先入為主,認定“剪徑”是個壞詞)的話,那么我們應該熱烈慶賀。2012年10月,中國的首座剪徑之城即將光榮誕生,而它就是咱們早年被稱為春城的昆明。
歡慶之余,我還是有些擔心,雖說這些年,咱們在防盜籠拆了一半不到的時候,地鐵工程上馬了;地鐵才剛開修,雨污排流工程開工了;雨污排流工程尚在進行,為“創造全國衛生城市”,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拆遷、挖路、栽樹;“創衛”成功之后,為打造全新的“橋頭堡”,據說算是全國第四大規模的“長水機場”也急忙啟用,甚至都來不及給這個機場的歸去來者們如何訂立收費標準;也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昆明的老大換人了,后來者愛花不喜樹,于是動用龐大的挖掘隊伍,開始了對全市道路重新開膛破肚、刨樹種花,說是要用3到5年時間,讓昆明的兩百多條街道都成為“景觀大道”——經過秘密啟動的圍擋挖路和刨樹種花,近半個月之后,市民們才發現,原來把“路”變之為“徑”,那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現在,眼看就要獲得剪徑之城的榮光了,萬一猝遇什么“不可預測的因素”,像20多年前我那位車管所的哥們所預測的那樣,“道路越來越寬廣”了,那怎么辦?“徑”復成“道”,還怎么剪?或者,某些心胸狹窄、小肚雞腸如秋菊者,要一根筋地認為,自己分明是被強奸者,都還沒來得及喊冤,憑什么反要繳納強暴者的體液損失費和體力透支費,因此堅決抗交,那又怎么辦?
莫非,學那“梁山妖艷第一”的母夜叉孫二娘,去開個酒店賣人肉弄錢?那也太不成話了吧?須知,古往今來的剪徑者,雖然都基本有其固定的路線,但絕不會專門開個店來干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孫二娘和她老公張青在孟州道十字坡開酒店賣人肉包子,也并不主動出擊,只對進店的人下手,讓人有進無出,這的確很強盜,但人家有固定的店面,就不能算是正宗的剪徑者。咱們就算學得了他們百分百的手段,要自稱剪徑高手,那也太牽強,經不起推敲。
更何況,昆明也不是宋徽宗時孟州道的十字坡。
想通了這一節,我的郁悶與難堪之情略有緩解:如果都不興玩剪徑了,那咱和你們開車一族,豈不是也有了同樣的尊嚴。
蓮花池記
從1985年10月到1986年底,我托人在蓮花池邊租了間民房,搬去獨自蝸居。
房東的大名,現今已經忘了,只記得當時都叫他老五。老五媳婦是關上那邊種菜的,她習慣上把老五叫做“老藕”,因此我們也習慣叫她“藕嫂”。藕嫂長得短粗短粗的,真的很像是一截飽實的藕,任誰都能大面積感覺到她的潑辣熱情。比如她說:“你們不學昆明話咋個行,買菜都要吃虧!”那么我們就非得跟她“疑鵝三俟藕”地念叨不可了,以至于事隔多年之后,我講昆明話一開腔就別扭。
老五沒讀過多少書,但他自己說他崇尚文化。據我后來所知,自古至今的文化人,他就只崇拜一個明末才子吳梅村。吳梅村那么多作品,老五也只推崇一首《圓圓曲》——這首長詩,老五能從首行“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背誦到最后一行“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一字不拉,還抑揚有調頓挫有情。末了少不得言歸正傳:“格曉得?陳圓圓就是在這地兒淹死的!你把窗子打開,我指給你看她淹死的塌塌!”初始我很驚乍了兩回——按他所指的準確位置,那是在我的窗下了!就算當年還沒這房子,陳圓圓也是站在咱們這墻腳起的跳——后找書來對照,才發現一條鐵路把蓮花池割成兩半之后,傳說中陳圓圓投的是那邊那半個湖。但老五說:“啥子破書!絕對是整錯了!”言之鑿鑿。每逢這種時候,藕嫂總是氣得呼呼:“放你的賊屁!書上還會整錯噶!你小砍頭的腸子還花哦,咋個不說人家陳圓圓是跳你家水缸淹死的!”老五喏喏。我目測他們的胳膊,估計如果放手一搏,老五對付藕嫂的難度很大。
老五也崇尚娛樂運動,但只有一項:麻將。那時候麻將與娛樂還沒公然沾邊,它有個不分青紅皂白的渾名叫做賭具。賭具這個詞實在不好聽,藕嫂于是對麻將活動滿懷仇視,偏老五對從事這項運動熱愛太深,雖經藕嫂多次現場“捉贓”并施以老大耳括子教育,無奈老五像迷戀做賊似的癡心不改。某個周末,藕嫂回娘家,老五又邀約了三個賣鱔魚的在家里娛樂。天熱,氣氛也熱,就開了窗,就“小搞搞”——賭二角四角人民幣輸贏,照老五后來的話說,那晚上他是撞了陳圓圓的魂了,從下午七點到晚上十點,他居然一把牌也沒“福”,直到十點過“藕分”,他才撞到個清一色夾二筒自摸,氣怒驚急之下,他花了大力氣把那“二筒”砸在桌上,不料“砰”的一聲,牌被砸成兩截!他的座位面對著窗,牌的前半截就飛出窗外,落到湖里去了,以至于他中指拇指死死夾住的,只是“一筒”,是“炸福”!“蓮花池的水那么臟,你還真跳下去摸那兩筒的一半呀你?”事后我問他。他說:“你格曉得,我當時連砍人的心都有啊!幸虧嗆了口臟水,才清醒。”老五自那以后再不摸麻將牌,弄得藕嫂納罕不已。
后來我決定離開昆明,到外面闖蕩世界。離開蓮花池時,我告訴藕嫂:哪天蓮花池的水干涸了,老五找到了那“一筒”——也就是那“兩筒”的前半截——他就會再度崇尚麻將娛樂的,你可要當心。
藕嫂于是擔心蓮花池的水干涸,據說終日惴惴。
我得以近距離地接觸蓮花池的時候,蓮花池早就沒有了什么綠樹成蔭、繁花似錦和亭臺樓榭、小橋流水,它只是夾在師大、民大、昆工、蓮花小學和云大北院之間的兩個開始污濁的水潭——本來應該是一潭的,被一條米軌鐵道給劈成兩半了。潭里漂浮著水葫蘆、浮萍,就是沒有蓮花。水里有魚、黃鱔,還有些不明真相的小生物。湖邊不時有人垂釣、洗菜,晚上還有人偷著談戀愛。因為附近居民習慣了把垃圾傾瀉到水潭里,所以周圍的氣味比較奇怪。
在1985年底到蓮花池邊租住房子之前,我早就知道了關于陳圓圓、李廣田與這個赫赫有名的池塘的故事,并且心向往之。去租房子時,房東也說,早些年,陳圓圓因為對自己名譽上的老公吳三桂越來越絕望,最后干脆跳到蓮花池里自己把自己給淹死了,不過你不用怕,這里的陳圓圓是個好女鬼,不害人的。與其說房東是在揭房子位置的“短”,還不如說是在做誘惑廣告:誰不愿意與曠世美人的香魂作伴呢!
在蓮花池邊蝸居那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始終困惑于一個問題:李廣田處身于一個污濁的時代,選擇在這里淹死倒也罷了,可陳圓圓那么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尤物,怎么會選擇如此一個水污景陋的池潭里自溺呢?
很多年之后,我從外地返回昆明,故地重游,發現那個被叫做蓮花池的兩個水潭已經無影無蹤,在我當年租居之房邊上的那個水潭上,矗立起了一排七層高的住宿樓。陪我重游故地的朋友指著其中一幢告訴我,“那一個房間,就是當年馬加爵的宿舍”。我無語,但終于明白,滄海桑田啊,當年陳圓圓噗通一聲跳下去的時候,蓮花池的水一定還是清凌凌的。
但我又疑惑了,即便蓮花池被商品經濟大潮給沖刷掉了,陳圓圓總不能像流星一般消失在昆明的煙塵中吧?朋友說:“從這里,沿著鐵路直走一兩公里,是新修的蓮花池公園,陳圓圓移居那里了。”
在這個自然景物越來越凋敝的時代,陳圓圓自然可以移居,我這樣想著時,眼前突然浮現出一種古怪的、諢名叫做“水耗子”的小生物來——學名叫什么不知道,但在當年的蓮花池里數量眾多,我把它們歸納為不明真相一族,尚在蓮花池邊租住的時候,我就常常拿它們來嘲笑堂堂大秦帝國的宰相李斯見識也有限,他把老鼠分為“倉鼠”和“廁鼠”其實偏頗,至少“水耗子”也該納入其中——此時想到它們,倒不是要像李斯那樣以老鼠的處境論述人之命運,而是想知道,它們都到哪兒去了?不管新修的蓮花池公園如何亂真,修建者大約都不會把“水耗子”們也遷移過去的吧。如果它們依舊想存活在陳圓圓的傳說里,自行遷徙,那么會不會在越來越錯綜復雜的城市大街上迷途?
據《云南府志》記載:“商山之麓皆桃林,下有冷泉,名蓮花池。浴之可去風疾”。也就是說,早在明朝洪武年間,蓮花池就已經是滇中勝景了。據說,那時的蓮花池中有五個龍眼,隨時清泉涌流、碧波蕩漾,故有“龍池躍金”之譽。但現如今,嚴格意義上,蓮花池之于昆明,像許多古建筑和老街一樣,事實上如今都只留存了一個其實不符的名詞。
雖然我們以絕對經濟而宏觀的氣魄,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于2008年就搞出了眼下占地81.7畝的蓮花池公園,并定位為“歷史文化名園”。據說,為了尊重歷史和注重文化內涵,其間特別營造了美輪美奐的安阜古韻、五華聚秀、四面荷風、妝樓倒影、商山夢痕、云廊煙柳、龍池耀金、冷泉映月……等精致美景,但這些斧鑿出來的、江南水鄉特有的清秀風韻,當真能夠體現歷史上蓮花池的“十畝荷花魚世界,半城楊柳拂樓臺”么?徜徉于“集景式”的安阜園門、玉石玲瓏、翠海妝樓、龍池躍魚、蓮池沉香、高山桃林、永歷遺冢、長橋波飛、荷月黃昏、盛世花潮,誰還能感受到那么一星半點真正的歷史文化氣韻?
但必須承認,在嶄新的蓮花池公園里憑吊曾經的蓮花池,是一樁比較滑稽的事情,在一個合伙顛覆歷史和文化的偉大時代,人工秀出來的“三山一水”,或許比真正的林木參天,以及一池碧波與蕩漾在碧波間花紅葉碧的一池蓮花,更具誘惑。
這么說吧,無論怎樣旖旎通幽的自然景觀,若無人文情愫的投注,都不可能成為生命力強大而久遠的風景。事實上,昆明的蓮花池之所以名揚宇內,其實也得益于陳圓圓和吳三桂的驚天愛情。有史為證:沖冠一怒為紅顏之后,成功當上了“平西親王”、從上海關一路征戰到昆明的吳三桂選中了蓮花池,在里面專為寵妃陳圓圓興建“安阜園”作為住宅。園內,亭臺樓閣、水榭假山、奇花異卉、書畫奇珍應有盡有。吳三桂還令人修筑棧道,由五華山直通蓮花池,供其往來于美人與政務之間……據說,吳三桂身亡之后,陳圓圓自沉于蓮花池,即葬池畔。越明年,池中曾放并頭蓮——雖然只是傳說,陳圓圓死后究竟艷骨葬于何處的爭論,至今也沒有停息,除了流傳較廣的昆明之說外,還有上海說蘇州說四川說等等,很無聊也很“商品經濟”,但沒人能否認,風光旖旎的昆明,曾經是陳圓圓的第二故鄉——自清順治16年起,她便跟隨吳三桂來到昆明,于蓮花池畔生活了19年。四季如春的昆明,伊甸園般的蓮花池,記載著陳圓圓幽怨一生的喜樂,也記載了陳圓圓與世永訣的悲涼。正因為這段歷史,鑄就了蓮花池作為風景的盛名——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通過了解這段歷史,才認識了蓮花池,而蓮花池也因此才具有了穿越時空的力量和令人難以抗拒的磁性。
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地鋪排陳圓圓和吳三桂與蓮花池的故事,是想說,雖然歷史上那個曾經的蓮花池已經不復存在,昆明現在的蓮花池公園與我們記憶中的那個文化底蘊厚重的“蓮花池”絕不等同,但正如由于史料的缺失和沒有陳圓圓墓葬的文字記載,中外文史工作者長期以來為探尋這位一代尤物的蹤跡和魂歸何處,雖做了種種努力卻依然“茫茫一片都不見”,最終成為難解之謎,可蓮花池里陳圓圓的梳妝臺、衣冠冢和永歷帝陵等遺跡,依然成了最具亮點的自然與人文風景,而蓮花池,也因此成為昆明自然風景與人文地理的“雙料勝地”一樣,如今公園里那許多虛假的文化勝境,雖然再怎么亂真畢竟都是虛幻,但再過數十數百年,歷經商品經濟時代風雨的洗滌,積淀了足夠厚重的底蘊與滄桑之后,誰又能斷言,它們不能成為昆明的另一道歷史文化景觀?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蓮花池公園里憑吊曾經的蓮花池,懷想冷泉的“龍池躍金”,雖不乏文化意義,但卻不失做作。
重歸升庵祠
1992年至1993年間,在昆明升庵祠的幽遠和寧靜中,我獨守一座飛檐雕欄的大殿,完成了六本刀光劍影的武俠小說。另外一座殿宇里,住著蔡師和蔡師母,以及一條大得像小牛的狼犬。蔡師母是個虔誠的在家居士,吃素,臥室里設得有一個小佛龕,每日早晚必拜的,拜前也必焚香沐手,弄得蔡師不得不學樣,久了,也吃起素來,吃得漸漸慈眉善目。只有我和那條名叫“雄獅”的狼犬不習慣——“雄獅”無葷不食,我是葷素均沾,以至于在一段時間之內,我覺得自己只比狼犬稍微善良一點點。
升庵祠是一座三院三殿的中式庭院,最重要的一個殿堂里存著楊升庵的大量手書真跡,平時上著兩把大鐵鎖,沒有特別的介紹信,一般不讓外人進入。我仗著近水樓臺,得以隨時出入,因此對楊慎是格外的景仰。升庵祠緊鄰徐霞客紀念館,中間沒門,只有一個小小的拱洞,也歸我們三人一狗看管。徐霞客紀念館的規格和升庵祠差不多,也是三院三殿,只是正院中多了塊照壁一樣的巨碑,上面刻錄著徐霞客的《碧雞精舍記》,每座殿也都鎖著,除了每周一次去擦擦窗撣撣灰,我們照料得并不太多(歷史上徐霞客也許比楊升庵偉大,但他與云南的淵源的確沒有后者深厚),只有“雄獅”最忠于職守,每日都要花一半時間過去察看動靜。
想一想吧,與徐霞客和楊升庵這樣兩位大名家比鄰而居,誰敢懈怠?因此除了吃飯和心煩之時聽聽蔡師母唱經,其余的時間,都被我用來寫字了,所以一年寫出六本書,別說讀者感覺蹊蹺,就連我自己,也大為意外。在后來浪跡天涯以筆謀生的歲月中,每念及此,必因感慨而至羞愧。
一晃,十數年匆匆過去。日前回“家”,發現蔡師和蔡師母已經退休,“雄獅”也已不知所終。只是祠堂依舊,霞客升庵二公塑像依舊,庭院中的花草樹木也依舊,它們的守護者,已換成兩位英俊的年輕人了。
責任編輯 張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