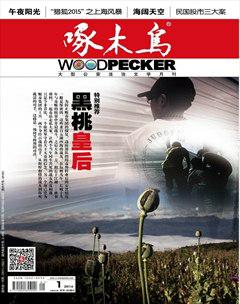你不是向日葵
韋延麗

卡點(diǎn)設(shè)在向日葵地旁,我拉了拉警服,與地里朝向太陽的向日葵一樣,情緒飽滿,斗志昂揚(yáng)。
那輛三輪摩托車便是從凡·高《向日葵》畫里駛來的,當(dāng)我給它敬禮時(shí),車后廂里的孩子正歪著葵花一樣的腦袋,認(rèn)真數(shù)著車前懸掛的葵花:“1、2、3、4、5。”
車上是一對(duì)父女,父親黝黑的臉上布滿溝溝壑壑,一看就是老實(shí)巴交的山里人。此時(shí),這山里人正努力撐起臉上笑的幕布,畢恭畢敬地向我敬煙。
我沒有接煙,而是低頭飛速開罰單,想趕在師傅到崗之前,獨(dú)自處理完這起違法載人事故,以證明自己的能耐。
就在我將罰單遞給他時(shí),這個(gè)很高很壯的男子,驀地拉著我跪了下來,仿佛一座山在我面前轟然垮塌。我看到了十多年前父親淚水漣漣的臉,是的,也是在這樣葵花盛開的季節(jié),騎三輪摩托送我上學(xué)的父親為了減免罰款,給當(dāng)時(shí)執(zhí)法的警察長(zhǎng)跪不起。如今,我仍記得,當(dāng)時(shí)警察的臉跟旁邊的向日葵一樣,面向陽光,卻將可憐兮兮的父親丟進(jìn)了身后的黑影。如果當(dāng)時(shí)他們放過父親,沒有扣押父親的車,那么父親也不會(huì)…
扶起他,我看見一朵一朵的葵花在陽光下怒放,仿佛大山迸發(fā)出的燃燒的火焰,凡·高說那是愛的最強(qiáng)光。是的,你猜得沒錯(cuò),我放過了他們,雖然那父親的車后廂里違法載了人。說實(shí)話,剛放他們時(shí),我是滿腹的焦慮和不安,可當(dāng)那叫小葵花的孩子抬起葵花似的臉,甜甜地說“謝謝警察叔叔”時(shí),我所有的焦慮和不安頓時(shí)融化在了黃燦燦的葵花里,我甚至看到了葵花叢中父親的臉,笑得跟葵花一樣。
向來守時(shí)的師傅那天并沒到崗,我是回隊(duì)時(shí)才撞上他的,他雙眼紅腫,嘴里念念有詞,正在說誰車禍沒了。
“誰?誰沒了?”我的心臟突然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跳得厲害。
“我的表弟……騎個(gè)破三輪還把命搭了。”師傅邊揉紅腫的雙眼邊說。
“車上還帶了個(gè)小女孩是嗎?”
“是,帶了她女兒,不過,你聽誰說的?”回答后的師傅奇怪地看著我。
記不清后邊跟師傅說了什么?只知道我轉(zhuǎn)身跑出了交警隊(duì),并鬼使神差地來到了事故地。
事故現(xiàn)場(chǎng)已被清理過,幾朵葵花沾著星星點(diǎn)點(diǎn)的血,雜亂地散落地上,我數(shù)了數(shù),不多不少,剛五朵。
一定是我哭得太傷心,讓路旁的老大媽看了不忍。她安慰我說,雖然孩子的父親走了,可孩子還活著呢。大媽說這話時(shí),我看見太陽從云層里穿了出來,原本耷拉著腦袋的葵花又開始努力抬頭。
再見小葵花是在醫(yī)院門口,值完勤的我剛要收隊(duì),卻見斑馬線上有白點(diǎn)緩慢移動(dòng),紅燈就要亮了,可那白點(diǎn)還沒過半呢,我急忙向斑馬線跑過去。
我跑過去時(shí),白點(diǎn)嚇了一跳,葵花似的臉白得像她腿上的繃帶,這便是小葵花。倔強(qiáng)著不讓我扶的小葵花,說她得加強(qiáng)鍛煉,盡快好起來,她要照顧好媽媽,她還要當(dāng)警察,當(dāng)跟我一樣的好警察。說完,她的小臉仰向夜空,跟葵花一樣,盡管那時(shí)天上只有月亮。
后來,我又在執(zhí)勤的路上遠(yuǎn)遠(yuǎn)地看見小葵花幾次,每次見時(shí),她都像在千萬朵葵花中,向我露出太陽一樣的臉,我甚至聽見她說,她是葵花,向著太陽的葵花。
一年后,我和師傅又來到那片長(zhǎng)滿向日葵的地段值勤,這時(shí)的我業(yè)務(wù)已經(jīng)很熟。又一輛三輪摩托車駛來,似曾相識(shí)。師傅說,那就是他去年出車禍的表弟的車,可惜孩子就那么跟著表弟走了。
孩子走了!原來孩子當(dāng)時(shí)就走了!可我分明看見,之前練習(xí)走路的葵花,仍端坐在三輪摩托里,笑吟呤地說:“叔叔,我要當(dāng)警察,當(dāng)好警察。”說時(shí),火紅的太陽正從她腳下升起,哦!我看清了,她原來不是向日葵,而是太陽,從我心里升起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