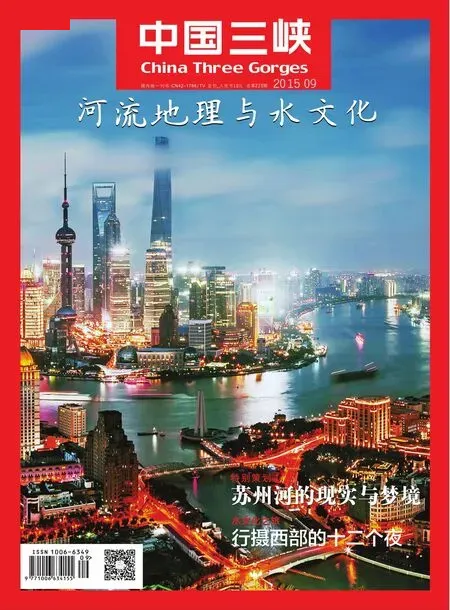中西河流文化比較
文/劉冠美 編輯/吳冠宇
中西河流文化比較
文/劉冠美 編輯/吳冠宇
【主持人推介語】
自古以來,人類“逐水而居”,這是生存的本能。生存之上,衍生出了文化與文明。起源于大河的中華文明與起源于海洋的其他文明相比,自有特色。劉冠美先生作為長年研究水文化的專家,在這篇文章中將中西方的河流文化予以整體而系統的比較,從而深刻和客觀地將中西河流文化的不同予以表達。

航拍富饒的江漢平原,在長江水的滋養下,這里向來是魚米之鄉。 攝影/黃正平
對中西方而言,每種文明既有河流文化又有海洋文化,但有母文化與子文化之分。
特殊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經濟結構不僅影響著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還會對其社會政治形態、思想意識以及人們的心理結構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對中西方而言,河流文化是母文化還是子文化,海洋文化是母文化還是子文化,這要從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尋找答案。
中華文明發展的第一個地理環境特點是黃土高原地理生態的相對同質性。同質、松散的黃土層,小型沖積平原,溫帶氣候——這些都非常適宜于發展單一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我們從遍布甘肅到山東東海之濱的龍山文化考古發掘中可以發現,出土于先人生活遺址中器物的大體雷同,表明了小農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的近似性。小農生產的單一性,決定了人們生產方式、生活習性、價值觀念以及社會組織結構諸多方面的同質性。
中華文明發展的第二個地理環境特點是在這些農耕共同體之間并不存在使它們長期彼此隔絕的天然地理屏障。散布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這些同質農業村社小共同體,均可以不受障礙地彼此溝通與相互影響。中華地理環境的相對無障礙性,可以使這一廣大地區內的各部族、各諸侯國人民在語言上、思想觀念的交往上相當自由。孔子、商鞅、韓非子周游列國,從來用不著帶翻譯隨行,這就是一個例子。當歐洲大地上異質的小共同體發展為分屬于不同語言、風俗、宗教的民族與國家時,中華大地上的小共同體之間正由于這種不受阻礙的相互交流導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漸在文化上形成同質體的中華文明大板塊。

希臘伯羅奔尼撒。 攝影/hemis/東方IC

馬賽和很多法國城市不一樣,這里不僅僅有著傳統的西歐、古羅馬文化,還有不少阿拉伯、古希臘文明的印記。這一切全因為馬賽的地理位置,因為地中海。 攝影/robertharding/東方IC
第三個地理環境特點是中華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之間進行文化交往相當困難。首先,中華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是舊大陸諸多文明中最遠離古代文化交流圈的文明。眾所周知,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希臘羅馬文明與印度文明之間,存在著廣泛持久的文明互動與交流。印度雖然離地中海相對較遠,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山口卻很容易被外來征服者打開,異族人只要進入這些山口,就可以如洪水般地涌入恒河平原。正因為如此,那些身材高大的亞利安人,追隨亞歷山大東征而來的希臘人,以及此后的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埃塞俄比亞人,都可以浩浩蕩蕩地進入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帶。相反,中華文明卻因為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遠遠地孤立在東方一隅。除此之外,中華文明四周又被東面的大海、北面的戈壁沙漠與西伯利亞寒流、西北面的青藏高原、西南面的熱帶叢林所環繞,在古代,這些巨大的地理屏障切斷了它與外部世界的廣泛交流。我們可以把中華文明的這種封閉性稱為地理上巨大的“悶鍋效應”。正是這種地理的“悶鍋效應”,使中華文明在成熟以前,極少從其他文明中獲得異質文化信息與營養的滋潤。我們可以將處于這一地理環境內生活形態等方面具有同質性的各部落與共同體比喻為“悶鍋里的芋艿”,而在這“悶鍋”的內部,漫長歲月中彼此之間的戰爭與相互交流,如同慢火,使其中一個個同質的芋艿逐漸融合在一起,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態。這一比喻可以形象地解釋中華地理環境為什么會促使這一地區文明走向大一統的趨勢。這種同質個體在“悶鍋效應”中的互動,最終導致板塊型的中央集權帝國文明的出現。由于這個“悶鍋”體積龐大,里面能容下許多大大小小的“芋艿”,一旦演變出統一的大帝國,這一文明共同體就具有巨大的規模效應。在前資本主義時代,農業帝國的巨大體量可以抗衡外來民族沖擊,保持民族長期生命持續力的巨大優勢。
西方文明起源于歐洲。這個歐洲并不是今天地域意義上的歐洲,而是指地中海沿岸,西方文明正是起源于此并向北發展。地中海島嶼星羅棋布,該地域的農業不像東方的大河流域那樣發達,基本上屬于農牧混合型經濟,所產糧食甚至不能自給。在人口稠密的城邦,如雅典等,要從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購進谷物。于是,西方文明發展成為商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產生基于市場意識,而市場意識基于交換意識,交換意識又基于承認各自獨立的平等意識,平等意識則來自于分立、獨立意識。因此,西方文化對人顯得相當尊重,個人主義盛行。地中海美麗的海灣波光及希臘半島貧瘠的土地、綿延的山嶺造就了開放自由的古希臘文化,賦予希臘人不畏強暴、迎難而上的精神,同時也使他們認識到在航海中必須尊重和依靠科學,否則就會葬身魚腹。古希臘文化就在對海洋的挑戰、應戰中逐步走向成熟,鑄成了海洋性的文化模式,自然條件的多樣性引發經濟多樣化并進而促使了思維多樣性。
對中西方而言,每種文明既有河流文化又有海洋文化,但有母文化與子文化之分。對中華文明而言,河流文化是母文化,海洋文化是子文化;對西方文明而言,海洋文化是母文化,河流文化是子文化。
從河流形態上看,長度、流域面積、年徑流量等水力參數的不同也會造成河流文化內涵的巨大差異。
同樣是河流文化,中西方又有差異。中國的河流文化是大河文化,西方(歐洲)則是小河文化。黃河與長江的長度、流域面積、年徑流量等水力參數,遠非歐洲的塞納河、萊茵河、多瑙河等可比。黃河與長江的“四同”(同源頭、同流向、同國度、同歸宿)是區別于歐洲河流形態的最大特點,也造就了中西方河流文化內涵的巨大差異。從宏觀水系來看,與歐洲水系不同的是,中國內陸水系具有明顯的統一性。
歐洲由于地勢低平,陸地輪廓破碎,所以河網密集,水流平緩,河流短小;氣候又多為溫帶海洋性氣候,年降水量均勻,河流流量季節變化不大;河流流經國家數量多,多為國際性河流,航運價值高;這些是歐洲河流的主要特點。歐洲大陸從東北到西南斜貫著一條由烏瓦累丘陵、瓦爾代丘陵、喀爾巴阡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安達盧西亞山脈構成的分水嶺,使得歐洲大陸形成兩個斜面——北冰洋-大西洋斜面和地中海-黑海-里海斜面,因此歐洲水系是散向四方的。
孕育一個民族的河流的走向與該民族性格的形成也是有一定關系的。梁啟超在他有關地理環境與文明關系的文章中,通過比較中美兩國的地理環境,探討了中美民族性格差異及其原因之所在。他認為,河流的走向與氣候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會對民族性格產生影響。“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則能連寒、溫、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使種種之氣候,種種之物產,種種之人情,互相調和,而利害不至于沖突。河流之向東西者反是,所經之區,同一氣候,同一物產,同一人情,故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往往各為風氣。”中國的河流基本上是東西向的,而美國的河流則大多是南北向的,這就影響了中美兩大民族性格的不同。
黃河、長江與密西西比河雖均屬世界性大河,但密西西比河從本質上說是歐洲的移民文化,僅有200多年歷史。這些河流在形態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在流向上,自西向東與自北向南的區別;在流經國家上,有一個國家與多個國家的區別;在支流分布上,有大致均衡與嚴重失衡的區別。同樣是大河文化,但在歷史積淀上有悠久與短暫之分,在總體文化類型上又有河流文化為主與海洋文化為主的區別。
比較河流所影響的中西方文化內涵,中國河流文化的多樣性體現在空間性上,西方河流文化的多樣性體現在時間性上。
中國的河流文化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西方則是開放性與多樣性相結合。中國河流文化的多樣性體現在空間性上:黃河文化為北方文化,按上、中、下游又可分為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長江文化為南方文化,按上、中、下游又可分為巴蜀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
西方河流文化的多樣性體現在時間性上,如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多瑙河:“這些遺跡采用的是受到了好幾個時期影響的建筑風格,是世界上城市景觀中的杰出典范之一,而且顯示了匈牙利都城在歷史上各偉大時期的風貌。”多瑙河邊的建筑突出了文化在各個時期的積累,不同時期的建筑具有不同的風格,如希臘式、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古典主義式、浪漫主義式等,反映出時代的變遷。而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建筑風格變化并不明顯。

俯瞰易北河谷。 攝影/Thomas Eisenhuth/東方IC

三江并流峽谷風光。“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這三條發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內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穿越擔當力卡山、高黎貢山、怒山和云嶺等崇山峻嶺之間,形成世界上罕見的“江水并流而不交匯”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觀。 攝影/王文鴻/CFP
從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來看,西方整段河流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有塞納河、萊茵河、多瑙河等,而中國錄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沒有整段河流僅是流域內的單個景點,如岷江的九寨溝、都江堰、峨眉山等,而“三江并流”也只是作為自然遺產錄入的。這種現象說明在中西方河流文化遺產分布上,前者是點狀分布,而后者是線狀分布。
造成這種現象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由于中西方建筑材料的差異,前者是木構,不易保存;后者是石構,保存年代較為久遠。二是中國古代改朝換代時,為清除上一個朝代的影響,往往連同文化遺存一并清除。三是自然災害造成歷史文化遺存的消失,如開封歷代都城遺存被黃河泥沙掩埋。四是西方很早就重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相比之下,新中國建國初期在這方面有所欠缺,建筑學家梁思成提出保留老北京城的建議甚至曾被視為異端邪說,被上升到“要把我們趕出北京”這樣的政治層面加以批判,實在可嘆。
遺產保護與開發的矛盾在中西方是共同存在的,而結果卻可以不同。
對世界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是中西方共同面臨的課題。要么就不去爭取錄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榮譽;要么爭取到這個榮譽,就要嚴格遵守遺產公約,切實保護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2004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2009年又被除名,該案例教訓尤為深刻。
易北河谷為易北河流域之一部分,包含了文化與自然景觀,2004年7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并于2005年7月授予官方證明,2009年6 月25日因新建工程破壞景觀而被除名。
2006年,因德累斯頓政府計劃在河谷上興建一座被認為可能會破壞河谷風貌的現代橋梁,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橋梁的建設會使易北河谷不再符合名列《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故而將易北河谷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此后,多次與德累斯頓市政府的協商并未能阻止建橋計劃。2009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宣布將德累斯頓易北河谷這一遺產地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去除。
由于堅持建造一座有爭議的橋梁,德累斯頓易北河谷被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成為自該名錄設立以來繼阿曼阿拉伯羚羊保護區之后第二個下榜的景觀。
德國媒體評論說,這是德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黑色一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三江并流”于2003年錄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04年曾因保護區內規劃修建水電站而被警告,也連續三屆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列為重點監測保護項目。這一修建計劃最終被凍結,“三江并流”依舊得以名列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這兩個案例揭示了選擇開發,則被除名;選擇保護,則維持了世界遺產的圣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