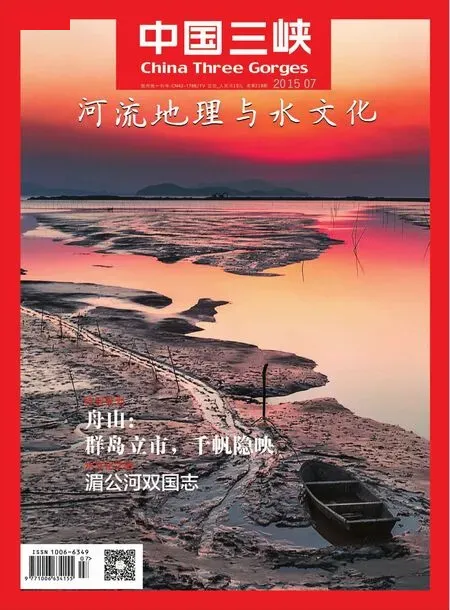把水的權力關進籠子,讓它更合理地流淌
把水的權力關進籠子,讓它更合理地流淌
又到汛期。
司馬遷在《河渠書》中曾言:“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甚哉,水之為利害也。”
從夏而今,凡幾千載。水之利害,意也遠矣。防洪、水運、農田水利,甚至軍事國防,水是文明史上的大主角,水與人的關系也是文明史上最重要關系的一種。水并不像抒情詩人一廂情愿的比喻——母親;更多的時候,水更像一位震怒的暴君,不羈的浪子,任性的孩童……人所能做,就是把水的權力關進籠子。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水才會呈現出它靜美、寬仁、容忍和善意的一面。無論是圣如禹王,霸如楊廣,功如潘季馴,敗如錢四娘,巧思如李冰,聰穎如蘇軾……他們所做,無非就是把水的權力關進籠子,讓它們為人所用,讓它們更合理地流淌。
水德即為道德。舉凡跟水相關項,必涉及巨大,耗費國帑甚眾。然而,即使投入巨大,也常會有無功而返的可能。如果國庫本就單薄,治水興利亦更多艱。故而才會誕生鄭國這樣思量“疲秦之計”的工匠,豈料結局是只延韓數歲之命,卻令秦關中千里沃野。不過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尚屬孤本。有時則會因糜費巨大,主事官員遭人詬病傾軋;此間因涉及利益巨大,亦有以身犯險的貪狼,致陷囹圄者眾。所以,把水的權力關進籠子之時,亦當將人的權力關進籠子。
但治水本身又需要給官員足夠的自由度,讓他及時得到錢糧、人力的補給。如果朝廷處處掣肘,錯過天時地利,也只能令人扼腕。遍覽水利史,官員的心寒,無奈的喟嘆,兩難的取舍,并不少見。所以舉凡涉水事項,國主的膽識,大臣的才具,官員的良知,人心的歸向,缺一不可。故而,若“筑堤無學理之研究,守護無完善之方法,官吏無奉公之才德”,亦難功成。
1998年,長江流域曾發生了自1954年以來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洪水大量決口分洪,圩堤普遍潰決。當時的抗洪親歷者孫志禹先生曾經對我說,他抵達洪湖干堤抗洪一線時,正值傍晚。站在大堤頂上,放眼遠眺,堤外是天水相連,一片汪洋,幾乎望不到對岸;回首一看,堤內的洪湖市華燈初放,已是萬家燈火,遠處的田野,微風輕撫,掀起層層稻花的漣漪,一片靜謐祥和。可這燈火、這稻花大部分都在腳下,因為大堤的高度約與五層樓房的高度相當,堤外洶涌而至的洪水水位,剛剛好與在堤頂壘起的、及于胸高的、單薄的編織袋子堤相平。堤內的家園,就靠這風雨飄搖的大堤和子堤保護,隨時都有一瀉千里的危險,廣大人民命懸一線的感受至今記憶猶新。
最近常讀水利史。讀史本身或者并不能給人直接的生活助益,但會有某種東西悄然沉入血管,在生命中靜靜燃燒,成為理解世界的一個方法或者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