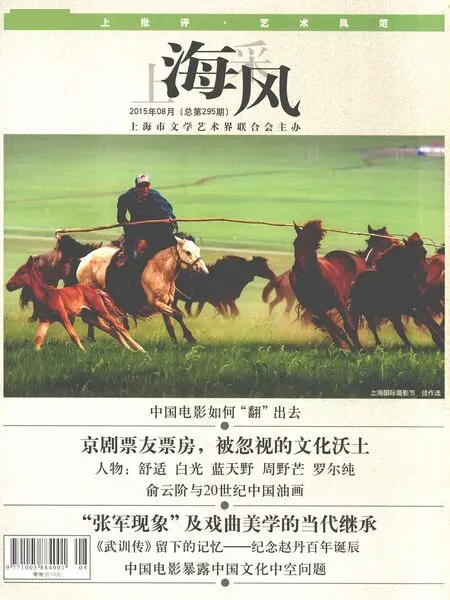烽火歲月憶龔玫
文/郎慕中
烽火歲月憶龔玫
文/郎慕中
抗戰中期,我還在浙西戰時第一臨中讀書。這是抗戰時期一段十分艱苦、使人難忘的日子,尤其使我不能忘懷的是我的同學龔玫。
當時,日寇瘋狂進攻,步步進逼,烽火燃遍了江南大地,大好山河遭到鐵蹄踐踏,成為淪陷區。軍政機關大撤退,我們學校也隨之從內地搬遷到浙西山區偏于一隅的天目。天目山區海拔150米,周圍山巒疊嶂,雄峰峻巖,深壑險谷,千里云山逶迤,成了防御日寇的天然屏障。學校設在天目山麓的禪源古剎,旁邊就是浙西行署所在地。當時,天目山區已成了浙江省抗日在浙西的半壁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也成了日寇的眼中釘,差不多每天都從杭州筧橋機場,廣派飛機來進行循環搜索,不休止地狂轟濫炸。由于這一帶自然條件好,崇山峻嶺,壑深山高林密,敵機很難找到目標,雖天天來,也只能盲目丟幾顆炸彈,向叢林掃射一陣機搶,就飛走了。可是敵機頻繁飛臨,對我們學習干擾很大,差不多每天要逃警報,逢到晴朗天氣,我們就進原始森林里,坐在軟軟的松針上,松樹杈上掛著小黑板,聽老師講課。生活十分艱苦,晚上點的是青油燈,吃的是霉糙米,而精神食糧就更少,沒有書報。可是課余學生會組織抗戰宣傳活動卻十分活躍。
我和龔玫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都是學生會宣傳積極分子,我負責編輯出版墻報,油印快報;龔玫她是從淪陷區大城市來的,性格謙和靦腆,會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歌也唱得特別好,成了話劇組的臺柱。她父親原來是東北軍的一個團長,“九一八事變”東北軍撤至關內,部隊潰散,他被分派到南方的一個縣當縣長。縣城淪陷,他帶著部下撤離縣城,上山打游擊。關于這,龔玫在我們面前卻從未提及過。這次她給我們帶來了巴金的《家》《春》《秋》在報紙連載的剪報合訂本,還有曹禺的《野玫瑰》等。看到這些,我們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真有點像久旱逢甘霖,大家課余經常在田邊、溪邊、林中一起閱讀。逢到星期天,就一起順著狹窄崎嶇的山路,穿過茂密的竹林,在潺潺蜿蜒的溪流旁,幾棵蒼天紅松拱圍的巨青石上,團團圍坐暢談文學,抒發理想,或者商量學生會的事。清晨山谷繚繞的嵐霧還未消散,朦朦朧朧的竹葉、樹葉、草葉上還掛滿大大小小晶瑩剔透的水珠,青翠欲滴、綠如翡翠,一碰樹枝,或一陣山風過去,玉珠便帶著清涼的潤膩滑過臉龐落入頸項。我們都已習慣了這種野趣,感到生活仍充滿激情。
當時,最轟動全校的一件事,是慶祝校慶。學生會在老師指導下,演出話劇《野玫瑰》。這是一個頗具浪漫傳奇的大型抗戰話劇。大意是抗戰時期,我方女特工夏艷華“天字十五號”奉命打入淪陷區做臥底,與北平大漢奸王立民結婚。王立民前妻侄兒劉云樵留學英國,畢業回國,王為他謀職。劉云樵住在王家,被王立民女兒曼麗愛上。另外和王立民共事的警察局長,也被明艷嫵媚的夏艷華傾倒,形成三角戀愛。原來劉云樵也是重慶派來的特工,在一次竊取情報中,身份被識破,危急之際,夏艷華利用警察局長對她的迷戀,巧施計策,放走劉云樵。夏艷華又利用王立民與警察局長之間的矛盾激化火并,順利完成了任務。最后王立民得怪病自殺。
演出這天,學校非常隆重,還請了行署機關領導。演出結果大大出于我們意料,尤其是龔玫演的主角,將美艷妖媚的女特工夏艷華,面對漢奸、日寇時的美、媚、狠、脆,演得絲絲入扣,惟妙惟肖。演出獲得觀眾一致好評,應行署的邀請,第二天還特地加演一場,招待軍民。當時的《東南日報》還特地開辟專版報導演出盛況。
然而,戰爭的災難終于又降臨了。
清晨,峰巒、深谷、林梢一團團霧嵐剛消散,陽光驕傲地撥開云層,湛藍的天空云彩輕柔地在群峰上空流溢。我們剛上完第一節課,突然一聲“嗚——”凄歷的長嘯,警報聲又響了。我們沖出教室,直奔大山深區的紅松林躲避敵機,剛爬上一座山崗,我該死的瘧疾又發了,全身發抖,腿腳發軟不聽使喚。同學曹榮,是我的同鄉,平時大家給他取綽號“山里漢子”,他身體魁梧,力氣大,人又好。他好容易把我背進紅松林,讓我躺在軟綿綿還發散著芳香的松針上,自己則爬上一棵合抱粗的紅松樹梢,久久注視著山下。這時,我熱已退,舒服一些,但全身軟乏無力。曹榮從樹上下來,憂心忡忡地告訴我,今天發現有個奇怪跡象,周圍高山頂上出現白色標志和記號,還不時出現白光。忽然,他問道:“有沒有看見龔玫?”我猛地就像被火灼著驚叫起來:“啊?她今天未來上課,一定瘧疾病發作(抗戰時日寇散布的瘧疾病菌,當時廣為傳染),還躺在宿舍里。那怎么辦?”這時,碎心裂肺的警報聲剛停下,隨即遠處天空就傳來飛機群的“隆隆”聲。
曹榮輕輕對我說了聲“我去看看”,他一轉身,順著長滿長茅草的山坡滑下山去。這時飛機就像蜂群一樣在空中盤旋,越飛越低,清楚看得到機翼上紅色的膏藥旗。突然一陣尖利呼嘯聲之后,接著傳來震耳欲聾的“轟隆轟隆”炸彈聲。山下我們學校所在的大雄寶殿冒出一股烈焰。敵機狂炸了半個多小時之后,飛走了,山谷林間一下沉寂下來。仍不見他們回來,我心里焦急萬分。聆聽了一會,山溝邊傳來“悉悉簌簌”的聲音,聲音漸近,樹葉掩映中出現兩個熟悉的人影,是曹榮和龔玫。
“啊!是你們回來了。”我們三個一見面,緊緊抱在一起,高興得熱淚盈眶。
整個天目山區,我們學校所在的禪源古剎和行署機關所在地,還有村莊,均遭到日寇毀滅性的轟炸。原來日寇在轟炸前,利用漢奸在高山密林中設置標志信號(曹榮在紅松樹上看見的白色標記和白光,就是信號),我們學校幸虧師生在預警報發出后不久,都已隱蔽進入原始森林,沒有遭到傷亡。可是,古剎被炸,已蕩然無存,變成一片瓦礫。戰時臨中師生無處棲身,學校就遷到距我家較近的印渚鎮凈山寺的古廟里。從此,我與龔玫交往更密切起來了。
有一次,她喜孜孜地送我一本油印刊物,神秘地說:“這是我哥托人從淪陷區捎來的,你一定喜歡,你看完給曹榮看,可不要隨便借給別人弄壞了。”我打開扉頁,眼睛一亮,正是作家姚雪垠寫的小說《差半車麥秸》。這是寫一個農民參加抗日游擊隊的故事:為了保家衛國,忍痛離開新婚妻子和比生命還珍貴的家,投奔抗日游擊隊。他作戰十分勇敢,一次與敵人肉搏時受了重傷,送他到后方醫院,躺在擔架上他還夢囈嘮叨著,而他家為了蓋間房屋還差半車麥秸。我入神地讀著,連龔玫在一旁也忘掉了。等她轉身走遠,我才發覺。
戰時臨中,好多同學來自杭嘉湖淪陷區(日寇占領區)。他們無家可歸,龔玫也是。我家離小鎮只有15里路,當時淪陷區來的學生都以學校為家,因此假期中我常邀他們到我家作客,我家住在山溝溝里,村舍都散落在高高低低的山崗塢坳里,開門看得見、叫得應,可是從這頭到那頭,翻山越嶺得大半天。
媽媽見是大城市來的學生,又都是無家可歸的,況且龔玫又是位嫵媚嬌憨、亭亭玉立的姑娘,當然另眼相待,變著法兒弄好吃的。那時八年抗戰,農村很苦,只能用山芋干、包米餅招待,龔玫更喜歡蕎麥餅醮著自家養的蜜蜂釀的蜜糖吃。
她總是邊吃邊贊不絕口地說:“好吃,賽過城里的面包、蛋糕。”說得大家都笑了。
淪陷區離鄉背井的同學,都盼望有個溫馨的家,因此他們并不嫌棄我們山塢窠里貧寒的生活。可是媽媽每次總是顯出不可捉摸的喜悅,她已從心底里喜歡上了龔玫,還十分關切地對龔玫問長問短。我心里直暗笑,龔玫瞥了我一眼,臉上倏地映上了赧紅。
突然傳來消息,說在城里的鬼子又在蠢蠢欲動,八成又要開始下鄉掃蕩了。鬼子掃蕩就是所到之處實行毫無人性的搶光、殺光、燒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學校當局提前放假,把學生疏散回家。可是淪陷區來的無家可歸的學生、教職員工仍留在學校里,跟隨學校一起疏散。這時正遇上新稻還未收割上,農村普遍缺糧。媽媽叮囑我等新稻收割上,再邀請他們來家作客,因此龔玫和班級里幾個同學沒有跟我回家。
七月流火,田野已是一片金色,到了豐收季節。這時從城里傳來了可怕消息,杭州、富陽城里的鬼子,又開始沿著公路線地毯式地掃蕩。兩天前堂兄小狗哥在城里買鹽的路上,被鬼子抓去當了挑夫。
已是日暮時分,血紅的夕陽低低地懸掛在西天,半個天空都被夕陽染紅了。在燦爛的晚霞里,一群歸巢的鳥兒在飛翔著。恬靜的山村彎彎的山道上,突然出現一批批背著包袱、擔著箱籠逃到山村來避難的人,帶來更可怕的消息是:鬼子這次沿著公路兩側,采取三光政策,所到之處搶掠、燒殺、奸淫。
我的家在大山塢的山坳縱深處,有一個人跡罕至的天然溶洞,據傳說洪楊造反時期,附近二十里地的百姓就在這里避難,里面可以容納三四百人,四周是叢篁密筱、翠煙如織,十分安全。我們全村人,還有鎮上逃來的親友,都躲到了洞里。
整整躲了一天一夜,鬼子撤回城去了,大家又回到村里。小狗哥向大家訴說了他親眼目睹的小鎮上發生的鬼子燒殺、搶劫、奸淫婦女的慘狀。第三天,逃難的人陸續回去了,媽媽不放心,要我到鎮上去打探龔玫的消息。我一走進小鎮,眼前就出現一片斷墻殘垣,十室九空,一副劫后余生的慘景。那天,傳來鬼子出城掃蕩的消息,留校學生和教師人多目標太大,分散與鎮上居民一起躲避。龔玫來不及離開小鎮,只得躲到一家居民三層閣的稻草堆里,卻被這群豺狼不如的禽獸糟蹋了。
聽到這個消息,真同晴天霹靂,心里難受極了。曹榮也唏噓嘆息不止。第二天,我就去探望她。她已被校方送到縣衛生院,躺在病床上昏迷后剛醒過來,已痛不欲生,身體也十分虛弱。媽媽要我帶了半筐雞蛋和糯米,到了病房,她躺在床上,聽說我來看她,忙用被單蒙著頭凄凄啜泣。我在她床邊足足坐了一頓飯辰光,再三勸慰她。她沒吭聲,也不肯回過臉來。最后,我懷著同情和凄切的心情離開。
局勢平靜下來,新學期也快開學了,這是高中最后一個學期。本來學生會幾個干部都準備畢業后結伴去南方桂林報考西南聯大,可是開學了,仍不見龔玫來上課,爾后她也杳無音信。我和曹榮到處打聽龔玫消息,后來聽說她已跟著父親、哥哥走了,我和曹榮沒有能再見到龔玫。我們畢業后結伴南下桂林,報考西南聯大。抗戰時期,交通十分不便,缺乏交通工具,完全靠步行,又要通過鬼子封鎖線,一路上宵行日宿,饑寒交迫,到了桂林,西南聯大早已開學了。在桂林停留期間,得到征招遠征軍的好消息,我和曹榮倆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遠征軍。
轉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是抗戰八年艱苦生活中一段心路歷程,龔玫的倩影和我們之間萌發的朦朧情愫,仍像彩虹永遠留存心間。當年她提供給我的《家》《春》《秋》的剪報和文學書刊,在當時的艱苦環境中,猶如沙漠中見到的一塊綠洲。這一切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使我記憶猶新,彌足珍貴。也正是這些青春朦朧萌發的愛情和文學的啟蒙,使我有著執著的追求,在人生的道路上,從未改變學生時代的初衷:即使是在風風雨雨嚴峻的生活面前,仍堅實地走自己的路,并對文學作出微薄的貢獻。而且我確信龔玫在這五十多年風云變幻的崢嶸歲月里,一定也會發出自己的光彩。我遙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