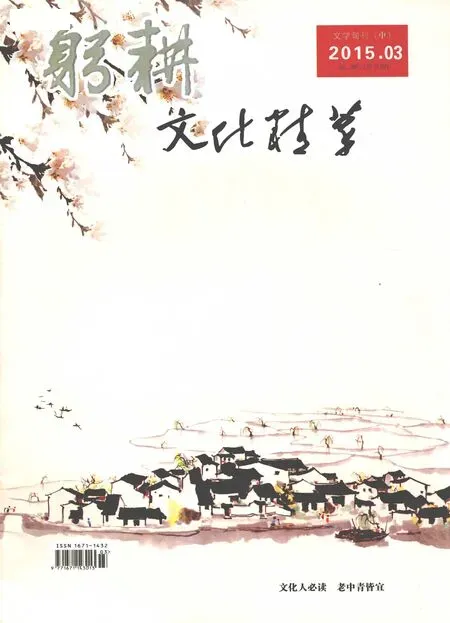打麥場
◆ 周文光
打麥場
◆ 周文光
老家的打麥場,在我家的房后,與我家只隔一條大路。打麥場不大,十幾畝地光景。打麥場是詩意的,是過去我和村民們的精神家園,有著無法形容的美好,總是蕩漾著歡聲笑語。
打麥場是在春末夏初被村民恢復了往年的模樣的。在漫長而寂寥的冬天和春天,打麥場往往被人和家禽、家畜踩踏出一行行凌亂的腳印,甚至被豬拱得坑坑洼洼。臨近麥收,老隊長興致勃勃地敲響村里的銅鐘,把村民召集起來,高腔大調地講幾句,麥收之幕就嘩啦一聲拉開了。
首先是平整打麥場。老隊長領著村民,到打麥場虛土、潑水、撒麥糠,然后,讓牛拉著套有磙框系有竹掃把的石磙,嘰扭嘰扭地反復碾壓,把打麥場碾壓得瓷實平展、干凈光滑,像用泥漿精心抹過似的。打麥場如一位待嫁的新娘,靦腆而激動地等待著一場盛大的婚禮,憧憬著為人婦、為人母的喜悅。
平砥如鏡的打麥場開始成了我們小朋友和村民聚集的地方。我和一群小朋友,脫著赤腳,在打麥場推鐵環、抽陀螺、跳繩,玩老鷹捉小雞游戲,玩得眉飛色舞。上了年紀的老人們,或蹲或坐在場邊,滋滋地吸著劣質煙,津津有味地談論著麥收和秋播的話題。在我們快樂的玩耍中,小麥像凱旋的戰士,被村民們熱烈地恭迎進了打麥場。
麥收時節,是村民們一年內最繁忙的日子,虎口奪糧,搶收還要搶種。村民們往往在秋播之后,開始碾麥。一大早,麥場上就熱鬧開了,麥垛被扒開,男女老少齊上陣,有的拿麥捆,有的解麥腰,有的攤麥,沒多大功夫,就把麥子橫七豎八地攤了厚厚一場。吃過早飯,待陽光曬去了麥子的潮氣,幾個牛把式就開始套了牛,拉著沉重的石磙在麥子上碾壓。父親那時正值壯年,身體健壯,又熟稔碾場技術,隊長每年都派他碾場。父親披著上衣,戴著草帽,一手拉著牛撇繩,一手揚著長長的鞭子,吆喝著牛,在麥場一圈一圈旋轉著碾壓麥子。父親的臉曬成了褐紅色,滿臉的汗水順著臉頰、脖頸與脊背上的汗水,形成了一道道細細的水線,無聲地落在干燥的麥子上。但這絲毫減弱不了父親的激情,她有力地吆喝著牛。父親渴了,喊我或母親給他舀瓢井水,咕嘟咕嘟一喝,仍然高聲揚氣地吆喝。父親響亮的吆喝聲,與麥稈發出的噼噼啪啪的破裂聲,石磙發出的轟隆隆的滾動聲,構成了美妙的交響曲。這動聽的交響樂在麥場盤旋、飛揚,溫暖和陶醉著父親,也溫暖和陶醉著場邊樹蔭下等待翻場的村民。
麥子碾壓一遍后,父親大聲地吆喝:翻場了。場邊樹蔭下的女人們放下針線活,男人們掐滅了煙,擱下茶碗,拿起工具,疾步走進麥場,將麥齊刷刷地翻弄一遍。父親和幾個牛把式套上牛,拉著石磙,再次碾壓,連續幾遍,方可起場。起場是一片比較忙碌的勞動景象。村民們涌進麥場,有的用桑杈攏麥秸,有的用木锨攏混合著麥草、麥糠的麥粒,有的用掃帚凈場,整個麥場草糠飛舞,工具齊響,灰塵飛揚,充滿了詩情畫意。
最熱鬧,最富有詩意的,要數揚場和搭麥秸垛了。晚飯后,在夜壺燈的光亮下,脫著光脊梁的漢子們,穿了短褲的女人們,舞起了桑杈,舞起了掃帚,舞起了木掀,忙得心潮澎湃。汗珠子從村民們的發際眉梢、胸脯和臂膊上冒出,像冒泡的泉眼,他們沒有手巾,用那用過鋤頭、鐮刀、镢頭、桑杈、掃帚的大手一抹,摔在地上,發出響亮的聲響,像山坡上菊花噼噼啪啪的開放聲。
揚場是技術活兒,要根據風的大小,或直或斜地把臟兮兮的麥子拋到空中,動作要到位,拿捏的分寸和力度要適中。村中,揚場水平最高的是光棍兒豁嘴兒大叔(因嘴唇裂缺,被人們稱為豁嘴兒),他每次揚場,都要先撂起一掀,試試風向,估估風速,然后,鏟起一掀,輕抖一下掀柄,“唰”的一聲,把摻著草糠的麥子撂到空中,碎麥草、麥殼順風飄遠,麥籽兒成一條線落在地上。大叔好玩,特別是好跟村里幾位他叫嫂子的玩,平時在村里或地里遇到她們,他總要說幾句粗話,摸一下她們的頭、臉,甚至屁股,惹得幾位嫂子經常合起伙來收拾他。在揚麥中,他多次故意把麥子撂偏,讓碎麥草、麥糠和麥灰落了裝麥的嫂子們一身。幾位嫂子生氣了,在裝麥時,偷偷一合計,趁他休息不注意,把他按到地上,往他褲襠里裝了一褲襠麥糠。“你娃子夜里總是想婆娘,睡不著,今黑兒(今天夜里)叫你娃子徹夜睡不著,使勁想。”幾位嫂子,報了“仇”,邊說邊嬉笑著跑開了。休息著的村民,看著這一幕,都放聲大笑起來,笑聲響徹了整個麥場,振得場周圍的楊樹葉嘩啦啦直響。
那時,我大約只有七、八歲,正是懵懂淘氣的年紀。我和小朋友們像小魚一樣在打麥場里追逐打鬧、竄來竄去。我們往往忘乎所以,跑到搭麥秸垛和揚麥的地方,被大人責罵,還落了一身臟東西,但我們都不介意,嘻笑著跑開了,繼續瘋狂地追逐打鬧,繼續在麥場竄來竄去,把笑語和童趣傾灑在麥場的角角落落。
不知什么時間,燒餅般的圓月,在打麥場東邊的那棵大楊樹枝葉間移動,像鄰居家三女白皙的臉蛋掩映在青枝綠葉間。我興奮起來,大聲向小朋友們報告了這一新發現。大家立即停止追逐打鬧,嘰嘰喳喳地議論起月亮來。過了一會兒,月亮跑到了樹頂,沒有什么遮擋的月亮,把銀灰色的月光傾灑在打麥場上,打麥場像淹沒在銀亮亮的水里。去場邊撒尿的一位小朋友,在缸水里發現了月亮,興奮地大喊,月亮掉水缸里了,月亮掉水缸里了。大家疑惑地飛跑過去,看水缸里的月亮。我想把月亮撈出來,就把雙手伸進落滿灰塵的水里捉月亮,但月亮在水里蕩漾著,像捉弄我似的,一直忸忸怩怩地躲著我,引得小朋友們都嘿嘿直笑,我感到很無尊嚴。就在這時,豁嘴兒大叔大叫著說,嘿嘿,月亮掉到我的茶杯里了。我們又一溜煙地跑到豁嘴兒大叔跟,果真,他的茶杯里有個月亮在慢慢移動。我們更加疑惑了。這時,父親走過來說,傻孩子,這是月亮的影子。月亮能倒映在水里!我和小伙伴們于是紛紛回家,用碗,惑瓢,舀了水,端到打麥場,坐在一起,睜著大大的眼睛,看著一個個碗里或瓢里的月亮和星星,嘰里呱啦地品評著。月亮很亮,星星很稀。打麥場沒有我們的追逐打鬧,安靜了許多。不知什么時間,我們都困了,瞌睡也咬住了眼,先后躺在光光、涼涼的打麥場上。我仰面朝天,四肢放肆地展開,迷迷糊糊地望著那輪明亮的圓月和稀稀疏疏的星星,又想起了奶奶的話,每個人都有一顆星星,人死了,星星就落了。我不知道,哪一顆星星是奶奶的,一定是最大最亮那顆吧,我希望它永遠掛在美麗的天幕上。奶奶那么疼我,她一死,就不能疼我了。想著想著,我閉上了眼睛,進入了夢想。
夏收之后,打麥場會有一段時間的寂靜。但在秋莊稼一下地,綠豆、芝麻、玉米、黃豆漸次登場,這時的打麥場還會熱鬧一陣兒。待秋莊稼收拾完畢,村民們就很少去打麥場,只有幾個鍘草喂牛的男人,隔三差五地來到麥秸垛跟鍘草。只有在演電影時,村民們才紛紛來到打麥場。但我和小朋友們在冬天和春天,是經常光顧打麥場的。對我們來說,沉寂蕭條的打麥場也有很多的歡樂和幸福。
那時,老百姓家里都沒有電視,有收音機的人家也是寥寥無幾,文化生活非常單調。人民公社為了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在冬、春農閑時間,就會派放映員到各村放電影。來我老家放電影,地點就選在打麥場。放電影的設施很簡單,在打麥場南邊栽上兩根五六米高的細楊木,再用兩根竹子做橫擔,系上白色的電影幕布。在一根楊木上安一只大喇叭,在打麥場中央放一張大桌子,桌子上放一臺放映機和幾盤電影片子,再接上電源就可以放電影了。
天還沒有黑定,各家各戶都已吃了飯,扶老攜幼,來到打麥場。待放映員不慌不忙的架好機器,燈光一亮,小孩子們就站在凳子上,興高采烈地跳著揮舞小手,有的做老鷹狀,有的做青蛙狀,有的做小貓狀,形形色色的怪狀在幕布上顯現,大家看著自己的怪狀,都高興得眉飛色舞、心花怒放。
可電影放映了,我們倒是索然無味了,一個個在人群里鉆來鉆去,或在高高的麥秸垛和楊樹上爬上爬下。也曾一不小心從麥秸垛上滾下來,惹得滿場人哄堂大笑。我那時還不算太調皮,往往能安安生生地坐在凳子上看一會兒。我很喜歡槍,看了《地雷戰》《地道戰》后,夜里做夢總是夢見槍。第二天,我就早早起床去打麥場拾槍。可找遍打麥場的所有地方,我一支槍也沒有撿到,就連子彈殼也沒有撿到一個。死那么多敵人,咋會沒有槍呢?就是沒有槍,也應該有子彈殼的。我看著空曠的打麥場和蒙古包似的麥秸垛,非常地失望和沮喪。
我們在打麥場玩耍、推鐵環、抽陀螺、抓子兒、打翹子、捉迷藏、扮家家……盡情享受著童趣。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在麥秸垛里撿到雞蛋、鴨蛋。這是我和幾個小朋友的秘密。村里總有一些丟蛋的雞和鴨,吃著主人的食物,卻不在家里下蛋,偏偏鉆到麥秸垛下邊下蛋。我們發現后,偷偷地撿了,拿到代銷點賣后,買了我們愛吃的零食和玩具。
最大的樂趣和幸福莫過于在打麥場捉麻雀了。冬天,下雪了,到處白茫茫一片,麻雀餓得饑腸轆轆,在打麥場和麥秸垛上,嘟嚕飛過來,嘟嚕飛過去,焦灼地四處尋找吃的,但到處是雪,哪里有吃的呢?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在打麥場掃去一片雪,露出地面,在上面撒了麥子惑麩子,蓋上篩子,用一根木棒把篩子支起來,在木棒上綁了繩子,遠遠地拉著,待麻雀走到篩子下面吃食時,用力一拉,麻雀就成了我們的“甕中之鱉”。我們在村外的地邊或溝里,用泥巴把麻雀包好,丟到籠著的活里燒,待泥巴干裂爆開,用木棍扒出來一掰,泥巴粘著鳥毛就下來了,露出了白花花香噴噴的麻雀肉。那真是難得的“珍饈佳肴”呀!在那艱苦的歲月里,能吃到這樣的麻雀肉,實在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幸福!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集體解散后,實行了生產責任制,打麥場被分割成了很多塊兒,幾家合用一個小打麥場,各家輪換使用原來隊里的小脫粒機打麥,打麥場的熱鬧勁大大降低。再后來,聯合收割機直接進到地里收麥,麥稈屙到了地里,只有麥子被村民拉了回去。打麥場廢棄不用了,被隊里分給村民。村民們在里面種了樹,或種了菜。再再后來,打麥場的一大半被幾家村民蓋了房子。打麥場徹底消失了,麥場里曾經的故事和熱鬧景致也早已漸去漸遠,成了人們遙遠的記憶。只有那碾過場的青白色的石磙還臥在打麥場四周的溝里,用昔日的記憶,打發著一個個寂寞的日子。
我和當年的小朋友們也在打麥場的熱鬧、寂寞中漸漸長大。不安分的我們帶著家鄉的溫暖,紛紛走出家鄉,走向外面的世界,有的在工作,有的在打工,有的在做生意。我們像一只只飄蕩的風箏,手線永遠系在家鄉那幾個石磙上,系在家鄉的土坷垃上,系在父母的心上。我們一有空閑,就回老家。每次回家,我們都要去看那些石磙,把石磙摸一摸,對石磙聞一聞,聽一聽,我們從石磙身上感受到了當年的溫暖,聞到了當年的麥香,也聽到了當年那美妙而溫馨的聲音,心里不禁波浪翻涌!
家鄉那生我們養我們的熱土,那曾經給予我們歡樂和幸福的石磙,那惦念我們冷暖的父母,時刻都在呼喚著我們的乳名啊!靈魂里有了這樣親親的呼喚,我們怎能迷失回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