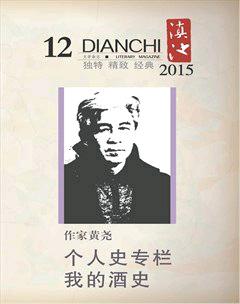風起
東巴夫
天擦黑,街上很熱鬧。屠大剛肩挎工具包,手提一捆尼龍繩,從前邊的小巷斜插過來;沒有紅綠燈,他站在馬路中央,一輛藍色小汽車擦膝而過,他打了個趔趄,肩往左邊一閃,差點兒栽倒;他再穿過一個小廣場,過了馬路就到了家門口。
屠大剛是一個門窗制作工,他技術好,活兒多,每天都很忙碌。這天大清早,他就接到顧客電話,他要去安裝防盜門,早飯是在路邊買了個饅頭。他一個人一忙就是一整天,中飯沒顧得上吃。待活一干完,他就匆忙往家里趕。他妻子叫余歡歡,他倆是贛州同鄉,五年前經鄉里的媒婆牽線結了婚,婚后她就在家,沒出去工作。他們現在有一個三歲的女兒,叫倩倩,余歡歡的主要職責就是在家照顧女兒。
快到家門口,屠大剛卻放慢了腳步,說實話,他有點怕余歡歡。余歡歡三天兩頭跟他吵架,一天安生日子都不讓他過。吵架時,他只是退讓,聽任余歡歡惡罵,他知道只有等余歡歡把滿肚子的怒氣噴射出來,她才會停歇,反駁或犟嘴只會讓咒罵無限升級。他怕見余歡歡那張臉,他怕她那一抹輕蔑的眼神。但他一想到馬上就能看見他那懂事又可愛的女兒,雙腳又不覺加快了速度。他做什么怎么做都是為了這個女兒,女兒是他的心頭肉。
家門口有一個花壇,長著齊腰深的冬青,花壇邊有一個三米多高的飛馬銅雕,這條街叫打馬街。屠大剛走到花壇邊上,就看見女兒一個人蹲在銅雕下,玩她最喜歡的橡膠小黃鴨。
“倩倩——倩倩——”喊聲剛落下,屠大剛已大步走到女兒跟前。女兒抬頭看見屠大剛,臉上笑瞇瞇的,露出兩排小米粒樣兒的牙。“爸爸,你回來啦!”“爸爸不在家時,倩倩有沒有想爸爸?”他放下工具包,把女兒抱在手上。“我想爸爸啦!我玩了一會兒小黃鴨,我想爸爸!”他笑起來,一臉的褶子溝里粘著黑灰。他用自己的額頭頂了頂女兒的額頭。
屠大剛放下女兒,一扭頭,看見妻子余歡歡赤腳坐在家中央的竹木床上,妻子的頭向兩腿間彎下,拱起的膝蓋遮住了她的臉,她腳邊平放著一部新手機,他知道她又在搶微信紅包。余歡歡是玩微信紅包的專業玩家,這部新手機就是她用搶得紅包的錢購買的。
屠大剛放下手里的尼龍繩,發出一聲悶響。余歡歡抬頭瞄了一眼,很快又垂下頭。
“菜買了嗎?”聲音是從襠部傳出來的,甕聲甕氣。
“嗯?你說啥?”屠大剛沒聽清。
“問你晚上要吃的菜買了沒有?”余歡歡的頭一抬一垂,丟了一句。
“沒買,我剛回來……”
“沒買你回來做什么?晚飯吃什么?你吃屎啊?!”余歡歡抬頭說了這么一句,她的手指慣性似的在手機屏幕不停往上滑。
“你怎么這樣說?我剛回來,手里也沒閑著,什么吃屎,屎能吃嗎?”屠大剛說著笑了起來,笑得很勉強。
“狗能吃屎,你怎么不能?難不成你還比狗
金貴?”余歡歡板著臉,兩眼一橫說。
女兒看看屠大剛,又看看余歡歡,嘴撅著,一副緊張又害怕的神情。三歲的娃兒多少懂點事,親歷了父母太多的爭吵,只要父母臉色一變,說話的語氣一變,她就知道一場爭吵即將上演。
女兒拉了拉屠大剛的手,說:“爸爸,我們買菜去吧!”
“你的火氣真大,你看,女兒都害怕了。”屠大剛拍拍衣角,騰起一團灰塵。
“滾出去拍!”
屠大剛在門外脫下外套,換了一雙拖鞋。他走進左屋的一間內室,那是一個小單間,窗戶口對著護城河,他們用來做廚房。他揭開電飯煲,是空的,他從柜下拉出一袋大米,舀了兩碗,淘米,擦干鍋底的水,放入煲盆中,通電,先煮著飯。
屠大剛牽著女兒的小手到菜市場買菜。晚飯是屠大剛做的,女兒不愛吃米飯,他在飯中蒸了一碗雞蛋花。開飯了,余歡歡沒在飯桌上找他的碴,她唯獨這點好,不挑食,吃得順嘴就行。
晚上八點,余歡歡給女兒洗澡。女兒坐在大澡盆中,玩她的小黃鴨。屠大剛坐在左側方的一只小凳上,他手里捏著一根煙,卻遲遲沒有點燃。他看見妻子用毛巾輕輕擦洗女兒的后背,額角上的一綹頭發散下來遮住了她的半張瓜子臉,她的嘴唇,紅潤,翹翹的,充滿挑逗、誘惑,她尖尖的下巴上滲出細密的汗珠,在燈光照射下,亮晶晶的,她的皮膚白嫩得能捏出水來。屠大剛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又看了看自己裸露的胸膛。正如別人說的那樣:他看起來比妻子老十歲。而實際是余歡歡跟他同年,還大他三個月。他想,他畢竟是男人,掙錢養家是應該的,辛苦點累點,也是理所當然的,看起來老些就老些吧,大男人,年輕也不能當飯吃。他看著妻子,心想,真是個小美人。“真好看!”他輕聲說。
“你嘀咕什么?”余歡歡說。
屠大剛回過神來,吧唧一下嘴巴。他說:“老婆,我想跟你說件事兒。”“有什么話直說,別喊我老婆,我聽著惡
心。”“怎么就惡心了?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嘛!”“喊我名字,別喊我‘老婆!”屠大剛方才流露出的混合著各種情愫的目
光,突然就黯淡下來,好多個話語涌到舌尖,一陣亂撞,找不到出口。屠大剛緊閉嘴巴,頭往前傾,上身僵硬,像一塊化石,擱在凝滯的空氣中。
余歡歡把女兒從澡盆里提溜起來,用掛在脖上的干毛巾給女兒揩身子。見屠大剛一聲不吭,像石墩似的杵在那兒,她忍不住問了一句:
“你剛才要說什么?”屠大剛還沒融化開。他沒反應,依然保持那
個站姿。“哎!神經病!”“你說啥?”“你剛才要說什么事?”“噢,我原想跟你說,我想買塊機械手
表。”“買手表做什么用?你兜里不是揣著手機
嗎?”屠大剛搖搖頭。“算了,不買了。”“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愛買不買,不用問
我。”“不買了。”余歡歡把女兒從澡盆抱出來。屠大剛慌忙把
準備好的睡衣遞過去,余歡歡騰出一只手接住。屠大剛彎腰,想把洗澡水端出去潑掉,他的手無意中碰到余歡歡的小腿肚。
“啊——啊——”余歡歡尖叫,左腳啪啪啪跺地。“怎么啦?怎么啦!”屠大剛忙問。“你不要碰我,不能碰到我!”“我碰到你哪兒啦?”“你不要碰我!臟!臟!……”說著,余歡
歡急得哭起來。女兒被她光屁股放在一邊的椅子上坐著。
屠大剛把端起的澡盆往地上一丟,許多粒水珠蕩彈出來,一潑水浪出來打濕了他的鞋。
“我怎么臟了我,我是心里骯臟,還是身體骯臟?我不過是手指頭不小心碰到了你,這是手指頭又不是針,你至于搞得一驚一乍嗎?”
“你要是再碰到我,我就把皮膚用刀割下來,你碰到哪我就割哪,我就是嫌你臟,從一開始我就是這樣想。”
余歡歡淚漬未干,就露出一副兇惡決絕的面孔。
“這些都是你的心里話?究竟因為什么讓你發這么大的火?我一直弄不清,你現在已經失控了,瘋狂了,一點理智都沒有了,你知道嗎?”
“你只要同意簽字,我們離了婚,這些就都不存在了。”
女兒小聲抽泣起來,她最怕從父母口中說出“離婚”兩個字,小手背不停地抹眼淚,晚飯前那會兒她就害怕,想哄著爸爸,讓他不說話,讓媽媽干說一會兒,等她氣消;她不知道怎么勸說,去年他們吵架,她大哭,她大哭也不能阻止什么,反而會招來媽媽一個大耳光,她就不敢嚎哭,她真是害怕,很無助,小肩膀一顫一顫的,嚶嚶地哭。屠大剛看了女兒一眼沒說話。
“你就死賴著,不簽字,害死我了,我跟你說。”
余歡歡給女人穿衣服。屠大剛絞心絞腸地氣,胳膊一陣陣發麻。
“你老把‘離婚兩個字放在嘴邊說,離了婚對你有什么好處?我不簽字不同意離婚,是在給你時間,給你機會,讓你好醒悟。我心疼你,心疼女兒,你感受不到嗎?這幾年我一直在奮斗,為了這個家,你是看得到的,你捫心自問,我有沒有讓你吃一丁點兒苦,再說我們過得也不比別人差,房子蓋了,你說喜歡車,車也買了,你說不愿意出去打工,我依你,你在家玩,我養得起。我做的這些你都視而不見,反而三天兩頭吵著離婚,你是閑出毛病來了?”
“別說了,你到底還是不懂,什么都不懂,我們壓根就不是一路人,你知道嗎?不是一路人啊,怎么能一路走下去?從結婚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錯了,這些都不是我要的。”
“你現在說跟我過不下去,離了婚你再找個人,那個人就跟你過得下去?你自己的性格你的怪脾氣你自己不清楚?這世上,除了我屠大剛,誰還能容忍你?啊!你說說,你找出一個來讓我看看。你把我的寬容當成迂腐無能!你仔細想想。”
余歡歡一時語塞,屠大剛的話擊中了她的要害。她是那樣的強勢剛硬,不打一點兒彎,不服一點兒軟。脾氣很不好,怒火一旦爆發出來,誰都安撫不了,親爹親媽都拿她沒法子。在她十二歲那年,因點小事,她覺得母親在她與弟弟之間偏袒了弟弟,一氣之下,她連夜跑出了家門,她往孤山上跑,往亂墳崗里鉆。父母慌了,一時尋不到,就喊來村里的親戚友鄰,執手電筒打火把,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尋了一夜,才把她給找出來,她就藏在墳崗邊的一棵大樹下,不哭不鬧不作聲,就悄悄坐在那兒,她也不知道害怕。跟屠大剛結婚后,余歡歡也跑過幾次,可這是在城里,這么大,屠大剛上哪兒找?一個人成心想躲你,不必天涯海角,她就隱藏在你眼皮底下,你沒辦法找到她。屠大剛找了一回兩回就不找了,找也找不到,就隨她去。好心朋友提醒他說,一個小婦人半夜三更在街上游蕩可不安全,出點啥事不好收場。屠大剛坐在椅子上,兩眼一閉,像在幻想什么,然后突然睜開,盯著面前的墻壁說:“我有什么辦法,我有什么辦法呢?……我照顧好女兒,女兒是我的,我管得住。”一般情況下,余歡歡夜里離家出走,第二天清晨,她自己就回來了。
他們的住房不大,還要堆一些貨物,一樓有一半分為工作間,一半是生活區。他們搭了個閣樓,平時余歡歡和女兒在閣樓上睡,屠大剛在一樓睡。夜晚臨睡前,屠大剛就把一米五寬兩米長的工作臺收拾一下,鋪上棉絮,這就是他的床。
夜里九點半,他們在各自的床上睡下。屠大剛平臥在床上,頭枕在兩條疊加的胳膊上。他睡不著。屋里異常安靜,那些白天驚叫的機器:切割機、鉆孔機、點焊槍、噴釘槍,統統安靜下來,變成一堆冰冷的鐵;菜刀睡著了,鍋和飯鏟掛在墻上;筷子入籠,碗壓著碗,都睡死了;用手拍拍被子,也沒什么特別的聲音,眨動眼皮,那是皮膚摩擦碰撞發出的聲音,很細微的,像手心在水面平滑地走過,多么可愛的纖細之聲。屠大剛想買一塊機械手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在夜深時,他可以把頭枕在手心里,側身傾聽手表秒針“錚錚錚”走動的聲音,像一條連成線的水珠不停地滴打在破瓦上。那是時間的腳步聲,他知道這似乎暗示著,每個人都應該珍惜眼前的一切,珍愛自己所擁有的。真奇妙,他就想聽聽,一個人的時候,在夜深,在無眠時。
可惜他沒有得到這么一塊機械手表。
“唉……”這時,屠大剛聽到閣樓上的余歡歡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聲。原來她也醒著。
屠大剛抬起腦袋,立直了耳朵,聽閣樓上的動靜。余歡歡翻了一下身,床板咯吱一聲響,過了一會兒,床板又響了一聲,余歡歡又翻身過來,接著她吧唧了一下嘴巴。屠大剛翻身下床,往茶杯里倒了一杯涼水,小心翼翼爬梯子上閣樓,上至樓口,他停下來,說:“想喝水么?我倒了一杯。”
余歡歡從里面伸出一只手,接住水杯,咕咚咚喝了大半杯,把水杯遞出來,屠大剛連忙接住,快步順溜地下了梯,把水杯放在飯桌上。
屠大剛沒有回到自己的床上,他稍作停歇,也就是站在那兒想了一會兒,接著,他手扶梯脊,悄悄往閣樓上爬,像做強盜似的,不敢弄出一點聲響;他爬到閣樓口,單膝跪在邊緣上,一探身,鉆進了閣樓。他想碰碰婆娘。給娃兒洗澡那會兒,對屠大剛最后說的那些話,這余歡歡沒有反駁,剛才給她遞水,她也沒拒絕,屠大剛以為余歡歡應該是消了一些氣,心里也應該有一點兒觸動。他想,他再趁熱打鐵,好好和余歡歡做一次愛,身體上再敲敲打打交融一番,這場爭吵帶來的僵局應該就暖化了。
可誰曾想,屠大剛的手才摸到被褥,他的臉啪地一聲,重重挨了一腳,他兩眼冒金光,腦袋
也碰到了床頭的隔板上。“哎呦!你踹我干嗎啊你?”“你偷偷摸摸上來做什么?”“你是我女人,你說我上來做什么?我想你
嘛!我想陪你睡覺!”“你滾開!聽到沒有?滾下去!”“又怎么了?你要鬧到什么時候?”“誰跟你鬧?你想女人,你身體需要,你去
找小姐啊!扒弄我做什么!”
扯了布簾,光線微弱,但還是能看清余歡歡那張冷絕僵硬的臉龐,她坐在那兒,被褥抹胸纏在身上,細嫩的脖頸泛著幽幽的光。
“你再不下去,我就用腳把你踹下去!”余歡歡冷冷地說。“這樣鬧有啥意思!”屠大剛說了一句,他
挪動屁股,從閣樓上溜了下去。屠大剛重新躺到自己的床上。“是沒什么意思,老拖著有什么意思,想有
意思就同意離婚唄,你好,我也好……”從閣樓傳來余歡歡一聲冷笑。“真到那一天,我也認了,什么我都不要,我只要女兒。”屠大剛無奈地說。“你憑什么要女兒,女兒是我生的。”余歡歡用手一捶床板說。“沒有我,你一個人就能生?女兒是我的命根子,別的東西我可以不要,包括財產全給你。 ”
“你別做夢了,我的東西你是得不到的,我寧愿親手毀掉也不會留給你,你要女兒,我就掐死女兒,讓你得不到。”
“你說什么?你再說一遍?”屠大剛從床上
彈起來,他知道余歡歡說得出做得到。“你想要什么,我就偏不讓你得到……”“瘋子,你就是個瘋子……”屠大剛三下兩下爬上閣樓,把余歡歡從被窩
里撈出來,抱到閣樓門口,像夾草把子似的,把余歡歡攔腰夾在腋下,帶到一樓,兩只手抓住余歡歡的屁股,把余歡歡扔到自己的床上。余歡歡拳打腳踢,像個耍脾氣的熊孩子,她在屠大剛的床上打了個滾,一把坐起來,指著屠大剛的鼻子罵:“你這個畜生!”
“罵我畜生,你這個蠢女人,真不知好歹 ……”
屠大剛說著,猛一吸氣,唰地一聲跳上床,“啪啦!”一聲把余歡歡扳倒,兩只手像鐵鉗,一下子撕開余歡歡的上衣,余歡歡慌忙用手遮住奶子,他又十分迅速地扯開余歡歡的內褲,余歡歡不再遮擋什么,光身子大喊:“你瘋了?”
屠大剛沒說話,他很快褪掉身上的衣褲。兩個人光溜溜互相對視著,屠大剛的喘息越來越重,他的身體就像一架出了故障的機器。余歡歡感覺渾身冷,瑟瑟發抖。屠大剛的心像一張撕爛的紙,他迫不及待,他沒法控制自己,他渾身的血在往腦帽頂上沖。他伸出右手,抓住余歡歡的腳,往他跟前使勁一拖,余歡歡已經坐在他腳下,他熟練地爬上了她的身。
畢竟是兩口子,都是熟悉的。余歡歡剛開始還掙扎,尖罵,用手掐屠大剛的胳膊,那兒鼓搗了幾下,余歡歡就安靜下來了,低低地呻吟,不時用牙咬屠大剛的肩膀,屠大剛渾身是勁兒,他越干越有勁。
可冷不丁地,余歡歡在興奮中說了一句:“天啦!我要告你,告你強奸……啊!”
屠大剛像個鼓脹脹的氣球,被人用針一扎,撲哧一聲,泄了氣。他一把倒在床上,兩眼怒睜,頃刻,他眼里的氣焰也萎下去了,代之以兩行濁淚流出,打濕了他的耳朵。
余歡歡的欲火被撩起來,燒得正旺呢!她旋腰爬起來,一屁股坐到屠大剛的肚皮上,噼噼啪啪又折騰了半個鐘頭,這才翻身下馬,歪身躺在床的另一頭,忽兒,她低聲抽噎起來。
天蒙蒙亮,屠大剛打開門,天空陰沉。晨風裹挾著落葉,呼啦啦向他襲來,街上沒有人,一個人都沒有,屋頂黑黑的,馬路冷冷的,斑駁的墻壁還是那樣陌生,他的心突然很痛,他覺得很難受。
天啦!這是一個殺人的深秋。
責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