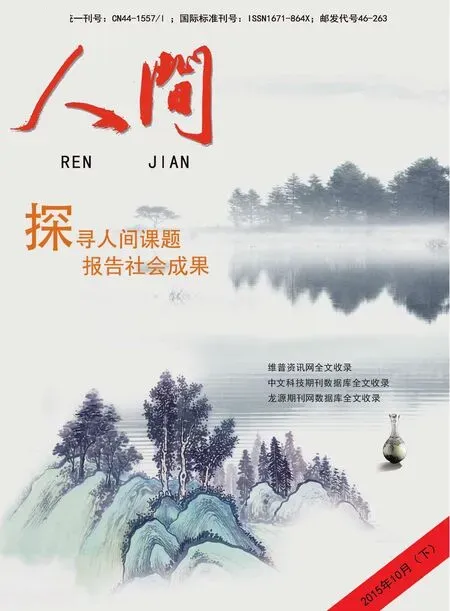無墻體的門扉
——象征主義藝術的折中性
劉文菲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1331)
無墻體的門扉
——象征主義藝術的折中性
劉文菲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1331)
本文著重對19世紀末的象征主義藝術展開探討,并認為象征主義藝術在藝術史乃至文化區域的經緯上存在著“模糊”的特征,于是我選擇從縱向的藝術史上的體現,象征與圖像符號的概念間的對比這兩個角度論述其折中性。
象征主義;圖像;符號
自兩戰以來,西方藝術從現代主義跨入后現代時期發展至今,藝術本身的涵義已被消解。在這種多元化環境下成長的我們,在面臨藝術時往往面臨諸多的干擾,我們在整和知識背景或建立知識結構的過程中常常不知所措,對于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也很難迅速地找到它在美術史上的上下文關系。同樣,我們十分警惕以尖銳或單一的方式對一個藝術流派著重地探討,在當下語境中。我們更多的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一個角度作為出發,對美術史進行研究,所以我非常強調個人的標簽,因為只有在確保個人原始感受的完整的同時,對外界標準進行吸納,或挖掘一件事物的內部結構,才能堅持和而不同的學習狀態穩步前進,只有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介入自己身處的人云,才能在無意識的洪流中幸存,并慢慢膨脹。
所以,我接下來重點描述的象征主義的內容在這個語境下也應該被賦予更廣義的含義,本文將從三個角度對“象征主義”展開討論。即:象征主義在美術史上的上下關系;象征與圖像,符號的關系;“象征”在東西方文化差異下的表現。
一、藝術史中的象征主義
首先,在藝術史的定義中,象征主義出現在19實際末,和當時前后出現的幾個重要流
派同樣,象征主義是一個很廣義的定義,它涉及文學,詩歌,戲劇,藝術等各個文化領域,因為根據當時的大社會環境,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和資本主義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都經受著巨大的變化,因此這一時期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名稱通常都包含了文化中的各個領域,而相對居于中間位置的象征主義則更加模糊,它在文化上的表現不如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那樣先鋒,尖銳,也沒有像它們那樣形成具體的社團,發起近乎革命式的運動,從各個角度來看,象征主義都以一種非常折中的狀態“浸潤”在當時劇烈動蕩的文藝思潮之中。
比如,象征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如波德萊爾和愛倫坡,他們作品中的荒誕性和非現實性明顯具有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例如尼采所主張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在其作品中的表現就極其突出。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文學作品又掛著古典主義的顯著標簽,如對莎樂美這樣的古典題材的描寫和作品中沉重的宗教意味。同樣,這種鮮明的折中色彩也體現在象征主義繪畫中,雷東和莫羅的作品中一反古典主義以來的“摹仿自然”的主張,也沒有印象派以后的科學與客觀,其作品中“不真實”的意味與象征主義文學中對現實的反逆不謀而合,而在其作品中包含的象征形象上,同樣出現了許多古典主義時期的影子,如雷東作品中出現的獨眼巨人,和莫羅作品中施洗約翰的人頭,均充滿了鮮明的神秘主義色彩。
因此,我們根據當時象征主義藝術的定義——它是一種藝術家不愿意直接表述自己的意思,往往采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在幻想中虛構另外的世界的藝術,如弗萊德象征理論所述:“無論我們閱讀什么,我們都會發現自己的注意力同時向兩個方向運動。一種運動是向外的,或者說是離心的,此時我們不斷走出自己的閱讀,從單個詞語走向他們所指稱的事件,或者說實際上走向我們對它們之間的對應的傳統記憶。另一種運動是向內的,或者說向心的,此時我們企圖從這些詞語中得出一種由它們構成的更大的語言模式。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接觸的都是象征,但是當我們賦予某個詞語外部的意義,它除了語言象征,還包含它所再現或所象征的那樣東西。”(1)由此我們可見,象征主義藝術雖然取材古典主義時期的圖像,卻未曾為這個圖像賦予外部的意義,這里的圖像是藝術家內心訴求的載體,它已經失去了古典主義范疇圖像學“指示”與“教化”的功能;而它又有別于表現主義那種現實而激烈的情感,表現主義更多的是將個人情感注入客觀外在的世界,而象征主義則不然,也沒有那么暴力。同樣,若從構建幻想空間的角度切入,象征主義又不同于超現實主義那樣純粹意識的流動,超現實主義在虛無主義的影響下呈現出一種完全無跡可尋的狀態,畫面中所出現的元素甚至只有藝術家本人可以解碼,觀者往往很難將那些圖像對號入座地去解讀。所以,我們幾乎可以認為,象征主義在藝術上的定位更類似于一種極其混沌的“狀態”,我把它看作一扇孤立的門扉,連接著內在世界與外部環境,且既不是緊密的連接,也不是架空般地存在著深深的鴻溝。
二、象征,圖像與符號
就上文所述,象征主義繪畫如雷東,莫羅等藝術家并不賦予其畫面中的圖像以外部的意
義,從這一點上來說,它沒有古典主義時期時圖像的教化功能。因為雖然涉及宗教題材,但無論是從藝術家遵從內心主觀感受為出發點而言,還是從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上看待,其圖像不具備為宗教服務的功能與義務——象征主義藝術中的圖像往往并不清晰,它很可能只是日常世界中一些普通元素的重組,或根本就沒有形成圖像,因為作為藝術家私人感受的載體而言,圖像的意義似乎僅僅滿足于隱喻程度的表達就足夠了,太過具體或標簽化的圖像反而會阻礙這一訴求的輸出。
同樣,符號是圖像更進一步的純化表現。比如在一篇描述“塔”的文章中,作者通過象征性的角度看待“塔”這一事物,并做了如此的闡述:“塔這一空間能指符號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闡釋社群中,通過無數次的社群復用,高度理據化為文化象征,從而獲得了普遍的符用理據性,及符號使用的透明度。作為建筑物的塔一旦脫離了其原初的功能實用性,則開始滑向意指抽象概念或品質的象征符號。如巴黎的埃菲爾鐵塔,日本東京塔,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其建設之初或多或少都攜帶著不同的實用性功能意圖,然而在文化的集體復用中,逐漸理據化為一個城市乃至國家的地標性象征建筑物。在介紹這些國家地區的旅游觀光的文本中,這種地表象征往往成為提喻性的伴隨文本符號,而其象征符號的特征,又反過來形成鏈文本,將符號接受者的目光引向相應的國家地區之文化品質,民族精神。”(2)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觀察到,象征主義藝術語境下的“象征”與我們現在通俗認為的圖像與符號之間有著很長的距離,這種距離在某種意義上也表現了藝術家的私密性與生命集體之間的距離,個人與世界之間的距離,而此處的象征物則成為了像門把手一樣的存在。
[1]《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73頁 弗萊
[2]《符號與傳媒》雜志2012年第一期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李璐茜
作者簡歷 :劉文菲(1988-),女,漢族,湖北武漢人,學術碩士,單位: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方向:當代繪畫研究。
TS941.2
:A
:1671-864X(2015)10-0034-01